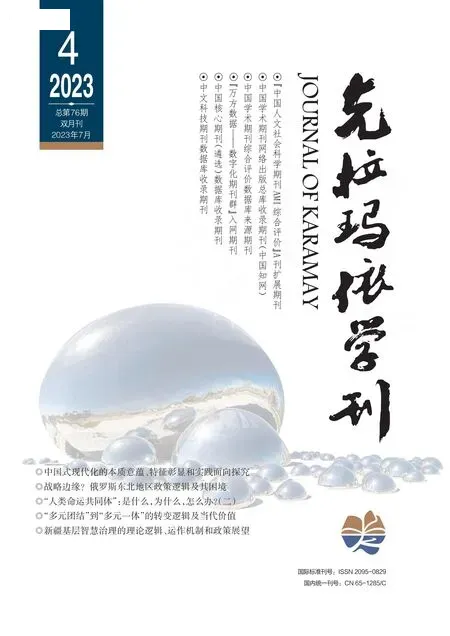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
——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阿达莱提·图尔荪
(1.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010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2017 年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宪法、党章,这一党章已成为全党和各民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意愿和基本坚持。[1]2019 年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2020 年8 月9 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被纳入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治理西藏和新疆的重点战略。[3]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政治话语中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各个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和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的基本概念,“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怎样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时代课题。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国族的整合历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中华民族通过“回忆”本民族的“历史”凝聚团结中华各民族、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由此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回忆”本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记忆之场”:既有如博物馆、档案馆、节日、仪式、庆典、照片、展览等有形之“场”,也有影响相对更为广泛的无形之“场”,如历史传说、英雄事迹、苦难遭遇等。[4]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博物馆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可以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集体记忆。[5]
博物馆与记忆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苏珊·克兰曾经说过:“博物馆不只是文化机构或是藏品的展示地,它们是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记忆与历史、信息与知识产生互动的场所。”[6]“博物馆与记忆”是2011 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是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无论是学界还是公共领域的讨论,博物馆与记忆的紧密关联显而易见。但是在阐释其关联性时,我们必须对(集体)记忆本身的定义进行明确阐释,只有厘清“记忆”概念的内涵和机制(什么记忆?谁的记忆?怎样记忆?),有关博物馆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集体记忆与物体
记忆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很早就被心理学家所关注,但早期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内,较少关注人类记忆的社会基础。随着认知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逐渐开始关注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学家巴特莱特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他提出人们在回忆或重新叙述某一故事时,事实上,这是一个在其自身的社会文化中重新构成“心理构图”。[7]
社会学、人类学家哈布瓦赫受老师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首次关注记忆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指出,集体记忆能够得以形成和延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个人和群体形成自我认同方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一个群体通过分享共同的“历史知识”,能够获得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集体和社区。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及理论从根本上让记忆与集体的勾连成为可能,同时,这种集体层面的记忆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维度中创造、延续、再生。在现代社会中,社区群体所依赖的记忆环境将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有机社区被机械社区所取代而消失。历史的书写将发生在过去的信息以一种权威式的话语模式化、固定化,而曾经鲜活的“记忆”——凝塑群体精神的神话、故事、口头传说等,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现代文明所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下,记忆的产生空间发生了变化。有机的记忆空间和传统记忆空间被皮埃尔·诺拉称之为“记忆环境”,而机械的现代记忆空间被称为“记忆场所”。在诺拉的理解下,记忆的载体变成记忆的场所,那他所创造的记忆就不再是独立于权威话语的控制之下,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些记忆,也不会变成新鲜有生命力的记忆,更不会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而是会成为一种叙事的话语结构。[8]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仅存的四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全世界仅有的两个我国和这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是敦煌和吐鲁番。”[9]吐鲁番自古便是沟通天山南北和我国内地的交通要塞,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重镇,曾生活过车师、汉、匈奴、柔然、鲜卑、粟特、回鹊、蒙古等多个民族;流行过25 种语言和18 种文字;汇聚了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曾是中原丝织品、西方香料、北方马匹交易的集散地。
如今,吐鲁番的古城遗址、千佛洞、纪念塔、坎儿井、火焰山、葡萄沟、艾丁湖、古墓群、清真寺、壁画、古堡、博物馆及收藏文物仍在无声地述说着这块文明交汇之地曾经的繁荣与沧桑。笔者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集体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通过一系列的纪念物、文献搜集,甚至节日符号等物质与非物质手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被不断强化。博物馆是最典型的“记忆场所”之一,在诺拉的理论架构里,博物馆的很多展品不得不从“记忆环境”中抽离出来,重新整合在一套权威并有话语权的体系中,展示了一些特有的知识和信息[10]。
作为“记忆之场”的吐鲁番博物馆所表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并非自然而然地从这个空间中产生出来,它必然要依赖于一些特定的过程和机制。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试图描述并阐释作为“记忆之场”的博物馆如何唤起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笔者认为,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第一,博物馆陈列展品所蕴涵、表现、传达和映射的信息激发参观者的集体记忆;第二,博物馆陈列展品的解说词形成了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叙事系统,并形塑参观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第三,博物馆自身的历史过程,即其建馆目的、展馆的设计与建设、展陈的叙事构建等,促使并强化当下参观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二、博物馆展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这里所指的博物馆展品,是抛开展品说明、摆放方式、灯光、保护技术等一切外在因素,纯粹物理状态的展品本身。这些陈列展览精品的存在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基本要素,参观者在观看展品的同时,会与展品形成一种沟通、对话的关系。
(一)构建儒学共同体
儒学是一门实用、实践的学问,它在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准则,历来是官方推崇的主流文化。它在历史沉淀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和心理认知对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吐鲁番博物馆收藏的纸质文书中,有一卷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①手抄本(见图1)。从文字记载来看,它是1 300 多年前一个年仅12 岁的少年卜天寿的家庭作业本,长538 厘米、宽27 厘米,内容分别是《论语》中的《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一部分,卷末还有《三台词》《千字文》和其他诗句等。[11]在这件《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的卷末标记着“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和“景龙四年三月一日”。这两处题记清晰地说明,公元710 年的吐鲁番,12 岁的学生卜天寿学习的场景。更有趣的是,卜天寿抄写完还即兴发挥,做了两首“打油诗”。第一首打油诗写到:“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侧书—侧读—侧眼,可以想像到卜天寿抄写、阅读、习诵《论语》时的样子。

图1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
卜天寿侧着身子抄写《论语》,很费劲,还希望老师别怪罪他。因此,抄写行将结束之时,他又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见图2):“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图2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
孔子及其弟子问答讲论的记录被整理成《论语》,其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问世以来长期作为古代小学阶段的教科书。这卷“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给当下观者反映了唐朝时西州地区②建的学校与中原相似,学校还将以儒家学派为主的中原文化教育进行普及和推广,并且当地教育被正式纳入了朝廷科举取士的轨道。这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正是中原与西域交流、融合、凝聚的结果。“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现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文物名录。
陈列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见图3),同样反映了儒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从中原地区流传到吐鲁番,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

图3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
《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左起第一幅画是“欹器”,它是古代盛水盛酒的器皿,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告诫人们物极必反,做事留有余地才能保持盛而不衰。接下来的是四幅人物画像,第一个是“玉人”,意思是年轻人应勤奋好学,培养良好的品质;第二个是“金人”,用三层布包着他的嘴,意思是警惕祸从口出;第三个是“石人”,张着嘴,意思是可以畅所欲言,作出一番事业;第四个是一位老者,意思是应保持中庸之道。最后一幅图画有三样东西:生刍(青草)一束,劝人不可以把待遇厚薄作为去留标准;素丝一卷,劝人不要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为;“扑满”告诫当官要清廉。这幅包含了儒家学派核心价值观的《六屏式列圣鉴训图》壁画,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相互渗透,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二)建构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
在春节的时候吃饺子是习俗,这一习俗来源于“交子之时”的说法。而因为饺子谐音叫作“交子”,即是新年与旧年的相交时刻,在除夕夜与新年交替之际一般都会食用,所以取的是“更岁交子”之含意。饺子作为春节的文化符号之一,其代表了“年”。在吐鲁番博物馆陈列的几枚唐代的饺子(见图4),同样指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西域人民在至少1 500 年前,和中原一样也过春节。

图4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饺子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代表幸福、欢乐、团圆、丰收、富贵、平安、通顺、健康、长寿等美好的文化精神都会集中呈现在这个节日。一切的人际交往、经济消费、环境美化、生产贸易、自然和谐、总结开启等社会行为,都会以这个节日作为节点标志。春节已成为中华文化集大成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此外,通过康氏家族墓志的记载我们得知,定居在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基本与中原地区相同,去世后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实行家族土葬,并刻字立碑,在思想上也认同了中华文化。北凉沮渠蒙逊的夫人彭氏的随葬“衣物疏”③记录了彭氏随葬的遗物。这种“衣物疏”深受中原民间传统旧俗的影响,印证了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镇墓兽是一种冥器,用来保护死者灵魂不受打扰,放置于墓葬中,起到镇慑“鬼怪”的作用。镇墓兽是古人想象出来的一种虎头豹身虎尾的神兽,它来源于中原墓葬文化,也是中华文化在吐鲁番传承的重要物证。高昌乐是一种新产生的乐种,指的是西州人用中原的雅乐与西域的胡乐结合而成的新乐种,充分印证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自古就是往交流交融的。
以上案例显示出展品本身在唤起“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中的作用,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个体的记忆,但在更深层次上,这样的记忆更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体现。因为,这样的个体记忆必然与该个体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在其生活背景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构图密切相关。
三、博物馆叙事与集体记忆
吐鲁番博物馆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的机制不仅依赖陈列展品的物质存在,而且更取决于通过对展品的讲述和对参观者的引导,还原、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正如厄恩斯特指出的:“历史信息是复杂凌乱的,无体系的,甚至相悖的。如何将这些凌乱的信息裁剪,又如何从这些表面上毫不相干的展品信息中凝练和构建出一套成体系的‘故事线’,需要靠叙事,而这是一个博物馆建构集体记忆的能力基础。”[12]再说记忆具有选择性,甚至是扭曲和虚构的。吐鲁番博物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媒介,其展品遴选、历史叙述、图片说明等一系列展陈方式和手段,都是记忆“选择性”的一种体现。如何选择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展品,将其用“正确”的叙事逻辑进行有效讲解,这是吐鲁番博物馆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吐鲁番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传播一种被各族人民所认可的权威话语,更是在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一)构建同源共祖
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同化合并,同一民族亦有分化离散,出现许多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同族异名或异族混称等情况。如果不同族群需要进行联盟或文化认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追溯或拟制一位共同的祖先。而在古代,拟制的祖先主要显现在神话传说中,如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女娲兄妹成婚、洪水泛滥等。
吐鲁番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件唐代绢画,记载的内容是《伏羲女娲交尾图》(见图5),伏羲女娲以人头蛇身呈现,并呈双螺旋状缠绕在一起。画上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描绘伏羲女娲像,二人上身呈单手拥状人形,四目相对,含情脉脉;上身穿红色广袖对襟上衣,下身合穿一条带有连云图案的白色裙子。女娲右手高举,手持圆规;伏羲则左手高举,手拿矩尺,下身为七段双螺旋状交缠的蛇尾;周围围绕着74 个白色圆点,相邻的几个圆点用黑色实线相连接。

图5 吐鲁番博物馆里展出的《伏羲女娲图》
传说中伏羲氏就是三皇五帝之首,也是中华人文始祖;并且女娲是造人之神,也是华夏的孕育之母。根据文献记载,伏羲女娲的信仰最早见于先秦,西汉时期受到阴阳学说的影响,伏羲女娲开始以对偶神的形象出现,代表了阴阳相对、生生不息。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在内容和构图上,基本和中原地区出土的文物一致,说明吐鲁番地区的这种墓葬文化和中原一脉相承。从画像上不同人物形象特点来看,中原文化在传播到西域后,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如人物形象上出现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等特点,服饰上也出现了对襟胡服等。
同源共祖神话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叙述各族群的同源,而这样的叙述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吐鲁番博物馆将“伏羲女娲”神话看作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将对同源共祖神话进行探讨,上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吐鲁番博物馆讲解员在介绍《伏羲女娲交尾图》时说:“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葬群曾陆续发掘出土上百幅伏羲女娲画像,年代均集中在晋唐时期。几乎在每一处合葬墓里都出土了一幅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图’,或固定在棺椁之上,或叠好放在夫妻二人头顶处。与中原地区发现的汉代伏羲女娲画像石、砖不同,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年代为公元6 世纪至8 世纪,主要为绢、麻两种质地,颜色鲜亮。少数图像伏羲女娲深眉高鼻,穿胡服,伏羲还留着络腮胡,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胡风的伏羲女娲图在继承中原画风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说明古代各民族在祖先崇拜上达到了认知上的高度统一,也更加说明新疆与中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伏羲女娲”神话在吐鲁番博物馆中被反复讲述,强调共同祖先下的多民族关系,构成了“一国多民族”的共祖、共生的集体记忆。
(二)构建命运共同体
吐鲁番博物馆中珍藏了一件非常美丽的刺绣品——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红底鸟龙卷草纹绢绣,又被称作共命鸟刺绣(见图6)。这件刺绣长38厘米,宽26 厘米,大部分为红色,刺绣手法非常精美,是一件少见的丝织品。在红色绢底上绣有图案,上方是五座倒立的山峰,中间是一只两头一体的神鸟,在神鸟两侧对称绣有两只身姿矫健的龙,在下方分别绣有两只鸟,在鸟和龙的周围,还有一些卷草纹布满其间。整件刺绣的图案,均匀对称、造型生动,显示出绣工高超的刺绣技艺。鸟龙卷草纹绢绣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位于中间的双头一体的神鸟,被称为“共命鸟”。

图6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龙鸟卷草纹绢绣

图7 新疆吐鲁番“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
先略微介绍一下作为佛教吉祥鸟之一的“共命鸟”。共命鸟是一只两头鸟,两个头的名称有多种版本,比如“一头叫念堂,一头叫居林”“一头叫法,一头叫非法”,还有“一头叫迦喽嗏,常作善想;一头叫优波迦喽嗏,常作恶想”。故事的内容基本一致,有一只两头鸟(这里用迦喽嗏和优波迦喽嗏来称呼),这两个头,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有一天迦喽嗏看到一枚甘美的果子,刚好优波迦喽嗏睡着了,迦喽嗏就想,我们一个身体,我吃了等于优波迦喽嗏也享受了,它在熟睡就不打搅了,自己吃了这枚果子。优波迦喽嗏醒来之后闻到果香,就问怎么回事,迦喽嗏如实而言,结果优波迦喽嗏怀恨在心。后来有一天迦喽嗏睡着的时候,优波迦喽嗏看见一枚有毒的果子,就把毒果吃了,结果二鸟同时中毒而死。
“共命鸟”的启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两头鸟,有着善与恶的抗争、梦与醒的矛盾、觉与迷的徘徊,善念善行获善报结善果,恶念恶行得恶报结恶果。虽然其叙事主线为善恶,但展览的真正核心价值是现代中国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命运与共等。吐鲁番博物馆的讲解员在介绍红底鸟龙卷草纹绢绣时说:“共命鸟是佛教艺术中的常见的题材,它今天寓意着各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的象征,告诉人们要珍惜民族团结,也只有民族团结,才能有社会和睦、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在某种程度上,吐鲁番博物馆叙事中所呈现的历史是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
四、博物馆建设过程与集体记忆
我们已经阐述了博物馆中集体记忆塑造的两个层次分别是文物自身的记忆与展陈方式所营造的记忆。但记忆的塑造过程并未止于这两个层次,而且博物馆自身的历史过程也不少,即其建馆目的和展馆的设计与建设,加上展陈的叙事构建等,促使并强化参观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笔者曾多次参观吐鲁番市的“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红色教育基地,该基地筹建于2016 年12 月。收藏馆门前的对联上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共产党”,叙说着多年来蕴藏在收藏馆主人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收藏馆的主人努尔丁·沙塔尔是一名老党员,已经70 岁了,工作起来还很认真。8 岁那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他从小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茁壮成长。参军入伍后,他慢慢理解、感受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收藏“红色记忆”。在他看来,红色藏品是伟大革命的见证,直观地反映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说:“不管社会怎么发展,红色精神都需要每个人去铭记和传诵,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收藏,让他们更加热爱伟大祖国、维护民族团结。”在他的影响下,周边村民也加入读书行列,他家自然而然成了村里的“公共图书馆”,变成人们了解国家大事的生动课堂。
集体记忆是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和基本依据,它从来都不是个体回忆的总和,更不是其他,而是社群成员共享的记忆,唯有共时性下的某种情感唤醒,方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凝聚共识。努尔丁用自办“图书室”的方式来储存关于党和国家的记忆、传递信息,其储存和传递的信息容量与空间范围都十分有限。在当地镇党委、政府多方协调争取下,新建成这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
“面孔墙”是博物馆话语构建的手段之一,有规律地铺陈群体或者个体的面孔肖像,五官、表情和其他细节被刻意地放大。因为“面孔”对人类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所以,面孔墙的使用可以有效集中观众的注意力,更有效地吸引观众,也会带来直接的冲击和感染力。[13]“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也有“面孔墙”。展馆以时间为第一线索,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肖像严整有序地铺陈开来,分别为“太阳最红和毛主席最亲”“革命岁月和光辉形象”“红色教育和伴我成长”“大美新疆和亲切关怀”“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等五个展厅。展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孔墙”虽由个体构成,但它所反映的却是一段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精神和事件,在潜移默化地向参观者传达着历代仁人志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先进力量,挽救国家命运、捍卫民族尊严,造福人民大众的共同记忆。
皮埃尔·诺拉称博物馆这一类的纪念场所为“记忆之场”,这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形式,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将记忆“档案化”。[13]“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对毛泽东及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孔的集中展示就是这样的过程,其借助被符号化的人物面孔,将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完成了与观众的共情共鸣。
五、流动博物馆策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2020 年初,吐鲁番博物馆调整服务策略,迅速策划、用最快的速度组织并推出了“流动博物馆”送展活动。活动秉持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文、同宗”的理念,精选高昌故城遗址、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共命鸟、苏公塔、开元廿年石染典过所、墓主人生活图、六屏式鉴诫图、开元四年《论语》郑氏注、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文物制作成图文并茂的专题图片展板,将文物展览办到城镇社区、机关学校、偏远乡村等地方,让更多群众在与文明的交流、与历史的碰撞中,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截至目前,组织开展“流动博物馆”送展活动300余场,受教育群众10万余人次。
如此,各族群体广泛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的塑造和再现过程中。“流动博物馆”作为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的场所,其影响力不容忽视,逐渐成为吐鲁番的“文化名片”。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各族群众产生对中华民族更强烈地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被不断增强并有了新的认识。
结论
博物馆是记忆的场所,是话语建构争夺的空间。博物馆的建设不仅仅要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物和历史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按照特定逻辑构建起体现某种价值的叙事话语体系,以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正如对历史的掌控便是对未来的掌控一样,对博物馆的争夺本质上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博物馆通过对藏品的展示、叙事,让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在沟通、共享中不断塑造、再现和重构,从而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博物馆发挥功能的核心机制。笔者对吐鲁番博物馆的田野考察,印证了知识与话语的互相联结、互相塑造的关系。表面上是在普及和传播历史知识,而本质上却是通过特定的叙事逻辑塑造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以凝塑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文化认同。
注释:
①《论语·郑玄注》中“郑玄注”的意思就是郑玄对《论语》的相关注解。据文献记载,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二三岁就能诵读和讲述“四书五经”。郑玄中年时期开始倾注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作为官方教材,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②吐鲁番古称姑师,汉代为车师前国,唐代置西昌州,后改称西州。
③“衣物疏”是记载死者随葬衣物名称和数量的墓葬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