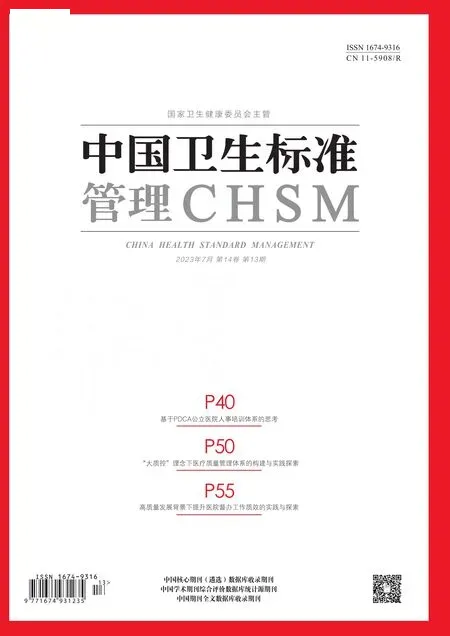血栓弹力图在小腿肌间静脉血栓诊疗中的研究进展
张中清 孙金磊
小腿肌间静脉已被证实是发生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venous thrombosis,DVT)最常见的区域之一,研究表明,23%~41%的疑似DVT患者中存在小腿肌间静脉血栓(calf muscular venous thrombosis,CMVT)[1]。被诊断为DVT的患者中,存在CMVT的比例高达47%~79%。由于DVT是造成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或术后PE[1-2]并且导致猝死[3]的重要危险因素,对DVT进行积极抗凝治疗在临床上已经达成普遍共识[4]。但与近端DVT相比,CMVT的发病因素和治疗方案等仍有许多争议[5]。目前临床诊断CMVT主要依靠下肢静脉彩超、造影及CT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孕妇和危重病患者可能因不能配合影像检查而延误治疗。血栓弹性图(thromboelastography,TEG)用全血模拟从血液凝固开始到纤维蛋白完全溶解的整个过程,可用于血液凝固异常的筛选,血液凝固障碍和血栓形成的诊断[6]。随着技术发展,TEG现被用于特殊人群的筛查和治疗效果的评估等,能够准确地显示患者的凝血状态,用于指导治疗[7]。本文总结了TEG近年来在CMVT诊疗中的进展。
1 TEG
TEG的基本原理是物理旋转测试杯使血液凝固,并记录血栓形成的过程。其中包括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R值)、血凝块形成时间(blood clot formation time,K值)、血凝块形成速度(blood clot formation rate,α角)、最大振幅(maximum amplitude,MA值)、凝血指数(coagulation index,CI)、血栓溶解的百分比(the percentage of thrombi dissolved,LY30值)6项指标。TEG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临床推广,现在也被用于凝血功能的监测和抗凝效果评价等。
2 TEG与CCT对凝血状态评估的比较
临床上传统凝血功能检查(conventional coagulation tests,CCT)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D-二聚体(D-dimer,D-D)等。CCT等指标是对分离后的血浆进行检测。CCT可以检测凝血的外源性、内源性途径,纤维蛋白原的状态及凝血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成分,但很难评价血液凝固及纤维蛋白溶解的整个过程。CHOPARD等[8]研究发现CCT提供的凝血信息并不准确,其敏感性和可靠性较差,作为目前较好反应纤维蛋白溶解过程的D-D,其敏感性达96%,但特异性仅40%,且阳性预测值只有48%。TEG检测的是全血,对血液凝固、纤维蛋白溶解的全过程进行模拟。对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凝血因子等凝血变化的检测较为全面。其检测结果与人体内凝血过程颇为相似。且JING等[9]认为在预测血液低凝方面,R、K值的灵敏度高于PT、Fib、TT。故TEG能更准确反映患者体内的凝血状态[10]。
3 TEG在CMVT诊断中的应用
随着血管超声的广泛应用和检测仪器精准度的提高[11],CMVT的检出率也随之增高,在临床上较为常见。研究表明,血管超声对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已超过90%[12]。但对于部分高危患者来说并不太适用。而TEG为CMVT诊断的补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朱家佳[13]对75例接受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手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治疗的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患者进行了研究,术后下肢静脉血栓者13例(胭静脉血栓 1例,胫周围静脉血栓3例,CMVT 9例),无静脉血栓者62例,将其分成血栓组和非血栓组,发现CMVT患者K、α、MA、CI指标相比无血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TEG能较灵敏的反应异常凝血状态,该研究中,TEG的α,MA,CI指标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0.739,0.692,0.850;CCT中D-D的AUC为0.916。该结果中CCT指标仅有 D-D有较高诊断CMVT的价值,而TEG指标比例则占到了75%。通过综合D-D与TEG指标可提高诊断效能,成为诊断CMVT的依据。在郭瑛等[14]对1 512 例肿瘤患者的研究中亦发现,实验组中DVT 患者的 α、MA 值、CI 值均高于对照组,TEG结合D-D对DVT的较高诊断率为DVT的诊断依据提供了新的参考。但在ABU ASSAB等[15]研究中,分析了不同的TEG 参数,无论是连续变量还是分类变量,TEG在阳性与阴性患者数据做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暂时无法证明TEG在CMVT、DVT等引起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方面是否有诊断价值。目前国内外对于CMVT的无创诊断仍存在广泛争议,TEG能否用于CMVT的辅助诊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 TEG在CMVT治疗中的应用
4.1 CMVT抗凝治疗的争议
目前对于CMVT是否需要抗凝治疗尚有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CMVT抗凝治疗带来的出血风险远大于抗凝治疗带来的收益,建议采用非抗凝治疗手段。MACDONALD等[16]对135例CMVT患者进行前瞻性分析,3个月的随访显示,非抗凝组中只有16.3%的血栓扩散到邻近的胫前、后静脉和腓静脉,发生DVT和PE的概率极低,另外45.9%的静脉血栓会在随访过程中自然消退,因此对CMVT患者建议采用非抗凝治疗。LAUTZ等[17]回顾分析了抗凝疗法对CMVT进展和PE等预后发生的影响,结果显示,不接受抗凝治疗患者的VTE发生率为30%,而进行抗凝治疗患者的VTE发生率仅为12%(P=0.000 3),非抗凝治疗的栓塞风险显著高于抗凝治疗,在患者排除出血危险的情况下建议采用适当剂量的抗凝药物治疗CMVT。赵纪春等[18]在骨科大手术加速康复围手术期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专家共识中指出:对于术前单纯肌间静脉血栓患者不予处理,术后常规按照DVT预防方案执行。但目前针对CMVT临床治疗的选择仍有很大差异。
4.2 TEG在抗凝疗程中的监测
在CMVT抗凝治疗过程中,抗凝的药物选择、持续时间和剂量调整是关注的重点,需要更多的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研究来指导临床治疗。既要避免抗凝时间过长、强度过高而导致出血的风险,也要规避抗凝时间过短、强度过低而延展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如果 CMVT患者抗凝药物选择正确、时间适当、药物剂量适中,那么既可以减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又能降低长期抗凝所带来的潜在性出血风险。因此为了对抗凝药物选择、持续时间和剂量调整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建议,则对于抗凝疗程中凝血指标变化的监测显得尤为重要。临床常用CCT做凝血测试,观察抗凝期间凝血功能的动态变化,其中D-D是评价抗凝溶栓药物效果的重要指标,但只能检测纤维蛋白原及其分解产物,特异度偏低,易受外界环境干扰。而TEG能全面监测血样的凝血变化,对抗凝疗效评估起到不错的效果。
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是最早应用于治疗静脉血栓疾病的一类代表性药物 ,在治疗过程中需对患者凝血功能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抗凝时间和药量,防止出血[19]。ZOSTAUTIENE等[20]采用TEG监测LMWH治疗期间患者的凝血情况,在术前1 h给予LMWH肌注,可获得很好的抗凝疗效。此外,抗Ⅹa活性浓度的监测辅助LMWH用药在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患者中逐渐得到重视,并发挥了降低VTE发生率的重要作用[21]。抗Ⅹa可用于肝素活性的监测试验,但临床上因其特异度偏低故不常使用[19]。TEG中的K 值对标抗Ⅹa活性,可替代抗Ⅹa试验用于LMWH 的活性监测。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血栓形成和止血协会指南建议:去除血栓形成危险因素的远端深静脉血栓患者口服抗凝药6周;此外,持续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抗凝治疗时间为3个月。远端深静脉血栓即小腿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 in the calf,DCVT),包括发生在膝关节以下的胫前、后静脉血栓,腓静脉血栓和CMVT[22-23]。CMVT患者口服作用于凝血通路Ⅹa和Ⅱa靶点的抗凝药利伐沙班等,目前已广泛用于临床。TEG可实时监测新型抗凝药物的活性,如利伐沙班,实现风险的早期发现并干预。此外,对于口服利伐沙班抗凝期间的患者,TEG可客观反映其当前的凝血状态,动态监测凝血全过程。综上,TEG对于抗凝药的效果评估起到较好的作用。
5 TEG在CMVT预防中的应用
杨军等[24]的研究表明,预测DVT发生的诊断价值较高的指标依次是TEG的CI、MA、α及D-D,其中MA对DVT预测的诊断效能最好,当MA>68.35 mm时DVT的发生概率较高。当R 值缩小、MA 值增大时,对DVT风险预警也有一定提示作用[25]。GONG等[26]对172例胃癌合并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行术前1 d、术后1、3 d和5 d静脉采血,提出术后3 d的R 值、K值、α角、MA值对患者DVT起中等有效的预测作用。在SMOLARZ等[27]对病毒肺炎感染患者进行有创操作前的TEG 监测中出现凝血功能障碍时,这时提前使用抗凝药物干预可减少DVT的发生风险[27-29]。国内外关于血栓预防的指南指出,肌间静脉血栓与深静脉血栓的处理措施趋于一致。那么TEG在DVT中的预警作用对于 CMVT的预防就提供了参考价值,预测DVT发生的诊断指标CI、MA、α及D-D亦可作为预防CMVT的参考指标,尤其是当MA>68.35 mm时,CMVT发生概率增高。此时提前干预,予以预防剂量的抗凝药物常规抗凝,如低分子肝素等(参照药物说明书根据体质量调整剂量),可减少肌间静脉血栓的发生。
在临床中患者术后已经进行规范的抗凝治疗但仍有CMVT形成,甚至DVT发生VTE,而且同一抗凝强度下不同患者的出血副作用并不能完全规避。这类问题在骨科、血管介入科鲜有探讨。TEG在这方面可否提供帮助,根据术后第1天、第3天、第7天等时间点外周血中凝血功能变化,动态调整抗凝药物和剂量达到更为有效的预防效果。如术后采血经TEG回报提示血液低凝,则根据其检测值R值增大(凝血因子缺乏)、K值增大(纤维蛋白原缺乏)、MA值减小(血小板缺乏)采取对应成分输血;若回报提示血液正常,则常规预防剂量抗凝(如低分子肝素钙),注意观察皮下瘀斑情况;若回报提示血液高凝,则根据TEG检测值如MA 值偏高(血小板增多)对应采取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要注意采用血小板图评估血小板抑制情况,R值偏低(凝血因子增多)对应更换抗凝血因子药物(如利伐沙班),注意观察皮下瘀斑情况;如果回报提示有血栓形成,则常规治疗剂量抗凝(如低分子肝素钙)。当然最为理想状态若能将TEG回报的R值、K值、MA值、CI值超出正常参考范围的具体数值进行量化,参考对应抗凝药物说明书中药物剂量调整制定更为精确的抗凝方案,那么此项研究成果将会为骨科手术术后个体化抗凝预防CMVT形成的标准制定提供借鉴内容。进而为临床降低VTE风险作出巨大贡献。后续将采取临床试验佐证其有效性、可行性。总而言之,在TEG监测下动态调整抗凝治疗方案可能会降低CMVT发生率,仍需更多的临床研究和试验数据提供支持 ,进一步明确其客观性、准确性。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临床对VTE疾病的重视程度以及超声检查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孤立性远端深静脉血栓(isolated distal deep vein thrombosis,IDDVT)被发现,其中对CMVT患者[22],有症状的往往能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而无症状的和高危人群的诊疗效果监测目前仍是难点。而准确了解CMVT患者的凝血状态,对无症状和高危人群的诊疗效果监测具有重要意义。TEG可全面直观地反映患者的凝血状态,在指导临床用药及预测 CMVT风险方面有重大价值,为在VTE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误区的临床医师提供参考[30]。但是TEG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检测成本较高等。对于TEG在CMVT形成诊疗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的探究。在不久的将来,相信TEG将广泛应用于该疾病的诊疗及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