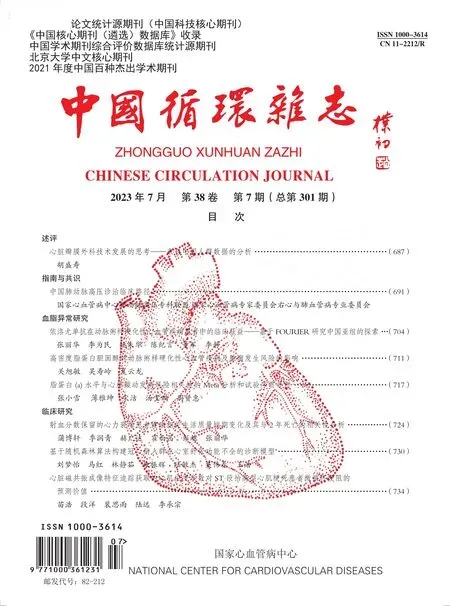围绝经期女性代谢异常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进展
孟旭 杨伟宪
围绝经期反映了卵巢卵泡功能的丧失、卵巢分泌激素的减少和月经周期的永久性停止,包括从临床上或血激素水平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的迹象,持续到末次月经后1 年。心血管疾病(CVD)是绝经后女性的主要死因[1]。既往研究发现,与同龄男性相比,女性绝经前CVD 患病率较低,这或与雌激素对女性的保护作用相关[2]。女性绝经后,冠心病患病率显著升高,在绝经后10 年尤为显著。大量研究发现,绝经后的病理生理改变不仅局限于激素水平的变化,还可能带来血脂异常、脂肪再分布、血压升高、胰岛素抵抗等代谢异常,引起血管结构的改变,进而导致CVD 风险升高[1]。因此,早期识别围绝经期女性的代谢异常对于及时采取适当干预措施以降低CVD 风险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围绝经期女性血脂、血糖、血压等的变化特点及其与CVD 的关联。
1 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的变化
激素水平变化是与围绝经期相关的主要生理变化之一。卵巢主要分泌雌二醇和孕激素,其中雌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之一,支配第二性征,影响女性生殖系统的发育和功能。雌二醇在育龄女性体内持续存在,绝经前平均水平为100~250 pg/ml,绝经后逐渐下降到10 pg/ml[3]。更年期综合征与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有关,如睡眠和情绪紊乱、血管舒缩症状(包括潮热和盗汗)、泌尿生殖器官萎缩、骨质减少和骨质疏松、精神障碍、性功能障碍、皮肤损伤、CVD、癌症、代谢紊乱和肥胖等[4]。
2 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
一般认为,女性代谢综合征风险在绝经前较同龄男性低,但绝经后风险反超男性,且高于绝经前女性[5]。SWAN 研究结果显示,不论年龄与现存CVD 危险因素如何,代谢综合征发病率从末次月经发生前6 年到后6 年逐渐增加,13.7%的女性在末次月经时检出代谢综合征[6]。WOBASZ 研究对随机纳入的20~74 岁的7 462 名女性进行横断面分析,发现绝经后女性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比绝经前女性高3.3 倍[7]。这均提示女性在围绝经期存在代谢综合征患病率上升的趋势。
3 脂质代谢紊乱
3.1 性激素与脂质代谢
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主要由于雌激素本身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作为底物在卵巢中合成,而绝经期卵巢不能利用循环LDL-C合成雌激素,从而导致雌激素产量下降和循环中LCL-C 水平升高。SWAN 研究指出不同脂质成分变化与更年期状态的改变以及相应的雌二醇和促卵泡激素(FSH)的浓度有关,雌二醇与总胆固醇(TC)和LDL-C 水平呈负相关,FSH 水平最低的女性TC 和LDL-C 水平最高[8-9]。此外,高水平的游离雄激素指数与较高的TC、甘油三酯(TG)和 LDL-C 水平以及较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相关,且低水平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高水平的游离雄激素指数与CVD 风险密切相关[9]。
动物实验表明,雌二醇在线粒体中脂肪酸β-氧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芳香化酶(一种雌激素合酶)敲除小鼠模型中,肝组织中未检测到雌二醇,信使RNA(mRNA)的表达也减少,参与脂肪酸代谢的酶活性降低;雌二醇替代治疗可恢复雌激素合酶敲除小鼠模型的mRNA 表达,并增加参与脂肪酸代谢酶的活性[10]。因此,雌二醇水平的降低可能会下调人体有效能量消耗所需基因的表达以及脂肪酸和脂质分解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导致绝经后女性发生脂质代谢紊乱。
3.2 血脂谱的改变
围绝经期之初,女性血脂谱开始改变,主要表现为TC、LDL-C、TG 水平的升高。SWAN 研究发现TC、LDL-C 和载脂蛋白B 均在绝经期前后1 年内显著升高,且这种效应独立于绝经年龄,可进一步导致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11]。一项纳入593名中国健康女性的队列研究发现,校正年龄、体重指数、身体活动和降压药使用等混杂因素后,TC、TG 和TC/HDL-C 比值均在围绝经期晚期显著升高并达到峰值[12]。一项纳入韩国人群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结果,且进一步发现血脂和脂蛋白水平异常的趋势在体重指数<23 kg/m2的人群中更为显著[13]。
在围绝经期女性中,HDL-C 与CVD 风险的关联趋势不同于年轻女性,且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在年轻女性中,HDL-C 具有独立的心脏保护作用,这种作用可能与HDL 颗粒可促进胆固醇外排,从外周细胞中清除胆固醇相关。在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中,HDL-C 升高可能与CVD 风险升高相关。有研究发现,在HDL-C 水平较高的绝经后女性中,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水平更高,可能与围绝经期HDL 颗粒的质量发生了变化相关[14]。SWAN 研究显示,HDL-C 水平从绝经前逐渐升高,在绝经过渡期达到峰值,随后HDL-C 水平逐渐下降,直至绝经后晚期[15]。也有研究表明围绝经期HDL-C水平下降。一项对541 名健康中年女性随访的队列研究发现绝经后女性HDL-C 水平下降(平均0.53~0.43 mmol/L),LDL-C 水平逐渐升高(平均3.14~3.33 mmol/L)[16]。纳入6 908 名中年女性的WHILA 研究也发现绝经后女性HDL-C 水平明显低于绝经前女性[17]。不同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由于血浆总体HDL-C 水平难以全面反映HDL-C 伴随绝经状态发生的变化。因此,近年来许多研究针对HDL 亚类进行分析,发现HDL 亚类比例的变化比HDL-C 总量的变化与更年期状态关系更加密切。如大多数研究表明,围绝经期和绝经期的特征是颗粒较小的HDL3-C 水平升高,而对心脏有保护作用、颗粒较大的HDL2-C 水平降低[14]。对HDL 亚类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有助于发现更有效的围绝经期女性CVD 风险的预测因子。
3.3 血脂新指标与围绝经期
尽管HDL 与CVD 风险的关联尚不明确,有多项研究报道绝经状态的进展与高水平的TC/HDL-C比值呈正相关,且TC/HDL-C 比值可能比TC 具有更好的CVD 风险预测价值[18]。WHILA 研究17 年随访结果证实,TC/HDL-C 比值的升高与缺血性心脏病相关(HR=2.30,95% CI:1.70~3.11),对中年女性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风险有很好的预测作用[19]。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队列研究探讨了中国女性在更年期期间血脂谱的变化,发现与绝经前女性相比,TC/HDL-C 比值在围绝经期阶段达峰值,但HDL-C 在不同绝经状态的分组中无显著变化[12]。目前多数研究认为TC/HDL 比值对女性CVD 风险具有潜在的预测价值,但目前相关研究依然较少。
多项研究证实,非HDL-C 比LDL-C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CVD 发病风险的预测能力更强[20]。非HDL-C 也包含脂蛋白a[Lp(a)],Lp(a)不仅具有促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还具有抗纤溶作用和促炎作用[21]。但非HDL-C 和Lp(a)在围绝经期女性人群中的研究较少。之前有横断面研究显示,绝经后女性非HDL-C 水平高于绝经前女性[22]。一项中国队列研究发现,在40 岁以上女性人群中,代谢综合征发病率随着非HDL-C 水平的升高而升高,多因素校正后,非HDL-C 是增加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23]。SWAN 研究表明,Lp(a)水平在围绝经期后期和绝经后早期达峰,但研究随访时间有限,缺少绝经后Lp(a)水平变化的长期随访数据。美国女性健康研究发现,中年时期所测的Lp(a)水平每增加1个标准差,未来冠心病事件风险增加10%~20%,且与冠心病发病年龄无关[24]。目前极少有研究针对非HDL-C 和Lp(a)水平随月经状态的变化进行纵向观察,围绝经期是否为非HDL-C 和Lp(a)水平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仍需进一步研究。
4 体重与体脂增加
内源性性激素水平的改变可能影响女性脂肪组织的脂质代谢。生理状态下,卵巢雌激素可促进外周脂肪的储存,主要分布于臀部和下肢皮下区域,而雄激素则主要增加内脏和腹部脂肪的积累。在围绝经期,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而雄激素水平的相对升高是导致体重增加和机体脂肪重新分配的主要因素。
女性绝经后较绝经前体脂含量显著升高,且更易表现为中心性脂肪积聚,腹型肥胖发生风险显著高于绝经前。Kim 等[25]报道,尽管绝经前后女性体重指数无显著差异,但绝经后腰围更大。SWAN 研究发现雄激素相对过剩(较高的基线睾酮/雌二醇比值)可预测围绝经期脂肪代谢紊乱和肥胖的发生[8]。此外,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在围绝经期开始时下降,循环中活性睾酮水平升高。有研究表明,增加活性睾酮可以通过腹部脂肪的脂肪细胞中的雄激素受体直接调节内脏脂肪的积累,游离睾酮水平与绝经后女性的体重指数和腰围相关[26]。
5 血压水平升高
女性高血压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NHANES 研究报道,根据2017 年美国心脏病学会与美国心脏协会高血压指南制定的标准,绝经前女性高血压患病率为19%,围绝经期(定义为45~54岁)女性为44%,绝经后女性则上升至75%,其中围绝经期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增长速度最快[27]。但是,绝经期女性高血压患病率的升高由衰老所致还是与雌激素水平的变化相关,或与两者均相关,目前尚无高质量临床证据予以证实。近期一项Meta 分析发现,早绝经(绝经年龄<45 岁)女性比正常年龄绝经(绝经年龄>45 岁)女性高血压风险增加(OR=1.10,95%CI:1.01~1.19,P=0.03)[28]。
内皮功能障碍和血管功能减退是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关键启动因素[29]。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雌激素受体(ER)在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中表达,雌二醇可以通过ER 依赖和ER 独立的机制引起血管舒张。雌二醇可诱导内皮细胞内游离钙浓度升高,促进内皮源性一氧化氮的产生。此外,雌二醇可激活腺苷环化酶活性,增加环磷酸腺苷(cAMP)的合成,而cAMP 可作为第二信使扩张血管。雌二醇还能减少血管紧张素Ⅱ、内皮素-1 和儿茶酚胺等缩血管物质的合成[30]。以上均表明雌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是导致围绝经期女性血压升高的原因。此外,最近的一篇综述总结了T 细胞在免疫介导的高血压中的作用,发现绝经前女性在雌激素的保护下可抵抗免疫介导的血压升高,但这种保护作用在绝经后消失[31]。此外,肥胖以及伴随围绝经期发生的一系列代谢紊乱均可能通过导致胰岛素抵抗、交感神经活动增加、钠潴留和内皮功能障碍等机制导致高血压。
6 胰岛素抵抗与2 型糖尿病(T2DM)风险升高
围绝经期与较高的T2DM 风险相关[32],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围绝经期T2DM 风险的增加或独立于年龄的增长。SWAN 研究发现,围绝经期雌二醇水平的降低可增加47%的T2DM 发生风险[33]。一项中国观察性研究发现,早绝经(45 岁之前)可增加20%的 T2DM 风险[34]。WHI 研究发现生育寿命较短(<30 年)的女性较生育寿命中等(36~40 年)者增加37%的T2DM 风险[35]。这些结果均为校正年龄后所得,表明雌二醇缺乏是导致绝经期T2DM 风险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35]。
在围绝经期,内源性雌激素显著下降,并伴随体重增加、脂肪组织重新分布和代谢水平的下降,研究表明内脏脂肪组织质量和中心性肥胖与胰岛素抵抗显著相关,进而导致围绝经期女性T2DM 风险升高[36]。
7 CVD 风险升高
女性CVD 患病年龄高峰比男性晚10 年,在45~54 岁之后显著增加。Framingham 研究于1976 年报告了绝经后女性比同龄绝经前女性的心血管事件风险更高,首先提出绝经后女性可能伴有CVD 风险变化[37]。随后,多项研究着眼于女性CVD 风险与年龄和月经状态的关联。研究发现,女性围绝经期心血管结局可能劣于同龄男性,如女性首次心肌梗死死亡风险是男性的两倍[38]。此外,多项研究着眼于探索女性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心血管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发现CVD 危险因素的积累(如血脂、空腹血糖和血压升高,腹部脂肪积累等)在这段时间前后增加[39-40]。
8 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围绝经期对心血管危险因素影响的证据十分有限,并且由于方法学的限制,相关研究结论的外延性不佳。首先,各研究对绝经状态分期标志不一致[33]。目前绝经的诊断依旧依靠临床诊断,无准确生物标志物可被用于绝经的诊断,因此各研究在评估绝经症状和生理变化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影响围绝经期定义的准确性。其次,只有少数纵向研究通过长期随访观察了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随时间的变化,有助于确定围绝经期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之间的关联。然而,各纵向研究的分析方法和所使用的协变量之间存在差异,结果的可比性较差,且普遍缺乏以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等硬终点为主要终点的前瞻性研究。第三,纵向研究可能产生一些时间相关偏移,如“永恒时间偏倚”[41],导致时间和结局之间的关联分析存在误差。因此,未来研究可招募年轻女性,并进行足够长的随访,观察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以明确时间-事件关联[41]。最后,围绝经期和CVD 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尚不清楚,当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尽管有研究探讨了铁代谢、DNA 损伤反应机制和环境因素等可能在围绝经期与CVD 的关联中起的作用,但相关研究并不深入,进一步进行探讨有助于为临床提供潜在的干预靶点[28]。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