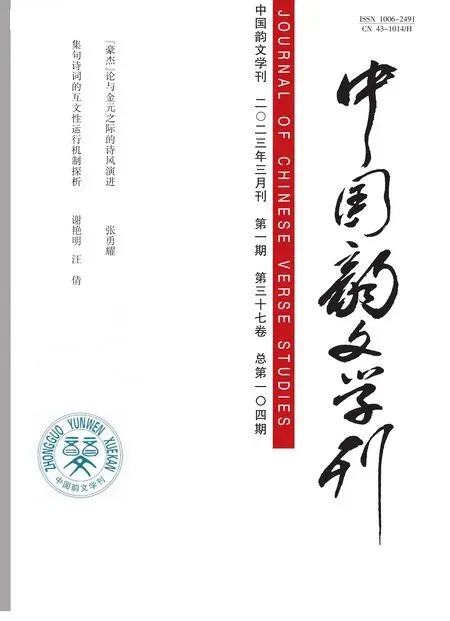查士标诗画会通生成路径探赜
戴欢欢,任声楠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清初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画坛推崇得“古人之匠心”的复古主义画学观,新安画家与此不同,他们论画不仅主张向古人取法,而且以天地为师,注重师法自然,以描摹黄山、白岳等新安山水为能事。新安画家大多以遗民自居,在画作中抒发遗民“幽怀”,显示出对清皇室宠眷下的正统画坛的扞拒。故黄宾虹曰:“独新安四家,趋向超逸,不为邪甜俗赖。”[1](P193)新安四家中,查士标的诗画作品传世最多且成就较高。查士标(1615—1697)字二瞻,号梅壑,又号梅壑道人、邗上旅人、懒标、后乙卯生等,徽州休宁人。有《种书堂遗稿》《种书堂题画诗》传世,其中《种书堂遗稿》三卷分别收录五言律诗111首、七言排律99首、七言律诗50首(卷三间有少量七绝和七言排律),共260首;《种书堂题画诗》二卷分别收录五绝82首、七绝142首题画诗。查士标一生画作甚多,据《查士标书画作品目录》仅有纪年的各类卷、轴、扇、屏、册等就有260余幅,无纪年的作品有180余件,这些画作在国内主要散布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地,在国外主要流向美国和日本。查士标的诗画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声名显赫,清代著名诗论家查慎行评曰:“古来绝艺兼者罕,钟王顾陆名各专……吾兄妙手靡不备,书法入圣诗能仙。偶然点染作图画,别有天授非人传。”[2](P244)查慎行以“圣”“仙”“天授”称誉查士标的书法、诗歌、绘画的艺术特征,高度赞扬了查士标的艺术成就。查士标诗画兼善,其门人金之缙论其诗画曰:“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在创作实践中,查士标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还依据诗句作诗意画,如故宫博物院藏《唐人诗意图》款识曰:“柳边人歇待船归。士标画唐人诗意。”此图是查士标据唐人温庭筠的《利州南渡》诗而作,画面近景在枯柳前的水边滩涂上有两高士坐于岸边,与中景小舟上的老翁相呼应,将诗句中人对船的“待”意表现了出来。以画笔写诗情,于诗句绘画境,查士标通过理论互涉、技法互用、审美互补三个路径实现了诗画会通。
一 理论互涉:“有神”诗与“天真”画
诗歌通过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实现“言志”“缘情”的功能,绘画则抓住某一特定瞬间的空间形象表达画家的意趣,所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二者本属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诗和画的契合点在于它们都是通过描写客观物象来表达创作者的情趣。因此,自苏轼“诗画一律”论提出之后,中国文人画家均强调诗与画的融合统一,在理论层面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等,在创作实践中,文人画家通过据诗作画或赏画题诗等方式实现了诗与画共生、相得。查士标诗画会通的路径之一是融合诗学与画论,并将诗画相融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在诗中描写画的意境,作诗题画,在画中描绘诗的意趣,以画绘诗。
查士标好友曹中翰寄诗曰:“鹤品梅胎迥不群,坡仙诗句柳公文。墨痕点染倪高士,笔阵纵横晋右军。千里素心通海岳,几年幽梦隔江云。联床夜雨知何日,明月清风总忆君。”[3](P581)对查士标的个性和诗文书画的艺术特点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他以“坡仙诗句”类比查士标之诗,正是基于二人的诗歌都具有天真神韵的审美风尚。查士标化用苏轼诗句,将诗学引入画论之中,其论画云:“‘画不求工笔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二语画家丹髄也。”[4](P102)查氏此语化用了苏轼“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之语,苏轼认为诗歌不必刻意追求工巧,即反对雕琢,注重坦率、真朴、自然之诗。苏轼的诗画理论是相通的,其题画诗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5](1525—1526)认为虽然诗与画的艺术形式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重形似,注重写物之神韵风度,追求天然工致、清新脱俗的艺术旨趣。查士标的诗画理论与创作实践都体现了这一艺术主张,他论诗重“有神”之作,即强调诗歌要抒发作者的真性情。查士标认为好诗出自诗人兴致,其《重九前一日登木末亭同方木大》诗曰:“兴至自矜诗句好,时危谁识客游艰。”[3](P584)而自然山水可以引发诗和画的创作兴致:“……三山遗胜迹,题品待词人。兴到留高韵,诗成信有神。”[3](P575)认为诗人之“兴”得自然山水等物象之助,诗之神韵正是由诗人“兴到”而成。又如其题画诗曰:“堤边茅屋柳丝丝,隔岸晴岚荡碧漪。谁向桥头归策蹇,锦囊应贮看山诗”诗的前二句写画中景物:岸堤、茅屋、嫩柳、小桥、和风、碧波等,这些意象的组合共同构成查士标诗、画的主要内容。后二句则是诗人由画引发的想象,用李贺“锦囊贮诗”的典故意在表达画中人由自然美景引发诗兴而成大量佳句。查士标的诗画都本乎性情,是他个性、才情的流露,正如其门人金之缙所谓:“先生诗本乎性情,如白云自流、山泉冷然,不事雕饰,而神韵淡远,是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也。”[3](P602)査诗不尚雕琢,抒发其淡泊的性情,故其诗如“白云”“山泉”,具有真朴自然的特点。查士标将重天真神韵的诗画观运用到其创作实践中,其题画诗曰:“谁欲沧江着钓蓑,野云野树荡烟波。老来作画嫌工细,也似诗篇漫兴多。”[3](P603)认为其精巧细致之画与率意而为的诗篇有相通之处,而二者的契合点正在于它们是作者天真个性与诗画观念的呈现。
查士标论诗重抒发性情的“有神”之作,论画则推崇表现画家“天真”意趣的写意画,主张以画写“幽怀”,强调师古不泥古,反对蹈袭不化形成的“纵横习气”。查士标《题为淑南作溪桥策杖图》曰:“常见世人论画,率以工致为难。至元四大家得写意三昧,超然笔器蹊径之外,则非常格所测,求解人不易得也。”[6](P264)认为追求工巧精致的画工画为“常格”,而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得写意真味。元四家之一的倪瓒论画曰:“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7](P309)黄公望曰:“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才多便入画工之流矣。”[8](P96)倪、黄二人所谓“逸笔”“逸墨”是文人写意画的主要特点,即追求画之神韵而不求形似,用笔要洒落有致,能表现画家的个性才情。查士标论画强调以画写意抒情,他评好友王铖的画云:“公余暇日开书卷,兴写幽怀入画图。”(《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为任庵画意并题》)[3](P588)绘画的创作动机需要画家兴致的催发,而画的内容需要表现隐藏在画家内心的情感,即主张以画写“幽怀”。因此,查士标推崇能在画中抒发真性情的“天真烂漫”之画,其《题为天一作仙居飘渺图》曰:“余家旧藏王孟端《溪山萧寺图》,又从小辋川得观《长林书舍图》,二图皆穷幽极缈,细入毫发,而天真烂漫,一一自然,信绘事名家也。”[6](P264)认为两幅图精微自然、天真烂漫,而要实现这一艺术境界,则需要画家在画中写胸中逸气。查士标题程所作山水册云:“间乘作画,写胸中磊落之气,深得摩诘神理……故多飘逸之致。”[6](P259)认为程画中的飘逸风格正是其胸中磊落之气的体现。查士标论画尚“天真”“自然”,其画亦有“天真”之趣,《国朝画识》评曰:“其画以天真幽淡为宗,无一点纵横习气。”[9](P526)查士标画之“天真幽淡”与其诗之“神韵淡远”不谋而合,都是他淡泊情志在诗画作品中的流露。查士标论画既重写“幽怀”,又重师法古人,他创作了大量拟二米、倪瓒、黄公望等人的仿古画作,模仿前人的笔墨技法、构图造境等。但査氏反对拘泥古人成法而不变通的做法,其《题自作山水册》云:“余近日专师倪迂,觉梅花庵主犹未脱纵横习气,乃知善学下惠,正不必拘泥古人蹊径,所谓老僧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也。”[10]认为倪瓒仍未脱“纵横习气”,因此主张灵活地取法古人,师古不泥古。“吾山学米,方壶亦学米,然源同而派异,以各具性情,故能专家也。”[6](P262)查士标认为他和方壶都师法米氏云山,而源同派异的原因在于二人各具性情。
概而言之,查士标论画与其诗学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论诗重“有神”之作,不尚雕琢,强调诗要本乎性情,论画推崇“天真烂漫”之作,主张在画中抒发性情,表现画家的“天真”意趣。在创作实践中,查士标在诗画中抒发性情,达到了诗画交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学与画论的交互作用促成了查士标的诗画会通。
二 技法互用:诗画中的象征表现
查士标不仅从理论层面探索诗画交融互通的路径,而且在写诗与作画的创作实践中共用象征的技法,将诗情与画意融合为一。查士标成长于理学氛围浓厚的徽州地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查士标对明王朝有着强烈的忠贞之心,对明清易祚的战乱充满愤懑之情,其门人黄逵序《种书堂遗稿》曰:“先生于壮年时弃诸生,无以发泄其奇气而尽寄于骚雅。”[3](P565)查士标目睹明朝山河破碎、家乡乱离的惨况后,以“弃诸生”的人生选择彰显其不与清廷合流的遗民态度。明亡后,新安画家的处世态度与趋附清皇室而获得画坛正统地位的“四王”不同,渐江反抗清廷、孙逸流寓芜湖、郑旼终身布衣……查士标以遗民自居,与清室权贵不合流:“二瞻性疏懒,嗜卧,或日晡而起,畏接宾客,盖有托而逃焉。先时有王额驸者,贵甚,拥高赀,人冀一见不可得,三顾二瞻终不答。”[11](P113)于是,查士标运用象征技法将其遗民“奇气”宣泄于诗画之中,其胞弟査士模所著《皇清处士前文学梅壑先生兄二瞻查公行述》载:“崇祯之末,先兄因乱弃去举子业,以六经子史为尽性修身之学,而寄兴于歌诗书画。”[12](P65)在查士标诗歌的话语体系中,桑梓之情象征故国之思,其《生日寓感》曰:“山稀江枫霜叶赤,犹思故国旧桑麻。”[3](P587)“桑麻”借代故乡,故乡象征故国,査氏诗中还大量使用“羁旅”“故人”“故乡”“客”等词,流露出他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象征着他对故国的眷恋。查士标还以具象的景或物象征遗民的忠贞气节,其《赠周勿庵道士》:“……最爱岳王坟上月,楼开时节照孤山。乾坤不改旧苑庐,种出桃花万历余。”[3](P595)诗中的“月”不仅是诗人眼前的景,还象征着他对明王朝的赤子之心。
山水林泉为遗民高士提供了栖身之所和精神寄托。北宋郭熙云:“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善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林泉者,正为佳处故也。”[13](P574)明亡后,查士标“矢口不谈当世事”,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寄情山水,以诗画自娱,其诗曰:“行尽千山更万山,终朝蹑屐不曾闲。幽人自信无他事,只与渔樵共往还。”[3](P609)他自称“幽人”,在山林中与渔樵交游,表现出超脱尘俗的淡泊。查士标笔下的山水空间是可居可游的,汪憺漪曰:“仆取之画,则必有别情别趣,生气飞动,其峰岭林壑,俱另是一番境界,迥出意表,令观者神情轩豁,恨不将身跳入其中……吴岱观、查二瞻庶几超俗,真可人之意。”[14](P259)汪憺漪观査氏画有“将身跳入其中”之感,正是由于其画有多重语义的“别情别趣”。总之,查士标可居可游之画是其避世隐居的心理投射,在画中通过时空造境和笔墨皴擦营造出的诗意画境象征他的隐逸情怀,如其《青山卜居轴》,此轴以平远之势写近水远山,用笔简约,以淡墨勾勒山的轮廓,再施以皴染虚擦,水景以留白技法造境,构建出一片气韵荒寒、萧疏冷寂的画面。图中虽无人烟,却在近景枯木下构一小亭,暗示画中之境为高士卜居之所,画作上端空白处有款识曰:“坦腹江亭枕束书,澄清洲渚见空虚。疏篁古木悠悠思,何处青山好卜居。仿倪云林画法。查士标。”诗人在广袤的画境中重点关注了江亭、疏篁、古木等可居、可游处,这正是查士标心中的佳居之所。查士标在画中寄寓情志,立象以尽意,将隐逸山林的淡泊志趣采用象征技法在画中予以呈现。
查士标的象征技法还体现在其画作对题画诗意的兴发,清人沈德潜论题画诗曰:“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又如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拈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15](P19-20)认为题画诗自杜甫始,其特点在于“不粘画上发论”,即题画诗的主旨与画作本身并无直接的联系。查士标题画诗的内容并非对画面进行全景式的描绘,而是注重表现由画中的人、物、景等意象引发的诗意联想,即画可以通过象征引发诗兴。如查士标的《仿倪瓒山水图轴》,此轴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院,其中款识曰:“不见名图近十年,壁间林壑尚依然。秋来景物清如水,谱入南华第几篇。丁未八月,旧藏倪迹。查士标。”此卷用笔简约,画中的山石树木大多采用墨线勾描轮廓而不作渲染的白描画法,中景为大片的空白水域,近景竹、树枝疏叶稀,呈现出一片萧瑟、荒寒的清秋山水。查士标赏画时,萧疏的画面引发了他的诗意兴致,他从画中体会到清秋的虚静、空灵,“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16](P376)。虚静、空灵的画面与以虚静为美的《庄子》成为查士标画作与题画诗的契合点。
三 审美互补:诗画时空造境的虚实与动静
查士标论画尚简远,其画跋曰:“大痴画以《江山胜览卷》为最,恨微伤繁冗耳。元人画以趣胜,惟用笔淡远得之,以是益悟简贵之难,不独在画也。”(《题为五老道翁作山水册》)[6](P261)认为黄公望的《江山胜览卷》的不足在于用笔烦琐庞杂,提出元画的高妙之处在于能够表现画家的意趣,而只有用简练的笔墨营造出冲淡高远的意境才能实现对画家意趣的表达。查士标所谓“用笔淡远”“简贵”即在画面中通过留白实现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绘画中的虚实相生是将实写的笔墨线条与虚写的空白交融渲染,把实与虚、有与无融合成圆融一体的完整意境。这一审美意境与道家对虚实、有无的哲学思考有关,《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17](P5)认为有与无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转化,生生不息。道家将这一哲思运用于绘画、音乐领域,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7](P102)苏辙《道德经解》训“大音希声”曰“非耳之所得闻也”,训“大象无形”曰“非目之所得见也”。从听觉与视觉的角度将有无、虚实统一成整体,这一观念在明清画论中大量存在,笪重光《画筌》曰:“画之空处,全局所关,即虚实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处妙在通幅皆灵,故云妙境也。”[18](P195)秦祖永《画学心印》曰:“气韵自然,虚实相生,此董巨神髓也。”[19](P555)查士标之画用笔简约,形成虚实相生的审美境界。清冯金伯《国朝画识》论曰:“画初学倪高士,后参以梅华道人、董文敏笔法,用笔不多,惜墨如金。风神懒散,气韵荒寒。”[9](P526)其气韵荒寒画风的形成原因之一在于画面笔墨不多,如其作于康熙十四年(1675)八月的《溪亭独眺》,此图模仿倪瓒《林亭远岫图》章法,以平远视角写近水远山,近景以寥寥数笔写水边枯树以示荒寒之境;中景以留白之法示平静开阔的水面,以虚补实;远山以淡墨渲染,用笔极简,化实为虚。图画中以笔墨实写的枯木、小桥、滩涂、远山与以留白技法虚写的水面、天空交相辉映。画幅上端空白处有款识曰:“时乙卯桂月,写于待雁楼,查士标。”与画面中的山水之境浑然一体,使画面和谐有致。
传统诗学中亦注重通过实境的营造引发审美想象的虚境空间。晚唐诗人司空图论“含蓄”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20](P40)主张意在言外,认为诗人的情思可以在虚实相生的诗镜中表现出来。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1](P688)以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类比盛唐诗在有形的诗句中传达出无形的意趣。清薛雪《一瓢诗话》云:“诗有从题中写出,有从题外写入,有从虚处实写,实处虚写。有从此写彼,有从彼写此。”[22](P98)主张化实为虚,虚实相生。查士标对道家思想十分推崇,曾灿说查士标曾学习道家的“吐纳之法”,其《生日寓感》诗曰:“梅妻鹤子安知老,李耳庄周实可师。”[3](P587)在老庄思想影响下,查士标形成崇尚虚静、淡泊的个性,其好友曾灿序其《种书堂遗稿》曰:“先生襟怀洒落,无往而不自适,盖其心定则神凝,神凝则气全。庄生所谓‘蒸成菌,乐出虚’者,其殆是欤?”[3](P566)用庄子“乐出虚”的典故解释查士标心定、神凝、气全的性格特征。查士标在其诗画造境中融合虚、实,其题画诗曰:“短策秋林下,虚亭水竹间。无人成独往,惟与白云闲。”[3](P599)水竹间的亭子中是无人的空境,但却给人留下审美遐想空间。又曰:“听松是何季,画松是此日。有声与无声,请向画中识。”[3](P599)画中的无声“松”让人对现实中“有声”松产生联想,将对立统一的有声实境和无声虚境的矛盾体熔铸于诗画之中。除题画诗外,查士标其他的诗同样注重虚实相生的审美趣味,如其《双峰闲眺时欲往金山》:“推窗四面江无际,最爱金山供席前。明日若从山上望,不知何处起孤烟。”[3](P591-592)前二句写窗前江面、远山的实景,后二句则是诗人想象的虚景,设想视角转换后可能产生不知身处何地的情状,而将从山上望山下的情景通过留白引发读者对诗歌意境的再创造,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查士标的诗画空间造境注重呈现动静互补圆融的审美特征,其诗中的动与静通过营造意境来实现,如其《送书云》:“送客江亭望,沉吟野日斜。一帆何处泊,离思满天涯。”[3](P591)诗中“日斜”“江亭”点明了此诗的时空布局,玩味这首送别小诗,仿佛一幅动态的送别画卷在读者眼前展开。诗人在江亭送友,主客吟诗寄情,久久不忍相别,“望”字描绘出主客别离后,诗人独立江头遥望故人的情态。查士标之画亦呈现出动静圆融的审美意境,他通过在画中题诗或抓住画面中物之形、人之态两种方式呈现画中的动态特征。如其题画诗曰:“苍翠入溪流,熏风吹水榭。不用执蒲葵,开窗消长夏。”[3](P597)图画本是反映特定空间的静态画面,查士标此诗表现出他在赏画过程中关注的是画中的动态之景,流动溪水中倒映着嫩绿的草树,和风吹入水边亭台上的屋子里,给画中人带来阵阵凉意。查士标通过在画中题诗,在诗画空间中表现动与静的情态,二者相得益彰,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张力。查士标还善于抓住画面中物体的形貌和人的姿态来表现静中含动的审美空间,辽宁省博物馆藏其《山水图》有画跋曰:“翠山献连平野,垂杨覆古堤。斜阳人欲渡,风色满前溪。此余癸丑年所画,距今六年矣。画成颇自见赏,藏之笥中,未易示人。偶汉白道兄鉴而爱之,不能释手,感其意刻以相赠,而绻恋之色犹见于眉字间。大凡物必归于所好,况翰墨雅事。时节因缘,不可强也,并记之。”此图采用倪瓒的三段式平远构图,近景写水边滩涂上青翠欲滴的嫩柳,中景为平静的水面,岸边有成片的柳林,远景山峦以淡墨设色,绵延起伏,若隐若现。画面采用典型的“以大观小”的空间视角俯瞰近水远山,中景水边刻画精微的渔人、行人、小舟、驴等最能体现画面化静为动的特点,渔人的撑竿向后倾斜力图使已经抵岸的小舟保持平稳,行人身体向前而头转向后方,绳子短而直,驴腿微微弯曲,这些姿态表现出行人欲渡河,而驴子不肯上船的情态,查士标将这一动态特征在题画诗中以“人欲渡”三字写出。
查士标诗画会通的生成路径具有内外一致性。从外在形式的角度来说,赏画题诗是查士标进行诗歌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以诗人敏锐的视觉感受和独特的想象力欣赏自己或他人的画作,发掘画中的诗意,“一遇虎头为点染,品题又见画中诗”[3](P594),其《种书堂题画诗》中的两百多首题画诗都是他赏画时的诗意生成。查士标不仅赏画题诗,还以诗作画,其《题自作山水图》画跋云:“春水孤村过,荆溪累画西。晓日鸣柳起,山雨竹鸡啼。樱桃花已落,靡芜绿未齐。酒船寻贺监,早晚到幽栖。倪高士《西溪草堂诗》。意其时当有佳图,惜未流传。偶补此作,并录其诗于上。画成殊类《耕云轩图》笔法,脱去云林本家习气,视余平日仿倪画大有径庭也。”[6](P262)此跋记录了查士标据倪瓒诗作画的情形,他仿倪瓒的画力图摆脱倪瓒的画风,体现了他仿古出新的画学思想。大自然中的山水美景是查士标诗画创作灵感的“触发器”,其《和文同舟中早起看雨之作》云:“雨余忽听诗中画,急起推篷对米颠。”[3](P592)此诗的创作兴致由查士标欣赏雨景引发,并由诗兴触发画兴,用米氏云山之法写眼前充满诗意的雨中山水。从内容表现的角度来说,查士标的诗画以描写自然山水为主,他重“有神”之诗,尚“天真”之画,主张以诗画抒发性情,实现诗画在情、境、意等方面的圆融会通。在创作实践中,查士标通过在诗画中互用象征技法,形成其诗情与画意的多义语境,拓展了其诗画表现的艺术张力。查士标还注重在其诗画时空造境中呈现虚实相生、动静圆融的审美意蕴,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查士标诗画会通艺术境界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