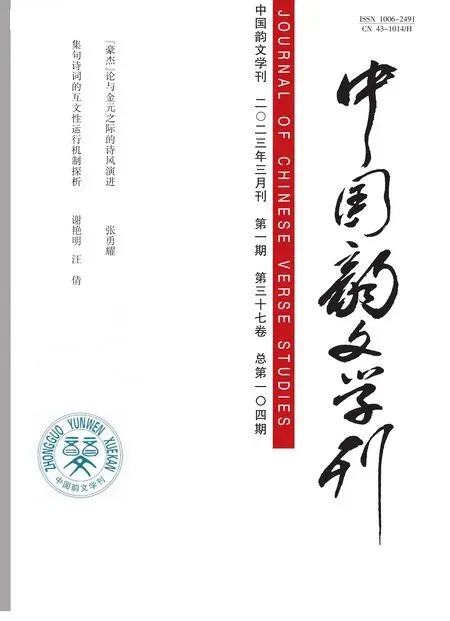论白居易与韦应物诗歌惭愧表现之异同
吴嘉璐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绪言
惭愧,是人类常见的情感,但遍寻中国诗,却发现中国诗人较少在其中表现惭愧的情绪。即使最早如《古诗》中的故夫遇前妻,忏悔自己不该喜新厌旧的诗句,其惭愧也是建立在“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的市侩的、现实利益的比较上的,似乎欠奉真心。因高尚人格被赞许的诗人陶渊明和杜甫,其诗中虽有自省的惭愧、悔恨,但亦较少围绕道德做文章,比如陶之名句“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不过是对自己既缺乏自由又不在高位而表示遗憾,再如杜甫“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与陶诗出于同一机杼;但陶与杜的诗中已经出现了对他者表达惭愧情绪的端绪,如陶之“顾尔俦列,能不怀愧”,是诚挚的对农人的惭愧,杜之“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是由衷的对妻子的惭愧。
中国诗人中,最集中表现对己对人的惭愧情绪的,当数白居易。白居易诗出现的单音节语汇惭、愧、悔、恨甚至连言惭愧的频次之高,相当惊人,从数量上看,惭有75首,愧有57首,惭愧连言的有10首;与之相近的悔有33首,恨也有67首。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不论是在官场或是日常生活中,都伴随着惭愧的情绪。目前虽然已经有论者注意到他与众不同的惭愧情绪,如陈家煌(1)陈家煌将白居易的惭愧全部归于“不自信” 心态,似可以商兑,参考《白居易诗人自觉研究》第三章第五节“尽责的任官态度所产生之‘不自信’心态”,台湾“中山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焦尤杰(2)焦尤杰从理想的崇高和知足心态分析白居易惭愧心理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辞官、饮酒和信佛是摆脱惭愧的途径,而事实上,知足与惭愧的关系并非是单线的,辞官以后白居易也未必不言惭愧,焦之观点也有所偏,参考《从白居易诗歌看其居官惭愧心理及摆脱途径》,《钦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土谷彰男(3)土谷大体上是从对君的惭愧转向对民的惭愧这一点来分析韦、白二人惭愧情绪的共性的,参考《白居易青年时期的选良意识——白居易和韦应物的惭愧的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3期。等,但尚未挖掘他惭愧表现中的矛盾,没能深入地分析其惭愧情绪与其人生理想、思想观念的关系。
在唐代诗人中,与白居易表现出相似的惭愧情绪的还有他的前辈诗人韦应物,假如对照韦、白二人的惭愧表现之异同,便能更深刻地分析中国诗人在诗歌中表现惭愧的原因、表现与影响,由此得以揭示缘何在白居易诗中,会展露如此高频、如此复杂的惭愧情绪。
一 韦应物、白居易诗中惭愧之情的类似表现及其成因
(一)韦、白“进亦惭,退亦惭”的惭愧表现
韦应物、白居易惭愧表现的相似性,最集中地体现在二人不论是在位为官、积极进取,还是暂不在位、急流勇退之时,都以有愧之人自居,对自身的外在境遇和内在心性都多有不满之处。韦之“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登楼寄王卿》)[1]( P162)一句很好地概括了这种不满,即不管是隐逸还是做官都有遗憾;白之“但愧烟霄上,鸾凤为吾徒;又惭云林间,鸥鹤不我疏”(《和朝回与王炼师游南山下》)[2](P1760)以“正言若反”的方式,道出自己既不配在人才济济的朝廷为官,又因凡俗之性未退,羞惭于在林间与高人隐士交往的心境。
具体而言,意欲在官场上有所“进”的二人,表现出了因未能尽到为官的责任,同时又违背隐逸的志向而感觉到的惭愧,这种惭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力感。如,韦应物将其郡守的职责称为“累”,一方面,他不断想要摆脱这种世俗的负累,逃离“烦”与“倦”的为官心态:
符竹方为累,形迹一来疏。[1]( P461)
(《游开元精舍》)
常负交亲责,且为一官累。[1]( P354)
(《答故人见谕》)
公府适烦倦,开缄莹新篇。[1]( P343)
(《酬张协律》)
同时提出自己虽然勤苦于政务,却又因政拙、无术而深感惭愧:
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1](P328)
(《答王郎中》)
牧人本无术,命至苟复迁。[1](P328-329)
(《答崔都水》)
政拙劳详省,淹留未得归。[1](P199)
(《赠李判官》)
特别是官事暂罢,得以小憩之时,他愈发感觉到自己的片刻逍遥对不起皇帝的恩宠: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1](P55)
(《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即使在大有作为的尚书省、任宰相的协助者左司郎中的职位,韦应物惭愧于自己居然拥有官员身份的情绪,也无法抑制:
顾迹知为忝,束带愧周行。[1](P499)
(《夜直省中》)
另一方面,与“摆脱负累”的愿望相应和,韦应物还在郡斋暂憩的场合,提到自己存有“退意”,即隐逸的志向: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1](P66)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每虑观省牵,中乖游践志。[1](P186)
(《因省风俗与从姪成绪游山水中道先归寄示》)
朝宴方陪厕,山川又乖违。[1](P340)
(《答令狐侍郎》)
韦应物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游赏山水、隐逸山林的愿望的诗人;本来在他的心灵图式中,“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仕与隐并非不能调和,但现实却屡屡事与愿违,正因不能彻底从官场中脱身,便导致了其在短暂的郡斋休憩里,也不能在山水的怀抱中得到愉悦感。上言之“乖志”,正是因无能感所造成的“惭”“愧”的写照:
宰邑乖所愿,僶俛愧昔人。[1](P527)
(《西涧种柳》)
徒令惭所问,想望东山岑。[1](P314)
(《答冯鲁秀才》)
与韦应物类似,白居易时常感觉有愧于自己现时的官位,因为自己没有才能,甚至是一个“虚薄”“懒慢”之人:
自愧阿连官职慢,只教兄作使君兄。[2](P1917)
(《奉送三兄》)
虚薄至今惭旧职,院名抬举号为贤。[2](P1515)
(《晚春重到集贤院》)
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
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2](P107)
(《纳粟》)
回首从前,提到自己能坐稳官位,不过是碰到了好时机:
偶当谷贱岁,适值民安日。
郡县狱空虚,乡闾盗奔逸。
其间最幸者,朝客多分秩。[2](P1712)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不配加封:
我转官阶常自愧,君加邑号有何功。[2](P1532)
(《妻初授邑号告身》)
在公务的闲暇,白居易亦想到自己还处在尘世中的汲汲宦场,未能满足隐逸的心愿,与韦应物时常流露的情绪一致,且其隐逸的愿望较韦更为强烈,出现的频次更高:
今年到时夏云白,去年来时秋树红。
两度见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2](P1025)
(《再因公事到骆口驿》)
遥愧峰上云,对此尘中颜。[2](P463)
(《病假中南亭闲望》)
顾我犹俗士,冠带走尘埃。
未称为松主,时时一愧怀。[2](P889)
(《庭松》)
悔从白云里,移尔落嚣尘。[2](P728)
(《寄题周至厅前双松》)
见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2](P619)
(《题元十八溪亭》)
自惭容鬓上,犹带郡庭尘。[2](P1929)
(《题报恩寺》)
不论是作为隐逸之符号的山,还是山上的云,不论是山下的松,还是清净的寺庙,都让白居易自惭形秽。与韦不同的是,白以无法隐逸为愧的诗作中,还突出了由老、病与愁带来的时间的迫促感,强调为官是出于回报君恩,但志业的实现总是充满重重阻碍:
病添心寂寞,愁人鬓蹉跎。
晚树蝉鸣少,秋阶日上多。
长闲羡云鹤,久别愧烟萝。
其奈丹墀上,君恩未报何。[2](P1070)
(《晚秋有怀郑中旧隐》)
唯惭老病披朝服,莫虑饥寒计俸钱。[2](P1504)
(《早朝思退居》)
与“进”的状况相对,即使韦、白两人已经完全处于“退”的状况,仍然时不时有惭愧的感觉涌现出来,韦应物的名作《晚归沣川》正说明了这样的情形:
名秩斯逾分,廉退愧不全。
已想平门路,晨骑复言旋。[1](P389)
平门是长安的城门,还想着平门的路意味着韦应物并非甘心退出官场、离开长安,辞官归隐本身,是让韦遗憾甚至惭愧的。由此可见,韦应物的官吏意识已经在心中生了根,即使是归隐了,也还在惭愧自己过去没有“当好官”,现在也没能从官场好好退出。当白居易真正选择闲职,过上类似隐逸的生活之时,他亦深感“退而有愧”,不过其惭愧之意较韦显得更复杂:
好住旧林泉,回头一怅然。
渐知吾潦倒,深愧尔留连。
欲作栖云计,须营种黍钱。
更容求一郡,不得亦归田。[2](P1996)
(《答林泉》)
衡门蜗舍自惭愧,收得身来已五年。[2](P2241)
(《履道居三首·其二》)
杭老遮车辙,吴童扫路尘。
虚迎复虚送,惭见两州民。[2](P1873)
(《去岁罢杭州今春领吴郡惭无善政聊写鄙怀兼寄三相公》)
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
始惭当此日,得作自由身。[2](P2198)
(《苦热》)
由上述诗句可知,首先,令白居易感到惭愧的是,他退居以后,仍然是穷困潦倒的,为了营生,他仍然需要“进”;其次,“退”时回想过往,深感于为官之道有所欠缺,于是,他竟然得出了自己不配为“自由身”的结论,即处“退”仍有所思虑,心灵无法平静,这与一般观念所想象的中国诗表达的宁静致远的隐逸情调有极大的落差。加之,白居易任州府长官之时,对统管、治理的区域,乃至其中的州民依依不舍,他惭愧于未能将民众的生活提到更高的水准线上。
(2)韦、白“进亦惭,退亦惭”的成因
对中国历代文人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成就了韦应物与白居易二人惭愧意识的表达。孔子虽未明言“惭”,但已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中更直接出现了对惭愧意识的具体论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更重要的是,孟子把“羞恶之心”纳入四端之一的“义”上,提出羞耻感是人类重要的道德情感之一;由此,“耻感意识”作为儒者自省的内在思想倾向,逐渐在古典文人的潜意识层面生根。
韦、白二人之惭愧表现得较他人突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者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基础。
首先,二人都积极仕进。韦应物以儒家用世思想为核心人生观。肃宗乾元二年(759),韦入太学读书,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此后,他始终没有远离仕途的念头。无论是早年所作的“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无路相追攀”(《观早朝》)[1](P440),还是晚年教育子侄的“纻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1](P485),皆是渴仕之辞。韦应物一生多次隐居,但每一次隐居之后官位都有所提升。其诗“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示从子河南尉班》)[1](P70)、“罢官守园庐,岂不怀渴饥”(《洛都游寓》)[1](P445),更表明在隐逸与从宦之间,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韦之隐居更多出于策略之隐,比如因为家庭经济的贫困而暂时居住在寺庙中休养生息,因此不能将他看作一个隐士,反而正是因为他的隐,才显示出他对仕途不变的追求。与之相似,白居易“世敦儒业”(《旧唐书·白居易传》)[3](P4340),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仕之后,更以“兼济天下”为志向,以入相为目标,积极进谏,乃至遭贬和遭斥。韦、白二人对仕进有如此强烈的愿望,但现实往往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或是社会的不稳定,或是上位者的阻挠,导致了他们在宦途上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挫败。我们可以在两人诉说惭愧情绪的诗作中体会“进而有难”的状况:韦应物的“仰恩惭政拙,念劳喜岁收”(《襄武馆游眺》)[1](P463)、“逍遥池馆华,益愧专城宠”(《春游南亭》)[1](P457),白居易的“我为同州牧,内愧无才术。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2](P1712)、“身为百口长,官是一州尊……病难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晚岁》)[2](P1609)所体现出的惭愧情绪,从积极的层面上看,成为二人在为官道路上努力进取的动力;从消极的层面看,是因“政拙”而无法回报“君恩”、略显迂腐的书生气的表现。
其次,韦、白二人不仅积极仕进,对儒家提倡的道德亦十分重视。韦、白二人同样具有刚直的性情,且均更多地表现在因“为国”而“忠君”上,这与儒家之价值观念是相符的。
韦应物曾自我评价“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再游西山》)[1](P458),又自言“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白居易自言“况余方且介,举动多忤累”,可知,白与韦的自我认识在内在之“直”与外在之“忤”上是高度相似的。史官作为盖棺定论者,对白居易的道德评价也很高。《新唐书·白居易传》的“史臣论”作了如此表述: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4](P4305)
性情忠直的诗人,不免以其性情书写诗作,干预现实政治。可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终生不歇的,虽然后世之人更认同的是他贬谪江州之前所作的讽喻诗,或许功在迎合上峰的时机,又或许功在白本人以编集的形式所进行的“鼓吹”。
值得一提的是,给予白居易讽喻诗创作最大影响的前代诗人,正是韦应物。白《与元九书》中首肯的便是韦“兴讽”性质的歌行:“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韦之创作,在讽刺的手法和力度上也的确与白之评价一般别无二致,其《长安道》《贵游行》《夏冰歌》《鼙鼓行》《采玉行》等歌行体的作品也直接给白“新乐府”以形式、内容甚至风格上全方位的借鉴模板。即使脱离“歌行”的形式,白仍将韦《汉武帝杂歌三首》等“以汉喻唐”痛心民隐、痛责权贵的“兴讽”诗风放置到《秦中吟》《杂体五首》等作品中,形成具有新的风格的讽喻诗歌。除了以现实故事兴讽之外,韦、白二人还共同表现出以“禽鸟寓言”兴讽的倾向,比如,韦应物有《乌引雏》《鸢夺巢》《燕衔泥》讽刺现实,白居易的《新乐府·秦吉了》《乌夜啼》《和答诗十首·和大觜乌》《池上寓兴》《池鹤八绝句》《禽虫十二章》《山中五绝句》等亦寄托了诗人的愤慨和忧虑。白《续古诗十首》对韦《拟古诗十二首》的全盘承续,则体现出韦、白二人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对历史上的士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影射现实的传统,韦不独“才丽”更融于“兴讽”,白则以“复六义”的诗学思考和实践创作名之为续、实之为复的模拟之作,表达对社会现象、人性内涵的戚戚之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感伤传统以讽写感,以感表讽,从二人对“古诗”这条承继的线索也可以看出来。
由二位诗人之诗所反映的政治理想来看,他们不但忠于君主、意欲仕进,且意欲为民得利,导致了二人更深层次惭愧意识的展现。在芸芸百姓之中,韦、白二人最感愧疚的对象,是农民。战争导致的土地丧失与兼并,让农民流离失所,无法耕种;即使战争结束,刚刚恢复耕种的农民又因为缴不起税,而陷入赤贫。韦应物慨然长叹“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亦深刻地揭示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国家、战争的问题。两位“不耕者”思考农民问题角度竟然惊人的一致: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1](P452)
(韦应物《观田家》)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2](P22)
(白居易《观刈麦》)
两诗表现手法虽有所差异,但表现的视角却惊人的相同:诗题中的“观”点出了两位诗人旁观者的身份,正因为只是旁观,使得他们无法替农民分忧,甚至还要从农民的劳动所得中分得一杯羹,诗句“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与“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表现了同出一辙的惭愧情绪。即使暂时不在官位上,只要韦、白二人“有闲”,便会用类似的视角,观农人以观己,以惭愧表现自省。比如韦应物“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夏至避暑北池》)[1](P484)。在办公之余,闲暇避暑的时间里,韦应物仍然惦记着在田中辛苦劳作的农人们,担忧他们抵挡不住暑热。又如白居易“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观稼》)[2](P547)。在一片闲适与喜悦的气氛中,白居易与获得丰收的农人友善地饮酒交谈,农人“勤且敬”的劳作让白自愧弗如,“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的生活又不得不引起人的忧心。
韦应物之仕宦历程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作为一州刺史有着清廉的官声与不俗的政绩。韦在江州刺史、滁州刺史、苏州刺史任上,均以勤为吏政的循吏心态为政且有所作为,他的政治作为在他的许多诗作中被保留下来:
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
宾朋未及宴,简牍已云疲。
昔贤播高风,得守愧无施。
岂待干戈戢,且愿抚惸嫠。[1](P505)
(《始至郡》)
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1](P458)
(《再游西山》)
同韦应物一样,白居易既做过江州刺史,又做过苏州刺史。他虽然不以刺史之职为炫耀的资本,但也不忘竭尽所能做一名良吏:
自顾才能少,何堪宠命频。
冒荣惭印绶,虚奖负丝纶。
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
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
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
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
襦袴提于手,韦弦佩在绅。
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4)见《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该诗自注写道:“除苏州制云:‘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鲠之志,阖境有袴襦之乐。’”见《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876—1877页。[2](P1876-1877)
在这些透露地方官员的小心翼翼与兢兢业业的字字句句中,惭愧自己的吏能不足,或者说前文所言之“政拙”,是良吏心里绕不过去的自省情结。与之相对同时又被韦应物强调的,是对仍然处于生活困境的百姓的惦念与关心,是即使以“游”暂时摆脱俗物困扰,还萦绕在心头的“未完成使命”的歉疚: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物累诚可遣,疲甿终未忘。[1](P477)
(《游琅瑘山寺》)
明人刘须溪曾提到“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5](P399);清人乔亿与刘之观点暗合——“韦公多恤人之意”[6](P1172),似乎以韦“受命恤人隐”的自述为依据。在这些真诚地表现惭愧情绪的诗句中,真诚度最高、恤人之心最著的是坚持严律的酷吏意识和坚持民本的循吏意识两者所产生矛盾之时,韦应物所表现出的煎熬和无措:
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
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1](P323)
(《答崔都水》)
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
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1](P505)
(《始至郡》)
行政时,官员采用酷吏的手段是无法避免的。傅璇琮曾经提及韦应物任苏州刺史之时,为了催逼民众缴纳赋税的一些严酷事迹[7](P319):其一是李观代一位彝姓之人写信向韦应物道歉;其二是戴察卖琴卖书缴纳赋税;此二事件中韦应物未必直接行使了苛政、对象也不能说是平头百姓,可见当时的百姓因为税收的繁重而难以安居更是事实。韦应物意识到了人民的困苦和窘迫,但又不能不完成税收的任务,这样的矛盾心理也成为惭愧情绪的要因。
与韦应物一样,白居易在处理郡务上,亦面临酷吏意识和循吏意识的矛盾。不过,白居易的酷吏意识相对于韦应物,出现得更早、更为自觉,甚至已经形成了和循吏意识分庭抗礼的趋势。邵明珍指出,白居易早年的诗作《放鹰》是给唐皇朝的统治阶层的、有关如何驾驭臣子的说明书;白居易全体诗作中的“鹰喻”,均以猛禽鹰象征为君之左膀右臂的酷吏的。[8](P130)如果说韦应物“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以犬马恋和骨肉情并言,表现了其对李唐王室的深深依恋乃至亲情般的情感寄托,是自降人格的忠君表决的话,那么,白居易的“鹰爪之譬”则是锋利而高姿态的表忠体现。然而,在苏州实践吏治的时候,白居易看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芸芸百姓,不禁因自喻为“鹰爪”的自己而升腾出愧意:
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
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2](P1683)
(《自咏五首·其三》)
浩浩姑苏民,郁郁长洲城。
来惭荷宠命,去愧无能名。[2](P1691)
(《别苏州》)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两位立志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诗人官员身上,所存在的循吏和酷吏意识的矛盾,亦是导致其惭愧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然,做一名良吏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直接复制某个模板的“纸上谈兵”显然不是良方;更难的是,如何完美地接纳可能没有达到良吏的标准的自我。比如,韦应物时有负气之论:
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贫。
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1](P495)
(《任洛阳丞请告一首》)
此外,韦之郡斋诗中时常提到“宴集”,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调剂为政之苦。韦此诗之句“群公尽词客,方驾永日游。朝旦气候佳,逍遥写烦忧”“遽看蓂叶尽,坐阙芳年赏。赖此林下期,清风涤烦想”“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看似营造了一种散淡的气质,但实际是诗人消解内心矛盾,舒缓负累感和愧疚感的方式。
至于白居易,他常常直接感叹刺史工作的劳苦,言及一郡之长需要平衡各方势力,十万户的郡民和五十口的郡厅工作人员都需要“给养”,天时的寒暖、关系民生的一切问题更需要及时的解决。不过,作为父母官是不能轻易说苦的,身在苦中却必须甘之如饴,这才符合儒家的观念与说教: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万户。
出为差科头,入为衣食主。
水旱合心忧,饥寒须手抚。
何异食蓼虫,不知苦是苦。[2](P1682)
(《自咏五首·其二》)
韦、白为了能够在诗中“云淡风轻”地表现良吏的生活,花费了大量的情绪成本,于此,以闲适为审美趣味的郡斋诗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丝丝点点的苦味。“身处其位,仍觉己苦”的不该是导致惭愧情绪产生的另一要因。二人不能言苦的平淡诗句与严苛的良吏标准所带来的情绪拉扯,营造了诗作内部更为强大的情感张力。
二 韦应物、白居易诗中相异的惭愧表现与成因
(一)诗歌表现惭愧广度和深度的差异
1.白诗表现惭愧的广度大于韦诗
白居易同韦应物表现惭愧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诗“事事”“时时”表现惭愧的惊人广度。如果说韦应物的惭愧投射出一个封建文人乃至官员的君臣意识和社会理想的话,白居易的惭愧则常常表现出接近于平凡人的样态。
首先,在官位职阶不如别人的时候,白居易便流露出羞惭的情绪,其心灵视野全然与凡俗之人等观齐论:
虚薄至今惭旧职,院名抬举号为贤。[2](P1515)
(《晚春重到集贤院》)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见君。
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
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2](P574)
(《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
惭君独不欺憔悴,犹作银台旧眼看。[2](P1419)
(《重赠李大夫》)
不论是不配举号集贤、不配与韩舍人同伦,或是量移贬谪后官位不及银台之上的要员,仕进路上的挫折都造成了白居易强烈的愧意,而此等愧意接近于一般人所认知的自卑感。
其次,白居易时常因为过于关注自己的外貌是否老丑,而与他人比较。当他自感老丑或比较以落败告终便会感到感伤。大多时候,他亦不忘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乐天知命”的志趣,即使在无病呻吟式地表现对自己老丑容貌的惭愧时,还要故作洒脱地以调侃的语气写出,甚至竭尽全力地表现出对现状的满足,像是在一场又一场刻意的演出中,吐露着言不由衷的台词:
我惭貌丑老,饶鬓斑斑雪。[2](P795)
(《以镜赠别》)
我归应待乌白头,惭愧元郎误喜欢。[2](P843)
(《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
且喜身无缚,终惭鬓有丝。
回头语闲伴,闲校十年迟。[2](P2140)
(《游平泉赠晦叔》)
半头白发惭萧相,满面红尘问远师。[2](P1555-1556)
(《萧相公宅遇自远禅师有感而赠》)
病肺惭杯满,衰颜忌镜明。[2](P1342)
(《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
每愧尚书情眷眷,自怜居士病绵绵。
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于君六七年。[2](P2769)
(《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
上述诗作中,白因为满头白发而自感老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别人的喜欢,甚至连照镜子都会产生自我厌恶感,回过头来,他又体会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和别人比年龄不再有任何优势,剩下的只有浓浓的“惭愧”:不但遗憾自己曾经枉费时光,还自卑于现在老病的自己无法在闲适的生活中获得真心的愉悦。
再次,白居易在诗中时常表现出对亲人,特别是妻儿的愧疚,这在韦诗中也是罕见的。亲人和众人不同,是被儒家文化所特重的角色。白居易对妻儿的愧疚,亦源自儒家思想的差等观念与自省意识:
药停有喜闲销疾,金尽无忧醉忘贫。
补绽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赖交亲。[2](P2798)
(《狂吟七言十四韵》)
老去愧妻儿,冬来有劝词。
暖寒从饮酒,冲冷少吟诗。
战胜心还壮,斋勤体校羸。
由来世间法,损益合相随。[2](P2456)
(《老去》)
自己的贫病连累到家人,自己的任性让家人不安,在白居易看来,都必须去反省一下。不过,白对家人的愧疚,其情感力度显然是低于对民众困苦的反思的,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把对家人的愧疚放在“由来世间法,损益合相随”的感悟后面。由此可见,愧疚是优先于反省摆出的某种姿态,此种状态下白居易反省的结果却是合理化自己“先己后亲”的行为。
最后,白居易在享受饱足、温暖时,常常流露出自己配不上优裕生活的惭愧之意,似出于己身不能满足儒家“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对士人高标准的道德要求:
省躬念前哲,醉饱多惭忸。
君不闻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2](P2314)
(《春寒》)
食饱惭伯夷,酒足愧渊明。
寿倍颜氏子,富百黔娄生。
有一即为乐,况吾四者并。
所以私自慰,虽老有心情。[2](P2257)
(《首夏》)
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
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2](P2720)
(《新沐浴》)
陷入困顿而德行愈发光辉的前哲与困苦无著的羁囚,都能够引发白居易在道德上的自省,只是他的自省并非都导向对美、善的追求,有时反而是以一种别扭的、试图消除高尚道德感的自慰来结尾,甚至于他也不晓得“愧”从何而来,“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似乎只是为了愧疚而愧疚,为了反省而反省。
白诗出于道德自省的惭愧表达,呈现出格套化的倾向。他的“惭愧”往往是由人及己的,即从对他人困苦境遇的恻隐之心转向在自我较优的境遇比较下的“惭愧”,或是他人境遇较佳自己未能与之比肩,无能而“惭”;对比韦应物而言,白之过分提及、强调惭愧情绪,斤斤计较,与凡俗的距离过近,反而造成了文学情感上的“不动人”、思想表达上的“没厚度”。
2.韦诗表现惭愧的力度强于白诗
白居易以惭愧表现的自省,不若韦应物的自省勇敢、坚决,从二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情绪力度的强弱可以感受出来。韦应物之诗的本身即在真诚改过。忏悔的概念,来自佛教(5)忏悔实际上是梵语和汉语合成词,“忏”是梵文忏摩的音译之略,是“容恕我罪”之意,于是,忏悔一词中,忏指陈露先恶,悔指改往修来,见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38页。,惭愧与忏悔都因心灵的震颤在情感上表现出强烈的不安,但忏悔具有比惭愧更大的情绪力度,韦诗所表现的接近忏悔:
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
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
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
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
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
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
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
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1](P424)
(《广德中洛阳作》)
韦应物的忏悔,是中国古典诗人中少见的、极度真诚的自我反省。上述诗作中,他从少不更事时“不知太平欢”反思起,批评王师的刚愎自用,导致整个时代的溃决,他痛切地找到症结并想要拔出毒瘤,可以说,他的不安不仅是一种朴素的直觉,还带着对无力改变现实、自我转变不够彻底的惭意。如果说这样的惭意不够具体的话,下面的这首诗则巨细靡遗地展露出他荒唐的前半生: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
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1](P361)
(《逢杨开府》)
上述诗中,韦应物所忏悔的不是自己无伤大雅的、道德上的小瑕疵,而是从学识、作风、性情全面地忏悔少年时的胡作非为,“改过”而得“今是”固然没有被他所忽略,却不是他所强调的,处于“今是” 状态下的自己并不是完美无缺,让人无可挑剔、交口称赞的,“论旧涕俱垂”的忏悔姿态才是他意欲突出的。
相比于韦应物,白居易的忏悔往往来自人生的某一个截断面,且颇有“今是昨非”之感,“昨非”是作为“今是”的对照组出现的,“今是”才符合白诗中的真意。白居易《和梦游春》《渭村退居》《东南行》等长韵叙事诗作均以书写人生刚刚踏上仕途、面对荣光时的心理迷失为主题。此类诗作反映出随着对佛禅思想理解的加深,白居易开始意识到后悔、忏悔是一种无益的情绪,“必若不能分黑白,却应无悔复无尤”,把握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做到是非分明、判断精准,就不会有后悔和怨恨的情绪。白刻意地避免、克制忏悔情绪,或许只是出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白诗中还有一种韦作没有的抵挡惭愧情绪散发的倾向,亦弱化了其诗惭愧表达的力度。白居易体认自己为“性拙”之人,因此不合时宜,不适应官场,而这种“拙”既是生而即来,便不必感觉惭愧:
我性愚且蠢,我命薄且屯。
问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
亦曾举两足,学人蹋红尘。
从兹知性拙,不解转如轮。
亦曾奋六翮,高飞到青云。
从兹知命薄,摧落不逡巡……[2](P552)
(《咏拙》)
既登文字科,又忝谏诤员。
拙直不合时,无益同素餐。[2](P561)
(《游悟真寺诗》)
我受狷介性,立为顽拙身。
平生虽寡合,合即无缁磷。[2](P574)
(《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晚遇缘才拙,先衰被病牵。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
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
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2](P1526)
(《初著绯戏赠元九》)
自惭拙宦叨清贵,还有痴心怕素餐。
或望君臣相献替,可图妻子免饥寒。
性疏岂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
分寸宠光酬未得,不休更拟觅何官。[2](P1581)
(《初罢中书舍人》)
在不同时段充满“拙”的论调里,白居易强调自己与一般人无异,甚至更劣,是“才拙”之人,所以在宦途上晚得成功,并屡屡遭受跌挫。他又意识到“性拙”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拙直不合时”“我受狷介性”“我性愚且蠢”,本性蠢钝无力改变,加之“我命薄且屯”,命是天定的,强求不来,只能选择认命。勉励自进并不是顺应天命,过分哀伤也是没有必要的,“穷而乐”才是得以“终吾身”的正确径路。“拙”与“惭”在白居易大多数诗作中是一对性情互补、正负互嵌的概念。只要以“拙”为前提,强调了自己的“拙”性,就不必有惭愧的情绪,便能实现人生境界的超越。与之相对的,如果宣告了自己处于“惭”的心境中,“拙”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减弱,因为真正具有“拙”性的人是不会被外在世界,以至内在心灵所烦扰的,所以在表现惭愧情绪的场合,白居易几不言其“拙”。在“拙”与“惭”的宣言中摇摆的诗人白居易,不但大大降低了他诗中惭愧的力度,还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形象建构破碎的境遇中。对比韦应物诗中的“拙”,虽言及“工拙”“拙直”,但并未与自我命运建立关联,且韦诗中之“政拙”,较白主观假想的自我能力不足而言,更多是客观呈现政务复杂难以处理的情况:“淹留未得归”(《赠李判官》)[1](P199),“赋繁属军兴”(《答王郎中》)[1](P328),“念劳喜岁收”(《襄武馆游眺》)[1](P463)。这些或喜或忧的情绪是具体可感的,因其真而更具有文学感染力。
(二)造成韦白诗歌相异惭愧表现的原因
1.白诗时时表现惭愧的原因
较韦应物而言,白居易诗在更多的方面表现或深或浅的惭愧,与其个人出身、性格与思想信仰均有关联。
其一,与韦应物相比,白居易求仕时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虽然韦、白人生中都曾经历过困顿与贫穷,但韦诗不过是叹“家贫”,如“家贫无旧业”(《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1](P85),“停杯嗟别久,对月言家贫”(《将发楚州经宝应县访李二忽于州馆相遇月夜书事因简李宝应》)[1](P357),“家贫无童仆”(《答裴丞说归京所献》)[1](P332),“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寓居永定精舍》)[1](P510),且其“家贫”的状况只短暂地存续在少年时期;而白诗更多地反映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俸禄及其背后安稳享受生活的在意:
冒宠已三迁,归期始二年。
囊中贮馀俸,园外买闲田。[2](P1543)
(《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
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
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2](P703)
(《自余杭归宿淮口作》)
欲作栖云计,须营种黍钱。
更容求一郡,不得亦归田。[2](P1996)
(《答林泉》)
白居易在人生各个阶段所做的选择,均出于“求俸”的目的,不论是任中书舍人、一郡之守甚至分司东都,诗中不落余俸、禄俸、种黍钱等字眼;但选择物质过后,冷静下来,却不免产生了道德上的自责,陷入惭愧的情绪。其诗句“惭愧稻粱长不饱,未曾回眼向鸡群”(《有双鹤留在洛中,忽见刘郎中,依然鸣顾,刘因为〈鹤叹〉二篇寄予,予以二绝句答之》)[2](P1990)正是白借鹤之口,表达高洁之志未能完成的遗憾,通过描绘鹤的睥睨姿态反衬出自己的凡庸。
其二,白居易出身中层阶级。与出身贵族的韦应物不同,白一直怀揣着阶层跃升的愿望,因此,他的内心时常有一种与周围的人比较的倾向与欲望。不论是作诗的才华、园林的大小、官位的高低,还是年龄的大小、样貌的美丑,都会引起他的比较,只要自己落入下风,他类似自卑的惭愧情绪便会滋生。前文曾提及,白居易书写为官时的惭愧,好谈病与愁,正是与他人比较的心态作祟;同时,也因为他的健康过早地被损害,样貌出现了早衰的现象,身体也跟不上奔放的心灵,他更是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中无法自拔,于是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其三,白居易是一位极度真诚的诗人,他的诗歌,可以说几乎是他人生的忠实记录,在诗中书写“本我”来体现“自我”是他诗歌突出的抒情特色之一。加之白居易自言其诗“理周而辞繁”(《和答诗十首序》)[2](P212),即有“好尽”的特点,故他所展现的“我”,几乎是全方位的、优缺点尽现的。一个真诚的人,又不可能不是一个会自我反省的人,因此,白居易诗处处都有惭愧,处处都带着他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痕迹。虽然他的部分真诚表达透露出自我怀疑的倾向,导致自我形象的破碎,但人性正是如此,白居易文学形象表达的缺憾反倒凸显了其为人为文的真与切。
虽然韦应物是白居易在为官与作诗这两方面所崇拜的偶像,但白对为官与作诗关系的认识却与韦有迥异之处,这亦导致了白诗所表现惭愧的广度和内涵都与韦诗不同。韦应物在刺史任上固然也吟诗论句,亦有苦于政拙的惭愧自责,但几乎未将二者同列考量。白对韦的肯认与接受,建立在其对韦诗酒风流与良政勤绩并立同存的想象之基础上,由此,当白诗中同时出现作为诗人的自满与无法成为良吏的惭愧情绪的表达时,其中的惭愧情绪便值得玩味了:
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
唯向城郡中,题诗十余首。
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2](P700)
(《三年为刺史二首·其一》)
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2](P1829)
(《重题别东楼》)
不难发觉,白诗一边表达着“勤恳为官者不应以空想作诗,作诗无益于行政,甚至应该被嘲笑”的惭愧,一边又表达着“因为善咏诗所以成为州民心目中的好太守”的自得。他的惭愧并不是严肃的,更似以戏谑的语气表达其对诗人身份的认同,“惭愧”于是成为他弥合官员身份和诗人身份的情感武器。他打卡式地叙己之“惭愧”,更像一个众人皆知的口癖“惭愧惭愧”,为其诗增添了不少凡俗感。
2.韦诗深刻表现惭愧的原因
学术界并不缺乏对韦诗惭愧意识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认为,韦应物的忏悔既是在唐王朝面临的种种忧患的情形下被激发出来的,又是对现时自我的不完善的不满而导致的,所以,他的忏悔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合力造成的结果。只是,因为缺少新鲜的研究思路,缺乏分析与对照,针对内在因素的分析在已有的论述中显得很不足够。笔者以为,与白居易比较,韦诗所表现的惭愧力度更大,原因在于:
其一,韦应物出身长安杜陵韦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曾祖父韦待价曾为则天朝宰相,祖父韦令仪曾任司门郎中 、宗正少卿,因为和皇室关系密切,所以比一般士人更加忠君、忠主,也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韦应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其较一般士人更强的行动力上。本文上述所论韦与白同样在为官时表现因“政拙”“无术”而感到惭愧的诗作中,韦想要改变为官之“拙”的现状的行动便更为积极:不论是滁州任上“为郡访凋瘵,守程难损益”(《郡楼春燕》)[1](P54),或是江州任上“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始至郡》)[1](P505),还是苏州任上的“于兹省氓俗,一用劝农桑”(《登重玄寺阁》)[1](P439),都是他对政事亲历亲为的写照。相较于白居易晚年社会关怀的消退,韦应物的行为驱动力则保持了更长的时间,这便从侧面说明了韦中青年时期之于己身的反省力度和效度都高于白。
其二,韦应物早年经历与白居易不同。韦因门荫得补右千牛,成为玄宗的贴身侍卫,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甚至在违法乱纪的边缘游走,前文所引之《逢杨开府》便全录了韦应物早年的荒唐生活。与之相反,白居易早年几乎是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苦读诗书即为了入仕;同时,因为社会动乱、父亲早逝、家庭贫困等原因,白长时间处在颠沛流离之中。因此,之于过去,韦应物需要“反省”的原本就远远多于白居易。加之,韦应物是武职出身,其个性气质中“高歌长安酒,忠愤不可吞”(《送李十四山人东游》)[1](P211)的魄力自然比“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与元九书》)[9](P321)的叹老嗟贫的文弱书生白居易要强得多。韦应物“壮士断腕”的魄力是他反省、忏悔之“破力”的最大原动力,白则相对缺乏深刻反省的原动力。
其三,韦应物亲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安史之乱前的盛世繁华以及安史之乱后的残破荒凉,因此性情、性格乃至看待事物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原本“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赠旧识》)[1](P203),但历乱失去官职,失去皇帝的荣宠之后,他“憔悴被人欺”,于是他开始发奋读书,力图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上。与此同时,国家之“干戈事变”亦让他反思皇权,反思社会,除了创作一些讽刺诗之外,他亦意欲从改变自身开始改变社会现状,不但直言“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寄畅当》)[1](P164)、“一朝愿投笔,世难激中肠”(《始建射侯》)[1](P542),还在重新踏上为官之路的京兆府功曹任上为民奔忙,《使云阳寄府曹》[1](P98)一诗记录下了全过程。他冒着炎暑,在大水刚退时跋涉灾区,细心巡视灾情。洪水退后,“良苗免湮没”,他由衷地喜悦;但“蔓草生宿昔”“颓墉满故墟”的现实依然触目惊心,他直言“贱子甘所役”,即使是“周旋涉涂潦,侧峭缘沟脉”亦无可厚非,可见其誓为好官之决心。相比于韦应物,白居易人生中并未经历如此起伏的、从社会到人生的转变,因此,二者由自省反思而引发的惭愧情绪的力度有所差异,自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