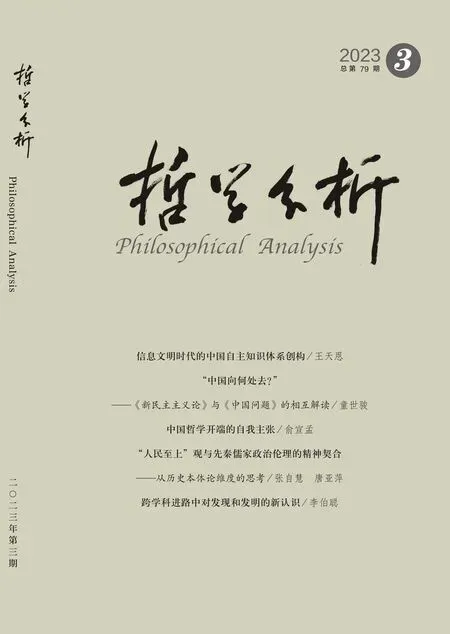“意愿”是如何被“经验”的?
——基于布伦塔诺“内知觉经验”立场的探究
张智涛 郝亿春
“意愿(will)”①对于英文“will”,国内主要有两种译法:“意志”“意愿”。由于“will”一词在英文中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而中文的“意愿”能更好地保留该词在英文中的这一用法,所以本文也采用了“意愿”。考虑到“自由意志”或“意志自由”这一术语在国内已被广泛使用,为了与此保持一致,本文只在“will”与“freedom”联用时采用“意志”的译法。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可谓历久弥新。尽管研究者们在古希腊有无“意愿”概念这一点上争议不断②关于古希腊有无“意愿”概念的哲学争论,参见Michael Frede, A Free Will: Origins of a Notion in Ancient Thought,A. A. Long (ed.),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Press, 2011, pp. 2—6。,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意愿”概念在中世纪特别在奥古斯丁③参见吴天岳:《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页。根据作者的考察,对奥古斯丁意愿(uoluntas)概念的现代翻译是:will(英语)、Wille(德语)、volonté(法语)。那里就已经广为流传了。在近代,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过这一概念,特别是在关于是否存在“自由意志”的争论中。他们普遍认为,“意愿”所指涉的是一种能够引发人之行为的心理活动。鉴于意愿与行为的这种特殊关联,不少哲学家将人的某种行为是否由行为者自身的意愿所引发,作为对行为和行为者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条 件。
然而,自20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些哲学家及心理学家,他们认为“意愿”概念是成问题的,理应被抛弃。①参见Gregory A Kimble and Lawrence C Perlmuter, “The Problem of Vol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77,No. 5, 1970, p. 362。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现代心理学及心灵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与“行为主义”派别。②国内也不乏这类观点的支持者。参见苏德超:《激进意志论的困难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兼与聂敏里、黄裕生二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019 年第4 期。如果他们对意愿概念的质疑以及由此对“意愿”的否弃是成立的,那么不仅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探究将会失去意义,而且各种以意愿为主题的心理学、哲学理论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鉴于此,本文将借助相关理论资源,特别是布伦塔诺哲学的相关思想,对试图否弃“意愿”的思想作一个正面回应,以期达到对“意愿”概念进行澄清,从而为“意愿”的真实性进行辩护的目 的。
一、意愿能否被经验?
在否弃“意愿”概念的各种观点中,赖尔的看法最值得关注。在其著作《心的概念》一书中,赖尔将“意愿”归为“燃素”“动物精气”一类的概念,他说:“‘电离’和‘越位’是专门概念,但它们都是合法的和有用的。‘燃素’和‘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曾经是专门概念,尽管它们现在已没有任何效用。我希望表明,意志活动这个概念属于后一族概念。”③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70 页。“燃素”和“动物精气”曾一度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但后来科学的发展表明,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因而,当赖尔将意愿概念归入诸如“燃素”和“动物精气”这类概念时,也就意味着,在他看来意愿并不真实存 在。
首先,就日常语言的使用来看,人们并不会用“意愿”这一概念来描述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因而意愿的存在就不能根据经验而被断定:“假如普通人从未报道过意志活动的发生……假如日常用语没有为它们备有非学术性的名称……那么就可以公平合理地作出结论说,它们的存在不是根据经验的理由而被断定的。”④同上书,第74 页。其次,人们普遍承认,能够被“观察”到的只是人的“身体行为”而非“意愿”:“大家都承认,一个人绝不能目睹另一个人的意志活动;他只能从观察到的公开行动推出产生它的意志活动……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理由从那些行动推出被认为是产生了那些行动的意志活动。”①赖尔:《心的概念》,第75 页。一方面,意愿是无法为他人所直接“经验”的;另一方面,从“行动”到“意愿”的推导又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对于他人的意愿活动,我们的确无法直接经验到,但通过某种直接意识,我们却能够把握到自己的意愿活动。但在赖尔看来,这也只是不符合事实的假设:“我们也不能主张,行为者本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任何公开行动都是特定的意志活动的结果。”②同上。
无独有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论及意愿时,也表达了与赖尔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从未有人通过对意愿的观察而获得对意愿的信念。它们在经验心理学的数据中毫无立足之地。……事实上,太阳底下是否发生过意愿这样的事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意愿理论的价值是什么,这至少是它的一个缺陷。”③Richard Taylor, Action and Purpos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p. 66.显然,在泰勒看来,意愿的真实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观察”来确证它的存在。可以看到,就据以质疑意愿之真实存在的根据而言,泰勒与赖尔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意愿无法被人们所经 验。
因而,“意愿到底能不能被经验?”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回答,我们从哲学史中了解一下以往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怎么 看。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一个人看他就感觉到他在看,听就感觉到他在听,走就感觉到他在走;同样,在进行其他活动时也都有一个东西感觉到他在活动,因而如果感觉就感觉到自己在感觉,思考就感觉到自己在思考。”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281 页。也就是说,所有身心活动都能够被当事人感觉和知晓。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中世纪哲学家的继承与推进。在奥古斯丁看来,我们不仅能经验到自己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所有经验中,对心理现象的经验是最可靠的。他在《论三位一体》第十卷中指出,对于记忆、意愿、思考、认识等能力是否源自气、火、血或是其他元素,人们会有所怀疑,但对于这些现象本身却绝不会有所怀疑。⑤参见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298—299 页。由此可见,在奥古斯丁那里,心理现象不仅能够被经验,而且对它们的经验还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不仅对中世纪哲学家思考相关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近代哲学家特别是笛卡尔也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尽管“心理现象可以被经验”这一点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代表性哲学家那里有着普遍共识,但对于“心理现象如何被经验”这一问题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说明。这个任务直到近代才得以逐步完 成。
对“心理现象如何被经验”的问题最先作出系统说明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近代哲学家首推笛卡尔。根据其“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唯独“思维”活动即心理现象是绝对确定因而无法被怀疑的。不同于“反思”,这种确定性经验是一种“内部的、永远在获得的认识之先的认识”①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408 页。,即一种先行于反思经验的直接经验。然而,正如有论者正确指出的,在笛卡尔哲学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对前反思经验之特征的确定,而是对心理现象之反思经验的确定与关注。②参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56 页。在笛卡尔之后,也有不少哲学家在解释我们对心理现象的经验时,将反思作为对心理现象的经验方式。于是,“心理现象经由反思来经验”似乎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信 条。
上述对哲学史的简单考察表明,不论是在古希腊、中世纪还是近代的代表性哲学家中,“心理现象可以被直接经验”这一点始终都是毋庸置疑的。按照这一立场,同样属于心理现象的意愿无疑也是可以被直接经验的。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否弃意愿的“声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反思作为经验心理现象的方式在19 世纪中后期所受到的反驳。进行这种反驳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布伦塔 诺。
二、从“反思”的心理学到“观察”的行为主义
布伦塔诺在其《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中考察并反驳了“心理现象是经由反思为人们所经验的”这一信条。他认为,“反思”首先需要将所反思的东西“对象化”,从而反思也就是“内观察”(Beobachtung/observation)的过程。根据他的考察,之所以会有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对将反思或内观察作为经验心理现象的方式,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③参见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郝亿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38—41 页。
一方面,对心理现象的反思或内观察要求正在从事某一心理活动的人必须把自己的思维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从事该活动,另一部分则在观察该活动,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对正在进行的心理现象进行反思或观察时,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如果一个处于狂怒状态的人想观察他自己的愤怒,那么在他观察之际愤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烟消云散,这样,他最初的观察对象也就消失了。”④同上书,第37 页。
“心理现象是经由反思为人们所经验的”这个信条被质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出现与兴盛。由于对心理现象的反思或内观察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些哲学家、心理学家便据此认为,心理现象其实是无法被经验到的。如此一来,如果还存在心理学这门科学,那么它的对象就不应该再是那些所谓的心理现象,而应该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行为。相应地,心理学的任务也就不再是探究心理现象的类型、特性与规律,而是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人类行为的观察和研究,探求其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由此便产生了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即行为主义心理学。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约翰·华生(John Watson)更是明确表示,心理学最基础的工作就是“从自己的科学词汇中抛弃了一切主观的术语,诸如感觉、知觉、意象、愿望、意念,甚至主观地被界定的思维和情绪”①约翰·华生:《行为主义》,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6 页。。
前文的分析表明,赖尔等人之所以否弃意愿,是因为它无法被人们所观察或经验。很明显,这属于典型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立场。对此,赖尔本人也并不讳言,他明确讲:“当我们谈论人在运用心理的各种才能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一些导致了人的公开言行的隐秘事件;我们是在谈论这些公开的言行本身。”②赖尔:《心的概念》,第21 页。问题是,这种绕开“心理现象”的心理学还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吗?另外,如果否弃了意愿这样的心理活动,那么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且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自由意志”问题还会有意义吗?总之,赖尔等人对意愿的否弃不论是对心理学还是哲学都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影 响。
要想有力反驳赖尔等人对意愿的否弃、继而证明意愿的真实性,我们就必须从其根基——“经验”——入手,争取在这个基础上有所突破。具体来讲,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可以把握心理现象但同时又区别于“反思性经验”的“经验”概念。这是因为赖尔等人对意愿的否弃是基于其行为主义立场,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又是在对“反思性经验”的批评中产生的。而在对“经验”的理解方面,布伦塔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 路。
三、“内知觉”:经验“意愿”的“新”方式
同行为主义者一样,布伦塔诺也反对将反思作为经验心理现象的方式,但并未像前者那样因此而背离“心理现象可以被经验”的哲学传统,他直言:“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心理学在知觉与经验(Erfahrung)中有其基础。不过,心理学的源头首先可从我们自己对心理现象的内知觉(innere Wahrnehmung)中发现。”③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37 页。显然,布伦塔诺在这里所说的“经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验”,而是“内知觉经验”。那么,何谓“内知觉经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经验”又有何区别?这就需要进入布伦塔诺对“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划分中进行厘 定。
布伦塔诺以是否具有意向性特征为主要依据,将传统意义上的经验所及的整个现象领域区分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两个大类,前者只能是意向“对象”,而后者的标志性特征是意向性“行为”。意向行为又可区分为“表象”“判断”和“爱恨现象”。与对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这种区分相对应,布伦塔诺也将“经验”区分为两类——“外感知经验”和“内知觉经验”。作为两种不同的经验,前者以物理现象为对象,后者以心理现象为对象。为了避免出现将“内知觉经验”混同于“反思经验”,布伦塔诺特别强调道:“不过请注意,我们是说内知觉而非内观察构成心理学最基本的源泉。这两个概念必须区分开来。内知觉的一个特征是,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内观察。通常人们讲,我们能够观察外感知的对象。在观察中,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一种现象,为的是准确地把握它。但是对于内知觉对象而言,这是完全不可能的。”①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37 页。显然,对于布伦塔诺而言,将内观察作为经验心理现象的方式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能够被观察的只能是外感知对象,而对于我们的心理现象,则是完全无法被观察的。布伦塔诺坚定地将此确立为一条普遍的心理学原则:“这是一条普遍有效的心理学规律,即,我们永远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知觉对象上。”②同上。
同样,布伦塔诺之所以认为心理现象无法成为内观察的对象,是因为当我们将注意力投向心理现象去观察它时,它已经失去了作为“心理行为”的特征,换言之,那个原初的要被观察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异,比如前面提到的对“愤怒”的观察。由此可知,“内知觉”作为经验心理现象的方式,它与其所把握的对象(心理现象)必定是直接伴随合一的,因为唯有如此,心理现象才不至于失去作为“心理行为”的明证性特征。可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进入布伦塔诺对“内意识”的分 析。
在一段关于“内意识”的概括性说明中,布伦塔诺指出:“每种心理行为都是有意识的;它在自身之中包含了一种对其自身的意识。因而,每种心理现象,不论多么简单,都有双重对象:一阶对象和二阶对象。”③同上书,第182 页。在布伦塔诺那里,“意识”与“心理现象”和“心理行为”是基本同义的。这即是说,但凡心理现象,其在指涉物理现象的同时也在回涉自身,前者为其一阶对象,后者为其二阶对象。每一心理现象所包含的这种对其自身的回涉即为“内意识”。根据布伦塔诺的看法,“内意识”不仅包括了心理现象对其自身的表象和对自身的判断,而且包括了对自身的情感。在这三种“内意识”中,其中指向每一心理现象自身的判断即为明证的“内知觉”——“一种对行为直接而明证的认识”④同上书,第170 页。。正因为每一心理现象在指涉物理现象的同时也在以“内知觉”这一直接而明证的认知方式回涉自身,所以每当我们在进行某项心理活动时,我们都清楚无误地“知道”自己在进行该项活动。比如,“看”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看”,“思考”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思考”,“欲求”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欲求”,如此等等。由此看来,“内知觉”其实“内在于”每一心理现象之中。正因为如此,“内知觉”才会伴随着每一种心理现象,并成为直接把握心理现象的唯一方 式。
总之,在布伦塔诺那里,“外感知经验”与“内知觉经验”共同构成了人类经验的基本形式,前者以物理现象为对象,后者以心理现象为对象。根据布伦塔诺对经验的这一理解,赖尔等行为主义者所谓的“观察经验”只能是“外感知经验”。所以,对于赖尔等人来说,其主要问题不在于对意愿的理解,而在于对经验的理解。正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人类经验的整全面貌,只将其狭隘地理解为“外感知经验”,因而当他们发觉意愿无法为“外感知经验”所把握时就断然否定了其真实性。问题在于,意愿现象恰恰不是外感知对 象!
既然人类经验包含了“外感知经验”和“内知觉经验”两种形式,而意愿又无法为“外感知经验”所把握,那么它能为“内知觉经验”所把握吗?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心理现象属于“内知觉经验”的内容,而意愿又属于心理现象①在布伦塔诺所划分的三类心理现象即表象、判断与爱恨现象中,第三类即爱恨现象就包含着情感和意愿。参见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277 页。,那么归属于心理现象的意愿当然能被内知觉经验到。因而,只要我们将布伦塔诺的“内知觉经验”引入心理学,意愿无法被经验的论断自然会被釜底抽薪。相应地,意愿的真实性也将由此得到保 证。
四、“意愿”被经验为何种心理现象?
指明意愿由“内知觉经验”把握只是给出了其通达的方式,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意愿”一般被经验为“什么”?由于在布伦塔诺这里,意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而这一问题就转化为:广义的意愿和狭义的意愿分别被经验为“什 么”?
在布伦塔诺看来,就其广义而言,意愿是一种复合现象,它涵摄了一系列要素,因而是个复合概念。根据布伦塔诺确立的阐明概念的基本原则,对于复合概念,其阐明方式是通过给出其构成要素完成的。②参见Franz Brentano,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 Elizabeth Hughes Schneewind (trans.),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009, p. 174。因此,为了说明“广义的意愿一般被经验为什么”,我们就必须给出它所涵摄的诸要素。那么,广义的意愿涵摄哪些要素 呢?
从布伦塔诺的相关论述来看,广义的意愿主要包含了五个要素,它们分别是“爱”(loving)、“偏爱”(preferring)、“决定”(decision)、“希求”(wish)和“选择”(choosing)。①参见Franz Brentano,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 p. 137。由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有关意愿的心理行为序列:爱——偏爱——决定——希求——选择。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行为环节都属于心理现象,也就是说就其本性而言都可以通过其所伴随的“内知觉”被行为主体经验到。下面我们将围绕上述序列展开对意愿各环节的分析和辨析。我们将表明,广义的意愿一般被经验为包含了上述所有行为环节的连贯的心理行为过 程。
对于爱与偏爱的区别和联系,布伦塔诺在对偏爱的界定中表明:“比起喜爱善好的B 我更喜爱善好的A,这并不意味着我更强烈地喜爱它,而是我偏爱它。这种偏爱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喜爱现象。”②Franz Brentano,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 p. 92.很明显,偏爱之所以区别于简单的喜爱或爱,是因为它无法同时容纳两个不同的事物,而后者却可以。以“做算术”和“写作”为例。对于爱而言,尽管“做算术”和“写作”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但我们却完全可以既喜欢“做算术”又喜欢“写作”。可对于偏爱而言,“做算术”和“写作”有且只有一个才能成为我们特定时刻所偏爱的对象。偏爱与爱的这种区别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对于某物的爱,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对它的偏爱。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对某物的爱,就必然会产生对它的偏爱。就像刚才的例子中,“写作”和“做算术”我们可能都喜爱,但在特定时刻,它们中只能有一个成为我们所偏爱的对 象。
对于意愿的另一个要素“希求”,布伦塔诺指出:“日常称为希求的心理现象,有时是希求未来之物,有时是希求当下之物,有时又是希求过去之物。我希求经常看到你,我希求我是一位富人,我希求我没做这件事——这就是三种时态的例子。”③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280 页。引用参照英文本有改动。Franz Brentano,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 A. C. Rancurello, D. B. Terrell, and L. L. McAlister (trans.), London:Routledge, 1995, p. 186.由此看来,所谓“希求”,就是想要某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心理活动。按照布伦塔诺的看法,就希求而言,我们不仅可以希求自己有能力实现的事物,比如上述例子中的“看到某人”,而且还可以希求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事物,比如“好天气”。一般来说,我们的希求要以爱和偏爱为基础,因为希求的东西必然是我们所喜欢和偏爱的。试想,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不偏爱某件事,他又怎么会希求它发生呢?不过,生活经验却告诉我们,即便一个人偏爱某物比如说“写作”,但他并不一定就会对之产生希求。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偏爱和希求之间还有一个环节,这就是“决定”。如果一个人对“写作”产生了偏爱,他实际上就会面临作出要不要希求它的决定。如果他决定希求它,那么一个对“写作”的希求就会产生;如果他决定不希求它,那就不会产生对“写作”的希求。由此看来,与偏爱相比,在希求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决定。这样,我们就将希求和偏爱区别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希求这里理智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在对某物产生了爱和偏爱后,到下一步会不会决定希求它,其实还有赖于我们对其他一些因素的考虑和认 知。
现在我们来看希求和选择的区别和联系。在布伦塔诺看来,希求和选择都必须包含决定,只不过选择所涉及的事物是自以为处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并且要去实现的事物:“它(选择——引者)必须指向一个对其实现是我们事务的并且通过我们对它的追求可以被实现的事物。”①Franz Brentano,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 p. 137.这也就是说,如果我认识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我能力之外,因而通过我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即便我多么希求它发生,它都不会成为我选择的对象。比如,由于周末我计划和家人一起去旅游,因为机会难得,所以我特别希求周末能有一个“好天气”。可无论我对“好天气”的希求多强烈,它都不会成为我所要选择的东西。因为选择所涉及的只能是处于我能力范围内并且我要去实现的事 物。
如果说在希求中只是开始出现了理智因素,那么在选择中理智所起的作用就大为增加,因为一个事物能不能通过行动得到以实现,从而成为选择的对象,肯定离不开行为者对自身行动能力、相关情境和所要选择对象的认知和考量。当然,希求与选择尽管存在着明显差别,不过它们也并非毫无关联。尽管选择所指向的只能是处于我们能力范围内并且要去被实现的目的,但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去实现该目的,必定是因为我们已对该目的有所希求。如果没有对某一事物产生希求,那么即便该事物处于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仍不会选择去实现它。生活中之所以很多时候不选择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一种可能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对该事产生希求。因而,就像偏爱要以爱为基础、希求要以偏爱为基础一样,选择也要以希求为基 础。
上述分析表明,在意愿的行为要素序列中,爱、偏爱、决定、希求和选择这些行为环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其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以在先的环节为基础。因此,当布伦塔诺将意愿界定为含涉这些行为要素在内的复合现象时,其实意味着意愿是一个包含所有这些行为环节的连贯的心理行为过程。这也表明,广义的意愿一般被经验为包含了爱、偏爱、决定、希求、理智以及选择等行为环节的连贯的心理行为过程。那么,狭义的意愿一般又被经验为“什么”呢?
根据布伦塔诺的看法,狭义的意愿一般被经验为人的“选择”行为:“我们还需要对意愿和选择作进一步的区分吗?正如我们对它们的界定那样,它们是一致的。”①Franz Brentano, The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thics, p. 138.上文的分析表明,就其所指涉的对象而言,选择的对象只能是自以为处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并且要去实现的事物;就其发动机制而言,选择必须以爱、偏爱、决定、希求、理智等在先的行为环节为基础。由于狭义的意愿与选择同义,因而我们就可以据此得出狭义意愿的一般性特征:首先,它所关涉的只能是自以为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得以实现的目的;其次,它可以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努力获得所选择的事物,或者将所选择的事物变为现实存在之物;再次,它的发动必须以爱、偏爱、决定、希求、理智等在先的行为环节为基础。正是这三个特性使狭义的意愿成了区别于其他爱恨现象的特殊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意志问题”中的“意愿”概念所指的便是狭义的意愿——选择行为,而所谓“自由意志”,所指的其实也就是人对自身选择和行动的控制。②参见Timothy O’Connor and Christopher Franklin, “Free Will”,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1 edition), https: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1/entries/freewill。
总之,意愿作为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是完全可以被经验的。就广义的意愿而言,它一般被经验为包含爱、偏爱、决定、希求、理智以及选择等行为环节的连贯的心理行为过程;就狭义的意愿而言,它一般被经验为人的“选择”行 为。
五、结语
我们对20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常见的对“意愿”的否弃进行了回应,借助布伦塔诺哲学的相关内容表明,意愿的真实性以及意愿概念的合法性可得到有效辩护。如果跟随布伦塔诺的“内知觉经验”方法,意愿是完全能够被经验的。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赢获“意愿”“选择”及“自由意志”等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本质性要 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