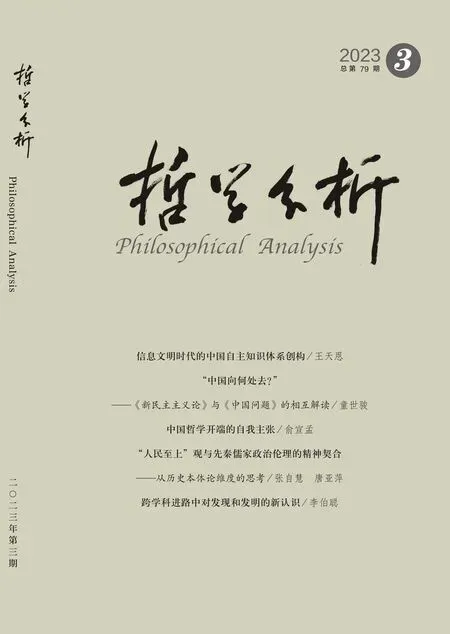“人民至上”观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精神契合
——从历史本体论维度的思考
张自慧 唐亚萍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政治伦理观,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设计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样式,是治国理政的基本伦理原则。政治伦理是政治主体在执掌国家政权或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处理各种事务和关系所遵循的伦理准则及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一个政党所秉持的政治伦理的正当性决定其治国理政能力的强弱与效果的好坏,也决定其生命力的久暂。从历史视域看,“人民至上”观滥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之所以能跨越历史时空,以“人民至上”的言说与实践方式植根于中国而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既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有关,也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民本”“家国天下”等理念密不可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从文明叙事的维度看,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所阐发的历史本体论思想,为“人民至上”观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本体论是对客观历史本质的反思,是对复杂历史现象背后必然性的探求,关涉到对历史规律、历史主体、历史动力、历史价值等的思考与追问。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这四个方面为“人民至上”观提供了历史本体论依据,具言之,“人民至上”观所遵循的历史规律、依托的历史主体、建基的历史动力、彰显的历史价值皆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遥契”和“魂 通”。
一、天命德延、敬德保民:“人民至上”观遵循的历史规律
“天命德延”是中国历史走向的“罗盘”。对一个民族而言,历史与文化不可分割,二者共同支撑着民族之存立,彰显着民族之精神。因此,历史规律常常蕴藏在民族文化之中。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而言,上帝是造物主,自然界和社会的秩序是由上帝安排的,因此,服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就是服从上帝,这种服从构成了西方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在宇宙中居于“首出”之位,人们尊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观念,笃信“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传·序卦》),“人为天之所生,地之所覆载”①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66 页。。因此,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源头是具有神圣性的“天”或“天命”,“天”是中华先民的准宗教信仰,其宗教精神表现为“中国人对‘天’或‘帝’的那种‘小心翼翼’的谦恭情感”②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9 页。。“天”不仅以日月流转、风雨雷电等可以感知的“形下”存在,佐佑着四季之更替,敬授着“人时”之移易;而且以“天命德延”“天人合德”等“形上”意识,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贞定着家国的未来。“天命”是“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54 页。。相较之下,“天道”比“天命”更为根本,更具有本原性,是历史必然性层面的概念。按照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叙事逻辑,如果说“天命”是当政者无法挣脱的“宿命”,那么“天道”则是先秦儒家政治观的“元伦理”和人道效仿的“元范型”。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中华先民心中的“天道”。先秦政治伦理肇始于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小邦周”战胜“大邦殷”的“牧野之战”。这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和文明走向的战争,揭开了“天”或“天命”的神秘面纱,引发了王国维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集》 (第4 册),周锡山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4 页。的感叹。一个崇信“天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强大王朝的快速覆灭,使周人对所谓的“天命”产生了强烈质疑,其统治者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道”,并由此催生了中华先民的主体意识,拉开了中国人文主义的序幕。《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殷周巨变打破了商纣王信奉的“我生有命在天”的神话,把“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基于“殷鉴”,周公将“明德”作为统治者遵奉的政治纲领,推行“以德居位”“以德配天”的贤人政治,奠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根基;他以礼乐纲纪天下,“纳上下于道德”②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7—288 页。,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天道”,奠定了先秦政治伦理的柱 础。
“敬德保民”是符合“天道”的“人道”。周人从殷商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皇天之“命”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而判断为政者有德无德的标准是其“爱民”与否。上天在为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同时,还通过倾听百姓心声来制约和惩罚那些作恶和失职的“大君”,保护处于弱势的下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听”在“天”“民”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渠道,构筑起独特的文化机制,即“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因为上天是通过“民”之喜怒哀乐的情绪来判断“政德”的,所以周朝统治者设立采诗官制度,以图通过诗之“兴观群怨”,让上天听到“民声”,来验证为政者之“政德”;更重要的是,为政者要先听“民声”以了解百姓疾怨,为自己提供一面自照自省自律的“镜子”,以实现德配天地、天命永祈的目标。如果说“天”或“天命”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发挥作用的前提,那么“敬德”就是“天意”与“民心”相通的灵媒。因此,西周的政治文化以“敬德保民”为宗旨,其宗教文化以“天民合一”③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13 页。为特征。正如王国维所说,古之圣人“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第301—302 页。。周公是“敬德保民”思想和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奠基者,孔子继承周公之志,提出了“为政以德”“为国以礼”的政治治理理念。“周孔之道”使“天命德延”“敬德保民”“以德配天”“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规律清晰地呈现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之中,并成为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观所遵循的政治伦理和历史规 律。
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至上”观依托的历史主体
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这不仅是唯物史观的要旨,也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中民本理念的意涵。“历史便是人生”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香港:邓镜波学校印刷1964 年版,第4 页。,“历史本就是个体与群体、社会、国家、人类各种不同关系的生存生活和命运”③李泽厚、刘悦笛:《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载《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1 期。。这表明,由个体汇集而成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其实,民本理念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在我国最早的政论典籍《尚书》中已出现“民本”思想的萌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出自其中的伪古文《五子之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④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135 页。《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大禹谟》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都是古代圣王尚民思想的体现,也是后世“民本”思想的端绪。西周统治者为了“天命永祈”,明确以“保民”作为得到“天命”青睐和眷顾的重要手段。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进一步看到了“民”的价值与意义,“民”不仅是邦之本、君之本,甚至被提到“神之主”的地位。据《左传》记载,季梁对随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谏追楚师》)先秦儒家对民本思想进行了精深的阐释,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孟子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提出了“王者以民人为天”(《郦生陆贾列传》)的主 张。
“以民为本”是君民关系的核心。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告诉世人,“君”因民而设,“国”赖民而存,为政者应基于自己的天职亲近民众并承担重任。孟子则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醒世之言。在儒家看来,爱民、仁民不应仅是动听的口号,而应是为政者的天职。《尚书·洪范》篇有“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之语,“天子”和各级“父母官”是接受上天赋予的使命来代行“天职”的,以民为本是其应尽的本分。从中国历史的叙事逻辑看,“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这里的“君子”乃指参天地之化育、管理天下百姓和万物的君王和为政者,他们是沟通天地和人类万物的中枢,是协调自然秩序和人伦秩序的关键。从政治正当性上看,既然君王代天统理民众,就理应仁民爱民,而民众亦自当事之如父母。先秦儒家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比拟君民关系,旨在强调民在君心中的重要性以及君“以民为本”的必然 性。
“仁民”“邦宁”是政治伦理的要旨。先秦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等,都是“仁民”思想的体现。孔子就把“养民”“富民”“安民”视为当政者的首要任务,要求其实行惠民政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孟子则把“土地、人民、政事”视为诸侯之三宝(《孟子·尽心下》),要求其“重民”“保民”“使民有恒产”,做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荀子认为“知爱民之为安国也”(《荀子·君道》),并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为喻,阐明民众与君位安危、国家兴亡的关系,“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可见,君之权力的巩固和拥有、国之秩序的稳定和安宁,皆以得民心为前提,得民心则得天下。因此,“善生养人”与“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一起被视为“君之道”。“四统者俱”则“天下归之”,“四统者亡”则“天下去之”(《荀子·君道》)。荀子还在“富民”“保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富国强国的任务,认为“裕民以政”才会民富国强,民富国强方可外服四夷,最终达至邦国安宁的目标。同时,先秦儒家反对暴政、苛政,反对用杀戮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在其典籍中,塑造了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圣王群像,旨在让这些以“仁民”“邦宁”为天职的圣王成为后世君王学习和效仿的榜 样。
综上,先秦儒家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存在的根本,是国家兴亡、社会有序的决定力量;“仁民”“保民”、筑牢邦国安宁之基是为政者义不容辞的天职。历史证明,一个政府或政党,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不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掉入“塔西佗陷阱”而走向灭亡。
三、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人民至上”观建基的历史动力
“凯弟君子,民之父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各级为政者既是人民群众集体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其对历史动力的凝聚与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乃至今日,天下百姓皆习惯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称为“民之父母”或“父母官”,对其寄予期待和厚望。从实践上看,为政者历史作用的大小、工作动力的强弱与工作成效的好坏,不仅与其道德素养、执政能力相关,而且与其遵行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伦理思想关系密切。在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中,理想的为政者被称为“凯弟君子”,其指具有宽厚与敬序之德的君子。“凯弟”一词在《礼记》中多用,其在《诗经·大雅》中表述为“岂弟”,《国语》 《左传》等文献引用《诗经》时,又常将其写作“恺悌”。“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吕氏春秋·不屈》) 《诗经》中多以“岂弟君子”或“乐只君子”来褒扬那些仁爱民众、尽心尽职的当政者,誉其为“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凯弟君子,民之父母”(《礼记·表记》)并用,旨在言说具有“恺悌”之德的君子与“为民父母”的为政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凝聚着历史理性和规律的思想彰显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卓越智慧。“民之父母”的政治伦理肇始于周王室的政治自觉,衍展和完善于《诗》 《书》①《尚书·洪范》中表达为“作民父母”,原文见《洪范》“九畴”当中的第五畴“皇极”畴中的“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等“五经”典籍,贯穿和成熟于先秦儒家的思想之中。另外,在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中,也有一篇被命名为“民之父母”的文献,阐述了有类于《礼记·孔子闲居》中“五至”“三无”的“为民父母之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先秦时期的“民之父母”观念并非偶然或零散的思想火花,而是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和丰富经典依据的政治伦理智慧,其与华夏民族“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儒家常将一国之君王比作一家之父母,认为只有“作民父母”者才能把对一家之爱升华和扩展为对邦国、天下民众的关切与仁爱;为政者既然是“民之父母”,理当像父母爱子女那样对民众“如保赤子”。儒家依此理路建构起一个能量充沛的动力机制,赋予了当政者作为历史“中流砥柱”的恒久动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观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与此相一致,因为只有对民众“如保赤子”的干部,才能与民众一道汇聚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 力。
“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以道德人格汇聚社会向心力。为政者欲赢得民心,就需以自己的道德人格为民表率。《韩诗外传》云:君子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俭而施博,……笃爱而不夺,厚施而不伐。……是以中立而为人父母也。筑城而居之,别田而养之,立学以教之,使人知亲尊。”①韩婴:《韩诗外传集释》 (第6 卷),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28 页。这里的“为民父母”者既有外在的“貌恭行肆”“身俭施博”的人格形象,又有内在的“笃爱”“包容”“中正”的德性修养,还有养民、富民、教民的责任担当。《诗经·大雅·泂酌》呈现了“民之父母”通过“挹彼注兹”的“爱民”之行让“民之攸归”“民之攸塈”,以赢得百姓心悦和爱戴的场景。在《礼记》 《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中,皆有对“民之父母”德行的褒扬,如“清明在躬”“纯德孔明”(《礼记·孔子闲居》),“其仁为大”(《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政善则民说(悦),民说则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大戴礼记·小辨》)等。同时,“民之父母”不仅有“爱民如子”的胸怀,而且有以远济近、化浊为清的智慧。先秦儒家在其政治伦理中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范式建构了“君民”关系模式,认为这种关系模式能有效化解因阶级地位差异所导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能高度融洽为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无疑,这种类似于血脉亲情的“君民”关系,有助于营造一个秩序和谐的“熵减”性社会,使君民一道形成恩格斯所说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之最大“合力”。历史证明,先秦儒家的这种政治伦理迎来了“民和而神降之福”,汇聚了历史前行的恒久动力,有效地保障了中华文明“动则有成”②《左传》之《季梁谏追楚师》记载,季梁对随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的绵延与繁 荣。
“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以教化和善政麇集社会凝聚力。先秦儒家认为,“为民父母”应“达于礼乐之原”“夙夜其命”“匍匐救民”。换言之,“民之父母”要将推行礼乐教化、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的使命,以赢得民心之“攸归”。《礼记》将“凯弟君子,民之父母”诠释为:“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礼记·表记》)古代的“为民父母”者以逊悌之道熏染民众,使其悦豫康安;以诗礼乐教化民众,使其自强不息;以威严庄重的仪态示范民众,使其身心安宁;以孝顺慈爱的言行引领民众,使其恭敬有礼,最终使天下百姓像尊敬父母一样爱戴他们。同时,先秦儒家认为,为政者要推行礼乐教化,不仅要了解礼乐之本,通过“五至”掌握礼乐相须为用的原理,而且要在行动上做到“三无”。此乃《礼记》所说的“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孔子闲居》)。所谓“五至”即“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在古代,礼乐是治国之大柄,为政者只有厘清诗、礼、乐的根源和本质,领悟三者相辅相成的规律,才能推行礼乐教化;只有体恤百姓疾苦,以民之乐为乐,以民之哀为哀,才能让志气塞乎天地,让百姓安宁、天下太平。所谓“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借孔子之口用《诗经》中的三句诗对“三无”作了解释:“‘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孔子闲居》)在儒家看来,为政者日夜秉承天命、夙夜在公,则民乐之,此虽非有钟鼓之声,却是推行教化的“无声之乐”;为政者仪容肃敬安和,则民效之,此虽非有升降揖让之礼,却是推行教化的“无体之礼”;为政者关心民众疾苦、对百姓之难匍匐救之,则民效之,此虽非有衰绖之服,却是身体力行、表达仁民之情的“无服之丧”。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三者皆为行之在心,虽无外在的形貌,却是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践履。在“民之父母”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的教化和善政影响下,社会就能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凝聚力。当然,先秦儒家“为民父母”的政治伦理,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观在仁民、教民、富民维度上与古代“民之父母”的责任和使命是相通的。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里“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与先秦儒家所说的“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也是契合 的。
四、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人民至上”观彰显的历史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3 页。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秉持着“人民至上”观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这样一批“中国脊梁”。他们所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熏陶和砥砺息息相 关。
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就是把国家的治乱兴衰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人民至上”观在空间维度上的历史价值。先秦儒家以礼乐教化推行其政治伦理,贯彻其民本思想,旨在为国家培养能担当历史重任的君子和民族脊梁,而成就君子的进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修身的方法和目的,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身先需“诚意”和“正心”,“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修己就是培养做人做事恭敬认真的态度,这是“安人”和“安百姓”的基础,也是成为平治天下之“凯弟君子”的起点。当然,要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仅有修身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齐家和为政的能力与持守“中道”的方法。如孔子所说的“入则孝,出则悌”“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为国以礼”“为政以德”“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等。作为君子的为政者通过“弘毅”“仁以为己任”,才能具备“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素养和能力,才能将“任重而道远”的“家国天下”担当起 来。
无私无畏,“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是指为后世太平开创基业,这是“人民至上”观在时间维度上的历史价值。要成为能为人类开万世太平的“民之父母”,需要具备“三无私”和“三达德”的精神境界。《礼记》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闲居》)在这里,先秦儒家以古代圣王“参天地”之德为仿照,以天、地、日月对万物覆盖、承载、普照作比附,认为“民之父母”要具备像天、地、日月那样的奉献精神和博大心胸,才能治理好天下。同时,为政者还要达到“知、仁、勇”之“三达德”境界,先秦儒家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如果说好学、力行、知耻是对为政者素质的基本要求,那么“三无私”则是对其精神境界的高标期待。只有具备了“三无私”和“三达德”,“为民父母”者方能在为政之路上无私无畏,才能为民众之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功 业。
综上,先秦儒家从历史本体论维度给担当天下的为政者设计了一套政治伦理架构。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激活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历史本体论“活性因子”,二者虽跨越两千多年,但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具言之,“天命德延”“敬德保民”是“人民至上”观所遵循的历史规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其所依托的历史主体,“凯弟君子,民之父母”是其所建基的历史动力,“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是其所彰显的历史价值。几千年来,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中华大地上涵养了浓郁的“民本”精神,浸润于其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由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所孕育的“人民至上”的种子,播撒到这片富含“民本”精神的沃土之中,并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百多年来,我们党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艰难困苦的考验,但始终坚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贯彻落实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让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呵护和辛勤耕耘下,这颗“人民至上”的种子已长成可以荫庇中华儿女的参天大树。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所阐发的历史本体论思想,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发挥重要影响,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中国智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