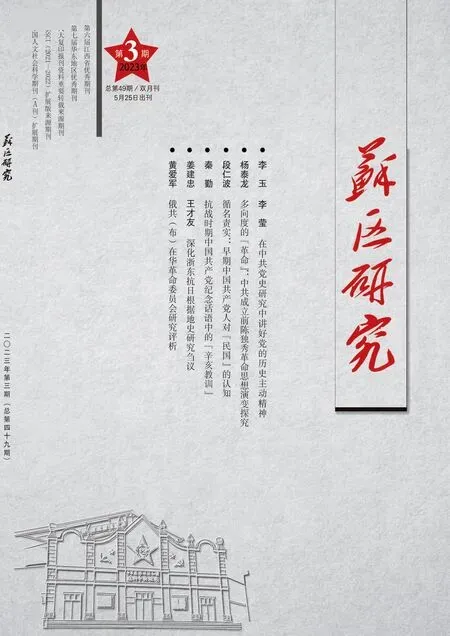深化浙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刍议
姜建忠 王才友
提要:既有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是:应从“长时段”中发掘中共浙东抗战的“中心意义”,并从更为整体的视角研究中共浙东抗战的战略演进和社会动员,还可从国民党和侵略者日本等“他者镜像”深化浙东乃至江南抗战的整体图景。
1941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皖南事变”以后的形势,作出了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4月,日军进攻浙东,宁绍地区沦陷。5月至9月,在中共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新四军第六师、第一师派遣的干部和浦东南渡三北的抗日武装,以及浙东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地方武装,三种力量合而为一,创建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于发展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浙东乃至全浙江的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较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而言,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起步较晚。(1)吕树本、杨福茂、金普森:《浙东抗日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尤其是近年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越来越有影响力,(2)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492页;吴敏超:《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齐小林:《关注地方和日常的抗战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11日。但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拟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边缘视野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意义
浙东抗日根据地位于杭州湾的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基本区和三东游击区(鄞县、奉化、镇海三县东部和定海县),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万。这些地区地缘上属于江南,多为经济富庶区域,传统意义上说,这些地区跟革命的关系并不明显。实际上,这一说法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误区。
有学者论及,近代以来,传统儒学文化在地域上表现为岭南、湖湘和江浙三个畛域分明的区域形态。(3)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其实,不仅仅是文化,在政治史,尤其在革命史的书写上,这三个区域同样具有极高的地缘地位。同盟会起源于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细察之下,三者所覆盖区域与儒学近代化形态的三大区域高度重合。因此,辛亥革命也是建基于这三大区域之上,两广、两湖和江浙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三大中心。从日后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言,国民党的政略中心也经历了由两广至两湖再至江浙一带的转变。
当然,中共革命也有其政略中心。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革命中心主要在京沪二地,体现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尤其江南地区更是中共建党的重心所在。(4)高红霞:《乡缘与建党:中共创立时期的另一种图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37—145页。大革命时期,随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推行,两广和两湖先后成为革命的中心。苏维埃革命时期,赣闽湘鄂豫皖等南方诸省建立起来的苏区成为了革命的中心。然而,南方各苏区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缘利益直接重合,国民党地缘政略制约了南方各苏区的生存和发展。而长征犹如一招活棋,既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地缘矛盾,又使中共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战略转变。(5)昆嵛:《地缘变化:长征不为人知的意义》,《人民论坛》2006年第21期,第62—63页。也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革命的中心一直在陕甘宁、华北和东北等广袤的北方地区。
浙东抗日根据地并非革命中心区域,但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未能得到“中心”视角的关注,与既有革命史的书写有关。既有革命史研究大多聚焦“中心”论述,即以各时期所覆盖的中心区域作为“代表”,进行深入研究。当然,这是一种惯常且正确的研究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心是变化的。如华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处于革命的政略中心,而在建党和苏维埃时期又处于边缘;湘赣闽等省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处于中心,而在两头处于边缘;对浙东所在的江南地区而言,建党时期是革命的中心,此后一直处于边缘。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似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存在本质性的“冲突”。
不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目的始终是夺取大城市。1945年8月11日,即日本政府要求投降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指出,目前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6)《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1页。为此,中共中央命华中局和新四军重点以夺取南京、上海和杭州等中心城市为目标。虽然这一计划因被蒋介石政府抢先一步而停止,而解放战争使江南重新回到中共革命政略的中心。
所以,在“中心是变化的”这一“常识”前提下,革命史研究应该还有一种研究路径,即聚焦一个区域进行观察,通贯地理解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无论其处于中心,抑或边缘,都可凸显革命的“中心意义”。就浙东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江南地区而言,既可考察伟大的建党时刻,又可剖析苏维埃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规模较小的“蛰伏”时刻,(7)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137页。进而关注中共革命成功的艰辛、不易和复杂性。当然,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意义”,要么与中共革命的核心议题有关,要么与其独特的地方要素有关。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与动员
长期以来,中共革命何以能够成功是中共党史和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8)《〈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614页。一定程度上说,中共抗战史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三大法宝展开论述。新世纪以来,学界围绕中共抗战军事战略、国共关系、抗日根据地史和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这些核心议题,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同样有不少成果,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1938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特别是1938年初中共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获得的意外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坚持山地游击战到下决心向华北平原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提出,是中共和毛泽东持久战理论形成的重要节点。(9)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第4—22、159页。由此,毛泽东将游击战上升到战争进程中的战略高度,并创立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10)金以林:《游击战略与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再思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9—23页。既有研究多从华北游击战场展开,论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层的战略运筹与布局。(11)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4—20、190页。近年来,已有较多学者关注新四军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问题。(12)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3—132页;李雷波:《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南下华中战略行动及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52—68页。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中共中央最早是部署八路军115师实施“发展华中”战略,中央对新四军的定位则是立足江南并兼顾闽粤赣地区的游击战争。然而,1939年初国共关系剧变,八路军暂停南下给了新四军全新的战略定位,新四军取代八路军上升为“发展华中”的主角。(13)李雷波:《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3—118页。
浙东抗日根据地就是“发展华中”战略下的产物。随着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一战略又进一步深化和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新四军华中作战分为三个基本战略区——鄂豫陕边区、江南根据地和苏鲁战区。浙东即在江南根据地的政略规划之内,中共中央原计划以中原局指导上海地方党组织赴该区创立游击根据地。(14)《浙东抗日根据地史》,第30页。5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令谭震林部署开辟浙东工作。在华中局的领导下,浦东抗日武装和浙江地方党组织开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新四军第一师十六旅和苏皖区委又奉命从苏南向苏浙皖边敌后挺进,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形,作出了华中新四军分批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发展的重大决策。(15)《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第406—492页。
从1941年2月至1944年间,从中央到浙东,从中原局到华中局,战略数变。关于这一问题,除官方党史和军史的一些总括性论述外,相较于华北和苏北,学界对浙东所涉战略变局的复杂性讨论较少。(16)劳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战略依据和斗争策略》,《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11—17页。近年来虽已有研究注意到浙东游击队的“分散游击”战略,(17)闫家威:《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分散游击与社会动员》,杭州师范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总体而言,皆未关注到战略转变背后的“整体故事”。如战略所涉各方皆有自身利益关照,新四军第六师和第一师先后入浙,当有其或全局或地方性考量,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如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南下即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局势的变化有关。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且毛泽东认为,“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毛泽东命新四军“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538页。。关于这一点,既有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论述较少提及。
根据地动员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另一核心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史研究路径方兴未艾,学界转向以根据地为中心从事地方研究。也正因为此,大量研究聚焦于各根据地干部因地制宜的革命动员。(19)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内部发行,2010年版,第144页。近年来,不少论述亦聚焦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动员,有从党群关系和的笃戏改造入手,(20)罗利行:《试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群关系》,《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第119—122页;汪湛穹:《乡村传统戏剧的时代呈现——基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笃戏”改造的考察》,《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第90—99页;还有从减租减息等经济运动着手,(21)萧宸轩:《中共在浙东的民众动员研究(1941—1945)》,浙江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都为发掘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动员的“地方性知识”提供了基础。此外,有学者结合《杨思一日记》和浙东游击队考察抗战时期中共游击队战斗生活的一般情形和扎根基层社会的一般路径。(22)任伟:《〈杨思一日记〉中的中共游击队战斗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第110—121页;任伟:《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19—128页。但是,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根据地动员还应从前述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战略需求出发,既关注中共中央对地方革命的顶层设计,也考察地方组织和社会对中央政略的因应,以更整体的视角诠释中共在浙东开展社会动员的纵深体现。
三、中共浙东抗战的他者镜像和视角
十余年前,何友良、王奇生和黄道炫等学者就提出,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革命“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23)何友良:《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05—114页;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在中共抗战史研究中,我们亦应在“他者”镜像中寻觅革命史研究的新维度。(24)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2—16页。研究浙东抗日根据地同样如此。诚如吴敏超指出,日伪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区域内博弈多年,狭路相逢勇者胜,正是在三方势力的比较研究中,映衬出新四军在反“清乡”等艰苦斗争中展现的韧性和灵活性。(25)吴敏超:《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37—41页。因此,引入国民党、日伪以及地方势力的视角,更能呈现浙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各种力量发展和斗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这一思路之下,统战工作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重点议题,其中既包括对浙东地方的上层人士,如吴山民、郭静唐和何燮侯等人的统战,也包括对根据地的经济统战,还包括对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的统战。(26)龙元平:《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统战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是,这些对统战工作的论述并不深入,具体而言,统战不仅是中共一方的“独角戏”,还牵涉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不对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涉各方势力的发展和变动情况进行考察,较难体现浙东游击队统战工作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尤其难以宏观把握时代环境和浙东的区域特征。当然,这其中牵涉到长期以来“他者镜像”资料缺失的问题。
近年来,已有学者在这一方面着力论述。如吴敏超结合浙东抗日根据地已刊史料和海峡两岸未刊档案,深入考察了浙东共产党人对田岫山和张俊升部的统战工作。作者认为,中共在弱势情况下制定了灵活务实、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是中共在浙东成功统战的重要原因;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是中共在浙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所在。(27)吴敏超:《浙东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第21—33页。除此之外,吴敏超还聚焦论述了国民党在浙西的游击战和绍兴沦陷的前线与日常,体现了国民党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冲突斗争与实力消长,以及宁绍前线的军政疲沓状况。这些情形均对理解战时中国的真实图景和浙东抗战的进展有重要参考价值。(28)吴敏超:《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第146—208页;吴敏超:《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第30—40页。
不过,笔者认为,从“他者镜像”切入,仍有一些讨论空间。黄道炫曾就中共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局势作了“弱平衡”的概括,即由于军事实力不足,中共难以用大兵力打垮敌人,故只能维持相持的平衡局面;而相对强势的日军要想彻底消灭自身控制区域内的中共武装,改变这种平衡关系,也无法实现。这一局势使得中共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瓦解和争取的统战策略。(29)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第4—22、159页。这确为理解和研究中共在多方博弈下的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路径。那么,浙东抗日根据地在1941—1945年间的形势能否用“弱平衡”来概括呢?似乎又相差甚远,因为浙东日军并不强势,相反国民党顽军势力较盛。那么,如何概括归纳浙东抗战的特征,并与华北、华南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形成对中共抗战整体图景的叙述,是进一步推进区域抗战史走向深化的一种趋向。
为了深化对浙东抗战局势变迁的研究,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在前述两岸已刊未刊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文资料进行深入发掘。如台湾方面曾在1987年翻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日本对华作战纪要丛书》,在“派遣军作战”部分的第一册即为“华中方面军作战”,其中记载了大量日军在浙赣作战的意图、策略和作战实施情况。(3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派遣军作战(一)——华中方面军作战》,“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第147—448页。此外,在日文出版资料中,亦有不少关于在华中作战和“宣抚”的资料,具有较大价值。(31)井上久士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不二出版社1989年版。综合利用这些史料,可以进一步阐释中共、日伪和国民党三方在浙东地区的实力消长和战争演进历程。(32)王士花:《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01—116页。
总之,既有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仍应从“长时段”中发掘中共浙东抗战的“中心意义”,并从更为整体的视角研究中共浙东抗战的战略演进和社会动员。同时,我们还可够透过国民党和日本的“他者镜像”深化浙东乃至江南抗战的整体图景。
———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