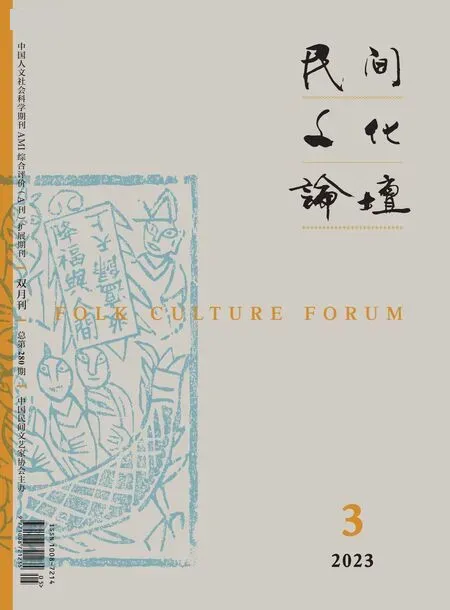中国社会科学实地研究的必要性*
李安宅 著 周小昱文 译 岳永逸 校
在西方,对社会科学中田野工作(field work)重要性的任何强调,听起来都像是在重复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在人类学家中间,实地经验是其突出的特点。但在中国,图书室研究在传统上一直是学术界唯一的研究形式,我们需要开展一场伟大的运动,把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从书籍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其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主义研究中得到体现。在这个领域的任何创造性工作之前,我们必须普遍认识到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之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验室研究之于自然科学。
如果中国没有这种意识取向,那么将会出现学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这种二分让学术工作变得徒劳无益,而现实生活则是一个没有洞察力或控制可能性的偶然。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唯一,但在中国这种混乱最为明显,且最不受人关注。当然,这样的观察并没有降低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她实际正在进行的为重生而英勇斗争的赞赏。正是基于此般赞赏,我们才更加迫切地需要改革和改变我们的科学兴趣。
在实地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上述二分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社会文化领域的实地研究可能有两种用途。首先,这些发现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并帮助我们从社会科学传统的权威类型中解脱出来,这种社会科学要么是简单的形式,要么是圣人的语录集,以前是中国人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外国人的;不过,它们可以作为扎实教学的重要基础。教学应该从直接的、已知的到遥远的、未知的,而不是像中国传统的教学形式那样,主要以牵强附会的外国文本为基础。其次,这些发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整合,以便真正洞察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明智的和有意识的生活方向成为可能。这可能表现为立即适应各种现有冲突,或为未来规划一个更为永久的建筑。通过此方式,我们可以将自身从其他国家借鉴制度公式或从社会历史背景中采用某一 “主义”的习惯中解放出来。
众所周知,除了因文化接触而产生的正常转变之外,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两个过程融为一体,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整体转变,即从农村的自给自足到工业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过程,以及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地位的解放过程。工业主义是外部强加于我们的。与此同时,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一个经济阶段的任何自发的和正常的演变,都受外国干预的制约。中国不可能解决一个问题而不介入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业革命的历史,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外国干预时,为创造一个现代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足够了。在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时,我们中国面临的困难可能很容易理解。这些问题,的确,这个组合问题,不是独特的。因此,智慧之路,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虽然我们意识到,要付出的代价将与问题的重要性成正比,但或许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改造成本低于其他国家。而社会科学家,如果想证明自己的任何用处,那么他们必须是动态导向的,而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在这样的危机中,固守学术性意味着死亡,而动态导向则意味着重生。以此为导向,发挥社会科学家的作用,最好的方法似乎不是埋首书本,而是从动态的实地研究中学习。唯有实地经验才是富有创造性的与务实的。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任何田野工作,都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只要有可能,都必须作为一项共同事业来完成,以便全面而有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处女地,国际同行有机会同时帮助中国及其科学。在这里,认真的工作必然会产生有意义的成果——无论它碰巧属于历史学派、功能学派,或者任何一种兴趣——即独立起源、传播、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以及其他。无论他们的兴趣是什么,中国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检验其理论的土壤,并以丰富的研究成果振兴他们的科学。其他伟大的文明已得到较为充分,有时甚至是过度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不系统地、更积极地尝试在中国做研究?
国际社会科学家,通过为其科学服务,也可以帮助中国。而且,他们在中国的研究越科学,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规划越有利。国际科学家不仅以超然态度,帮助中国工作者对自己的社会文化现象保有一种更有意识和客观的看法,而且通过他们在其他文化模式中具有的经验和知识,帮助训练被指派与他们一同工作的中国学生。反过来,中国社会科学家和学生可以消除语言,以及与中国社区建立联系的所有困难,这些困难可能会推迟外国学者积极参与这样的合作事业。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和学生可以消除一切语言的,以及与华人社区建立联系的困难,这可能会缓解外国学者积极参与此种共同事业的顾虑。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绝对花费更少,且更有利可图。任何在其他国家有定期田野工作预算的人,如果在中国使用这笔预算,比如两年,会发现中国其实并不遥远,甚至可能省下足够的钱来支付其来回的路费。只要合作研究产生的出版物是用不同语言编写的,那么在任何形式的合作中都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有任何疑问,燕京大学和本期刊很高兴能作为一个交流平台,服务于与此类事业相关的问题。
一系列全面的社区功能研究,将为中国的系统社会科学和明智的社会规划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学术世界和现实世界间的二分,将被证明是二手的产生于摇手椅上的理论与源于直接经验的具体洞察力间的对立,而非理论与应用间的对立。一手知识将产生创造性的理论与建设性的社会工程。
在对一个社区进行抽样时,一个单独的村庄或相当于一个村庄,极可能不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单位。最有可能的是,我们被迫研究城镇及其周边的村庄,或更广为人知的“村镇社区”(village-town community)。这类综合性研究不仅为其自身目的服务,而且还为那些更专门和独立的研究提供机会,然而它们本身,虽然数量众多,并不构成真正的社会学分析(sociological analysis)。因此,在对一个社区进行社区研究时,在提供功能分析,显示社区生活各个阶段相互关系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对有关社区的发展过程和外部关系的研究。在这样一项合作性的工作中,每位专家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当他自由地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时,他将不可避免地为描绘整个社区生活形态做出贡献。例如,一旦制定了涵盖研究不同阶段的大纲,每个研究人员就既有一般职责又有特定职责。其一般职责使他了解整个情况,其特定职责要求对他在共同分工中所承担的阶段进行专门的调查。他所关注的特定领域,同时也是其余研究阶段的工作人员的协调中心。他还可以通过同事们的具体立场来确定自己与整个研究的关系。换句话说,每位专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在与同事研究兴趣相关的领域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在不妨碍对特定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研究结果将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整体。可以预见,这种合作性研究,在强化每一门具体社会科学的同时,将鼓励一种真正的整合趋势,这可能使社会科学本身超越具体社会科学的传统本位主义。
为促进开展规模足够大的田野工作,满足上述设想的迫切需要,准备工作必须完成。这样的准备工作是给所有参与此工作的人,编辑一系列小册子。这套丛书可由两套专著组成,一套关于世界文化区与模式的描述,为中国学生提供必要的文化视角;一套是在理论上涉及方法论和典型专题,如财产、亲属关系、仪式、政府等,为学生提供解释的建议。有了这些基本手册,不仅使教学变得系统,材料容易获得,学生也会得到适当指导,而且全国各地的其他专业人员,如新闻记者、传教士、学校教师等,也可能会对社会科学产生业余兴趣,并帮助以统一的方式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积累到如此巨大,以使世界上此部分的科学变得丰富和重要。
由此可见,无论是积极参与实地研究,帮助编辑基本的系列专著,或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世界各地有共鸣的学者和科学机构都有机会,在他们的直接利益范围内帮助中国,以促进这两类工作在中国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手资料的积累,将给世界图景本身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为纯科学的利益和我们的实际利益服务,使世界更如我们所愿。
如果这些说明能引发对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其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不能声称已完全处理了此处所表达的观点。因此,我们希望那些感兴趣的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关于合作研究的整体想法,或者描述他们自己在田野工作中的经验与建议。也可以提出社区研究应该包括什么的问题。我们乐于接受意见、建议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