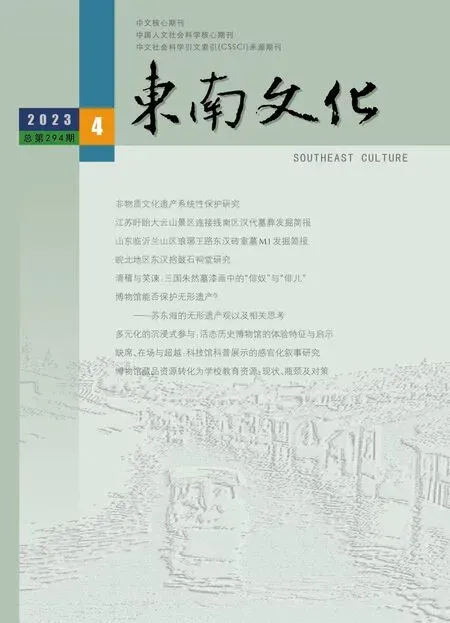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思路及实现策略
康 婧 郑 霞
(1.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2.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科普展览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其教育功能,目前博物馆学界尚缺乏学理支撑。具身认知理论为科普展览的学习体验设计提供了新视角。然而,部分科普展览由于对观众学习体验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式的认识不清晰,以至于将观众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简单理解为“动手做”与“互动式”。为解决上述问题,策展方应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深入分析身体作为媒介与展览场景之间的关系,构建感知层、交互层、映射层和意义建构层的设计思路,从整合感官元素、鼓励兴趣驱动的现象性体验,优化互动展品、引发问题驱动的探索性体验,激活身体图式、加强先验知识驱动的解释性体验,以及重视反思观察、支持个人意义驱动的相关性体验等四方面,来实现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
一、引言
科普展览作为科普教育的主要活动形式,旨在激发科学兴趣、普及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思想与精神。我国科普展览建设和运营思路基本对标西方的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模式,我国一般称科学中心为“科技馆”。科技馆当前的展览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普展览的展示现状:主要以学科定义和划分展览,如电学、力学、数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展览内容大多是对科学现象的阐释,如风、雨、光、电、磁场等,它们无法被三度空间直接收藏和展示,而是通过展品设计将自然现象中的科学原理进行再现,具有原真性的实物展品在展览中变得鲜见[1]。作为一个物与现象共存的场所,科普展览不再局限于传统基于实物的方法,而是关注呈现超越时间和地点的普遍抽象法则,倾向于提供一种脱离语境的互动展品,强调观众学习的互动性和在场性。本文重点围绕传播科普内容的这一展览类型进行研究。
随着新兴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不断融入,展示设计的重心逐渐从基于对象或展品的设计,转向为观众的学习体验而设计。目前博物馆学界已经意识到具身认知与观众学习之间存在契合点,在展览实践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具身化阐释。然而,今天国内的科普展览设计实践普遍使用动手做(hands-on)或互动式(interactive)展品来强化具身体验,并自然而然地在某种程度上追求趣味性与娱乐性,试图改变观众被动参与学习的模式。这样的展示方式在促进观众认知和学习方面确实具有明显优势,但也使科普展览的受众构成狭窄化、低龄化,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展品雷同等问题,对观众而言缺乏具有启发意义的学习体验。这种实践结果与观念实际上表现出对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式理解不清晰。那么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是否仅仅表现为互动的操作系统?观众在科普展览中实现具身学习体验需要怎样的过程?在科普展览中如何实现更有意义的具身学习体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对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思路及实现策略展开研究,以期为国内科普展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参考与启示。
二、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
科普展览似乎是比课堂的自然科学教育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作为产生直接体验的空间,科普展览为观众提供了自由的个人选择,没有教育者单向赋予学习者大量的展览信息和意义,观众有完全的自由跟随自身兴趣,在一个布满展品的公共空间中浏览学习,被各式各样的展品吸引注意力。当许多博物馆仍然被基于知识传递的线性学习理论支配时,科技馆接受了建构主义模式(constructivist model of instruction)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因为它将观众视为一种积极学习者的角色: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搜集证据、解释并得出结论。建构主义模式认为学习者不是在直接的知识传播过程中通过被动感知来获得知识和理解,而是通过经验和社会话语,将新的信息与先验知识结合起来,构筑新的理解。不可否认的是,建构主义框架在科普展览中迎合了观众学习的需求,鼓励观众自由表达与创造。然而,这种模式如何帮助观众在自由选择的状态下学习科学知识?它的局限性愈来愈明显。美国旧金山探索馆(Exploratorium)研究员苏·艾伦(Sue Allen)认为这种挑战是科技馆学习的“建构主义困境”(constructivist dilemma)[2]。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学习仅仅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一个过程,或者仅仅着眼于观众在参观结束后的测试中能够再现哪些内容,那么我们就很难充分认识这些情境中产生的学习体验。
与一般的历史文化主题展览不同,观众在科普展览中的学习并非完全基于实物,而是通过体验各种设计装置了解科学现象并学习科学原理,促使其依靠身体实践来完成认知过程,体验与感受事物属性的方式更加直接,因此科普展览学习具有更强的自主选择性和主动探究性。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为博物馆展览学习体验打开了视觉之外的大门,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具身认知理论是对传统认知理论中认知功能离身化的再思考,其理论框架出自哲学和经验科学的交汇。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调认知为身体及其活动方式所塑造,关注认知主体及其身体行动与具体情境之间的耦合过程[3]。然而,传统学习观将学习主体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心智作为学习主体的重要作用,将学习看作个人内在的过程,个人的先验知识成为学习的决定因素。这种去情境化和分解式的理解方式导致教育者和学习者忽视了身体参与的教育价值,丧失了对学习体验的整体性和情境性的认知。具身认知不同于传统学习观的单向线性发展模式,主张发挥身体对思维、记忆的作用来建构知识。换言之,学习的内容不应该直接呈现,而是由学习者独立探索,即通过身体获取知识,通过行动理解物、场景与主体之间的关系[4]。
三、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科普展览学习体验设计思路
身体作为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并非强行暗示肢体接触,而在于身体如何与科普展览中的场景进行关联。下文将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深入分析身体与展览场景之间的关系,构建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的设计思路。
1.感知层:身体感知场景
感知层的目标是对现象性体验的设计,注重观众的感知觉经验;感知层基于身体感知场景的设计原理,即通过不同的身体感知方式和感知程度,在本能的驱动下参与认知;设计表现在如何吸引观众注意力,激发观众学习科学的好奇心。具身认知强调个体对世界的感知并非一种反射或印象,而是身体参与塑造的结果。在科普展览中,观众关注对现象的解释并对其产生直接的感官反应,这便是通过身体的感官本能参与认知的过程。身体的感知方式和感知程度对科学学习具有重要作用,观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单一或多感官通道共同参与获得学习体验。按照具身认知理论,与环境交互涉及的感官通道越多,形成的具身体验就越完整。例如浙江台州博物馆“海滨之民”展项就很好地将多感官设计融入其中。该展项将海滨渔村搬入博物馆,将渔村的原本面貌进行了高度还原,模拟了海水的声音(听觉)、海风的吹拂(触觉),甚至有鱼腥味在空中弥漫(嗅觉),引发观众产生更多记忆与思考[5]。又如中国科技馆生命展区“鸟蛋的启示”展项,作为展品“十三种不同种类的雀鸟”的扩展,该展项以进化论知识为基础,让观众通过观察鸟蛋的颜色、斑点(视觉),听到对应的鸟叫声(听觉),触摸蛋壳的软硬、质感(触觉),获得对鸟类的直接经验积累以及动物适应环境的相关知识[6]。
2.交互层:身体反馈场景
交互层的目标是对探索性体验的设计,注重优化观众在展览中与媒介的活动关系;交互层基于身体反馈场景的设计原理,即通过物理或虚拟、直接或间接的身体交互形式接收并反馈场景信息;设计表现在引发观众对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促进观众持续参与学习。具身视角下,主体认知是在身体与环境互动所获得的经验中形成与发展,通过互动的方式内化生成认知。高度具身化的交互具有独特的学习启示,进而表现出知识的情境化特征。观众在博物馆中学习过程的相关研究表明,交互性促进了观众对展品的参与、理解和回忆[7],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人们对自己身体动作的记忆明显高于仅靠肉眼观察到的记忆[8]。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身体传感器和触摸屏等技术工具作为观众与展览场景互动的中介,融入观众的感知经验,并与之共同参与具身学习。科普展览中的具身交互形式既包括物理的互动,也包括虚拟的对话和交流,观众通过身体感知系统实时、同步地接收并反馈信息,重点在于身体与心理、环境协作交互的动态过程。例如,旧金山探索馆“从细胞到自我”(Cells to Self)展览为揭示人类细胞多样性而设计了微生物互动展项,旨在为普通公众理解与欣赏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建立新的方法[9]。当人体轮廓被投射到显微镜载玻片上时,这个微小场景以人体比例投影在交互式屏幕上,观众可以对微生物的行为作出反应并影响它们;欧盟(EU)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学习人类现存的珍贵知识”(i-Treasure)非遗数字化项目,将传统舞蹈等非遗资源进行获取、分析和建模,利用体感互动技术对观众进行舞蹈教学,屏幕中的虚拟化身与观众的身体动作实时对应形成“共同身体”,通过身体动作的模拟与反馈,观众可以及时纠正动作进而达到学习目的[10]。
3.映射层:身体隐喻场景
映射层的目标是对解释性体验的设计,注重观众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映射层基于身体隐喻场景的设计原理,即观众通过符合其先验知识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实现概念隐喻的认知过程[11];设计表现在观众可以理解抽象的科学概念和科学原理,通过探索学习过程与方法培养学习技能,最终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e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CMT)强调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隐喻化过程,认为人类要认识复杂的抽象概念,就必须借助已知的具体概念将其映射(mapping)到未知的抽象概念[12]。映射是基于人的日常身体活动经验所产生的身体图式,形成普遍存在于人类心智的认知结构。例如,观众根据顺时针转动旋钮会增加物理量的身体经验,形成了空间图式(spatial schema)及其隐喻;根据挤压物体使其体积缩小、拉伸物体使其体积变大的身体经验,形成了力量图式(force schema)及其隐喻。那么,观众如何在身体图式基础上扩展对于科普展览内容的认知?显然,映射层的设计取决于观众的先验知识,选择符合观众先验知识的身体图式有助于观众利用其直觉与展品进行互动。事实上,身体图式来源于个体的日常活动,正是由于身体图式的有限性、共享性和映射性,观众能以此调动无限的经验,加深对展品信息的理解并与之交互,使得利用身体图式开展意义学习成为可能[13]。
4.意义建构层:身体反思场景
意义建构层的目标是对相关性体验的设计,注重观众对特定情境中自身行为、感受、思想和经验的主动思考;意义建构层基于身体反思场景的设计原理,即观众有意识地将学习内容与先验知识和个人意义进行联系;设计表现在对个体情感态度的影响以及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塑造。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内在经验的重要性,即身体是意义的建构者[14]。大脑并不是感觉输入的被动接收器,而是对世界积极建构的预期,并与经验进行对比[15]。在此背景下,理解博物馆展品的观众不断地在记忆和现有的心理框架之间移动[16],在参与博物馆活动时,观众参考过去的经验,可以极大地提高意义建构的潜力[17]。可见,意义关系的建构过程是身体从先前经验以及现有的知识和期望中发展出对当前事件的理解。意义建构层的设计是确保观众认知升级、学习有效的目标导向。例如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的大卫·塞恩斯伯里展厅(David Sainsbury Gallery)面向中学生群体推出了“技术工作者”(technicians)项目,项目主题涵盖了健康、艺术、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18]。学生在专业人员的支持下扮演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角色,通过亲身体验特定科学职业的相关任务和挑战,形成了更为真实的职业感受,为其树立个人职业生涯理想奠定基础;又如新加坡科学中心(Singapore Science Centre)“DNA 学习实验室”(DNA Learning Lab)推出的犯罪现场调查活动,让观众亲历“破案”过程,了解DNA 作为犯罪证据的重要性,为科学实验赋予现实的应用情境,强烈的现实代入感不仅激发了观众对生命科学的关注和兴趣,还有助于观众深入理解生命科学的主题和事件[19]。
综上,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科普展览学习体验设计框架可以从感知层、交互层、映射层和意义建构层进行设计(图一),这四个层次并非独立运行,而是相互关联、依次递进。由于科普展览空间具有强化在场性、弱化历时性的特点[20],观众很难遵循一个限制好的学习过程。因此,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的设计重点是创造能够使观众充分探究的多样化环境,因为观众需要有足够的驱动力促使其在展览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即学习体验的每一步都依赖于个人动机,这种状态激发了其探索的欲望并更加鼓励学习。下文将基于感知层、交互层、映射层和意义建构层的设计思路,重点分析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设计的实现策略。

图一// 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框架(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四、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设计的实现策略
1.感知层:整合感官元素,鼓励兴趣驱动的现象性体验
科普展览以现象类展品为主体,在展览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安排、环境的创设等方面,应当注重观众多感官协同参与,促使观众通过感知来关注想象的科学世界,即鼓励兴趣驱动的现象性体验。在科普展览中运用多感官设计,可以改善观众的参观体验,观众的停留时间以及对科学原理和展区主题的理解都有大幅增加[21]。如今,多感官学习(multisensory learning)模式已经成为科普展览支持观众学习类型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展览内容增加了各种形式的感知元素,包括提供触摸、倾听和嗅觉等形式,提供多种方式帮助观众将日常感知体验与科学内容建立联系。然而,观众的实际学习过程并不能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在制造新奇现象的同时,科普展览也要注意“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带来的弊端,避免让观众沉浸在肤浅的、被动娱乐的具身体验中。由于受到具身体验的有效性、认知负荷等因素的影响,科普展览的策展人和设计师应当综合考量观众特征、学习内容、展览环境等要素,对科普展览中不同的感知模态进行选择与整合。
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将理想的展览学习过程描述为由兴趣或好奇心驱动并通过心流(flow)状态维持[22]。在这种状态下,观众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内在驱动的活动中。为了创造这种心流状态,科普展览可以通过多维度、沉浸式的空间表现形式,创造吸引注意力的情境刺激,全面调动观众的感知觉经验使其获得现象性体验。例如瑞典北欧博物馆(Nordiska Museet)通过“北极——当冰融化时”(The Arctic: While the Ice is Melting)展览揭示北极地区的生活和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展览在入口处设有一件冰块被巨大裂缝分开的影像装置,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和对北极寒冷的直接感知。随着观众穿过“裂缝”进入展厅,自然标本展柜周围布满可以触摸的干草,白色的硬冰投影逐渐变成浅绿色和蓝色的融水,最终完全融入深蓝色的海洋,巧妙地暗示了展览“冰在融化”的主题。整个展览利用数字技术沉浸式地还原了极地氛围,为观众营造出强烈的穿越感和逼真的现场体验,使观众得以了解北极地区的生活方式[23]。
2.交互层:优化互动展品,引发问题驱动的探索性体验
为了使观众持续参与学习并掌握展览知识,科普展览需要优化互动展品的设计形式以及与人的技能密切相关的互动挑战设计,即引发问题驱动的探索性体验。交互性被认为是科普展览的主要特征,旨在为观众提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互动内容与互动形式[24]。尽管一些研究支持交互性增强了观众的学习效果,但它并不是提升学习体验的一个简单或普遍的解决方案。由于科普展示内容通常是具有标准答案的科学知识,缺少开放性问题驱动的思考,导致观众参与的过程难以持续。事实上,观众在可以直接触摸和操作的展品中停留的时间相当短,一些观众在展览中会重复进行毫无意义的互动行为[25]。由此可见,过多的互动功能反而会降低观众参与的兴趣和学习效果[26],甚至有时还会造成认知的混乱和误解。这表明科普展品的互动形式更要强调动脑,而不仅仅是强调动手,否则展览的教育目标和观众的学习体验将被淡化和削弱[27]。
观众在感到有方向性和舒适的情况下会更愿意参与互动挑战[28],所以科普展览需要优化的不仅是互动挑战的难易程度,还有互动的时长和环境氛围。在此基础上,科普展览可以设计一套明确的互动挑战目标和规则,而不是直接给出正确的答案或明显的结论,通过鼓励观众自主探究,将现象与深度的认知体验相结合,促使观众产生更多的驱动性问题,从而持续参与科普活动。例如,旧金山探索馆研发了能够引起观众“积极长时间参与”(active prolonged engagement,APE)的展品,旨在让观众提出质疑、问题与假设,深度参与科学调查[29]。又如,上海科技馆“能源挑战之旅”展项将能源和环境知识转化为游戏元素,融入多人竞技和社交互动,从而吸引观众探索。该展项借助多媒体将相关能源图标投影到地面,并通过体感交互技术获取身体数据,观众以踩踏图标的形式采集能源。展项将观众在开采能源过程中所取得的分数以及对地球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微缩地球的形式进行实时可视化呈现,同时要求观众迅速评判策略优劣并作出调整。策略思维的游戏比赛促使观众自主探索能源与环境平衡发展的关系,让学习体验变被动为主动[30]。
3.映射层:激活身体图式,加强先验知识驱动的解释性体验
观众对展品的学习往往是高度文字化和具象化的[31],科普展览可以选择观众熟悉的身体图式加强概念学习,使观众理解抽象的科学概念和原理,即加强先验知识驱动的解释性体验。面对一些难以在具体条件下展示的不可见概念,科普展览通常无法为观众提供真实的情境。大多数观众很难从多个单独设计的展品中完全领会科普展览预期的主题和概念,特别是当展示内容是抽象的而非现象的时候,观众已经普遍出现的“博物馆疲劳”加剧了其认知负荷,限制了观众在展览中的有效学习。身体图式的激活被视为一种接近于无意识的知觉过程,能够避免观众耗费更多的心智资源,从而提高对展品的即时可理解性。观众在共享身体图式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将其视为展览环境中的一个属性。因此,科普展览可以选择观众熟悉的身体活动,唤起观众已经存在的身体经验,帮助其理解展品的互动形式所表达的抽象概念。
身体动作和概念的一致性对于帮助观众轻松发现身体动作和认知映射之间的隐喻意义至关重要。然而,隐喻意义越复杂,展览设计的意图和观众的解读就越有可能出现分歧,还有可能导致观众的错误操作。可见,在科普展览中有必要建立一种标准化或系统化的身体控制或理解机制,并完善其映射规则,即对交互动作的描述和定义[32]。例如在地板上放置脚印的轮廓,帮助观众准确站立在指定的位置;在屏幕上提供头部的轮廓图像,帮助观众将他们的脸部定位在与摄像头的正确距离处。手势是展览中常见的具身化表达方式,科普展览还可以通过特定手势所传达的隐喻关联性,让观众注意到展品的具体规则和对具体展示现象的解释,使概念学习得到加强[33]。例如,一项基于手势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展览被设计用于阐释导体电阻现象,观众可以通过手势来改变导体的长度和厚度、灯泡的亮度、电阻和电流的强度,结果证明基于手势的具身体验提高了观众对复杂科学概念的理解[34]。
4.意义建构层:重视反思观察,支持个人意义驱动的相关性体验
具身视角下,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概念,也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身体,是经验中的身体。科普展览具身学习体验需要重视观众的反思性观察,而不仅仅是动手实验,应通过加深观众对展览主题的重新思考与认识,从而建立与自我之间的意义关联,即支持个人意义驱动的相关性体验。长期以来,科普展览通过对展品系列的选择、在展品集群之间统一的空间引导以及对主题展品组说明的加强,帮助观众在松散的分组、区域标题和标签文字之间找到不同展品组之间的联系,引导观众观察和思考。然而,由于科普展览中无序、活跃的环境和科学的非轶事性质,要想让观众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联系自身并唤起反思,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叙事或讲故事被证明是历史类博物馆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甚至被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然而讲故事的学习策略在科普展览中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35]。这意味着科普展览需要专注于展览主题对观众情感态度的影响和精神价值的塑造,力求探索一种让观众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表现事物的多样性。
身体的自主感(sense of agency)和拥有感(sense of ownership)被视为构成自我识别的两种基本体验:自主感即“我是行动的发起者”的感觉;拥有感即“我正在经历这个事件”的感觉[36]。通过对自主感和拥有感的模拟,科普展览可以引领观众亲临故事情境、进入第一人称角色,促使观众产生与自我意义相关联的学习体验。此时的观众成为故事的发起者和亲历者,而不仅仅是故事的听众。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8 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A4 纸的工程PARTY”活动营造了一个生产生活均围绕A4 纸开展的“纸张王国”的故事情境,让观众成为故事的主人翁,通过扮演国家工程师的角色(飞机设计师、飞机试飞员、飞机装配师、飞机记录员等),以分工合作的方式亲身体验飞机的工程“设计”,故事兼具连贯性、趣味性的同时,还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活动[37]。
综上,科普展览中的具身学习是由观众的内在驱动力实现感知层、交互层、映射层和意义建构层的探究过程,其实现策略可以遵循整合感官元素、鼓励兴趣驱动的现象性体验,优化互动展品、引发问题驱动的探索性体验,激活身体图式、加强先验知识驱动的解释性体验,以及重视反思观察、支持个人意义驱动的相关性体验等四方面来实现。理想的具身学习体验设计策略实际上也是完成不同阶段的科普教育目标,即从科学兴趣的激发和内容知识的获取到科学探究技能的培养和科学思想精神的塑造。
五、结语
事实上,身体在场已经成为科普展览发挥其教育潜力的重要因素。具身学习体验在科普展览中的意义也由此被揭示,它并非简单的动手操作,而旨在以身体为媒介激活观众的感知系统,并通过身体交互与映射强化认知过程,最终实现意义世界的建构。如果基于身体的学习策略在科普展示设计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那么具身学习在科普展览中的效果评估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此外,我们除了需要重视身体在科普展览学习中的意义和作用,还需要对认知具身性的简单化理解提高警惕。把身体及其行动放在认知的核心位置,并不是说要将身体的作用普遍化或者由此得出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为了向人类心智提供一种更积极的、更开放的思考方式。在科普展览设计中,策展人不仅为观众创造基于互动的具身体验,还应当注意观众是否能够在展览与自身之间建立联系,考虑吸引观众的身份、情感、动机、先验知识、期望和生活经历,通过策划个性化主题、唤起情感和引发共鸣来增强意义构建的潜力,在科普展览中设计更有意义的学习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