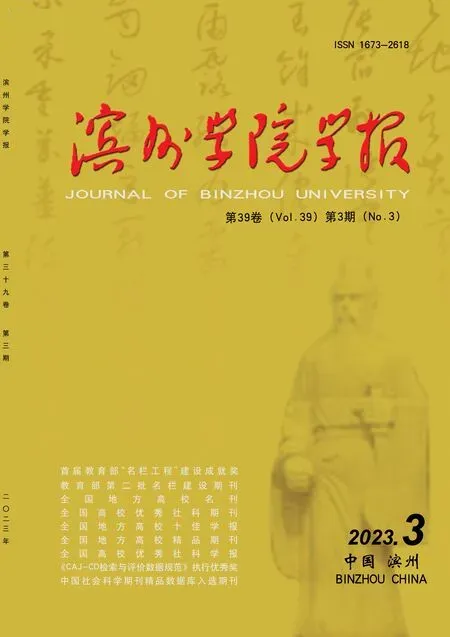战略学视野下的《唐李问对》历史思维研究
庞小条
(江苏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战略与历史关系紧密。战略是“对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1]79,其“长远性”涉及未来的时间维度。“历史思维指的是一种知古鉴今的能力,也即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2]17预见未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前进方向,既是历史思维也是战略思维的基本要求。“战略家的理想是控制历史的潮流,改变历史的趋势”,而“控制历史的演变,其首要步骤即为研究历史”。[3]302因此,从战略理论角度(视野)(1)视野指某种理论或知识领域。研究历史与历史思维(2)从历史角度研究历史,是为历史学研究。从哲学角度研究历史,是为历史哲学。从战略学角度研究历史,发挥历史“以古鉴今”的作用,遵循历史发展大势,属于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战略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战略理论(视野)探讨《唐李问对》(以下简称《问对》)的历史思维,原因有二:
第一,运用史例证明战略战术理论是《问对》文本的一大特点。《中国军事史》编写组在《武经七书注译》中指出:“《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贡献。”[4]512黄朴民教授指出,在《武经七书》系统中,其他六部兵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侧重于哲学推理,形成了“舍事而言理”的文化传统。《问对》则完成了古典兵书由单纯“舍事言理”向“事理并重”方向的转变。[5]144-145这里的“事”指的就是运用历史案例深化人们对战略战术理论的理解。《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战略学领域最重要的七部经典,《问对》是其中之一。用史例证明战略战术理论是《问对》独有的特点,那么,揭示《问对》引用史例的战略意蕴,自然具有相应的理论意义。
第二,用史例证明战略战术理论是《问对》区别于此前中国传统战略经典的地方。前辈学者对此也多有揭示。申杰宏对《问对》中提到的“牧野之战”“吴越之战”“淝水之战”等15个案例作了简要的介绍[6]。在注译《问对》时,黄朴民除了介绍《问对》中提到的一些战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马隆讨平树机能”“勾践笠泽破吴师”等外,还对这些战例作了精要点评。[5]除了介绍《问对》提到的史例外,有许多研究成果利用史例说明《问对》包含的诸多战略战术范畴。吴如嵩与王显臣[7]、陈相灵[8]307-330、赵良[9]、郑立娟[10]等在深入阐释“奇正”“虚实”“主客”等范畴过程中,也利用一些史例来证明这些范畴的含义。上述涉及《问对》史例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问对》史例自身的梳理和阐释;二是以《问对》相关战略战术范畴为中心,辅之以史例。这些研究既是我们进一步研究《问对》的基础,也凸显出《问对》“事理并重”的特征。《问对》“事理并重”的特征表明,不仅“理”蕴藏了深刻的战略思想,“事”(史例)同样蕴藏了深刻的战略思想。因此,以“史例”为核心,探寻其蕴藏的战略意蕴,也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立足于《问对》文本记载的历史事实,通过探讨其所要证明的“庙算”论、战略价值论、战略决策与驾驭论等战略学基础理论,亦即在战略学视域中,以古鉴今,阐释《问对》历史思维思想。
一、历史思维与庙算论
未战而庙算,是中国传统战略实践基本程序之一。(3)有学者强调,在我国古代,战略概念与庙算概念含义大致相同。“我国文献中,战略一词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晋代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此后,这一名词屡见于各种文献中。但是,含义同战略大致相同的‘庙算’‘兵法’等词,却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了。”见李继盛:《国家战略艺术:结构、原则和方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唐太宗说:“《孙子》谓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7]15庙算事关战争的成败,是战略实践不可缺少的程序。这一程序不仅军事领域须要用到,社会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都须要用到,凡事皆然。“无论任何事情,事先都要有紧密的计划或谋划,根据分析和判断,预测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结果,并相应地采取应付措施。尤其是在激烈竞争或情况复杂的情形下,事先的分析和谋划显得更为重要,必须根据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制定适宜的措施,采取不同的方法。否则,莽撞从事,一味蛮干,肯定不会有好结果。”[11]26
唐太宗与李靖(即李卫公)君臣以“淝水之战”史实为例,既说明了“少算胜无算”的道理,更说明了“庙算”对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383年,前秦君主苻坚准备讨伐东晋,完成一统华夏的伟业。当时,朝臣都反对苻坚攻打东晋,唯有鲜卑族的慕容垂、羌族的姚苌和地主家的纨绔子弟赞同苻坚的决定。苻坚之弟、阳平公苻融反对的理由是:“鲜卑、羌虏,我之仇讎,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以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12]3308苻坚不听。八月,坚发兵长安,讨伐东晋。其中,讨伐东晋的重要将领中,就有鲜卑族的慕容垂等人。慕容楷、慕容绍建言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12]3309慕容垂接受了他们的建言。
前秦军队阵容壮观,声势浩大,“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而东晋集全国之力,“众共八万拒之”[12]3309。强弱一目了然。东晋将领皆抱悲观态度,“(谢)安棋艺常劣于(谢)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12]3310。东晋名将桓冲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12]3310
秦晋之兵列阵淝水决战,东晋以弱胜强,战胜了前秦军队。
战后,前秦苻坚“诸军皆溃败,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亲党多劝垂杀坚”[12]3313。385年,苻坚被其信任的姚苌缢杀“于新平佛寺”。
淝水之战,以“未战先算、未战先胜”庙算比较,东晋谢玄战胜前秦苻坚,就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7]15。战前,东晋谋略集团核心人物谢安已无其他战略筹划,唯有游山玩水,以闲暇示成竹在胸而激励士气。前秦与东晋强弱对比悬殊,从军事实力角度讲,前秦胜利几乎是注定之事,给予谢安谋划发挥的空间特别少。谢安谋划空间少,意味着整个东晋谋划的空间少,对于前军将领谢玄来讲,更是如此。因此,李靖指出,以谢玄为代表的东晋集团,整体庙算谋略属于一点点“小术”、一丝丝“片善”。(4)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见吴如嵩、王显臣:《李靖问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页。唐太宗说:“知彼知己,兵之大要”。[7]79庙算之“算”以“知”为基础。唐太宗认为,现在的将领,即使不知彼,如果能够知己,也不会有失利,“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7]79苻坚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不知彼,更不知己,失利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战前苻融劝谏苻坚,鲜卑慕容垂、羌族姚苌、良家子等不可信,从后来事态发展可看出苻融谏言的正确性,而苻坚没有接受苻融的谏言,而为慕容垂等所陷害,“见秦军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7]15。可见,苻坚讨伐东晋,并没有接受、分析和判断相关信息,凭主观意志贸然决策,导致了淝水之战的失败,“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者,不亦难乎?”[7]15于是,李靖得出苻坚“无术”的结论,“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7]15,即苻坚战前没有任何综合性的庙算谋划。面对前秦强大军事优势,东晋谋略集团发挥空间较少,只是正常发挥;而前秦苻坚自恃刚强,不仅轻敌,而且对集团内部矛盾视而不见,并听信谗言。在唐李君臣看来,前秦“无算”“无术”“无善”,东晋只是“少算”“小术”“片善”,后者战胜前者,可见庙算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
唐太宗引用孙子庙算理论总结淝水之战,“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7]15。淝水之战,东晋以弱小的兵力对抗强势的前秦;东晋谋略集团只是少算,就战胜了无算的苻坚,形势逆转的关键原因就是“算”。这种“算”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凡事都是如此。因此,无论是大战略、军事战略,还是其他领域的战略,如果能够“算”,特别是充分地“算”,在敌我竞争时,必定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取得战争(竞争)的胜利。
《问对》选取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案例“淝水之战”证明“庙算”的重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战前,前秦实力远超东晋,正常来讲,前秦战胜东晋是必然之事。这是苻坚摒除谏言的原因,也是谢安在紧张的气氛中游山玩水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淝水之战中,前秦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地失败了。庙算以获得更多“敌人”和“自己”信息为前提,苻坚固执己见,不“知彼知己”,唐太宗评其为“无算”,李靖评其为“无术”“无善”,前秦败于“少算”“小术”“片善”的东晋,自是情理之中。这里,《问对》用“淝水之战”证明战略“庙算”理论,体现了历史思维在战略研究和实践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历史思维与战略价值论
“价值是因立场而产生的,不同立场的人对于同一事件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5)任俊华教授《当代战略哲学的建构》讲课笔记,笔者记录。贞观时期的战略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封建时代的“人本”意识上。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骨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3]1这里,唐太宗所讲的君主与百姓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那个时代的基本战略价值取向。在《问对》的许多地方,这个战略价值取向是以历史事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霍邑之战打开了李唐集团进入关中的道路,在唐朝建立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朝基本战略价值取向在霍邑之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同时,这种基本价值立场也构成了战胜敌人的重要工具。“师出有名”,这个“名”既是价值,亦是工具。唐太宗和李靖指出,霍邑之战是以“救民”的“仁义”为宗旨的。[7]5战前敌对双方战略态势为隋强唐弱,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人屯于霍邑,唐军适逢阴雨连连、粮食匮乏。唐军最高决策者李渊与其大臣裴寂商议,决定暂时退守太原后,再作安排。李世民反对退守决策,进谏唐高祖时指出,霍邑之战的战争价值取向是“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14]16。《问对》中,李靖将霍邑之战的基本战略原则总结为“仁义”之“正兵”:“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所谓“救苍生”“师以义举”体现了封建时代以“百姓”为本的战略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霍邑之战,唐太宗李世民把握“仁义”价值取向和判断民心向背,在更高层面扭转了隋强唐弱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唐太公和李靖将兵法源头追溯至黄帝兵法。在中国古代,因为“井田制”公平公正的特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井田制”也就构成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想象。因为“井田制”代表人民利益,可以凝聚强大的力量,所以兵法效法“井田制”的形式、本质、精神、价值,同样要求军队能够凝聚强大的力量。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仁义之兵”可以“无敌于天下”[15]342,“节制之兵”源于又次于“仁义之兵”,亦可以达到诸侯毕服的战略效果。这里,“仁义之兵”和“节制之兵”都以“井田制”的战略价值意象凝聚力量。《问对》通过黄帝制作兵法、太公借鉴并创新黄帝兵法辅佐武王牧野伐纣战争的胜利、齐桓公任用管仲成为诸侯霸主等历史事实,说明了战略价值立场对于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历史思维与战略决策论
《唐李问对》的开篇之问是关于如何“征讨高丽”的战略决策:“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7]1李靖以“正兵”决策征讨高丽回答唐太宗。为此,唐太宗和李靖在谈话中列举了“李靖平突厥”“诸葛亮七擒孟获”“晋马隆讨凉州”“霍邑之战”等战例,来说明“正兵”的含义。
“霍邑之战”突出了“正兵”政治战略的含义。李靖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7]5也就是说,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就是“正”,所谓“师以义举者,正也”;战场上运用奇谋诡道就是“奇”。[16]109纵观唐太宗征讨高丽,出师之名即政治战略,使用的就是“正兵”决策。例如,贞观十九年(645)三月,唐太宗谓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12]6217-6218
“诸葛亮七擒孟获”突出了“正兵”心理战的含义。诸葛亮南征孟获之前,参军马谡向他提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12]2222的战略原则。诸葛亮至南中,采取心战方略,“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12]2225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唐太宗手诏谕天下说:“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12]6214,唐朝出师,只针对“弑主虐民”的“盖苏文”,为高丽雪君父之耻,争取高丽民心。贞观十九年十月,诸军俘虏高丽军民一万四千余人,集合在幽州,准备奖赏给将士,唐太宗怜悯高丽军民夫妻离散,命令相关官员用国库金钱将他们赎为百姓,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唐太宗车驾至幽州,高丽百姓在城东迎接,拜舞呼号,宛转于地,尘埃弥望。[12]6231这些都突出了唐太宗运用“心战”战略征讨高丽。
“李靖平突厥”突出了“正兵”“西行数千里”“推赤诚、存至公”的“治力”原则。李靖征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7]65。唐太宗征讨高丽,为了凝聚士气,在悯恤士兵方面,见生病的士卒,召至御榻前慰问,托付给州县治疗,士卒感动喜悦,甚至没有列入东征名籍,但自愿以私装从军的数以千计,不求奖赏,但愿效死辽东。[12]6218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12]6221从军队组成来看,征讨高丽的将士都是自愿跟随,“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募千得万,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12]6216。这些征讨高丽的士兵皆为自愿,士气十分高昂,亦是唐朝政府“推赤诚”的“治力”之法在起作用。
“晋马隆讨凉州”突出了“正兵”原则:保存自己的力量、攻击抵抗的敌人、约束部队。这三个方面相互作用,融会于战争之中。无论是征讨高丽战争,还是其他战争,这三个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唐太宗和李靖通过历史战例来说明“正兵”各个方面的含义,这些含义融会为一体,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征讨高丽”的战略决策。
四、历史思维与战略驾驭论
“所谓战略驾驭,就是领导者在战略层面,通过对于各种关系的有效控制,时松时紧,张弛有度,从而确保战略实施的行为。由于针对的关系不同,领导者的战略驾驭功夫也有所不同。”(6)任俊华教授《当代战略哲学的建构》讲课笔记,笔者记录。战略驾驭关系众多,处理好“上下关系”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战略驾驭中,“上下关系”体现了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有效管理以及整个组织系统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性。从“以史鉴今”视角出发,唐李君臣深入探讨了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和汉光武帝刘秀驾驭“上下关系”的优劣。
唐太宗和李靖从治国战略层面谈论驾驭李勣的问题与办法。唐太宗说:“卿尝言李勣能知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若何御之?”李靖回应说:“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有损乎?”[7]82对于这段谈话,历史上,人们对唐李君臣这种驾驭方式的道德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过,这并不是本部分详细论述的内容,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和李靖以太子如何驾驭控制大将李勣展开“驾驭”的话题,并将话题引向了刘邦、项羽、刘秀对将领驾驭的优劣评判上了。
(一)刘、项“非将将之君”
汉高祖刘邦善于驾驭将领,这是中国人一项常识性认识。然而,唐太宗对此提出质疑:“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7]84“将将”二字,第一个“将”为动词,意思是“驾驭”;第二个“将”为名词,意思是将领;“将将”即驾驭将领。既然汉高祖善于驾驭将领,后来韩信、彭越被诛杀,萧何被下狱,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悲剧的结局呢?这里,唐太宗的疑问蕴藏了一种反问,即真正懂得“驾驭”的战略家,其集团内部必须要有充满和谐的上下关系,这种和谐的上下关系应该贯穿于整个事业的始终,而不仅是在某个阶段而已。
项羽不是“将将”之君。汉朝建立,陈平和韩信都立下不世之功。太史公司马迁评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17]369,评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17]554。像陈平、韩信这些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开始都隶属于项羽。然而,项羽并没有很好地任用他们,最终,他们都选择离楚归汉。范增是项羽集团首席谋士,对项羽十分忠诚,因受项羽猜忌,在辞官归家途中病死。[17]66-67陈平、韩信、范增都是当时顶级战略人才,项羽没有发现并尊重这些人才,更没有能力驾驭这些人才,这是导致西楚集团最终败亡的重要原因。《问对》中,李靖所言“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范增不用”等等话语,表明项羽不是一个“将将”之君,没有驾驭将领的能力。
项羽非“将将”之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人们对汉高祖刘邦的固有印象则是“善将将”,李靖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说:“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7]84其理由是:“当秦亡之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7]84在李靖看来,刘邦和项羽都不是驾驭将帅的君主。这段话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刘邦没有完全统御张良、陈平、韩信等人,这些人只是利用刘邦的势力来为自己谋出路而已。张良祖辈五世为韩王相国,对韩国充满了感情,张良忠于韩国,韩王韩成在时,并没有完全为汉王刘邦谋划,及项羽杀韩王成于彭城,才真正地归附汉王,时时从汉王,为刘邦谋划天下。明朝学者李贽评项羽杀韩王成说:“为汉驱一好军师。”[18]105陈平、韩信都是在项羽那里遭到冷遇后,才转归汉王刘邦。换言之,以张良、陈平、韩信为代表的许多人才并不是依靠刘邦统御将领的才华被吸引过来,只是他们需要借助刘邦势力为自己谋出路而已。第二,上下关系的战略驾驭是领导者在战略层面对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有效控驭,使其能够按照集团目标向前推进。张良、陈平、韩信等并不是被“汉”的理念吸引过来的,而是不得已投靠汉王,他们的目标只是在某一现实利益背景下具有趋同性。如同李靖所讲,假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主,即使汉王刘邦有将将之才,这些豪杰之士怎么能为汉所用呢?第三,在战略统御层面,汉集团战略目标之所以能够有效推进并最终取得天下,有赖于“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7]84,并不完全依赖于刘邦的“将将”之能。汉高祖三年(前204),项羽围荥阳,汉王恐忧,谋士郦食其向汉王献策,复立六国,共同攻楚。张良否定此计,并借用刘邦筷子筹划说:“今复六国……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陛下与谁取先天下乎?”[17]361刘邦遂不用郦食其之策。汉朝建立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萧何主要功劳在于后勤补给。楚汉相争,长达五年,刘邦数次失利,遭遇极大困难。萧何安定关中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转运粮草、兵源,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7]354第四,项羽不用范增,刘邦诛杀功臣韩信、彭越,这两件事都说明领导者和被领导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利益不一致等情况,进一步说明,领导者对驾驭整个战略集团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战略构想持有怀疑态度。因此,从驾驭上下关系讲,“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7]84。
(二)刘秀“推赤心,用柔治”,得“将将”之道
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的行为,使唐太宗和李靖都对汉高祖“将将”统御能力提出质疑,表明领导者并没有很好地驾驭被领导者。如果领导者能有效地控制驾驭被领导者,向共同的战略目标前进,就不会有“诛杀功臣”这样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这就有赖于领导者高超的战略驾驭能力。
东汉光武帝以柔道得“将将之道”。柔道不仅是刘秀人生态度,也是他治国平天下之道。42年,刘秀宴请乡亲,婶娘们相与说:“文叔(刘秀字)少时谨信,与人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9]18唐太宗和李靖对光武帝柔道战略十分推崇,他们认为,东汉光武帝用柔道治国,真正地掌握了统御的精髓。唐太宗问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李靖回答说:“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邓、寇未越于萧、曹,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7]84唐太宗之问暗含了对光武帝“将将”的肯定,李靖的回答充分解释了汉光武帝得“将将之道”的原因。
一方面,王莽势力不下于项羽,刘秀集团核心人才邓禹、寇恂的能力并未超越刘邦集团核心人才萧何、张良。两相比较,突显了刘秀卓越的统御能力。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高帝出关以后,仅一项羽,夷灭之而天下即定”,而光武争天下时,只以河北为根据地,群雄环侍;“高帝之兴,群天下而起亡秦”,皆知秦朝灭亡是不可逆转之时代大势,而光武乘人心思汉而起,当时刘玄、盆子、孺子婴、永、嘉等等都是汉室之胄,都有继承汉室江山的法统,刘秀只是这些刘姓宗室的一名成员而已;“难易之差,岂不远哉?”[20]129-130王夫之高度评价刘秀建立东汉的功绩说:“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20]130以此推之,可知光武统御天下能力之高超。
另一方面,刘秀统御能力以“推赤心,用柔治”为战略驾驭基本原则。这首先体现在保全功臣上。刘秀对待开国功臣十分优渥,解除他们的兵权后,保障他们生命的安全,给予他们丰厚的财富和崇高的名誉,“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19]24,真正做到了以“至诚”之“柔道”对待功臣。其次也体现在对待敌人上。刘秀为更始政权萧王时与铜马农民军作战,铜马投降后,投降者对刘秀如何处置他们感到担心。刘秀命令军队归营,亲自乘马进入铜马营中检阅,因而投降的铜马军士互相谈说:“萧王推心置腹,开诚相见,哪里能够不效命报答呢?”李靖对刘秀此举亦是十分肯定。李靖指出,他讨突厥,统御番汉军队,也是推心置腹,大公无私,才使战争胜利推进。“臣顷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7]65这和刘秀“推赤心,用柔治”是一样的。
《问对》引用了众多古典名著阐述其战略战术思想。其中,通过对历史典籍,如《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的相关案例以及唐朝建立历史中诸多案例征用证明其战略战术思想,成为《问对》文本叙述的一大特征。毛元佑指出:“综观《问对》全书,它虽然没有从总体上背离中国古代哲理谈兵的军事文化传统,但却结合了历代不少战例来阐述兵学哲理,由此而构成了不同于其他六部兵书的特点。由于作者能结合具体战例来阐述军事理论问题,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也更加令人信服。这种方法,把传统的军事理论研究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是对古典兵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21]552因此,对《问对》进行研究时,必须要对《问对》历史思维有充分了解,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和诠释《问对》战略战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