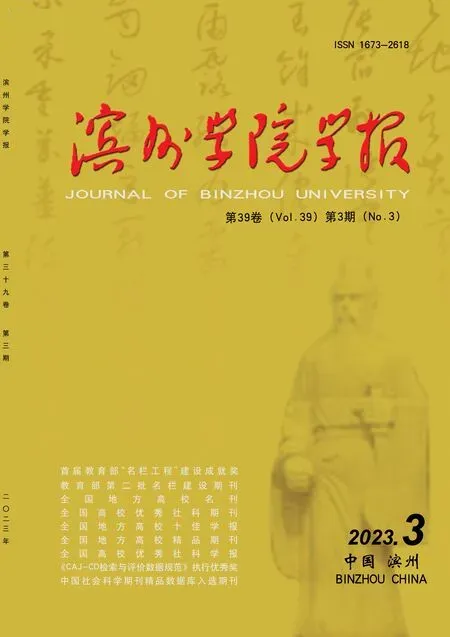明代《孙》注第一声
——刘寅《武经直解·孙子直解》的特点及成就
梁娟娟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刘寅的《武经直解》是明代武经的最早注本,他也是第一个为《武经七书》中除了《孙子兵法》外其他六书作注释的人。关于刘寅的生平,因史料阙如,所知不多,其《武经直解·序》中有一段话:“拱辰名寅,山西太原崞人,其先君菊斋处士尝以道学自任,间能谈兵,当元末教授乡里,入国朝,拱辰登洪武辛亥科进士,累历显任,并著能声。”[1]260《明史》不为刘寅立传,从这段序文中仅能略见其生平一二。刘寅,字拱辰,元末明初山西太原府崞县(今山西原平)人。其引用书目云:“张贲注。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2]33他在《九变篇》的注文中说:“愚十八九岁时,遭元季抢攘,尝从先人授读。亡其书(指张贲《孙子注》)四十余年,今尚能记其大略。”[2]236可知,刘寅年少时为避元末战火曾避居山中,跟随先人菊斋处士学习,并研读兵法。洪武四年(1371),刘寅中进士,其为官生涯如何,除了上文的“累历显任,并著能声”之外,未见其他记载。其著述除了《武经直解》,还有《集古兵法》一卷,已经亡佚。
一、《武经直解》的修纂
《武经直解》于洪武三十年(1397)动笔,其时刘寅已过知天命之年。“越明年稿就,又明年书成,凡二十五卷、一百一十四篇,总若干万言,题曰《武经直解》”,成书之速犹如神助,应与刘寅半生浸淫兵法成书在胸密切相关。其《武经直解·自序》直言写此书的目的有三:一是适应现实需要,响应统治者的号召。“洪武三十年岁在丁丑,太祖高皇帝有旨:俾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期试用。”明初面临的战争隐患不少,朱元璋居安思危,重视武备,要求军官子孙学习兵书,以为国家培养武备人才。二是补《武经七书》之不足。当时,《武经七书》诸本,除《孙子兵法》外,“《吴子》以下六书无注”,《吴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书均无注释,不便于传习研读。三是订正讹误,梳理观点,纠正时下版本的诸多问题。明初流传的《武经七书》“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2]21-22,《孙子兵法》一书的多种注本,各家说法不一,甚或互相矛盾,划一各家学说,有助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
《武经直解》二十五卷,包括《孙子》三卷、《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李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三略》三卷、《六韬》六卷;《明史·艺文志》载二十六卷,是将附录一卷列入。刘寅为注释《武经七书》,作十条凡例:
一,《武经直解》为初学者作,若失之略,恐未能晓,不若不解耳。一,七书次序,宋国子司业朱服校定,先孙、吴,而后《六韬》,亦未知何义,今姑因其旧耳。一,《孙武子》旧注互有得失,今选其理明而辞顺者取之,其不切于理而辞讹舛者,姑置之耳。一,《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其余篇内一句一字之误,并说见本条下。一,《汉书·艺文志》云:“《吴孙子》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篇”。今《孙子》止有十三篇、《吴子》止有六篇,恐是后人删而取之,篇章只依旧日次序,并不改易。一,《吴子》以下六书,自来未见有注,幼时所读七书并无差误,凡云旧本者,皆据幼时所读七书而言也;凡云今本者,皆指近来书肆所刊讹传讹者而言也。一,《尉缭子》乃商鞅之学,儒者所不谈,然中间亦多有可取者,不以人废言可也。一,《问对》中有阙误处皆据《左传》及《通鉴纲目》正之。一,《三略》本《太公遗书》,而中间亦有黄石公之说,今但一二处明之,余在学者例推耳。一,《六韬》传于周史,中间不无傅会之说,已于《文伐》篇内辩之,其余尚多疑似者,后学择焉可也。[2]29-31
由此凡例可以看出,刘寅作《武经直解》时侧重这样几项工作:第一,用浅显的语言详细解析武经七书。由于受众是初学者,因此用了“直解”的形式,用常人通晓易懂的语言解析兵书;为了避免解释不清,注解本着详细的原则;同时,还佐以相应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第二,参照古本,校正当时流传的《武经七书》的错误。其中《孙子兵法》旧注颇多,刘寅选取曹操、杜牧、张预、张贲四家之言,校勘方面继承了张贲[3]410-411的成果。第三,辨析真伪,疑者从疑,能明确辨别真伪的皆一一辨明,不能辨明存有疑问的录入文中,让后学自己思考,不轻易做出判断。
二、《孙子直解》的体例及校注内容
在体例方面,《孙子直解》的体例与其他六书不同,《吴子直解》等书多采用段注,《孙子直解》则采用句注,每篇篇名之后有题解,概括本篇主旨或梳理与前篇的内在关系,文中每句之后有解释,解释详细,引经据典,间有自己的看法或实例说明,有些篇末有作者的深思或阐发。
在《孙子兵法》的校注方面,刘寅主要侧重了如下四项工作。
第一,“讹舛者稽而正之”,即校勘,参照旧本校订当时流传版本中的错误。
如《九地篇》中,《武经》本、“十家注”本皆作“投之无所往,则诸刿之勇也”,刘寅注曰:“投之死地而无所往,故所向皆有专诸、曹刿之勇。专诸,公子光使刺吴王僚者。‘刿’,当作‘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执匕首以劫齐桓公者;若曹刿乃智士,非勇士也。”[2]314“曹刿”应为“曹沫”,首发此意者是南宋的张预,他提出“刿当为沬”之说,却未做仔细解释。刘寅重审此说,理由是:曹刿论战中的曹刿是知理有谋的智士形象,挟持齐桓公的曹沫才符合此处的勇士形象。虽然目前学术界认为曹刿与曹沫是同一个人[4-5],但因史书记载的不同,两人的事迹截然不同,刘寅改“刿”为“沫”更符合《孙子》原文的意境。再如“是故,方马埋轮不足恃也”一句,十一家注中,曹操注曰:“方,缚马也。埋轮,示不动也”。其他如李筌、杜牧、陈皞等人的注释都类似。刘寅却言:“或曰:‘方’,‘放’字之误也,言放去其马,埋轮于地,辕不得马而驾,车不得轮而驰,军士尚且奔北,散乱而不一,此放马埋轮之所以不足恃,以为不散之术也。”[2]316经此解释,“方”在此句中的意思也确实更为通顺。
又如《用间篇》有言:“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其中“乡间”《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皆作“因间”,刘寅注曰:“此五间之目也,旧本‘因间’作乡间,今从之。下同。”[2]354“下同”就是将下文中的“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中的“因间”依据旧本改为“乡间”。
第二,“脱误者订而增之”,即调整、校订《孙子兵法》的脱漏简。参照张贲的旧注,刘寅调整了《军争篇》《九变篇》《九地篇》的错简。《军争篇》调整错简两处。一是在“不动如山”之后,注曰:“愚按:张贲注本此句在‘难知如阴’之下,‘动如雷震’之上”。显然,这种调整是非常合理的:这几句隔句为韵,“林”“阴”“震”押韵,而作“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也恰好相互为文,二者映衬。二是在“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之下,刘寅注云:“此本《九变篇》文,脱简在此,下文乃详辩之”。[2]223-235
《九变篇》篇题题解之后,刘寅申明调整错简的重要性,曰:
愚按:此篇简编错乱,前人多因而傅会其说,惟张贲己能改而正之,其本刊行于世。……愚非敢佞于张贲而逆于牧、预诸公也,顾其理直与不直耳。或者曰:有一句解一句,何必改正。若如此说,《大学》《中庸》迷于《礼记》,程、朱不必表而出之,《尚书·武城》简编错乱,蔡氏不必订而正之。若直依旧说,目下可以欺人,其如识者何?后之君子宦游中国,必有得张贲注者,方信吾言之不妄也。[2]236-237
可见,在调整脱漏简方面,刘寅继承了张贲注的成就,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用“理直与不直”来判定调整是否合理。“据考现存各家《孙子注》,研究和调整《孙子》错简的,张贲是第一人”[3]410,由于张贲的《孙子注》并没有流传下来,刘寅的校订工作尤其具有学术价值。
《九变篇》中刘寅调整了两处错简。一是在“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之后:
愚按:杜牧、张预诸家注皆以此五者为“九变”之事。殊不详“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四句为《九地篇》文,乃强为之说曰:《九变》而止陈“五事”者,举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说“九地之变”唯言“六事”者,亦陈其大略也。又云:《九变》即“九地”之变。此言诚误后学。盖“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九地之变”者,遇“九地”而处之有变法也。两篇主意不同。张贲注:以上篇“高陵勿向”以下八句通此篇“绝地无留”一句共为“九变”,甚是有理。予姑从其说而解之。学者详焉可也。[2]237-238
二是在“绝地无留,此用兵之法也”句后,注曰:
“无”张贲作“勿”,盖“勿”者,禁止之词也。凡遇危绝之地,慎勿留止,若留止而不行,恐为敌人塞其险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备耳。绝地如所谓“绝涧、天井、天罗、天陷、天隙”之类是也。此以上九者,乃用兵之变法也。[2]244
《行军篇》调整错简一处,“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注曰:“张贲云:此句当在‘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之下。”[2]264经过修改后,原文变为:“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经此修改,语意更完整,后文也更通畅。
第三,“幽微者彰而显之”,即探究、挖掘孙子思想的真义。对一些重要的兵学问题和用兵原则,刘寅或结合战例或阐发议论,都能做出颇有见地的探讨。如在《军争篇》“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句后,注曰:“愚谓:孙子论举军争利有损上将之失者,谓不可全军而往,劲者在先,疲者在后,力不齐而为敌所乘也。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犹能取胜者,何哉?盖是时金刚既败,众心以沮,迫之则河东易平,缓之则别生他计。故兵有形同而事异者,不可执一观也”。[2]218-219孙子说日行三十里,只能有三分之二的士兵能到达目的地,战斗力会受到影响。刘寅用唐太宗日夜兼行二百多里却大败宋金刚的例子,说明孙子的本义是揭示战法的灵活性而非绝对性,“兵有形同而事异者,不可执一观也”。这一解释把孙子灵活用兵的精髓阐释出来,说明刘寅对孙子思想的认识和把握极为到位。
又如“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句后,注曰:“气者,三军之众所恃而战也,彼既夺其气,岂能与我战?心者,三军之将所主而谋也,彼既夺其心,岂能为之谋?”并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夺心”“夺气”。春秋时曹刿论战,是“阵久人倦而夺其气”;东汉时寇恂破苏茂,是“诳以声势而夺其气”;三国时张辽守合肥抗孙权,是“以勇战而夺其气”;北周宇文宪拒北齐段畅,是“以名位而夺其心”;唐朝薛仁贵抗击突厥,是“示以形貌而夺其心”。在敌我之间的夺心、夺气中,要谨防己方被对方夺心、夺气,“然必能守吾之气,使锐盛而不衰,然后可以夺彼之气也;能养吾之心,使闲静而不乱,然后可以夺彼之心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2]228-230。用易懂的语言将孙子这一带有辩证色彩的思想解释得清晰明了。
刘寅在《地形篇》最后讲:“此篇言地形,而中又以胜败言者,盖恐后世泥胜负之理于地形,而不尽人事之当为也,故于地形则曰‘兵之助’,料敌制胜则曰‘上将之道也’。孙武之意深矣。”[2]297-298孙子认为,地形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用兵不知地形,则战守失利,故地形为兵之助”,地形很重要但只是战争的辅助因素,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计险厄、远近为上将之道,学者不可不察也”[2]281。刘寅的解释把战争中“地”与“人”的关系讲清了,符合孙子思想的本义。
第四,“傅会者辨而析之”,即厘定各家言论,有定见的划一观点,存疑的则收录观点供读者思考。如对《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句中的“将”,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读作平声,有人读作去声。如张预就读作平声,“谓将者解也”,认为“孙子以此解,激吴王而求用,言吴王将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刘寅认为,若作此解释,“非忠厚之心,恐失孙子本意”。孙子作《孙子兵法》,“将欲传之后世为众人法耳,不应中间用此数语解,激吴王而求用”,这不合常理。所以,刘寅参考了张贲的注解“前‘将’字,指大将而言,此‘将’字指偏裨之将而言也”[2]119-121。刘寅结合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和前后文的意思判断,此处的“将”应为去声,意为裨将,而非为平声;前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将”为大将。大将的命令裨将执行得好,战争就会取胜,这样的裨将就是堪用的人才,“留之”;反之,如马谡不能很好地执行诸葛亮的命令,导致街亭失手,就非可用之将才,就可“去之”。这一解释既联系了前后文,还兼顾了当时的现实环境,非常有道理。
《虚实篇》“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一句,张贲作“诈之而知动静之理”,刘寅认为“作”比“诈”合适:
愚按“作”字不止激作,敌人凡有所施为皆“作”也,故杜佑引此为:候之而知动静之理。谓:远斥候,而知敌人之动静也。张贲本为“诈知而知动静之理”,谓:或诳之以言,或诱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诡道欺之,则敌之动静可知。夫两国交争,务知彼之动静,则我易为之胜。若韩信欲破赵,必先探知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言,然后敢出井陉,若不知彼之动静,不惟不可以取胜,又将自取其败耳。[2]207-208
可见,刘寅虽看重张贲的注解,却并不盲从,而是以“理直与不直”为标准判定注解是否切合孙子原意。
刘寅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其《武经直解·孙子直解》在校勘和注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明代兵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刘注《孙子直解》的特点
刘寅是明朝第一位给《孙子兵法》作注的学者,《孙子直解》校勘与注释并重,理论水平较高;且除了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之外,还没有为《武经七书》中的剩余六书作注者,而刘寅亦未见到施氏的《七书讲义》,故,他的《武经七书直解》对校注其他六书亦有开创之功。是书一经问世,即广为流传,成化二十二年(1486)李敏刊行此书时为之作序,赞称:“其注释详明,引据切当,开卷读之,不待师传而自会其意,诚兵家之宝也”[2]15。其《孙子直解》的校注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儒家之“仁义”注兵家之“机权”,带有明显的以儒释兵色彩。刘寅是洪武四年(1371)的进士,他饱受儒家经典熏陶,儒学的浸润是深入到骨子里的,在注解兵书的时候就自觉地以儒家理论解析兵学思想,使兵学理论处于儒家思想的统领下。在“序言”中,刘寅自己就说注释兵书的指导思想是:“取其书(指《武经七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微者彰而显之,傅会者辨而析之”。并“取儒家诸书、先圣先贤之所著述,有切于兵法者,编为附录”[2]21-22,即摘选《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学经典中切合兵法的内容,编为《兵法附录》一同收入《武经直解》中。刘寅认为:“《武经》言仁义、礼智、道德、忠信与儒家无异,但用之者自有大小、浅深、精粗、广狭不同,岂别有所谓仁义、礼智、道德、忠信者哉?”[2]34在他看来,兵家的“言仁义、礼智、道德、忠信与儒家无异”,区别在于所用之人不同耳,正如“李敏序言”中所说“是书也,岂徒专为权谋谲诈?顾人用之何如耳。汤武用之,则为仁义之师;孙吴用之,则为谲诈之术。仁义得之愈久而愈昌,诈术取之随得而随失”[2]18。此论固然值得商榷,却明显表现出刘寅、李敏等人以儒为宗的思想倾向。
《孙子直解》的注释中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随处可见,如《始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一句后,刘寅注曰:
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悌、忠信,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与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可与之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昔武王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是与上同意也;纣有亿兆人,离心离德,是不与上同意也。荀卿曰:“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而覆胸臆,斯可与同死同生也。”[2]111-112
孔子提倡的礼乐、孝悌,荀子提倡的仁义之兵,都被用来阐释孙子的“道”;并佐以武王得道、得民心,最终得天下,纣王失道、失民心,最终失天下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武经直解》“序言”中明确指出:“其书中论道德、仁义、忠恕、敬信,皆儒者之范模,辨尉缭之非,明李靖之失,折商英之虚无以阐《三略》《素书》之真伪,抑周史之傅会以昭文王、太公之本心,辟邪说、拒彼行,存天理遏人欲,又皆儒者之权度。”[1]260-261以儒家的济世救民情怀解析兵家的某些思想当然不够准确,却是如刘寅这些儒家学者在跳脱不出儒家束缚时对兵学的折中,亦反映出在儒学的全面笼罩下兵学独立地位丧失,不得不置于儒学统领的尴尬处境。
第二,校勘中广泛使用理校法。理校法是校勘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分析、综合、类比等手段,据理推断古书中的讹误。刘寅在《孙子直解》中校订了流传版本的一些错误,其校勘的依据就是“顾其理直与不直耳”,实际就是理校法。
《九地篇》言“诸刿之勇也”,刘寅认为“刿”当为“沫”,春秋时曹沫执匕首挟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以勇力著称,是勇士;曹刿在齐鲁长勺之战中因其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以智克力,一战成名,是智士。上古音“刿”“沫”二字皆入物部,“刿”当是后人传写致误,所谓同声而致误也。
又如《火攻篇》言“昼风久,夜风止”,刘寅引用张贲之言,认为:“张贲云‘久’字古‘从’字之误也,谓白昼遇风而发火,则当以兵从之;遇夜有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反乘我也,即上文‘可从而从,不可从而止’之义。若作‘久’字,甚无意味”。实施火攻要在放火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动兵力配合,毕竟放火只是辅助手段,关键还得靠兵力的配合,只点火而不出兵是无法取胜的。结合上文“可从而从,不可从而止”推断,此处若作“久”,意为白天风刮久了,晚上就会停止,不仅逻辑不通,与上文也联系不起来。若作“从”,白天视野开阔,顺风放火,军队可以跟进攻击;夜里顺风放火,为免敌人有伏兵,军队不能随之发起进攻。如此看来,这一解释是非常有道理,“昼风从,夜风止”比“昼风久,夜风止”更为贴切。
再如“水可以绝,不可以夺”一句,刘寅言:“张预曰:‘水止能隔绝敌军之前后,取一时之胜,然不若火能焚夺敌之蓄积而使之灭亡也。’张预云:‘水可以绝,火可以击。’谓水可以隔绝人之军,若韩信决壅囊,水大至,使龙且军分而为二,因奋击大败之;火可以焚夺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绍辎重,绍因以败亡,是也。但‘不’字为‘火’字之误耳”[2]343-345。经此修改,文义更加通畅。
第三,注意文章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刘寅在注释时非常重视各篇之间和上下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注释或联系前后文、或联系前后篇,解释通透。如《虚实篇》“故曰胜可为也”一句后,注曰:
吾故曰兵之胜可为也,《军形篇》曰“胜不可为”者,以敌之有备者言也,敌若有备,故胜不可为。此曰“胜可为”者,以越(接前句: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必不能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取胜在我,故可为也。[2]203
《形篇》讲“胜不可为”,《虚实篇》又讲“胜可为”,似乎前后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是因情境不同,故结论不同。
在《九地篇》开篇,刘寅解释此篇与《地形篇》的不同时讲:“九地者,谓地之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也;此篇言九地。因兵所至之地而势有九等之别也。上篇盖言地形之常,此篇盖言地势之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而为二也”[2]298。两篇都是谈地形,但各有侧重,《地形篇》谈自然地理,《九地篇》谈兵势地理,故分为两篇。
刘寅非常注重从整体上解析孙子思想,在《用间篇》最后,刘寅言:
愚谓:孙子首以《始计》而终以《用间》,盖计者,将以校彼我之情,而间者又欲探彼之情也。计定于我,间用于彼;计料其显而易见者,间察其隐而难知者;计所以定胜负于其始,间所以取胜于其终;计易定,而间难用。故曰: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皆难之之意也。孙子于篇终言之其有旨哉。[2]365
将首篇《计篇》的知彼之情与末篇《用间篇》的用间结合起来,揭示了孙子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将十三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第四,对待前人的观点上,是则称是,非则称非,疑者从疑。《孙子直解》一书中刘寅引用了魏武帝、杜牧、张预和张贲四家的观点,对于前人的观点,刘寅认为正确的就继承下来,如张贲校勘的《军争篇》和《九地篇》的错简,刘寅认为很有道理,就沿用了其观点;但前人的有些看法,刘寅认为不正确的,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虚实篇》“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一句,杜佑作“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张贲作“诈知而知动静之理”,但刘寅认为原文“作知而知动静之理”最准确,“作”就是探查敌情,就是“知彼”,并非只有通过“诈”这一途径,故用“作”比“诈”合适。
《九地篇》“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句后,刘寅注曰:“此专言‘为客之道’,故于九地中拈出衢、重、轻、围、死五者明之。杜牧、张预谓九地而止言五事,举其大略者。非也”[2]323。
对于前人注解中不能判断正误的,刘寅通常将观点列出,以便读者自己思考。如《虚实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一句中的“吾”,张预认为“‘吾’乃‘吴’之误也,言以吴之兵度越之兵虽多,无益于胜”。刘寅认为此解“亦通”[2]203。《军争篇》“故军争为利,众争为危”一句,张预解释为“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刘寅认为原文本无“智者”“庸人”字,“其说未知是否”[2]216。《行军篇》“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一句后,刘寅注曰:
一本作“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粟马”谓以粮谷秣马,“肉食”谓杀牛马飨士;“军无悬缻”,悉破之,示不复炊;“不返其舍”,昼夜结部伍,是皆穷寇,必欲决一战耳。未知是否。[2]275-276
不主观臆断、不无的放矢的注解态度,使得《孙子直解》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第五,大量引用战例,以更好地解释或佐证孙子的观点。事实胜于雄辩,兵法理论最终要回归到战争实践中,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刘注善用战例,让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鲜活。如在《始计篇》中就用了42个战例来解析孙子原文,这些战例的使用方式灵活多样,有的详细介绍分析,有的罗列几个相同的例子类比,还有的用正反对比的方法,加深读者对孙子某一思想的认识。如在解释“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一句时,刘寅详细分析了韩信的井陉之战:
韩信知赵王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计,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陉,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又选二千人,人持一赤帜萆山而望赵军,戒曰:“若赵空壁逐我,则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明日,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此因利制权之事也。
对“兵者,诡道也”一句解释时,则罗列了四个类似的例子,“如栾枝曳柴扬尘、孙膑令军减灶、田单神师火牛、韩信囊沙壅水”,并未展开详细论述。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时,则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方式,引用了周武王虽仅“有臣三千”却“同心同德”,故而能战胜“有亿兆人”却“离心离德”的商纣王。在解释“主孰有道”后,对比了汉高祖和项羽入关后的不同表现:“汉高入关,秋毫无犯,秦人大喜;项羽入关,杀子婴,烧宫室,掠妇女宾货,而东秦人大失望,此汉高所以终胜,而项羽所以终败也”[2]122-123。通过对比,孰胜孰负一目了然。大量战例的运用不仅为孙子理论提供了战例依据,还方便了学者的理解和阅读。
四、《孙子直解》的版本及影响
自宋代《武经七书》正式列入学馆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在注释方面,除了《孙子兵法》的注家代不乏人,《吴子兵法》等其他六书除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外,史不见载。刘寅的《武经直解》遍注七书,在《武经七书》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加之其在注解过程中的一些良好做法,一经刊出即备受时人好评。在成化、嘉靖、万历、崇祯等时期各有刻本,主要版本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赵英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现藏重庆北碚区图书馆;嘉靖年间刻本十九卷,现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万历九年(1581)莫与斋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内含清钞本《吴子直解》,现藏南京图书馆、重庆北碚区图书馆;崇祯十年(1637)翁洪业刻张居正增订十二卷本,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日本宽永二十年(1643)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1933年上海军用图书社、江苏省图书馆影印丁氏八千卷楼藏明万历九年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等地。
刘寅的《武经直解》解析详细,用语通俗,对于研读兵法或从事兵法研究,都大有助益,因此时人对此评价很高。成化年间刊印是书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敏为之作序,曰:
其注释详明,引据切当,开卷读之,不待师传而自会其意,诚兵家之宝也。……此书一出,则武弁辕门之家,英豪俊髦之士,朝讲夕读,自然增其智识,长其谋略,名臣良将接踵而出,守边疆于永固,保宗社于无穷矣。[2]15-17
他指出此书的优点是注解详细,引证切当,语言通俗易懂,将士和爱好兵法的学者自己就可以读懂。
万历刻本刊行时,何起鸣为之作序,言:
是书间出幻化,即不尽轨于正义,大较战守攻围、离合、奇正,了然指掌矣。……是书也,盖欲习者悟其机于迎刃转圜之间,以储干城腹心之选,匪直资若曹齿颊谭也。嗟乎,喜建竖者,儒吏抵掌乎韬钤,斗藻缋者,武吏饰名于觚管,比皆越俎治矣。文武攻其业,以为国家彪炳中外,庶几答百世之遇。是书可少之哉?[2]9-12
他认为《武经直解》在有关战争指导方面的攻守、分合、奇正等原则上解释详尽,无论是儒者还是将吏,要掌握用兵的基本问题,都不会舍弃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