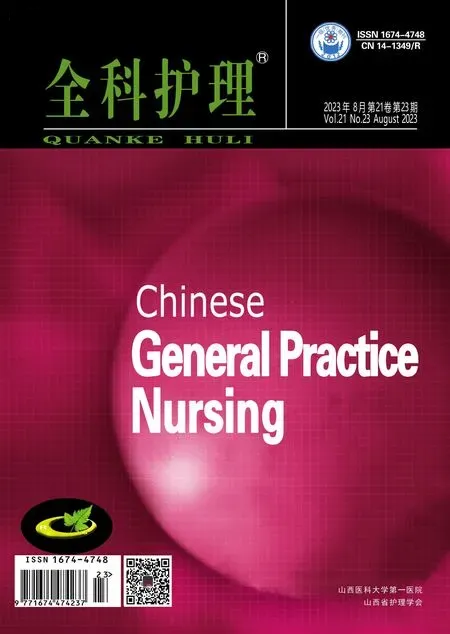癌症病人孤独感研究进展
郑晓娜,魏亚楠,韩智培,田亚杰,荆 华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癌症报告显示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 929万例,死亡病例996万例[1]。美国癌症统计报告及陈万青教授团队估算结果显示,2022年,中国和美国分别约有482万例和237万例新发癌症病例,以及321万例和64万例癌症死亡[2]。癌症的确诊、疾病的治疗、不良反应的产生等一系列应激事件,易让病人出现不良心理体验,影响其身心健康。其中,孤独感就是癌症病人常见的负性情绪之一[3]。孤独感会给病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加剧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反应,降低睡眠质量,更甚者会让病人产生自杀意念和行为,降低其生活质量[4]。积极开展癌症病人孤独感相关研究,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目前,国内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多是针对老年人群[5-6],而对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关注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癌症病人孤独感的概念、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减轻癌症病人孤独感提供帮助,引起医护工作者的重视,为临床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孤独感的概念
孤独感的概念是以心理社会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Weiss[7]在其著作“Loneliness: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中提出,孤独感并不是由孤身一人引起的,它是一种负性主观体验,是对缺乏某种特定社会供给的反应。De Jong-Gierveld[8]认为孤独感是指由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缺乏而体验到的不愉快,其严重程度取决于个体对自己实现新关系或改善现有关系能力的看法。Peplau等[9]提出,孤独是一种主观的、令人痛苦的负性体验,在一个人的社交关系中当个体期待的社交关系和实际的社交关系间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此情绪。朱智贤[10]提出孤独感是人处在某种陌生、封闭或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孤单、寂寞和不愉快的情感。李传银等[11]提出孤独感是个体期望的人际交往与实际存在落差时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表现为孤立、寂寞、无助等不良情绪反应和精神上的空虚感。虽然目前孤独感概念并未统一,但孤独感可认为是癌症病人在疾病体验过程中,由于情感、信息、经济等方面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
2 孤独感对癌症病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孤独感影响着癌症病人的心理健康、躯体健康、生活质量、认知功能等。一项研究对633例儿童癌症幸存者进行了为期2.5年的随访调查[4],发现孤独感是焦虑症状和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更甚者孤独感可预测2年后更严重的焦虑症状和自杀意念。Jaremka等[12]发现孤独感是疼痛、抑郁和疲劳的危险因素,通过对115例癌症病人及115例非癌症病人进行跟踪随访,随访2年后发现癌症病人孤独感高于非癌症病人,且与非孤独癌症病人相比,孤独癌症病人经历了更多的并发疼痛、抑郁和疲劳。Hyland等[13]对肺癌病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孤独感水平越高,其抑郁症状越严重,生活质量越差,且孤独感在社会认知与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Jaremka等[14]对乳腺癌病人的孤独感及认知功能进行测试,发现孤独的病人其注意力和记忆力较差。由此可见,孤独感与癌症病人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是癌症病人不良健康状况的预测因子,早期识别干预孤独感对癌症病人来说尤为重要。
3 癌症病人孤独感的评估工具
3.1 癌症孤独量表(Cancer Loneliness Scale,CLS)
是Adams等[15]于2017年研制的用于评估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单维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由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不计1分,总是计5分,总分为7~35分,分值越高表明病人孤独感越高。崔海娟等[16]于2018年将其翻译汉化,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
3.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感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UCLA)
该量表由Russell等[17]于1978年研发而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6。由20个条目组成,包括11个正向和9个反向计分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未计1分,经常计5分,总分越高表明病人孤独感程度越高。1996年Russell[18]对此量表进行修订,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94。该量表已被多个国家翻译使用,广泛应用于学生及癌症病人等[19-20]。但该量表并不是针对癌症病人的特异性量表。
3.3 De Jong Gierveld孤独量表(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DJGLS)
该量表由De Jong-gierveld等[21]于1985年编制而成。2014年Buz等[22]将其翻译为西班牙版本,信效度较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89,并得到广泛应用。包括情感孤独维度(4个条目)和社交孤独维度(7个条目)2个维度。中文版DJGLS量表由杨兵等[23]翻译汉化,Cronbach′s α系数为0.82,重测Cronbach′s α系数为0.889。有研究将此量表应用于癌症病人孤独感的调查中[24],但目前国内未见将其应用于癌症病人中。
3.4 癌症相关孤独感评估工具(Cancer-related Loneliness Assessment Tool,C-LAT)
该量表由Cunningham等[25]于2017年研发而成,用于测量已完成治疗的成年癌症病人的孤独感。量表由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各10个条目,第二部分量表各条目与第一部分量表各条目相匹配。第一部分询问癌症病人自诊断以来在人际关系中感知到的缺陷以及这些缺陷的来源,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 “强烈同意”计1分,“有点同意”计2分,“有点不同意”计3分,“强烈不同意”计4分。若选择3分或4分,则进行第二部分答题。第二部分采用视觉模拟尺评估面对所感知的缺陷及其来源时,癌症病人的烦恼/痛苦/不愉快的程度。视觉模拟尺两端分别“0”分端和“6”分端,“一点也不”计0分,“尽可能多”计6分。Dahill等[26]用此量表评估了头颈癌病人的孤独感。目前国内尚未引进汉化此量表,其在国内癌症病人中的信效度需要进一步验证。
4 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4.1 社会人口学因素
癌症病人孤独感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居住状态、文化程度等。有学者发现,年龄越大的鼻咽癌病人其孤独感越严重[27]。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病人对手机等通讯设备较为陌生,从而导致其与外界沟通交流减少,增加了孤独感。但也有研究发现老年癌症病人和年轻癌症病人在确诊后孤独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24]。有关年龄对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王小梅等[28]发现文化程度低、居住在农村的女性恶性肿瘤病人,其孤独感较高。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癌症病人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疾病相关知识、压力应对技能等,可以正面应对癌症打击。相较于居住在农村的病人,县城/城市的病人更具有丰富的经济条件和资源。
4.2 疾病相关因素
疾病分期、所接受的治疗、手术类型及患病时间是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影响因素。Dahill等[26]对140例头颈癌病人进行调查,发现晚期的、接受过化疗或放疗的病人孤独程度更高。可能是因为处于疾病晚期,虽经过相关治疗,但仍对未来抱有不确定性而感到孤独。接受化疗或放疗会使病人出现恶心与呕吐等不良反应,而这种消极的症状体验也会增加病人的孤独感。学者发现与乳房再造病人相比,未乳房再造病人的焦虑水平较高、孤独感水平较高及生活质量较低[29]。乳房再造病人的自身形象未发生改变,虽有癌症的打击但相较于乳房切除术的病人来说更自信些。Darcy等[30]对癌症患儿在癌症诊断初期、诊断后6个月及诊断后12个月时进行质性访谈,发现癌症患儿孤独感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表明随着患病时间的延长,在积极治疗促进生理健康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病人心理健康的重视。
4.3 心理因素
恐惧、绝望、病耻感及社会疏离感等心理因素影响着癌症病人的孤独感。一项定性研究中,乳腺癌病人描述了他们对癌症的担忧和对死亡的恐惧,并选择了向他人隐瞒这种负性情绪[31]。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性情绪却会增加自身孤独感,认为他人不能理解自己。Pehlivan等[32]对188例土耳其癌症病人调查发现,绝望感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也有部分癌症病人因患有疾病感到羞耻而产生病耻感,减少了与他人的沟通交流,隔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进而越发感到孤独[33]。Clifton等[34]调查疫情流行期间老年癌症病人的孤独感及社会疏离感现状,发现孤独感与社会疏离感呈正相关,即社会疏离感越高孤独感越严重。
4.4 社会支持
一项针对晚期癌症病人孤独感的横断面调查显示,家庭支持与孤独感水平呈负相关,即随着病人家庭支持的增加其孤独感减轻[35]。与吕仕杰等[36]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单位,为个体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情感环境。而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功能可缓解癌症病人的心理压力,从而减轻孤独感。社会支持其范围和类型是多样的,包括朋友支持、组织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等。因此针对癌症病人的孤独感,可从多方面提供社会支持,如亲朋好友的陪伴、医护人员提供疾病相关信息的支持、社会公益团体的爱心帮扶及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等。
4.5 其他影响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疫情流行的大环境、社会福利、痴呆及病人是否知晓自身病情等也影响癌症病人的孤独感水平。一项纵向研究发现,疫情流行期间癌症病人的孤独感有所增加[37]。Ashi等[38]发现有社会福利的病人和有痴呆症状的病人,其孤独感水平较高。孤独感也与病人是否知晓自身病情有关[21],可能是因为当病人知晓自身病情时会产生对疾病复发的恐惧或对死亡的恐惧,而增加了自身孤独感。
5 癌症病人孤独感的干预措施
5.1 正念疗法(mindfulness therapy)
正念疗法起源于佛教,由Kabat-Zinn[39]将其引入心理学领域,可引导个体专注于当下从而减轻自身压力,包括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及辨证行为疗法等。Creswell等[40]对40名老年人进行为期8周,每周1次,每次120 min的正念减压疗法干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孤独感水平较前有所降低,睡眠质量有所提高,且可以下调NFκB表达,降低C反应蛋白和白细胞介素-6。由此可见,正念疗法干预对孤独感十分有效,可将正念疗法应用于癌症病人中,以减少其孤独感水平。
5.2 同伴支持(peer support)
同伴支持是指具有相似经验的个体一起就某个主题互相分享、交流和鼓励,以得到情感或信息支持等[41]。一项关于334例带有未成年子女的癌症病人孤独感的调查[42],探讨了孤独感与使用线上同伴支持频率的相关性,发现频繁寻求线上同伴支持的受试者,其孤独感程度越低。由此可知,同伴支持能够让个体得到有效的情感支持,在面对挫折困难时不再感到孤身一人,能让其以足够的勇气应对。
5.3 支持-表达性团体疗法(supportive expressive group therapy)
支持-表达性团体疗法是指采用团体干预的方法,促进个体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感受,重建心理防线,从而促进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43]。Tabrizi等[44]开展了一项支持-表达性团体疗法随机对照试验,共12次团体会议,每周1次,每次90 min。通过对干预前、干预后及干预结束8周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孤独感、希望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比较,发现干预组病人的孤独感水平有所降低,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且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支持-表达性团体疗法对癌症病人孤独感等负性精神心理状态具有积极影响。
5.4 意义疗法(logotherapy)
意义疗法由维克多·弗兰克尔创立,是指协助个体从生活中领悟生命的意义,明确生活目标,从而实现积极乐观生活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意志自由、意义意志和生命意义[45]。Heidary等[46]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将晚期癌症病人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进行每周10次每次2 h的意义疗法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病人的孤独感和死亡焦虑显著降低,表明意义疗法对癌症病人的孤独感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6 小结
孤独感对癌症病人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但目前国内关于癌症病人孤独感的研究有限,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癌症病人孤独感开展相关研究。可结合国内文化背景,开发构建符合我国癌症病人孤独感的评估工具。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可依据我国癌症病人孤独感现状,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