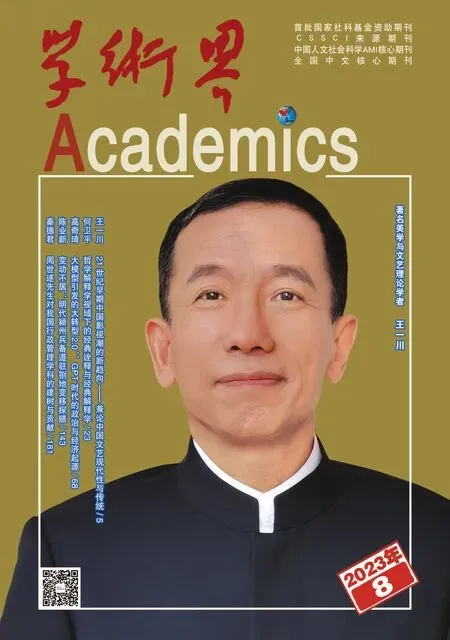冷战结束以来波兰侨胞政策评析
杨友孙
(上海政法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 201701)
随着交通和通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远离祖国发展。据2020年联合国估计,世界上至少有2.81亿人长期定居在远离祖国的他乡。〔1〕这仅仅是指近几十年离开家乡的移民及其后代,不包括历史上移居他国并成为少数族群的群体。随着侨居国外的群体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受到政治学、民族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
对于移居国外的群体,中文中一般使用“跨国族群”“离散族群”“离散群体”“侨胞”“侨民”等措词。英文中虽有不同称呼,但最常见的是“diaspora”。该词源于希腊语,原意为“撒下种子”,指经历过强迫或暴力驱逐的人群。〔2〕随后,它被用来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词含义已大幅拓展。2019年国际移民组织对“diaspora”作了如下界定: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其身份和归属感——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均由移民经历和背景塑造。他们基于共同的历史感、身份认同感或在目的地国家的共同经历,与故土及彼此保持着联系。〔3〕也就是说,“diaspora”不仅包括短期移民,也包括所有历史上移居国外但仍然保持着对亲缘国(kin-state,即最初来源国)的认同的群体;它也是“公民侨胞”与“非公民侨胞”的混合体。〔4〕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亲缘国均抱持这种广义“侨胞”概念和“大侨务”政策理念,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当前发展需要,更是藉此塑造一个“跨国空间的民族社会”。〔5〕而当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和跨境交流的便利为实施积极侨胞政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般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侨胞政策,因为它们将侨胞政策视为发展政策的工具。〔6〕然而,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侨胞视为一种“民族资产”(national asset),认为侨胞战略具有社会、文化、政治、教育、金融等层面的意义。〔7〕因此,不仅发展中国家,意大利、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实施积极的侨胞政策。
中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共性是历史上国家疆域的频繁变动,其结果之一是每个国家均有大量侨胞散落他国。在冷战期间,中东欧国家均未推出系统性侨胞政策。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再次出现大规模人口外流,给实行积极侨胞政策提供了新的动力。波兰是中东欧具有最多侨胞的国家,它因积极有力的侨胞政策,被认为是和德国、以色列并列的侨胞政策“引领国”。〔8〕
一、波兰侨胞的现状
由于多次遭瓜分、疆域多次变更的特殊历史,以及2004年入盟后大规模向外移民,波兰侨胞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据波兰外交部2015年的估计,大约有1800万至2000万祖籍波兰的人居住在境外,其中1/3为在波兰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新移民,2/3为长期定居国外的波兰裔群体。〔9〕其中,大约有250万侨胞保持着波兰公民身份。〔10〕侨胞人口与波兰国内人口占比高达50%,占世界第六位。〔11〕
波兰侨胞大规模聚居地主要是北美洲(美国、加拿大),约1100万人;西欧(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爱尔兰等),约420万人;后苏联地区(主要是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约100万人。〔12〕此外,在南美洲、澳洲、中东欧也有少量波兰人社区。在波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长期定居国外的亲人,因此,侨胞政策不仅涉及广大侨胞,也和每个波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根据侨胞的形成原因及其性质,波兰政府将其分为四类:〔13〕
1.历史性波裔少数族群:这个群体侨居国外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是因历史事件导致其家乡更换了国籍身份,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将这类群体称为“意外散居者”(accidental diasporas),他们的形成“不是由于人们越过边界的流动,而是由于边界越过人们的流动”。〔14〕波兰“历史性波裔少数族群”主要是指居住在十五个后苏联地区国家的“东部波裔少数族群”,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国人数最多。该群体的形成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在18世纪末至1918年波兰亡国期间流落东部国家的波兰人及其后代;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波兰国界西移而留在东部国家的波兰人及其后代。
2.“波洛尼亚”(Polonia)群体:“波洛尼亚”原指历史上移居美国的波兰侨胞,后来词义有所扩大,但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祖籍波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波兰移居他国的侨胞及其后代。他们通常与波兰传统及民族文化保持着联系,将自己与波兰的关系视为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但波兰语知识十分有限。广义“波洛尼亚”是指所有波兰侨胞群体,但一般不包括公民侨胞。
3.前入盟时期的移民群体: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04年之前,因政治、经济、民族冲突等因素从波兰移民国外的群体。这类移民通常与波兰保持着密切联系,仍然使用波兰语,抱持对波兰的爱国主义。他们是相对活跃并发挥着核心作用的波兰侨胞,通常是传统波兰社区和后入盟时期波兰移民之间的“桥梁”。
4.后入盟时期的移民群体:2004年5月1日,波兰加入了欧盟,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约200万波兰人移居英国、德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等西欧国家。〔15〕这些移民既懂波兰语,又懂英语或德语,与波兰的联系十分紧密,但在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也较少参与传统波兰社区的活动。这类群体大多数仍保留着波兰国籍,但正在争取入籍东道国。根据波兰法律,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公民可以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投票,这一事实导致各政党热衷于将海外波兰人问题纳入政治纲领,并在竞选期间对侨胞问题进行辩论。〔16〕
当然,也有学者对波兰侨胞进行了其他分类,其中较普遍的是三分法或二分法,即将上述第三类和第二类合并,或将前三类合并,统称“旧波洛尼亚”群体。〔17〕不过,不同类别的侨胞群体并非边界清晰,而是存在着紧密的文化、经济、家庭和个人联系。
二、冷战结束后波兰“侨胞”政治话语的兴起与政策发展
1990年前波兰并无系统的侨胞政策,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多年里,通过与苏联签订《遣返协议》,从后者分批次撤回了100多万波兰族人。〔18〕这些侨胞在1939年9月17日之前拥有波兰公民身份,由于当日苏联入侵波兰及战后波兰疆界变化而滞留在苏联境内,他们可申请返回并重获波兰公民身份。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转轨、回归欧洲的同时,也开始积极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而侨胞事务则与历史遗留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侨胞众多的波兰和匈牙利,以其积极有力的侨胞政策在中东欧引领一时之潮流。
在1991年和1993年的竞选活动中,大多数政党关注了波兰移民和海外侨胞问题,波兰人民党、民主党、基督教民族联盟、自由民主大会党、民主联盟等党派在竞选纲领中均提到了侨胞事务。例如,1991年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在党纲中呼吁:采取积极行动遣返东部国家的波兰人,为东部国家的波兰人有尊严的生活共同创造条件,向有意永久返回祖国的人全面开放,是一项爱国责任。〔19〕时任总理扬·奥尔谢夫斯基(Jan Olszewski)对海外侨胞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曾指出:“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协议中保护海外少数民族权利和利益,是波兰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波兰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援助——尤其是通过传播波兰语知识和推广波兰文化——以维护波兰利益。出于道德和历史原因,我们特别重视帮助东部的波兰人,尤其是在发展波兰语教育、满足宗教和精神需求方面。”〔20〕1997年4月通过的《波兰共和国宪法》将对侨胞的关注提高到了新高度。该宪法第6条规定:波兰应向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提供援助,以保持他们与国家文化遗产的联系;第36条规定:波兰公民在国外逗留期间,有权得到波兰国家的保护。〔21〕
随着侨胞政治话语的兴起,波兰侨胞政策逐渐强化,并出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局部到整体,从单一措施到多管齐下的过程。具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侨胞政策的局部实施阶段(1991—2004)
这个阶段出台的侨胞政策文件主要强调侨胞政策的重要性及努力方向,重点在后苏联地区国家实施,因为波兰对这些国家的侨胞负有“道德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文件:第一个是1991年11月5日波兰部长会议通过的第145/91号决议,决议包含一个名为“政府对波洛尼亚、移民和海外波兰人政策的目标和优先事项”的附件。文件指出,“维护和发展母国〔22〕和侨胞之间的多方面关系是国家的责任,国家行政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移民家庭成员、专业人士和其他社区都应致力于此。”文件要求“加强波兰民族在东道国的地位及其与亲缘国的联系”,“维护波兰人在世界的身份,普及波兰语、波兰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知识”,“为重建波兰争取国外波兰民族,并在国外建立支持波兰的游说团”,“加强与西方波兰社区合作,帮助东欧的波兰人”。此外,文件还区分了两个“波洛尼亚”群体:西部(例如德国、英国、美国)波洛尼亚群体和东部波洛尼亚群体,前者是东部波兰人和波兰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支持来源,后者则是需要重点照顾的对象。〔23〕
第二个是2002年12月10日,波兰政府出台了名为“政府与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合作计划”的新侨胞政策,确定了九项主要任务:①确保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有在居住国发展波兰文化、加强与亲缘国联系及享有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②提高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少数民族在居住国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③支持波洛尼亚的经济活动及其与波兰的经济联系;④支持年轻一代波洛尼亚活动的开展;⑤扩大波兰语和海外波兰人在国外教授和提高波兰语技能的机会;⑥为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提供有关波兰的可靠信息;⑦为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创造条件,使之尽可能广泛地获得波兰民族文化的成果;⑧要求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在与东道国利益相符的情况下,支持波兰国家和民族利益;⑨向东部的波兰人提供特别援助,包括重建波兰知识。〔24〕
这个阶段参议院在侨胞政策中发挥着较大作用,而且也掌管侨胞事务拨款。1997年3月5日,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海外波兰人、波洛尼亚与祖国关系的决议。〔25〕决议强调维护参议院在保护波兰侨胞方面的传统,恢复东部波裔群体的波兰公民身份;为了加强国内外波兰人的共同利益,拟设立“波兰日”;尊重神职人员在照顾波兰侨胞中的作用;拟建立一个数据库,主要涉及世界各地侨胞科学家、专家及其组织等。2002年4月30日参议院“关于波兰对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政策的决议”〔26〕则呼吁建立世界波洛尼亚理事会,并加强海外侨胞与祖国的联系,参议院将招募波兰国内外的地方政府组织、基金会、协会等为波兰侨胞服务。
可见,这个时期更多是为侨胞政策确定一些原则和方向,更多强调政府对侨胞的付出,但实际措施有限,主要聚焦在设立一些侨胞事务管理机构和对东部国家侨胞的遣返,侨胞事务也未上升为对外战略的重要事项。
2.侨胞政策扩展至新移民的阶段(2004—2015)
2004年波兰入盟之后,大量波兰人移居海外,使波兰成为世界上重要移民来源国之一。形势的急速发展给波兰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大政党均表现出对侨胞事务的极大兴趣。在2005年议会竞选期间,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iS)在竞选计划中提出应保护邻国的波兰少数民族,制定一项与所有散居国外的侨胞合作的方案。〔27〕左翼和民主党联盟(the Left and Democrats coalition)在其竞选计划中称移民为波兰“第十七个行政地区”,应该加强和保持他们与国家的永久联系。〔28〕
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十分重视将新移民纳入侨胞政策视野。在其积极推动下,2007年10月初,波兰政府制定了新的“与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合作计划”,〔29〕确定了四个战略目标和七个行动方向。四个战略目标为:保护海外波兰少数民族;维护国外波兰人的民族身份和民族遗产;支持国外波兰人和具有波兰血统的人回国;建立亲波兰的游说团和在国外宣传波兰。七个行动方向是:保护波兰裔人的权利和照顾新移民;加强对侨胞的教育,强化在高等教育和体育领域的措施;实施文化、民族遗产和历史政策;加强波洛尼亚媒体建设;加强侨胞组织建设;帮助东部的波兰人遣返和(向波兰)移民;推进与波洛尼亚的经济合作和波洛尼亚创业活动。可见,新侨胞战略在范围上已明显超过了过去的侨胞政策,例如提出保护侨胞权力,加强对侨胞的教育、保护民族遗产、加强波洛尼亚媒体建设等。
2011年,波兰政府再次草拟新的“与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的合作计划”,强调支出合理化;对参与实施侨胞政策的国内外组织引入竞争机制;向包括国内外侨胞事务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实体赋权。〔30〕但草案最终未获通过。2012年3月波兰外交部通过了《2012—2016年波兰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文件,〔31〕提出了以下任务:向海外侨胞和波兰人提供法律框架,以培育波兰特性和推动东道国对相关标准的尊重;确定符合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利益的外交政策目标;加强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的社会融合及政治动员;促进东部波兰人开展公民活动和新社会活动;使波兰公共媒体更具吸引力,并将其信息扩展到国外;改善现有的波兰语和波兰知识传播形式,包括在顶尖大学建立和赞助波兰语学习中心;充分利用波兰政治融资制度的变化,使资金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及侨胞;支持保护波兰海外文化遗产。
可见,这个阶段波兰已将侨胞政策提升到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中,侨胞政策力度明显强化,而且除了继续加强对东部国家的侨胞保护和吸引外,支持新移民侨胞也逐渐成为政策重心。不过,自2007年10月至2015年11月联合执政的公民纲领党(Civil Platform)和波兰人民党对侨胞事务兴趣低于法律与公正党,因此在这个阶段采取的新措施较为有限。
3.侨胞政策出现“政治化”倾向阶段(2015年之后)
“政治化”(politicization)属于政治学概念,它被认为是一个特定问题变得更具政治色彩,成为国家利益和/或国家权力斗争主题的过程。〔32〕通常认为“政治化”的表现包括:问题具有政治意义;需要国家机构的干预;出现了对某问题的两极分化或政治争端,在此背景下,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立场。〔33〕
2011年后,围绕法律与公正党、公民纲领党的政治差异开始扩大并出现了政治极化,国家政策和党争主要体现在中右派自由主义政党“公民纲领党”和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之间,其他党派弱化。法律与公正党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疑欧倾向,拒绝接受移民和难民(侨胞除外),对侨胞事务更加热心。
2015年8月,波兰政府重新通过了“2015—2020期间政府与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合作计划”,将移民和侨胞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其目标包括:支持为海外社区和移民工人的子女提供波兰语培训和波兰语教育;保护和加强侨胞波兰身份和接触波兰民族文化的机会;加强海外波兰协会的能力建设;支持近期移民返回(通过信息和激励);发展侨胞与波兰的联系。〔34〕具体内容和之前的计划并无太大变化,但侧重在国外采取措施,以加强对侨胞的影响力。
在“2015—2020年政府与波洛尼亚和海外波兰人的合作计划”通过三个月之后,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执政党。同年,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杜达(Andrzej Duda)成功当选总统。此后法律与公正党主政格局延续至今。在该党主导下,侨胞政策明显强化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化”倾向,主要体现在:首先,侨胞及侨胞事务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工具性凸显。在国内政治议程中,将侨胞政策嵌入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公共事务等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议程之中,力图实现协同效应。在对外政策中,对侨胞事务给予了极高定位。例如,在“波兰外交政策战略:2017—2021”中,认为与海外侨胞合作有助于打造波兰的全球品牌(Global Brand),波洛尼亚人和波兰之间的纽带有助于树立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即一个关心国外侨胞及其后代的国家。〔35〕杜达总统曾在2015年3月赴波兰公民侨胞聚居地——伦敦进行选举宣传。就任总统后,他出国访问时经常会见当地的侨胞代表。例如,2018年8月20日,杜达在澳大利亚访问时会见了当地侨胞,感谢他们为澳大利亚、波兰发展所作的贡献,并嘱咐他们勿忘故国波兰。〔36〕其次,更加重视国外波裔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及有关问题。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后,对中东欧、后苏联地区、北美等“旧波洛尼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西欧新移民侨胞,特别是对德国、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国波兰少数民族的权利更为关注。再次,加强对侨胞及侨胞组织的影响。除了进一步为侨胞工人子女开设波兰语、波兰历史文化教育课程,还积极与波兰移民目的国的工会、地方当局、劳工监察员、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2023年波洛尼亚与海外波兰人计划”预计拨款60亿兹罗提用于在特定领域开展活动,包括增加在居住国的公共活动,加强波兰社区的地位,提高其活动的有效性,普及有关其权利的知识,确保波洛尼亚和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能够接触波兰语媒体,激励海外波兰社区开展联合活动,〔37〕并力图通过开展针对侨胞的语言文化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加强侨胞对波兰的民族认同和以波兰身份为基础的爱国主义。〔38〕
三、波兰侨胞政策的主要特点
除了针对公民侨胞的常规领事保护之外,波兰侨胞政策还包括遣返、颁发“波兰卡”、对侨胞的语言教育、开展文化与体育活动等措施。相比世界很多国家,波兰的侨胞政策措施较为丰富,并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争取侨胞返回波兰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达的老欧盟国家对中东欧国家青壮年劳动人口和各类专家产生了很强的“虹吸”效应,这使人口稀少的中东欧国家普遍需要通过优惠措施吸引侨胞,以补充优质人口的流失,波兰则是这方面的典型国家,它主要通过遣返政策和发放“波兰卡”来吸引侨胞。
(1)遣返政策
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国家普遍推出“遣返政策”(repatriation policy),其主要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自愿流落他国的侨胞,他们在心理、精神层面依然保留着对故国的眷恋。鼓励、推动他们返回故国定居,被普遍认为是原出身国(country of origin)的“道德义务”。〔39〕
波兰政府在冷战结束伊始即鼓励东部侨胞返回波兰,起初每年有几百名侨胞自愿返回波兰。为了进一步推动侨胞回归,1997年6月25日,波兰政府出台《外国人法》,〔40〕对波兰民族或具有波兰血统的外国人推出便利的“遣返签证”。2000年11月9日,波兰政府出台《遣返法》,〔41〕主要针对东部国家波兰族人及其子女。遣返者仅需要符合两个条件:①有波兰祖先: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一人,或曾祖父母中至少两人曾为波兰国籍;②展示其与波兰的联系,尤其是展示其了解波兰语、波兰传统和习俗。被遣返者可免费参加语言、文化课程和职业技能培训。波兰政府还推出了“安置政策”,对他们购买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问题提供资助和支持。
加入欧盟后,波兰政府又将遣返对象延伸至入盟后的波兰移民。为了不引发居住国反对,2012年内政部出台的“波兰移民政策”文件中特别强调,“遣返移民的计划不是为了积极鼓励波兰人返回,而是为了在侨胞决定离开东道国的情况下促进返回”。〔42〕2017年扩大了遣返后的支持范围,例如将获得波兰公民身份的对象扩大到遣返者所有直系亲属。为了协助这批侨胞遣返,波兰采取了更多措施,例如提供关于波兰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和就业信息,对遣返者进行援助,对其实行税收豁免政策,推动遣返者融入波兰社会。再如,针对不懂波兰语的遣返儿童,设立了为期12个月的波兰语班和补习课程,通过儿童就读的学校组织,由市政当局提供资助。〔43〕
虽然《遣返法》至今仍然有效,但遣返者数量从2001年开始逐渐下降,至2010年之后基本结束。在1997—2010期间,共7079名侨胞通过遣返政策来到波兰生活。〔44〕
(2)“波兰卡”及相关优惠
鉴于遣返政策对侨胞吸引力有限,2007年9月7日,波兰议会通过了《波兰卡法案》(the Act on the Pole’s Card),〔45〕法案意图通过给予各种优惠来吸引侨胞进入乃至长期定居波兰。
“波兰卡”可授予声明属于“波兰民族”(Polish nation)并符合以下条件的人:①至少掌握波兰语的基本知识,将波兰语视为母语,并保持着波兰传统与习惯;②在波兰领事或波兰组织授权雇员在场的情况下,提交属于“波兰民族”的书面声明;③证明其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一人,或曾祖父母中至少两人属于波兰民族或拥有波兰公民身份,或者出示当地波兰侨胞组织的证明,确认他/她至少在过去三年中积极参与了当地波兰社区的波兰语言和文化活动。
“波兰卡”的潜在覆盖对象为所有波兰侨胞,不过,起初主要给东部国家侨胞发放,自2019年起扩展至所有无波兰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侨胞。而且,确认“波兰民族”的方式更加宽松了,即可以通过波兰的海外侨胞组织证明近三年来参与了波兰社区的语言文化活动,来代替“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一人,或曾祖父母中至少两人属于波兰民族或拥有波兰公民身份”,这使符合申请“波兰卡”的侨胞大幅增加。
获得“波兰卡”并不意味着获得波兰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但可享有以下权利:获得多次入境波兰的长期签证;在没有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波兰就业,即被允许充分进入波兰劳动力市场;有权在波兰境内与波兰公民一样开办和经营企业;可享受波兰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可在紧急时使用波兰的卫生保健服务;在波兰乘坐公共汽车、飞机和快速铁路旅行时可享受37%的折扣;国立博物馆可免费入场;波兰领事在职权范围内,在持卡人生命或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对其提供协助等。〔46〕此外,持卡人具有优先获得申请波兰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资格(一旦申请成功将被撤销“波兰卡”)。2016年,波兰政府为持卡人推出了快速入籍措施。自2017年1月1日开始,持卡人若愿意安居波兰,可获得永久居留证和安置财政补贴,以及从提交永久居留申请后的9个月的生活费。〔47〕
“波兰卡”在完全公民身份或双重公民身份之外,给予了海外波兰人获得低于公民身份的福利的机会,从而创造了一种“模糊公民身份”(fuzzy citizenship)。〔48〕这种身份的存在并不影响侨胞原公民身份,因而这部分侨胞可谓拥有“一个半公民身份”。截至2018年,波兰政府一共发放了25.5万多张“波兰卡”,〔49〕其中大部分持卡人为白俄罗斯公民和乌克兰公民。
此外,为了推动侨胞返回波兰,波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例如,2006年波兰外交部通过了“离工作更近,离波兰更近”计划,〔50〕为出于经济目的离开波兰的人制定了帮扶计划;2007年10月初,波兰政府提出了“返回方案”,〔51〕号召侨胞,尤其是最近5年的新移民返回波兰,并为他们提供以下返回便利:执行两年免税期,暂停缴纳养恤金两年,减少养老金缴款,协助在波兰就业,扩展波兰在欧盟的波兰语言文化教育,加强针对侨胞的远程教育等。
2.以推广波兰语和波兰文化为基础

“波兰海外教育发展中心”管理派驻各国的海外教育中心,在侨胞人数较多的国家设立了“学校咨询点”,在东道国开展波兰知识和波兰语教学。目前在36个国家设立了70多所“学校咨询点”,例如英国有2个,美国3个,德国7个,爱尔兰5个,荷兰2个。〔52〕在“波兰海外教育发展中心”框架下还设立了“波洛尼亚教师中心”,为在国外工作的教师提供培训、在线课程、教学方法和教材等。
“海外教育发展中心”还负责协调、协助各东道国涉及波兰主题和波兰语的教育机构。例如,海外波兰社区、家长协会或波兰教区创办和管理的社会学校(也称“波洛尼亚学校”),均受到“波兰海外教育发展中心”的财政支持和业务指导。2021—2022年,这类学校有1000多所,有14000名小学生就读于这些学校,授课教师约600名。〔53〕
在高等教育方面,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及“学术承认和国际交流局”为在波兰学习的波兰裔青年提供奖学金,侧重支持来自后苏联国家的波裔人或“波兰卡”持有者。例如,2018年创设了“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 Anders)将军奖学金计划”,该计划针对有兴趣在波兰大学全日制学习波兰语的青年侨胞而设。2018—2020年,共有1380多名申请者获得了该奖学金。〔54〕波兰裔学生若在波兰的大学的海外分支机构学习,也可申请波兰政府奖学金;在参加波兰语考试后,还可以获得相应的波兰语证书,从而有助于申请“波兰卡”。此外,波兰在侨胞人口较多的国家建立了一些“波兰学院”,主要任务是通过组织文化活动、电影节和讲座等,向国外推广波兰文化和民族传统。
3.以强化波兰身份和民族团结为灵魂
除了在语言、文化教育中注入波兰身份和民族团结内容外,波兰还通过各种措施强化侨胞的波兰身份和民族团结。波兰“外交政策战略:2017—2021”指出:应促使海外侨胞感到,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参与波兰丰富遗产和历史成就的途径。波兰身份应该被视为一种价值观,特别是应不遗余力地支持东部侨胞,因为他们表达了对波兰身份的坚定忠诚。〔55〕
在强化波兰身份、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波兰政府值得关注的举措主要包括:①2002年,波兰议会设立了“波兰侨胞和海外波兰人日”(简称“波兰侨胞日”),于每年5月2日在波兰国内外采取各种形式活动庆祝,以表彰“波兰侨胞和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在帮助波兰重新获得独立方面取得的长期成就和贡献,他们对波兰身份的忠诚和依恋,以及他们对祖国的援助”。〔56〕②波兰民族纪念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组织了系列涉及波兰历史记忆的活动。例如,与波兰教育机构共同开设波兰历史、文化的课程,举办历史展览等;自2007年开始举办年度“波兰侨胞与现代历史的相遇”活动,以使侨胞教育机构教师熟悉研究所的研究、资源和教育材料,更好地教授波兰历史和文化;自2002年开始设立“民族记忆保管人奖”,奖励国内外致力于纪念波兰民族历史的个人和组织;在世界各地设立“历史点”(history point),波兰侨胞不仅可以在这里聚会、交流,还可以共同体验波兰历史、价值观,并与祖国建立联系。③1992年,波兰政府组织、赞助了第一届“波兰社区和海外波兰人世界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f Polish Community and Poles Abroad),参会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组织的代表,就侨胞政策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商讨和辩论。大会每隔几年在波兰举行一次,至今共举办了五届。④自2018年开始,波兰联合各地侨胞及侨胞组织创办了每年一度的“全球波洛尼亚大会”(Global Polonia Summit),亦称“6千万大会”(60 Million Congress),寓意为全球6000万波兰人的盛会。波兰参议院、外交部高层官员、各地波裔组织代表均积极参与年度盛会。“大会”旨在团结侨胞,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尤其是为国内外所有波兰人之间的商业合作提供广阔舞台。⑤设立侨胞事务电视台。侨胞事务电视台主要有波洛尼亚电视台(TVP Polonia)和贝尔萨电视台(TV Bielsat)。波洛尼亚电视台由波兰电视台和波兰外交部共同出资,于1992年10月启用,面向波兰侨胞和国外波兰语观众播放世界各地的波兰侨胞新闻和节目。贝尔萨电视台为2007年12月启用,主要面向原苏联欧洲地区的波兰侨胞,它还与时俱进地通过脸书、推特、抖音、照片墙等媒介传播新闻和信息。⑥举办“世界波洛尼亚运动会”(World Polonia Games),运动会初创于1934年,起初每3年举办一次,在冷战期间一度长期停办。1990年,“波兰社区”协会成立并成为“世界波洛尼亚运动会”的主要组织者。自1991年后,运动会每年举办一次,奇数年份举办夏季运动会,偶数年份举办冬季运动会。⑦自2014年开始,波兰政府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创建了“波兰海外组织和机构及波兰侨胞组织和机构数据库”,对波兰社会及侨胞在海外的组织、机构,特别是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非官办组织、机构进行了全面统计,并创建了一个动态数据库。数据库每年至少更新一次,并对广大公众开放。〔57〕该数据库是波兰政府力图整合和团结全球波兰族人的重要举措,为个人、组织、政府之间的交互联系提供了便捷化路径。
四、波兰侨胞政策的优势与不足
侨胞已成为波兰社会资本和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经过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的努力,已成功“激活”各地的侨胞及其组织。据2022年波兰统计局的估计,海外波裔组织已接近9000个,它们在115个国家开展活动。〔58〕参与波兰侨胞运动会和教育、文化活动的侨胞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相比较而言,波兰侨胞政策属于“积极而务实”的政策类别。“积极”是指其政策措施广泛而有力。波兰著名侨胞政策学者马格达莱纳·列申斯卡(Magdalena Lesińska)认为侨胞政策措施可分为六类:①象征性措施(Dziaania symboliczne);②教育和文化措施;③社会经济措施;④强化侨胞政治权利和代表机构;⑤公民身份便利措施;⑥遣返和回归政策。〔59〕匈牙利学者达涅尔·加佐(Dániel Gazsó)则将中东欧国家的侨胞政策措施分为以下五类:①制定海外侨胞福利法;②族群优先的公民身份法;③授予非居民公民侨胞在国外的投票权;④推进侨胞对亲缘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故土归属感;⑤实施“象征性”政策措施,例如通过设立民族纪念日、侨胞大会等来加强民族团结。〔60〕波兰的侨胞政策基本涵盖了两位学者所列举的所有方面,因而属于“积极”的侨胞政策类型。
波兰的侨胞政策虽然很“积极”,有时甚至出现了轻微的“政治化”倾向,但总体来看未从“积极”滑向“激进”,而是在“积极”的同时抱持着“务实”的理念和维度。它聚焦于“语言、文化”这两个最有韧性、最持久和最不可替代的要素,充分挖掘波兰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文化软实力,通过给予优惠政策,加强波兰语的教学和各种文体活动,唤醒和激发侨胞对波兰的民族记忆和身份意识。这对于综合国力尚不突出的国家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也符合“利基外交”〔61〕的基本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波兰并未像俄罗斯、土耳其存在对侨胞进行政治动员,输出世界观、价值观〔62〕等激进做法,虽然曾强调要在侨胞中“建立亲波兰游说团”,但并未采取有力措施。总体上波兰侨胞政策尊重他国主权,重视与侨胞居住国协商解决问题,因而也未招致后者的广泛反对。
此外,除了在语言、文化教育等领域,波兰一般都将对侨胞的优惠政策限定在侨胞进入国境时才享有。因此,波兰较为严格地遵守了威尼斯委员会2001年《关于少数民族亲缘国优惠待遇的报告》〔63〕的精神,从而避免了类似2001年匈牙利的《邻国匈牙利族人地位法》将对侨胞的优惠措施“输出”至国境之外而导致干涉他国主权、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后果。〔64〕
虽然众多语言、文化教育和一些民族文化活动在国外进行,但在语言、文化方面,将侨胞政策措施延伸至他国境内,属于威尼斯委员会所指的“国际惯例”范畴之内,已为国际社会所默认。〔65〕
然而,波兰侨胞政策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侨胞政策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波兰侨胞政策的管理权限主要分属总统、外交部、参议院,部分政策还涉及教育和科学部、内政部、卫生部等。管理机构众多,职责并不清晰。参议院有“移民事务和与波兰人海外接触委员会”,众议院有“与海外波兰人联络委员会”,外交部有“波兰侨胞和海外波兰人合作司”,总统府有“与海外波兰人保持联系办公室”。内政部主管遣返事务,教育与科学部负责侨胞教育事务。总体上缺乏一个有力的总指挥机构,导致从事波兰侨民政策的机构之间的冲突、竞争、功能重叠。不同部门理念存在差异,例如,参议院看重价值观和承诺,更强调对东部波兰人的道德义务;而外交部的侨务工作愿景基于利益而非道德义务,即它视侨胞政策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外交的工具。〔66〕而侨胞事务各部门都在执行自己的“小政策”,例如侨胞事务的款项可来自参议院,外交部、教育与科学部、内政部、卫生部等部门,这增加了不同机构内部的权力竞争和内耗。〔67〕
其次,积极“引进”侨胞存在负面后果。虽然通过遣返政策、颁发“波兰卡”及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侨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波兰国内劳动力、人才流失和生育力下降带来的人口缺口,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减少了国外侨胞人口,“冲淡”了侨胞在居住国的存在和波兰侨胞政策的影响力,这点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已有明显体现。再如,各种政策优惠“吸引”作为侨胞的他国公民进入波兰,虽未明显干涉他国内政,但仍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例如白俄罗斯曾指责波兰发放“波兰卡”夺走了波裔群体的忠诚。〔68〕也有人批评指出,波兰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在邻国“制造”出新的波兰人——很多人以前未曾表明自己是波兰族人,这将危及邻国安全。〔69〕
最后,侨胞政策政治化导致了一些负面后果。虽然波兰的侨胞政策未出现类似土耳其那样的高度政治化,未出现将国内政治分野和政治斗争全面投射至侨胞群体和侨胞政策之中的现象,但即使低度的政治化也会引发一些问题。例如,为了吸引国外公民侨胞的选票,对侨胞聚集地和侨胞较多的英国、德国关注较多,对侨胞较少的国家则相对忽视,影响了侨胞政策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再如,过多强调侨胞的爱国主义、民族认同和波兰身份,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从而反过来使侨胞更难立足东道国。而且,由于将侨胞政策界定为外交政策和实施波兰国家战略的工具,以致海外波裔群体中的科学、文化、经济精英得到了重点关注,即它主要吸引了东道国社会地位较高的侨胞成员,而来自下层社会的侨胞成员被忽视。
五、结 语
波兰政府以语言、文化为抓手,恢复、激活侨胞及其后代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记忆,以此凝聚波兰民族和构建波兰身份,突出了侨胞与亲缘国最大的公约数,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然而,波兰力图通过侨胞政策扩大国际影响力,将侨胞群体打造成一种属于亲缘国的“稀薄成员身份”(thin membership),借此享有对他们的“稀薄主权”(thin sovereignty)。〔70〕亲缘国这么做需要把握适当的“度”,不然可能引发侨胞、侨胞东道国甚至国际社会的不满。
在2004年以前,波兰的侨胞政策以“道德义务”为出发点,强调“付出”而非“攫取”,即专注于对侨胞提供支持和援助,以及维持侨胞与波兰文化的联系。按照艾伦·甘伦(Alan Gamlen)关于侨胞政策的类型划分,〔71〕这一时期波兰的侨胞政策属于“能力建设型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东部国家的波兰侨胞的财政支持和基本权利的轻度关注。〔72〕此后,侨胞政策理念逐渐发生转变,主要是从强调亲缘国的责任到强调亲缘国的获得,以及输出亲缘国的影响,从“付出型政策”到“责任索取型政策”。〔73〕尽管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之后,其侨胞政策并非完全属于“责任索取型政策”,但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明显得到了加强,而波兰政府对侨胞的道德义务、协商合作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
随着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加,波兰不同地区的侨胞也会相互迁移,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侨胞会移居到欧美,这增加了侨胞群体的多元化。在俄乌冲突之后,大量定居乌克兰的侨胞涌入波兰和西欧国家,这使侨胞问题的复杂性倍增。目前,波兰已停止对来自乌克兰的侨胞发放“波兰卡”。然而,波兰的乌克兰侨胞问题很可能成为波兰今后必须重点应对的问题,这将对波兰侨胞政策带来长期的挑战。
注释:
〔1〕“At 18 million,Indi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diaspora population”,The Economic Times,January 15,2021,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ri/migrate/at-18-million-india-has-the-worlds-largest-diaspora-population/articleshow/80290768.cms?from=mdr.
〔2〕Floya Anthias,“Evaluating diaspora:beyond ethnicity?”,Sociology,Vol.3,No.32,1998,pp.557-580.
〔3〕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Glossary on Migration”,2019,p.49,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ml_34_glossary.pdf.
〔4〕一般来说,“公民侨胞”享有比“非公民侨胞”更高的待遇。随着各国侨胞群体流动性与变动性增加,内部多样性加强,公民侨胞与非公民侨胞边界变得模糊化,只针对公民侨胞的侨胞政策已不适合形势发展需要。
〔5〕Alan Gamlen,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What are they,and what kinds of States use them?Centre on Migration,Policy and Society(COMPAS)Working Papers,No.32,2006,University of Oxford,https://www.compas.ox.ac.uk/wp-content/uploads/WP-2006-032-Gamlen_Diaspora_Engagement_Policies.pdf.
〔6〕Graeme Hugo,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A Perspective from Asia,Genev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3;Krishnan Sharma,Arun Kashyap,Manuel F.Montes,Paul Ladd,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Diasporas,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11;Alejandro Portes,Cristina Escobar,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Immigrant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Study”,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No.1,2007,pp.242-281.
〔7〕Kingsley Aikins,Nicola White,Global Diaspora Strategies Toolkit,Diaspora Matters,2011,p.2.
〔8〕Y.A Ongarbayev,A.M Nurmagambetov,S.B Zharkenova,G.G Galiakbarova,“Legal Analysis of State Support for Compatriots Abroad Enshrined in Kazakhstan”,Utopía y Praxis Latinoamericana,Vol.25,No.Esp.6,2020,pp.29-39.

〔10〕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GUS),Informacja o rozmiarach i kierunkach czasowej emigracji z Polski w latach 2004—2016,2017,https://stat.gov.pl/obszary-tematyczne/ludnosc/migracje-zagraniczne-ludnosci/informacja-o-rozmiarach-i-kierunkach-emigracji-z-polski-w-latach-20042016,2,10.html.
〔14〕Rogers Brubaker,“Migration,Membership,and the Modern Nation-state: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41,No,1,2010,pp.61-78.
〔16〕〔20〕Magdalena Lesińska,Emigracja i diaspora w dyskursie politycznym w Polsce w latach 1991—2015,CMR Working Papers,83/141,September 2015,https://www.migracje.uw.edu.pl/wp-content/uploads/2016/06/WP83141-1.pdf.
〔17〕Renata Stefańska,“Between West and East:Diaspora,Emigration and Return in the Polish 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y”,In A.Weinar (eds.),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ies in the Age of Mobility,Cham:Springer,2017,pp.101-120;Magdalena Lesińska and Izabela Wróbel,“Diaspora Policies,Consular Services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Polish Citizens Abroad”,in J.-M. Lafleur,D. Vintila (eds.),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Europe and Beyond,2020,Vol.2,IMISCOE Research Series,pp.369-385.
〔21〕Poland’s Constitution of 1997,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Poland_1997.pdf.
〔22〕文件使用了“母国”(Macierzy,homestate)一词,但国内外对该词语的使用并未统一,有时“母国”被用来指代最初来源国,即亲缘国(kin-state),有时“母国”又被用来指代侨胞定居国,即东道国。本文根据威尼斯委员会的措辞,使用“亲缘国”指代侨胞最初来源国。




〔31〕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oland,Ministerstwo Spraw Zagranicznych,Priorytety polskiej polityki zagranicznej 2012—2016,2012,http://www.msz.gov.pl/resource/aa1c4aec-a52f-45a7-96e5-06658e73bb4e:JCR.
〔33〕Joost Berkhout,Changing Claims and Changing Frames in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1995—2009,SOM Working Paper,No.9,2012;Achim Hurrelmann,Anna Gora and Andrea Wagner,“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ore than an Elite Affair?”,Political Studie,Vol.63,No.1,2015,pp.43-59.
〔35〕〔38〕〔55〕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Polish Foreign Policy Strategy:2017—2021,https://www.gov.pl/attachment/869184c0-bd6f-4a20-b8af-a5c8190350a1.
〔36〕President praises Polish diaspora in Australia,news fromPrezydent.pl,20 sierpnia 2018,https://www.president.pl/news/president-praises-polish-diaspora-in-australia,36780.
〔37〕Polonia i Polacy za Granicą 2023,2023-01-02,https://ngo.leszno.pl/Polonia_i_Polacy_za_Granica_2023.html.
〔39〕〔59〕Magdalena Lesińska,“Polityczna rola diaspory na przykadzie krajów Europyi obszaru postsowieckiego”,Politeja,Vol.2,No,41,2016,pp.77-98.
〔40〕Ustawa z dnia 25 czerwca 1997 r.o cudzoziemcach,https://isap.sejm.gov.pl/isap.nsf/download.xsp/WDU19971140739/O/D19970739.pdf.
〔41〕The Repatriation Act of 9 November 2000,https://archiwum.mswia.gov.pl/en/document/the-repatriation-act-o/28,The-Repatriation-Act-of-9-November-2000.html.
〔42〕Ministry of the Interior,Polityka migracyjna Polski.Stan obecny i postulowane dziaania,2012,p.89,http://bip.msw.gov.pl/portal/bip/227/19529/Polityka_migracyjna_Polski.html.
〔43〕〔46〕Renata Stefańska,“Between West and East:Diaspora,Emigration and Return in the Polish 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y”,In A.Weinar (Ed.),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ies in the Age of Mobility,Cham:Springer,2017,pp.101-120.
〔47〕Magdalena Lesińska and Izabela Wróbel,“Diaspora Policies, Consular Services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Polish Citizens Abroad”,in J.-M.Lafleur,D.Vintila (eds.),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Europe and Beyond,Vol.2,2020,IMISCOE Research Series,pp.369-385.
〔48〕Brigid Fowler,“Fuzzing Citizenship,Nationalising Political Space: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Hungarian‘Status Law’as a New Form of Kin-state Poli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Zoltán Kántor et al.(eds.),The Hungarian Status Law:Nation Building and/or Minority Protection,Slavic Eurasian Studies,2004,No.4,pp.177-238.
〔49〕Demographic Yearbook of Poland,Statistics Poland,2019,p.450,https://stat.gov.pl/download/gfx/portalinformacyjny/en/defaultaktualnosci/3328/3/13/1/demographic_yearbook_of_poland_2019.pdf.
〔51〕Ministerstwo Pracy i Polityki Spoecznej Koncepcja programu 《Powrót》,Warszawa,2007,https://archiwum.mrips.gov.pl/gfx/mpips/userfiles/File/powrot_021007.pdf.
〔52〕Renata Stefańska,“Between West and East:Diaspora,Emigration and Return in the Polish 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y”,In A.Weinar (Ed.),Emigration and Diaspora Policies in the Age of Mobility,Cham:Springer,2017,pp.101-120;Szkoy w strukturze ORPEG,https://www.orpeg.pl/o-nas/podstawowe-informacje/.
〔53〕Anzhela Popyk,Key Trends and Practices in Diaspora Education Policy-Making.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Countries: Poland,Lithuania and Hungary, CMR Working Paper,128/186,March 2022. https://www.migracje.uw.edu.pl/wp-content/uploads/2022/04/CMR-WP-128-wersja-finalna.pdf.
〔54〕Joanna Czarnecka,“More than 46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receive NAWA scholarships in 2020”, from Careers in Poland,26 Aug 2020,https://www.careersinpoland.com/article/education/more-than-460-international-students-to-receive-nawa-scholarships-in-2020.
〔5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Republic of Poland, Polish Diaspora,2 May 2019,https://www.gov.pl/web/diplomacy/polish-diaspora-and-poles-abroad-day.
〔57〕截至2022年的数据库参见https://stat.gov.pl/download/gfx/portalinformacyjny/en/defaultaktualnosci/3502/1/2/1/polonia_inorg_1.6_2022_eng.xlsx。
〔58〕News of TVP World Nearly 9000 Polish organisations operate abroad: Statistics Poland,May 10,2022,https://tvpworld.com/60098831/nearly-9000-polish-organisations-operates-abroad-statistics-poland.
〔60〕Dániel Gazsó,“Diaspora Polic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Hungarian Journal of Minority Studies,2017,No.1,pp.65-87.
〔61〕“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是指中小国家利用自身的特征、优势和专长展开的外交活动。参见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
〔62〕波兰侨胞政策中也出现了“价值观”,但它特指对波兰身份和民族认同的价值理念。
〔63〕威尼斯委员会指出:国家可以合法地颁布涉及外国公民的法律或条例,而无须事先征得他国的同意,只要这些法律或条例的效力仅在该国境内发生。在某些领域——例如教育和文化领域,国际惯例是,国家向其具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亲缘族群(kin-minorities)提供奖学金或语言、文化教育,可以假定东道国是同意的,只要这些措施也适用于东道国其他公民(即遵守非歧视原则)。而亲缘国是否可以采取单方面措施保护其国外的亲缘少数群体,在于它是否尊重以下四个原则:①尊重他国的领土主权;②亲缘国签署的条约必须得到遵守;③遵守国家间的睦邻友好原则;④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禁止歧视。参见Report on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National Minorities by their Kin-State,adopted by the Venice Commission at its 48th Plenary Meeting,Venice,19-20 October 2001,CDL-INF(2001)19,168/2001,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INF(2001)019-e。
〔64〕参见姜琍:《〈邻国匈牙利族人地位法〉与匈斯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2期。
〔65〕波兰“海外教育发展中心”展开的语言文化活动,和中国的“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葡萄牙的路易斯·德·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Luisde Camoes)、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土耳其的尤努斯·埃姆雷学院(Yunus Emre Institute)、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一样,已成为国际惯例。
〔66〕〔67〕Witold J.Nowak,Michal Nowosielski,“Leadership Struggles and Challenges for Diaspora Policies:a Case Study of the Polish Institutional System”,Innovati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34,No.1,2021,pp.93-110.

〔70〕Robert Courtney Smith,“Migrant Membership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Transnationalization,the State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Conduct of Mexican Politic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37,No.3,2003,pp.297-343.
〔71〕艾伦·甘伦将侨胞政策划分为三类:能力建设型政策、权利扩展型政策、责任索取型政策。参见Alan Gamlen,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What are they,and what kinds of states use them?Centre on Migration,Policy and Society (COMPAS) Working Papers,No.32,2006,https://www.compas.ox.ac.uk/wp-content/uploads/WP-2006-032-Gamlen_Diaspora_Engagement_Polici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