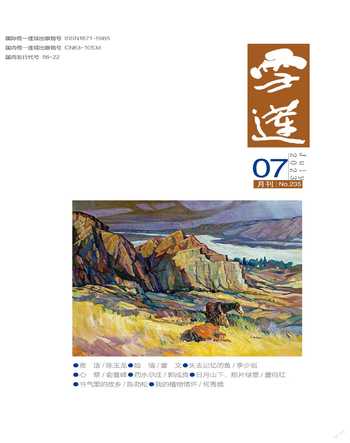如诗生活
时间过得极快,觉得还没干什么,便又到了周五。这一天我的心情总是愉悦的,想着接下来两天的休息,简直能快乐到飞。
其实我这办公室的活儿也没有多累,就是给领导跑腿、打杂、写材料,成天坐着,手不沾油,衣不染尘,坐得发际线不停地和我说拜拜,坐得肚子渐渐出怀,像怀孕几个月的大肚女人,坐得当年也算精神小伙的我变成了现在的油腻大叔。即便这样,一直在生产一线的发小郑同耀还老羡慕我,说我一天舒服得和什么似的。我说我很累,他愣是不相信,说自己倒班干活的还没说啥呢,怎么这世道变成了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我说我真的挺累,他说,你他妈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我的活干两天试试?
我和郑同耀是一个巷子里长大的,小学、初中、高中都一个班,这种缘分真是没谁了。唯一的区别是他高中毕业接了父亲的班,进了机务段,我考上了大专。他学习倒数,拿上毕业证,连高考都没参加。因为上的是铁路院校,我毕业又分回了铁路,还和他在一个段上。这让郑同耀心里一下子平衡了不少,他不止一次地给我说,你看你上了个大学,不还和我一样在这个破段上上班吗?的确没错,比工龄的话我还差他几年,我新工入段,他已经有了些资历,都可以当师傅了。当时到他们班组实习,幸亏把我分给了一个老师傅,要是让这小子带我,我简直能羞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上学时喜欢在一起踢足球,周末了还会一起约着玩,慢慢还有了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团体,只不过高中毕业后,大家联系得少,不算我,一起玩的那时候还有三个考到外地的,除了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回来一起去公园转了一圈,便再杳无音信,听说都留到了外地。说起来,就我没出息回来了。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虽然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什么的,不利于个人发展,可对于我这样一个没什么远大抱负的人来说,回来也不是一件坏事情,起码和父母家人在一起,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和我们班那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生吴晓敏好了。我本来暗恋着另外一个女生秦娟,但人家一上大学就谈了个男朋友,让我很是绝望,后来我就和吴晓敏在一起了。其实回来也没有什么,挺好的。加上现在的工作又稳定,不像我大学舍友张雷到现在还在北京打拼,前一阵子联系,说才买房,就是想自己开公司。他毕业没有回青岛的铁路单位报到,而是去北京进军他一直喜欢的软件开发方面的行业。我想换作我,首先我肯定吃不了那个苦,其次我也没有张雷那个比常人不知聪明出多少倍的脑瓜子。
上班后,我和郑同耀也少有一起的时候,除非某年过年某个外地的同学回来,才会聚一下,我结婚,他结婚,我们帮忙并参加了彼此的婚礼,然后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成天弄得灰头土脸的,别看一个段,也就是各忙各的,两个人连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工夫好像都没有。他在检修车间,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技术骨干,荣誉一大堆。我呢,因为喜欢写作,捣鼓了几篇文章发表后就来到了办公室,天天各种讲话材料没完没了。下班回到家里,也是鸡飞狗跳,吴晓敏倒班,她休息的时候我轻松点,回家吃现成,她上班的时候我就得回家给上初中的丫头做饭、干家务,忙完了,想搞点业余创作,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电脑打开了,眼皮也开始打架,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虽说零散着发表了一些东西,可是离自己的理想感觉还差了好多。作为一个文学中年,有时候会忍不住揽镜自叹,伤感于自己的碌碌无为,却总也放不下,毕竟有个叫情结的东西在那儿卡着。
此时正是早上十点十分,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用温暖的画笔给窗台和窗台上那盆我才买来没多久的绿萝、大半个办公桌、半拉椅子涂了一层明亮的丝绸般的光,我靠在椅背上,仰着头,想休息一下从早上八点上班就盯着电脑没动的眼睛。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几年前认识的一个文友月明打来的,说他开了个茶园,这个周末约几个朋友小聚一下。我脑子飞快地算了一下吴晓敏的班,月明说的那天吴晓敏刚好大休在家,我答应了。月明其实本名叫李大明,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死活想不通父母为什么给他起了这么一个普通而毫无意义的名字,就算是这个名字,哪怕把“明”改成我名字里的“鸣”也行。月明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朋友之间来往介绍,他从不提本名,只提这个,以至于和他关系特别好的人甚至都忘了他的真名。
而这种小聚,一般都是你来我往的。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这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几个月,有时候半年一年的。几个说得来的文友一约,有时候也是文友带来自己的朋友,一起吃一顿饭,舉几次杯,聊点乱七八糟过后一点也想不起来的东西,新朋友就成了新文友,新文友变成了老文友,男男女女的,彼此客气地相互称呼老师,一个个文质彬彬,有才艺的人便会唱歌、跳舞,比起单位上那些迎来送往的应酬真是有趣得多。也会有人给大家赠送自己新出的书,大多都是性情中人嘛,要的就是这个感觉。相比过于平淡无奇的岁月,这样的聚会多多少少好像都能激发我一点点想努力写作的冲动,然而冲动过去之后,依旧还是陷在现实的泥沼中,为自己的平庸和才思匮乏而感到暗自悲伤。有时候觉得还不如不去参加,可是别人一叫,面子上又抹不开,心里痒痒的,便又去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认识月明的,那时候他还在一个企业单位上班,穿着和我一样中规中矩,当时他的发际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潮水般向后退去,无论什么时候见他,总是一头蓬松黑亮打理得很有范儿的发型,散发着香皂或者洗发水的好闻的气味,一看就是喜欢干净的男人。他喜欢写诗,我也是,又都坐在一起,酒杯一端,碰了几下,没想到很是聊得来,当然不是聊诗。细问之下,竟然发现我们都是铁四中出来的,我比他大两岁,高他一届。于是互相留了电话,加了微信,一顿饭下来,好像认识了很多年。彼此感觉当时没有聊痛快。大凡那样的场合,总有一两位很厉害的人物唱主角,大家都是围着他们转,听他们说话,像我这种不太擅长在众目睽睽下口若悬河的人,通常也都是带着一双耳朵去。
我是打车去的,这种场合,肯定是要喝几口的。不比和单位的人应酬,总要端着些,拘谨着些,假的多,真的少,框框多,放不开。而和他们,就好多了,没有什么利益牵扯,合得来就多约几次,合不来,就此别过,从此不见。
因为和月明要好,我就去得比约定的时候早了一个小时。月明的茶园在市区近郊的马路边,远远就看见一个两米多高的广告灯箱上醒目的“明月河湟茶园”。看到这个名字,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出租车司机问我笑啥,我说,没啥,你停在那儿就行。
月明啊月明,这不愧是胸中有诗意的人,做个生意还要酸腐一下,不过还真别说,这家伙这名字起得不算差。想想,从去年冬天吃过饭到现在,我们再没有见过。
茶园的外观和其他附近的茶园并无不同,然而一掀帘子进去,却是别有一番洞天,里面的吧台顶上是一排圆木搭起的房檐,房檐上挂着一排红彤彤的灯笼,上面用隶书在每一个灯笼上分别写着“明月河湟茶园”,正好六个灯笼,每个灯笼分一个字。女服务员一律是蓝底白花的大襟上衣,黑裤子,黑布鞋,戴一方淡蓝色的头巾,质朴得好像个个才从过去某个时代的村里出来,男服务员则是蓝布中式褂子,也是黑裤子,黑布鞋。一个面容姣好、身量苗条的女子见我进来,迎上来,问我:“先生,有预定吗?”我说:“你们老板在吗?”她笑靥如花,说:“我们老板刚出去了,您要不在那边等一下。”说着,手朝一边的迎客大厅优雅地一摆。
迎客的大厅里摆着两张八仙桌,桌子上都放着一个圆形茶盘,茶盘里放着一个青花瓷的大茶壶,周围扣着六只小茶盅。桌子四周是一个个微型的农家旧物展览台。这是近几年的流行,抓的就是远离故乡的人的怀旧情绪。展览台中,很有年代感的面柜、斗、秤、针线笸箩、棉鞋,手绣的精美枕头、衣服和各种花型的手工鞋垫,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为何物的犁、磨、牲口笼头、背篼,还有牛槽,以及各种不知是从哪里搜寻收购来的从前的农家的物件,墙上挂的仿真玉米、成串的红翻天的线辣椒,不由得就勾起像我们这样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的思乡之情来。别的不说,看到那些鞋垫,我忽然眼底一潮。奶奶在世时,每年我和吴晓敏回去,她都要从柜子里拿出几双她戴着老花镜做的鞋垫送给我们,后来她年纪大了,自己做不了了,就买来机器绣了花,再找人在缝纫机上轧了给我们,我说奶奶你再别这么费心了,奶奶说,这是奶奶的心意,没有奶奶了,你想要也没有了。再后来,奶奶去世了,真的就再也没有人送我们鞋垫了。
我正想着,忽然听见后面一声爽朗的笑声,不回头也知道是月明回来了。我眨眨眼睛,把刚刚涌上眼眶的小情绪收了回去,转身看,果然是月明。他梳着大背头,不这样梳也不行,发际线退得有点快,露出发亮而富足的宽额头,一身中式的丝绸灰色长衫和长裤,仙袂飘飘的样子,淡淡的一双眉毛下,还是那双就算是睁大了也只能说是一条缝的眼睛,若不是挺直的鼻梁撑起了整个面部的立体感,他那双宽大的嘴巴可就显得太丑了。这家伙,竟然留了胡须,飘飘然挡住了脖颈。如果他的头发留起来,将大背头改成一个发髻,演个道士都不用化妆了。
“哎呀,一鸣哥,你来了啊,怎么不打个电话啊?”月明大咧咧地上来抓住我的手,说,“走,他们还没来,咱俩聊一会儿去。”又回头叫刚才那个女子,说:“小芳,给我们哥俩泡个茶来。”
一路走,碰见的服务员都在朝我们鞠躬。我说:“咋想起开茶园了?”
他笑:“没饭吃了呗,得想办法混口饭。”
我说:“去你的,你不是搞啥小商品批发吗?”
他说:“那一摊交给媳妇和小舅子了,我这人,你知道,是有追求的人。”
我明白他说的追求,便问:“最近有什么大作?”
他挠挠头说:“啥大作不大作的,咱就是喜欢,也算个精神支柱呗,要不成天挣钱,吃喝,睡觉,怪没意思的。你说是不是?也没有写啥,就是最近参加了几个比赛,拿了一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高兴,请几个朋友来聊聊,人嘛,总得有个追求不是?所以开这个茶园,就很适合我,喝酒,吟诗,哈哈哈。”
我说:“人活到你这份上,也算知足了,有钱,有闲,有诗,有远方,不像我,天天朝九晚五,搞不好还动不动要加班,熬到要奔五了,还没有啥名堂。”
他说:“一鸣哥,你说啥呢,我要是有你那样的单位,我也不瞎折腾了。其实干啥都累,别看我好像老板当着很风光的样子,你不知道,一天也是事情多得不行。唉,也就这点爱好,能让我在这粗粝的生活中有点乐趣。哎,哥,你说,咱这也写了几年了,也算是诗人了吧?”
我仰脸大笑,然后对他说:“无所谓,那就是一顶帽子,戴不戴的,关系不大,咱这是喜欢,只要喜欢就够好,还在乎那个?”
他一脸认真地说:“那是一般帽子嗎?是桂冠。”
我们俩同时大笑。他说:“今天我叫了个哥们,写诗挺厉害的,是咱们省现在数得着的。我们俩以前一个厂的,厂子不景气,我们都下岗了,那哥们后来凭着写东西调到别的单位去了,现在混得不错。我挺佩服他的。一会儿我介绍你们认识。”
我们这个包间穿过一方露天的院子,是长长的走廊中的一间,房间很大,推开窗户就是一片宽阔的草滩,草滩尽头就是奔腾不息的湟水河。我们俩说了一会儿话,人陆陆续续来了,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月明乐呵呵站起来招呼着,给大家互相介绍。大部分都是笔名,什么山中客、一夜秋风、跳舞的兔子,奇奇怪怪,根本就记不住。介绍完了就相继落座。主座和主座两边的位置还空着。看样子重量级人物还没有到,想必就是月明说的那个什么前同事了。月明要招呼大家,又要招呼生意,出出进进的,便顾不上我,我坐在那里,忽然有些后悔来这样的场合。这么大好的周末,干点什么不好呢?一群人坐在这么个小地方,胡扯八扯的,一顿酒后,第二天啥也想不起来。正想着,只见月明从外面进来,拍着巴掌大声笑着说道:“咱们的大诗人鲁峰老师来了。”
随着他话音刚落,他的身后走进了一个满面笑容、身材中等的胖乎乎的家伙。那家伙一边走一边朝大家拱手说:“不好意思,来晚了。”可能重量级的人物都是这样。
我定睛一看,这人不是我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鲁峰吗?这家伙,真是出息了。别的不说,比上学时至少胖了两倍,一副肥头大耳的样子,皮肤黝黑,圈脸的硬胡子茬托着的脸也圆了不少,若不是那依旧浓得像两条黑爬虫的眉毛和深陷的眼眶,我真有点认不出来。
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欢迎,我也就跟着站了起来。月明给大家一一介绍,介绍到我时,鲁峰脸上一惊,也认出我来说:“赵一鸣,怎么是你?”
月明说:“你们认识啊?”
鲁峰说:“我们高中同学。”
大家让着让他坐主位,他客气着,后来又叫我,让我坐他身边,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大家又都让我去他旁边。我推辞不过,只得挪过去。
月明手扶鲁峰椅背,在他耳边轻声说:“那,鲁老师,您看,还有谁要叫?要不,咱们开始?”
鲁峰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说:“我叫了个朋友,马上到。开始吧,大家都等半天了。”然后掏出电话,拨通,问:“到了吗?”
月明的茶园主打的就是青海农家菜,凉菜都是本地特色,凉拌鹿角菜、洋芋凉皮、农家青菜搅团、泡椒肚丝、糖醋萝卜皮、五香卤的牛肉片、煮花生、蒸红薯的拼盘。大家一边动筷子,一边赞叹。第一杯酒还没端起来的时候,外面娉娉婷婷地走进来一个穿着紫红色连衣裙的三十多岁的披发化了妆的美女。比起在座的几位素颜女性,她的出现让人眼前不觉一亮。
鲁峰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叫竹叶。大家把竹叶往鲁峰身边让,竹叶推辞再三,最终坐在了我们对面。
一开始,大家都听鲁峰说话,好像许多人都和他比较熟,但过了一会儿,就开始互相敬酒了。一般来说,一开始敬酒,场子就乱了。起先是礼貌性的走一圈,到后来,就是各自找各自想说话却没有在一起坐的人,几番下来,只要喝酒的人都是醉意醺醺,话格外多起来,之前的矜持和某种体面的东西也就放下了。我酒量不行,加上肠胃不太好,所以每次就是应个景,与其每次解释,不如每次端杯沾沾嘴唇。
先后不同的人来到鲁峰跟前,酒杯在前,话语在后,大谈仰慕之情。我这才算知道,原来鲁峰不仅诗名鼎鼎,最近还新任了单位的什么领导。不知怎么,我忽然感觉有些魔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拥有诗人桂冠的中年油腻男人和脑子里从前那个不爱说话喜欢在课间闷坐的、数理化常常倒数的男生联系起来。看样子,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人生了。
月明过来,端着杯和鲁峰碰,又和我碰,说:“鲁老师,我还真没有想到你和一鸣哥是老同学。”
鲁峰说:“那可不,同学三年呢。”
月明说:“那你们毕业后没见过吗?”
我说:“这快二十年了吧,中间好像见过一两次,再没有见过。”
我说的是实话,一次是郑同耀结婚的时候,他们俩从小一个家属院长大的,另一次在王府井商场,他和一个应该是他媳妇的时髦女人逛,我们不咸不淡打了个招呼,也没有留手机号就告别了。同学其实就是这么奇怪,能玩到一起的就算多少年不联系,见了也照样能合得来,玩不到一起的,见不见的,还是玩不到一起。
月明说:“鲁老师现在挺厉害的,他在我们厂的时候,我们住一个宿舍,大半夜的老爬起来看书写诗。鲁老师,以后还请一如既往多指导我。”
我说:“厉害,厉害。”
月明喝了酒又出去了,好像是那个叫小芳的服务员叫他。大家又都开始三三两两热烈交谈。
鲁峰问我:“这世界可真是小啊。咋样?还在铁路?”
我说:“不在铁路还能去哪?”
鲁峰说:“你们那儿有个叫罗文鑫的你知道不?诗写得还行。”
我摇摇头说:“不认识,铁路那么多单位呢。”
一时无话,彼此尴尬,在学校时我就没怎么和他打过交道,要不是他在我前面一排坐,我可能都记不住他。我盼着有人赶紧过来和他喝酒,可这会有两三个出去上洗手间了,剩下的头挨头还在说话。
我只得又说:“这么多年没见,没想到你已经成大诗人了啊?来,我敬老同学兼大诗人一杯。”
他端起酒,蹬着已经被酒染红的眼睛说:“干,老同学。”说罢一饮而尽,又问我,“你主要写什么?”
我听他这样问,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豆腐块,小小说,偶尔也写点散文,就是写着玩。”
他说:“老同学,我可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写小说,就没人写过我。说真的,很多人那写的都不是小说,或者干脆说,就不懂什么是写作。你比如,比如月明……”
我想他真是醉了,便纠正道:“月明写诗。”
鲁峰笑道:“他那叫诗?他那点水平。你手机号多少,老同学,来,我存上。以后多联系啊。”
他的话让我心里很是不舒服,我本来想和他说明一下我们不过是一点爱好而已,也没有多么远大的文学理想,他犯不着这么像掐烟头一样掐灭我们对文字的热情。你成就再高都是你的,成名也罢,成家也罢,和我们什么相干,本来都是走在平行线上的人,怎么走,都不会走向一个交点。
散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走了,只剩了月明还在认真地听鲁峰大谈诗歌艺术,我要走,月明拉着不让,竹叶是鲁峰邀请来的,自然不好意思早走。我干坐着没有意思,就和竹叶聊了几句,她说自己在单位财务,从小喜欢读小说,在学着写东西呢。
最后鲁峰大约是真醉了,说话舌头都打不过弯来。月明叫来一个小伙子,嘱咐他送鲁峰回家。临出门握手告别时,他又拉着竹叶的手不放,嘴里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说自己对某人的看法,对某事的看法,说某次在某个活动中如何如何。我很烦,又不好表露出来。我不知道他拉着人家竹叶的手是啥意思,是说得激动忘记了松,还是就愿意这样呢。竹叶有些尴尬,只笑着说鲁峰老师醉了。月明比我有耐心,依然如同對待尊师一样连哄带劝,最后终于将鲁峰哄进了车。也看着竹叶打了车。
我骂月明:“让他打的回去就行了,还折腾着送?”
月明说:“他喝大了,万一有啥事也不好说。”
我说:“他这样子回去,老婆没意见啊?”
月明说:“他老婆脾气好,由着他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让竹叶顺路送一下就行,还折腾着送,多大的人物。”
月明笑说:“一鸣哥,你懂啥,他属于喝上酒脑子就犯病的,你没看见黏黏叽叽的,再黏着人家也不好看不是?”
过了一阵子,有一天郑同耀突然到办公室来找我,说秦娟出差路过我们这里,说老同学聚一下。反正留在本地的老同学也不多,人生苦短,毕业二十年就聚这一次,下一次还不知在什么时候。郑同耀说这话时忽然有些伤感。
我一听秦娟,心莫名就突突突跳了起来。我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提起她我不会再有心跳的感觉。虽然和吴晓敏的日子过得也是磕磕碰碰,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也是很有感情了。至于无果而终的初恋,更像是个美丽的七彩肥皂泡,也像摸不着看不清的梦境。但现在,一听我曾经无数次在心里暗暗念过的名字又出现时,我还是感受到了来自内心深处那一声低低的潮涌。这和与吴晓敏的感情无关,它不过是年少时曾经拥有过的一种情愫而已。
同学聚会那天,能联系上的都来了,也有鲁峰。
秦娟没怎么变,在坐的大家好像都没有怎么变。
其实谁没有变呢?都变了,岁月能饶过谁啊?只不过曾经拥有过一段共同时光的人重新坐在一起的时候,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共同之中。
大家都打趣我和吴晓敏,说没有想到我们成了一家。我偷偷打量着秦娟,她的丹凤眼依旧明亮而好看,高高盘起的发髻让穿着浅紫色套装裙的她显得很有气质,听说在单位混得不错,老公还是个厅局级领导。秦娟显得很年轻,化了好看的淡妆,看上去端庄、高贵,果然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魅力啊,多少年过去,这个女人在一众女同学中依然是出挑的。如果眼前这个依然美丽的女人和我成了一家子,我们之间会不会也出现那种鸡飞狗跳吵嘴打架的时刻?这个女人会不会像吴晓敏这样,对我家人好,对我好呢?我们会如胶似漆地过着,还是早就离婚了?
我正胡思乱想着,郑同耀忽然悄悄趴在我耳朵边说:“你知道不?当时鲁峰那家伙追秦娟,被拒绝后要死要活的。你看他现在,你说是不是还对人家贼心不死?你看那眼神。”说完吃吃吃笑。吴晓敏坐我这边,大约听见了郑同耀的话,斜了我们一眼,转过脸去,继续吃瓜子。
我朝鲁峰看去,那家伙的眼神果然有点飘,时不时就停在秦娟身上。我忽然觉得一股莫名的气从肋骨间逸出,就赶紧端起眼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跟着郑同耀笑。同学聚会果然和网上说的差不多,重叙友情有些奢侈,成年人的世界的确太过复杂,总被名利和热热闹闹的东西所纠缠。鲁峰带了新出的诗集,给大家人手一册。众人在惊叹中对他刮目相看,秦娟更是对他口称“大才子”不断。又说起当年考学留到外地的同学,说谁刚当上了医院的副院长,谁才提了局里的一把手,谁才从国外回来。
那顿饭吃得很是没意思,吃得我在心底一点也找不到当年对秦娟的那点心思。回过头想想,老天爷让我和吴晓敏成了一家是有道理的,我无论在单位上还是在业余爱好上,都业绩平平,吴晓敏除了工作,就是围着这个家转,从不拿自己的老公孩子和别人的攀比,这大约是这个女人最大的长处。我们其实就是人群中最平常最不起眼的那种夫妻,没有发过任何意外之财,也没有走任何狗屎之运,干什么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挺好的。
告别时,大家都互相留手机号、加微信,我知道,仅仅就是留了而已,之后不联系的会一如既往不联系,联系的会一如既往联系。
之后,可能正是夏秋季的黄金时间,月明忙忙叨叨也一直没和我联系,我也没和他、没和其他人联系,单位上的事情也多,这个材料那个讲话没完没了,这一波检查刚过,那一波又来,我的工作毫无起色,还是老加班,加得有一天从凳子上站起来差点一头栽倒。单位人事变动了两回,也没有我啥事,办公室这个副科干了几年了,老主任都退休快一年了,领导们也没有把我扶正的意思,我自己干得也没有意思,感觉自己像那个盯着眼前挂着总也吃不到嘴里的胡萝卜的兔子,你说不在乎吧,胡萝卜就总在你眼前晃悠和诱惑你,说在乎吧,越吃不着越在意,这时候的在意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许多人的事情,有和我一样符合条件也盯着这根胡萝卜的人,也有没有条件盯却总是来向你打听的人,这就比较烦。这种烦我又不好讲给吴晓敏听。她是一线工人,我在办公室工作在她眼里就已经够体面了。我想,大约还是我这个人太过木讷的缘故吧。
有一天上班我忽然很烦,想找个人聊聊,翻出手机,翻来翻去,就翻到了月明。
月明說他上午没人,又是周末,下午来的人也不多,让我立马过去。下午上班坐了一个来小时后,我胡乱编了个去医院看病的理由就从单位出来,打的直接去了他的“明月河湟茶苑”。
我过去,没想到竹叶也在,他们面前摆着一瓶酒,几盘菜,竹叶眼睛红通通的,见我过来,勉强笑了一下,聊了几句就告辞了。送完竹叶进来,没等我开口,月明就说:“你看我像不像调解感情的知心大叔?”
我才知道竹叶原来和鲁峰还扯出了一段话。
我说:“鲁峰你不是说他老婆很好吗?”
月明说:“跟他老婆有啥关系?那家伙,如果我不开这个茶园,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人有名了,可能就飘了吧?”
我说:“某种程度上会,许多东西要是被自我放大,就是膨胀!”
月明一拍我肩膀,大声说:“一鸣哥,你说得对,就是膨胀,这家伙太膨胀了。你翻他朋友圈,你看看,今天到这参加作品分享去了,明天又到那参加啥活动去了。怪不得有时候我请教他,他假装没看见,太虚伪。他还老领朋友过来吃饭,我哪次不是给他贴啊?”
我说:“那这竹叶和他扯什么啊?”
月明说:“嗨,太当真了呗。小女人和自己老公过得不痛快,还以为跟鲁峰在一起就会诗情画意,这好了,鲁峰那种人,不过逢场作戏,光我看见他领的就几个。这诗是诗,千万不要和实际生活扯在一起。”
我说:“没意思。”
月明说:“是挺没意思。”
我说:“你最近写什么了没有?生意咋样?”
月明说:“偶尔写着,生意嘛,过得去。挺好。”
我说:“那就好。要不我来给你打下手吧?”
月明哈哈哈大笑,然后说:“一鸣哥,开啥玩笑。哎,我前几天看你写的那个小小说,就省报发的那个《父亲的手》,直接给我弄哭了。写得真好,哥,真的。来我们喝一杯。”
我想起来了,从收发室拿回来一沓报刊,看到那张印着我名字的报纸,我就悄悄把它藏到了抽屉里。在单位,我已经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业余时间我在写东西了。这令我很像两面人,单位一个脸,下班一个脸,又像一个人扮演的两个角色,一个为了糊口养家、赖以活命,一个只图精神愉悦、思绪自由。
月明的话让我格外感动,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热爱写作的价值所在。
夜色渐渐暗下来了,在和月明推杯换盏中,我第一次尝试着多喝了几口,很快,脑袋里好像有千重万重的云朵在绕,在迷糊和清醒之间的缝隙中,茶苑的客人陆陆续续来了。月明把我架到了门厅的沙发上,这是什么时候摆的沙发?还是原来就有?他给我盖了个毯子,说你先睡一会儿,等会我叫人送你回去。吧台屋檐上的红灯笼朦朦胧胧的,那些光好像不是从里面的小灯泡发出来的,而是一只无形的画笔涂抹出来的,人影绰绰。光线温暖,气氛迷蒙,突然一个熟悉的人进来,不是别人,正是鲁峰,他的臂弯里还挽着一个穿浅咖色风衣的披发女子,我虽是醉意盎然,却依然觉得她好像我们办公室才调来不久的刚离婚的马冬梅。
这世界怎么这么小啊?人影走过,便是一阵风掠过,我的眼皮渐渐沉重得睁不开了。
【作者简介】王华,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宁市作家协会理事。在《人民铁道报》《青海日报》《黄河文学》《飞天》《雪莲》《中国铁路文艺》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多篇,出版小说集《怎么和你说再见》《向西的火车》,绘本小说《藏城恋歌》。现供职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