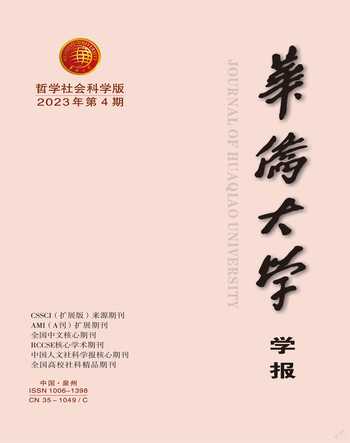放逐、死亡与回归:纳博科夫小说的“晚期风格”
林燕红 林元富
摘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晚期作品在他的整体创作生涯中呈现出明显的背离趋势。这种创作风格上的转变,基于爱德华·萨义德对“晚期风格”概念的阐述,是晚期的纳博科夫有意不走和弦、脱离时代艺术审美规范的必然结果。其晚期创作风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激进的游戏创作姿态和对性的反常关注背离成熟中期的美学范式,呈现出一种“晚期风格”的自我放逐特征;二是沉浸在死亡主题的书写中,透露出晚期的纳博科夫不愿向死亡妥协、试图在文本中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的生命态度;三是以回首创作生涯的方式向过去的复归,并借由庞大的互文体系在虚构的文本世界中获得重新开端的能力。
关键词:纳博科夫;《劳拉的原型》;“晚期风格”;萨义德
作者简介:林燕红,文学博士,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E-mail:lin.yanhong@foxmail.com;福建 福州 350121)。林元富,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间性视野中查尔斯·赖特的中华文化认同与利用研究”(FJ2022BF009)
中图分类号:I 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4-0144-08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1966)中,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螺旋形不同的弧段象征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他把在俄罗斯度过的二十年(1899—1919)在欧洲流亡的二十一年(1919—1940)以及移民到美国的二十年(1940—1960)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比作螺旋形的“命题”“反题”和“合题”弧。彼时创作这部回忆录的纳博科夫尚不知自己多年之后将再次踏上欧洲大陆,离开被自己亲切称为第二个国家的美国,在瑞士度过生命的最后十七年(1960—1977)。依照纳博科夫的比喻,这一阶段的经历在螺旋形上继“合题”之后又走向了“反题”,可以说是1919年受俄国革命浪潮裹挟而流亡后的一次自我放逐。在欧洲的最后十七年,纳博科夫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事业中,创作了《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Ada or Ardor: A Family Chronicle, 1969)(下称《爱达》)、《透明》(Transparent Things, 1972)和《看,那些小丑!》(Look at the Harlequins!1974)三部小说。然而,这最后三部完整出版的小说都没能让读者满意:“《爱达》的复繁造就了道德洞察与艺术控制的失败,《透明》不容置辩的简约显得
左支右绌,而《看,那些小丑!》表面的自恋又令人不适。”2009年,纳博科夫未完成的遗作《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在尘封了三十多年后首次向公众公开并出版。这份写在138张索引卡片上的手稿似乎也有意与读者疏离——“熟悉的纳博科夫特征几乎都不存在”“许多地方零散破碎”。可以说,这些晚期之作在纳博科夫的整体创作生涯中呈现出一种愈加明显的背离趋势。其中,未竟之作《劳拉的原型》在纳博科夫后期的美学风格激变中显得尤为突出。文本外的自我放逐与文本内美学规范的脱离相互映照,艺术上的创新被往昔主题的重复与修正所取代,而以往瑰丽的文学想象则被死亡的暗影所笼罩。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将艺术家晚期创作上呈现的这种与时代背反、支離破碎、不合时宜、弥漫着死亡氛围的美学特征,称为“晚期风格”(late style)。
一“晚期风格”之成说背景
“晚期风格”是萨义德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其灵感源自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37年,阿多诺在《贝多芬的晚期风格》(Sptstil Beethovens)一文中首次提到了“晚期风格”这一概念:“重要艺术家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果实之熟。这些作品通常并不圆美,而是沟纹处处、甚至充满裂隙。它们大多缺乏甘芳,令品尝者感到酸涩难当。它们缺乏古典主义美学家所习惯所要求的艺术作品的圆谐,展现历史的痕迹多于拓展未来方向。”阿多诺认为,贝多芬以Op.102两首大提琴奏鸣曲为代表的晚期之作蕴含着一种异于现存秩序的美学风格。在这些晚期作品中,贝多芬对古典调性(tonality)的偏离“造成调性动力整体性的碎片化”,使那些习惯于古典乐协调、统一风格的听众感到震惊。这种逆反潮流、批判时代的内在反思精神构成了艺术家晚期的否定性美学。阿多诺对贝多芬晚期美学风格的诠释打破了狭隘的纯形式分析,其目的是革新当时风格研究的既定规范,为艺术史提供一种“内在的批判理论”。
萨义德继承了阿多诺关于“晚期风格”的独到见解,并将这一批判思想继续拓展。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晚期风格”,直到临终前仍处于该论题的写作中。在其遗著《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2005)一书中,萨义德评述了多位音乐家和文学家的晚期作品,考察他们作品和思想上呈现的新风格。他将艺术家的“晚期风格”划分为两种类型:“适时”(timeliness)与“晚期”(lateness)。前者指的是艺术家创作生涯晚期阶段呈现出的成熟与智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在精神上达到的与时代同谋的“和解与静穆”。这类艺术家以莎士比亚、索福克里斯等为代表,他们的晚期作品是艺术家创造力臻于极致的例证。然而,并非所有的晚期创作都呈现出这种成熟的韵致。正如易卜生最后几部作品展现出的创作生涯上的断裂一样,年龄与衰老并非必然产生成熟就是一切的静穆。在最后一部作品《我们死者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 1899)中,易卜生对“意义、成功、进步”等艺术家晚期本应已经超越的问题重做探讨,“将圆融收尾的可能性彻底破坏,留下一群更加困惑与不安的观众。”易卜生代表的这一类型的“晚期”,就是阿多诺意义上的“晚期风格”。
自萨义德对这两种类型的晚期进行划分后,“晚期风格”概念在西方艺术人文学界就明确特指阿多诺意义上的“晚期风格”。萨义德进一步阐述了阿多诺的思想,指出,所谓晚期风格、晚期意识或晚期特质,是“一种放逐的形式”。这种放逐包括与时代之扞格,即艺术家放弃与他所属的社会秩序沟通,有意与那套秩序形成“矛盾、疏离”的关系。在这类作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置连续性于不顾的艺术家形象,其作品以“不合时宜”替代了人们期待的“平静成熟”。这种抵抗性的艺术姿态,既有艺术家对自己前期作品的反叛,也有其对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否定和对抗。和阿多诺一样,萨义德的“晚期风格”美学体现在对常规的超越上,在对“开始—持续—晚期”这一客观时间之流的适时与背离、放逐与回归中凸显出来。
这种对自己创作生涯“成熟中期”的背离与经历自我放逐后呈现的复归倾向,正是纳博科夫的晚期创作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其中,未竟之作《劳拉的原型》创作于纳博科夫生命的最后三年。由于作家身体每况愈下,直到1977年辞世之时仍未完成。然其未经打磨的特点,恰好提供了一个进入作家晚期创作的独特视角。
二“晚期风格”之自我放逐特征
“晚期风格”(late style)的late一词,与时间相关,但其涵义十分微妙。它常被用来形容一種比正确的、通常的或预期的时间来得要晚的状态。因此,作为一种存在于既定时间之外的状态,“晚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流亡意识。萨义德认为,“流亡”(exile)和“晚期风格”(late style)两个词条相似性之高,二者甚至可以互相替换。晚期艺术家拒绝与所属的社会秩序沟通,正如流亡者拒绝归属,而这种拒绝常常被贴上不可调和的标签。他们不再是时代的附庸,而是“苛求的创造天才”,高傲地与时代保持距离。因而,“晚期风格”作为一种“脱离普遍可接受的境地而自我强加的放逐”,是艺术家与时代扞格与背反的结果。
“晚期”中的流亡意识,超脱了地理空间的束缚,体现的是艺术家美学风格上的疏离。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的创作无一不充满了时空错置的离散之感。然而,这种离散之感,随着创作生涯趋近尾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早期的俄语创作阶段,纳博科夫自我经历的影子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其处女作《玛丽》中,西欧白俄流亡者的生活与心境、对俄罗斯故土的回忆和乡愁、迷茫的俄国流亡青年主人公,皆与纳博科夫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荣耀》(1932)、《天赋》(1938)也仍然沿用了俄国青年流亡者的主人公身份设定。在移居美国后的中期作品中,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依旧可辨,但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却更为丰富。在《普宁》(1957)中,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位古板滑稽而又温厚可敬的俄国文学教授普宁,流亡者在异质文化中的错位感和挫折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中,流亡的观念和时代的精神状况以一种作者的经验和感悟折射在作品中。相较之下,后期作品的流亡意识则更多体现在美学风格的背离上。
纳博科夫在创作《微暗的火》(1962)时已年逾六十,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迈向老年,死亡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部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作品中,那种后来在《劳拉的原型》中表现到极致的游戏创作倾向已经显而易见。小说由诗人谢德的999行自传诗和学者金波特为其所作的前言、注释和索引构成。声称是赞巴拉流亡国王的金波特以编著者的身份在谢德诗稿的评注中尽可能地插入有关“亲爱的赞巴拉”的一切回忆。他疯狂地游走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不断跳跃和倒错。虚实相间的序言,明显离题的评注,加上金波特身份的多种可能性带来的强烈荒诞感,使小说呈现出“游戏创作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以及创作身份一致性、权威性的怀疑,从而对我们所熟知的既定创作模式进行颠覆、对抗。”
这种游戏创作的姿态在之后的小说中愈发引人注目。与被批判为不道德的中期作品《洛丽塔》(1955)相比,晚期作品《爱达》不仅挑战了乱伦这一更为极端的伦理关系,还将它谱写成了一段堪比史诗的浪漫爱情故事。纳博科夫戏仿家族纪事小说,颠覆家庭伦理观念,以跨越时空的叙事、优美轻快的语言、狂野错杂的情节,书写了凡与爱达两兄妹绵延一生的不伦之恋。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布莱恩·博伊德认为,纳博科夫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出了创作生涯中前所未有的狂热与激情。和荡漾在炽烈爱情之中的凡与爱达一样,纳博科夫似乎无可挽救地沉迷于禁忌主题的书写中。两个情人共同发现了被隐藏的身世后,作者狡黠地让等待传统戏剧性高潮的读者期待落空——两个亲兄妹非但没有被震撼,反而欣然接受了这样的身世。他们狷狂的爱恋一直持续到九十多岁,毫不衰竭。除了凡和爱达惊世骇俗的爱情外,小说中人称的戏剧性切换、意识流的随意涌动、时序的颠倒错乱、互文指涉的繁复与多形、多语言的混用等等,都给阅读带来了晦涩然而巅峰的体验。在《爱达》的中文译后记中,译者韦清琦感慨,纳博科夫在文字的使用上已登峰造极、随心所欲到“甚至不惜为游戏而游戏”的地步。
与《爱达》相比,《劳拉的原型》没有那种头晕目眩的光辉。它虽远没有写完,但对性的反常关注和“错综复杂的设计”已然彰显了晚期的纳博科夫与以往既定的美学风格刻意保持距离、近乎自赏的创作姿态。小说围绕着年轻女主人公弗洛拉的生活展开。年轻貌美的弗洛拉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菲利普·怀尔德的妻子,她费尽心机嫁给了功成名就的怀尔德,却依旧与众多情人保持关系。其中一位情人在与她分手后,创作了小说《我的劳拉》(117,121) 。《我的劳拉》影射了弗洛拉和怀尔德不幸的婚姻,以及弗洛拉不胜枚举的风流韵事(219)。在这部书中书小说中,以弗洛拉为原型的劳拉也被叙述者“我”写进了一本书中,而这本书在情节上与《劳拉的原型》相似(85,101)。小说在结构上如同克莱因瓶一般内外勾连、时空交叠:“看似属于‘内部的《我的劳拉》在经过阅读和阐释之后又可以看成是‘外部,而原本看似属于‘外部的《劳拉的原型》在经过和《我的劳拉》的比照之后,也可以归属为‘内部”。跟随着层层嵌套的叙述,读者最终会惊奇地发现,纳博科夫又将我们带回了最外层的《劳拉的原型》。
对性的过度关注是纳博科夫偏离成熟创作生涯中期的另一个表现。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洛丽塔》曾因涉及畸恋而被贴上色情文学的标签,然而与书中婉转诗意的情欲描写相比,《劳拉的原型》可谓肆无忌惮。“性”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源泉,而在这里,这些露骨直白的性和性器官的描写不仅索然无味而且毫无生气,似乎有意背离了以往读者所熟知的美学风格。从弗洛拉少女时期便持续不断的放纵生活到弗洛拉婚后与怀尔德之间敷衍应付的性爱行为,纳博科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关注“性”,并以反常直白、无比赤裸的文字远离了读者。
博伊德说,纳博科夫总是在小说中重塑叙事结构。或许他的目标就隐藏在小说人物的口中,他要写一部“气得令人发疯的伟大作品”(221)。它不会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因为纳博科夫从来就不是一位传统型的作家。它必须是一次创作内容和形式上的自我放逐,一次对纳博科夫创作生涯最深刻的反叛。正如埃伦·皮弗(Ellen Pifer)所说的:“对我们来说,放逐似乎是历史上的不幸事件;但对纳博科夫而言,放逐既是一种存在条件,同时也是艺术创作上的必要。”唯有不附庸时代,他才能避免弗洛拉祖父的结局——一个名噪一时的艺术家,死于遗忘的痼疾(45)。
三“晚期风格”之死亡暗影
在艺术史上,死亡是最常被描绘的主题之一。正如E.M.福斯特(E.M. Foster)所言,死亡受小说家青睐,因为它能够干净利落地结束一本书。它是从一个场景中剔除不需要的小说人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将紧张或震惊引入情节的最佳方法。在哲学思辨上,死亡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阿多诺认为,艺术家的“晚期风格”并非年老或死亡的直接产物,但死亡仍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显现在作品中。萨义德也指出,艺术家的身体状况与审美风格之间的关联,乍一看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但它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意识到死亡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自己,艺术家开始思考自己过去的作品并重塑有限的余生,在创作上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貌。
死亡是纳博科夫作品中经常触及的一个主题。在以往的作品中,纳博科夫从未近距离地描绘过死亡,而是以或是隐喻或是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刻意回避。《洛丽塔》中,亨伯特谈及自己的童年时,只用一句话交代了自己的母亲:“我那位非常上镜的母亲在我三岁时死于一次反常的意外事故(野餐、雷击)。”母亲的死本该是句子的中心,他却只用了一对圆括号中的两个词就轻描淡写地带过,随即继续谈论起幼儿时期的感受。同样的例子也见于回忆录《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与父亲有着及其深厚的感情,但在整本书中,他从未提及1919年导致父亲死亡的暗杀事件,而是以一种及其迂回的方式将父亲的死掩埋在叙述中。在《庶出的标志》一书的前言中,纳博科夫宣称:“死亡只是一个风格问题。”而他偏爱的风格,即是以一种微妙、迂回的方式淡化死亡。然而,在《劳拉的原型》中,情况则大相径庭。纳博科夫非但没有像以往一样淡化死亡,反而一反常态,沉浸在死亡的游戏之中。在他的笔下,死亡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展现在读者面前,甚至覆盖了整部小说。
纳博科夫曾经为《劳拉的原型》定了一个临时标题:《死之乐》(Dying is fun),如今赫然印在扉页上。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书中遭遇了死亡。主人公怀尔德不堪妻子的不忠和病痛的折磨,在“自我消除”的心理实验中一遍又一遍地抹去憎恶的肉身,从而获得“人类所知的最大狂喜”(172)。弗洛拉被情人写进书中书《我的劳拉》,在神秘作者的安排下遭遇了“最疯狂的死亡”(228)。而弗洛拉的家人,也逃脱不了各式各样的死亡结局。她的祖父列夫·林德(Lev Linde)是从莫斯科移民到美国的画家,因“名噪一时的作品被遗忘”而郁郁而终(47)。她的父亲亚当·林得(Adam Lind)是一位喜欢特技摄影的时尚摄影师,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爱恋的男孩掐死了另一个他爱得更深却得不到的男孩”而在一家旅馆中开枪自杀,并用提前安置好的相机记录了这一幕(51)。她的母亲兰斯卡雅·林得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在弗洛拉的毕业典礼上意外身亡,而兰斯卡雅的情人休伯特则是在一次商务晚餐后在酒店电梯里中风去世的(76)。休伯特的女儿黛西,为了放学抄近路回家而被建筑工地上一辆倒车的卡车碾压而死(60)。怀尔德的初恋,奥罗拉·李,在十七岁时惨遭情人碎尸(206)。在这份未完成的手稿里,纳博科夫对这些人物的描述极其有限,但在他们的死亡描写上却反常地充满了耐心和兴趣。
毫不夸张地说,死亡成了《劳拉的原型》中的叙事重心,而艺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死亡中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纳博科夫以往的作品中,艺术是永生不朽的象征。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相信自己可以将家人保存在记忆中:“一切都是它原有的样子,没有什么会改变,没有人会死。”在《洛丽塔》中,亨伯特希望通过书写的方式使洛丽塔“永远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用写作赋予生命永续性是文学创作一直以来的传统,然而《劳拉的原型》中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弗洛拉被情人写进书中,其目的不是要使她像洛丽塔一样永生不朽,而是要将她摧毁:“书中的‘我是一个神经质的、优柔寡断的作家,他用描绘情人的方式来毁灭她”(121)。弗洛拉的父亲用相机记录下自己自杀的画面,将死亡永远定格在了艺术中。而弗洛拉母亲的死也被永远地存进了学校的资料中:“一张引人注目的‘资料照片留下了对这一幕的纪念”(104)。在怀尔德看来,死亡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强加的。對他来说,生活毫无意义。它用他庞大的身躯、脓肿的脚趾、扭动的肠子以及年轻妻子弗洛拉给婚姻带来的“耻辱选集”折磨着他(220)。“自我删除”(self-delete)成了他“控制自己生活的终极方式”。只有在自我抹去的心理实验中,他才能得到慰藉。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死了有五十次”(268)。他沉迷死亡,因为这种“自动消解的死亡方式能给人类带来所知的最大狂喜”(172)。怀尔德不仅自己沉迷在自我消除的心理实验中,还详细记录心理实验的工作原理,为那些“渴望死去的学生”给出具体步骤(132)。他沾沾自喜地将这种意念上的自我消亡称为“忘却自我的身体、自我的存在和思维本身”的“艺术”(245)。讽刺的是,怀尔德对死亡行为的操纵被突发的心脏病终止了。他最终无法控制死亡——死亡以自己的方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纳博科夫曾在访谈录中直言:“我笔下的人物是划船的奴隶。”怀尔德继承了纳博科夫彼时的体态和身体状况。因病痛而精疲力竭的怀尔德,让人想起年迈的纳博科夫。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纳博科夫本人,沉迷于死亡游戏之中,幻想自己的“自动消解”。在怀尔德的“自杀艺术”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不愿把死亡拱手交给命运来决定的纳博科夫。正如扉页上的“死之乐”(Dying is fun)所暗示的,死亡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嬉戏的方式呈现。临近生命终点的纳博科夫似乎想要违背和死亡之间的协议,决定自己的死亡时间,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在阿多诺看来,这种不承认死亡最终步调的态度,正是“晚期风格”的一大特征。
四“晚期风格”之重回开端
在萨义德看来,“历史,甚至过去本身,仍然是悬而未决、尚在构成之中的,仍然对现存和突发的挑战、对反叛者、有待回报和有待探究的一切保持开放”。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同样也非封闭的过去,而是尚在构成之中。正如萨义德在论述易卜生时所说的,作者在晚年撕碎了生涯与技艺,对那些本应已经超越的问题重新追寻,而戏剧作为媒介,为他提供机会搅起更多的焦虑。与“起源”不同,“开始”是人们可作的选择。晚期艺术家带着对当下的背离与超越的自我放逐精神向过去复归,从而“拥有未来与重新开端的能力”。
在《玛丽》《乔布的归来》等早期作品中,纳博科夫通过不可能的回归之主题来描画当下之狱——“我们无法直接接近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真实不虚的过去。”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出版了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但在70年代初,由于与传记作家费尔德的龃龉,也由于死亡的临近,他开始思考如何回首自己的艺术生命。费尔德的“荒谬错误、无稽之谈”激发了纳博科夫新作的创作。他在日记中提到了写一部新小说的想法:“‘他完成了任务。从那里开始,整个作品弥漫着兴奋、神采和雾霭,但仅通过暗示具体于几种艺术形式:诗歌、音乐、绘画、建筑等。”他很快开始创作这部新小说《看,那些小丑!》,并将自己的一生倒错用于其中。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反讽式地塑造了一位与自己既相符又相反的俄裔小说家瓦季姆·瓦季莫维奇,借他的自传回忆让自己的作品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场自得其乐的丑角巡演。
小说于1974年出版,但它并没有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在许多读者看来,这是一部文体驳杂破绽、充满复杂自我指涉的自恋作品。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部作品创作的直接原因是传记作家费尔德与纳博科夫在自传书写上的分歧。它促使纳博科夫重新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小说以“兴奋、神采”的成就结束,仿佛文本外的纳博科夫试图否认并竭尽全力超越自己晚期日益衰退的身体状况和创作能力,“但直到结尾,小说展现的都是徒劳、错误指引和没有到达的不安。”这种竭尽全力导致了风格上诡谲的变化——“既完全陷入又吊诡地远离了现代英语小说的传统。”
未完成的《劳拉的原型》手稿进一步验证了纳博科夫这种向过去复归的创作意图。书名中的“original”一词挑起了读者探寻人物原型和已有模式的兴趣。与年老的怀尔德的“自我抹去”相对的,是年轻的弗洛拉的被书写与创造——“她那精巧的骨骼结构很快就融入了一部小说——除了提供一些诗篇外,事实上,成为了那部小说的秘密结构”(16)。弗洛拉是书中书小说《我的劳拉》的原型,同时也是纳博科夫艺术想象力的起点。在她的身上,摇曳着纳博科夫笔下那些美丽、自私、多变的女性的影子。许多读者将弗洛拉看作是洛丽塔的翻版,然而随着阅读的推进,我们发现,她只是休伯特这个“生活在一片废墟之中”的男人想要复活的过去——他死于车祸的女儿,而非某个初恋(73)。休伯特想娶弗洛拉的母亲兰斯卡雅,也是因她长得酷似自己的亡妻,而“从照片上看的确如此”(74—76)。除了似是而非的洛丽塔主题的重复外,《劳拉的原型》还潜藏着其他丰富的互文指涉。叙述者捉摸不透的身份让人联想起纳博科夫早期小说《眼睛》中扑朔迷离的视角;弗洛拉对婚姻的玩弄颇似《透明》中的阿尔曼达;怀尔德对现实世界的绝望逃避正如《斩首之邀》中辛辛那提斯对尘世禁锢的反抗……可以说,在这部未竟之作中,互文性被运用到繁复的地步。在对贝多芬晚期美学的哲性反思中,阿多诺认为,“晚期风格”的特征“取决于更广阔的参照框架下的‘内文本关系(intra-textuality),而不再是对前辈文本或作者的直接参照。”通过繁复庞大的互文体系,纳博科夫在《劳拉的原型》中建构起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文本世界。在这个拥有无限性和可能性的文本世界中,文学的时空可以通过书写无限扩展,也可以通过抹去无限折叠。正是在这种对话式的回顾中,濒临死亡的纳博科夫实现了对过去的复归、对有限生命的超越。这也正是阿多诺所说的,“晚期风格”作家的“创作仍然在进行,却不是以发展的方式”,因为艺术家沉浸在游戏之中,试图改变或重塑自己的过去以适应艺术中的特殊世界。因此,对于晚期作家而言,开端便是终结。
在《劳拉的原型》下笔之前,纳博科夫就已经在脑海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然而三十年后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粗糙的文体风格和支离破碎的情节。《劳拉的原型》的支离破碎有其未完成的原因,但纵使纳博科夫将它写完,也必然不是一部“圆满”之作。其实,早在《透明》时期,博伊德就已经敏锐洞察到纳博科夫创作生涯的偏离:“《透明》的世界邋遢龌龊,人物狠心无情,似乎有意不想吸引人。”因此,《勞拉的原型》的支离破碎不单是作品未完成的特点使然,也是晚期的纳博科夫有意不走和弦、脱离时代艺术审美规范的必然结果。临近生命终点的纳博科夫在晚期作品中以背离以往的美学规范为乐,用“灾难性”的写作向读者传达出作为个体的创作者自我解放的自由与决心,进而呈现出一种“晚期风格”的自我流放特征。晚期的纳博科夫虽然年迈体衰,却不愿屈从于死亡的最终步态。在这些晚期作品中,纳博科夫以对死亡反常的痴迷和对创作生涯的戏谑式回顾演绎了晚期艺术家创作轨迹上的“断裂”。一方面,他不承认死亡的最终步调,试图用一种自我放逐的写作来超越死亡、对抗晚期;另一方面,他在晚期作品中又蓄意地远离了当下,回归到创作的起始点,以一种游戏的方式颠覆了以往的模式和既定秩序。风格方面的晚期和内容方面的逆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最终以一种回归的方式落幕。
Exile, Death and Reversion:
the “Late Style” of Vladimir Nabokovs Novels
LIN Yan-hong, LIN Yuan-fu
Abstract: In the late works of Vladimir Nabokov, a clear deviation from his writing style throughout his career can be observed. Saids concept of “late style” explains this deviation as a deliberate act of the artists refusal to conform to the aesthetic norms of his time and to follow traditional literary conventions. The late style in Nabokovs work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ree distinct aspects: firstly, a departure from the aesthetic form of his earlier works, characterized by a radical playfulness and explicit sexual content, which served as a form of self-imposed exile to deny his own lateness in his later works; secondly, an intense focus on the theme of death, revealing Nabokovs unwillingness to accept death as an inevitability and attempting to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of mortality in his fictional world; and thirdly, a retrospective examination of his writing career allowed him to start anew in a fictional world through a complex textual system.
Keywords: Vladimir Nabokov; The Original of Laura; late style; Edward W. Said
【責任编辑:陈西玲】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