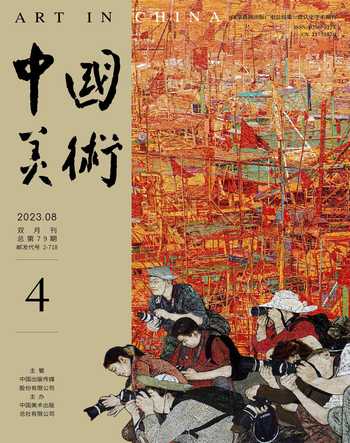论李公麟绘画中的禅学意蕴
何月舟



[摘要] 20世纪以来,有关李公麟的研究开展得十分火热,除研究李公麟本身以外,但凡涉及中国画“线条”、北宋“士人画”等话题也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及李公麟。本文力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尤其是禅学思想对李公麟画风的影响,探寻其画面中所营造的嗒然忘形、荒寒简远的禅学意境,并研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禅学是如何触发、带动以李公麟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对中国画内在精神产生了高度认知,进而赋予绘画特有的禅学韵味。
[关键词] 李公麟 文人画 禅学 白描
一、“宋画中第一”——李公麟
说起李公麟,夏文彦以“宋画中第一”[1] 来赞誉他。宋代著名画史评论家邓椿亦言:“郭若虚谓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观之,伯时既出,道子讵容独步耶?”[2] 李公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宋代绘画整体的审美走向、禅学的兴盛和李公麟的成长经历、精神修养息息相关。就目前学界对李公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他的家世、仕宦经历、绘画作品及风格方面的挖掘与整理已相对完善,相关研究文献有金维诺的《李公麟的绘画》[3]、徐邦达的《李公麟》[4]、单国强的《摹中有创 独出机杼——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5] 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班宗华的《李公麟与孝经图》[6]、日本学者板仓圣哲的《李公麟〈五马图〉》[7] 等文献,只是这些著述对他的思想脉络、绘画风格的形成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很少有人關注禅学对李公麟绘画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文人画审美转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禅学是儒、释、道三教交流融合的产物,[8] 而宋代绘画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文人们在参禅悟道的同时,积极地从事绘画创作,从而实现了中国画画风的转变——文人画的确立。在这一发生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李公麟深刻地把握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故而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生命力。李公麟作为中国人物画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既是一位院体画家,又是一位具有学养的文人士大夫,兼具绘画理论与实践基础,创立了“白描画”这一艺术形式,并且在鞍马、释道人物等题材方面也有创造性发展。李公麟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哲学观念在北宋时期发展、变化的具体体现,对后世影响甚大。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庐州舒城(今安徽舒城县)人。[9] 其父李虚一喜爱收藏名家书画、古玩器物,自小受到熏陶的李公麟好古善鉴、博闻广识,走上了书画艺术创作之路。熙宁三年(1070),李氏进士及第,直到元符三年(1100) 因右手麻痹而致仕,归隐于老家龙眠山。崇宁五年(1106)病逝,享年57 岁。总体来讲,李公麟的仕途并不顺意,终其一生“沉于下僚,不能闻达”[10]。
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11] 催生了士大夫们隐逸避世的思想。据称,李公麟“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12]。他常常将这种情感寄寓于书画之中,如其曾与苏轼合作《松石图》《憩寂图》,[13] 此外还创作过《渊明东篱图》《龙眠山庄图》《白莲社图》《归去来兮图》等多幅作品,表达出了对山林之乐的向往和对文人情怀的追求。不难看出,李氏人生态度和艺术创作的背后都隐含了当时盛行的禅学的影子。
二、“白描画”的创立与“形”“神”关系的落实
李公麟是中国古代绘画向文人画转变的标志性人物,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作为元祐文人集团的重要一员,李公麟与苏轼、苏辙、米芾、黄庭坚、王诜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文人画的理论奠基者首推苏轼。他高举“尚意”大旗,主张书画应注重个人内在情感的表达和主观意趣的抒发,即所谓“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李公麟结合自身感受,大胆进行着文人画的创作实践,形成了“画皆其胸中所蕴”的创作理念。他曾为黄庭坚作《李广夺胡儿马》,两人之后探讨了院体画与文人画在画面意趣和格调上的差异。黄庭坚在《题摹燕郭尚父图》中说:“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李公麟的意思是,文人画追求“意气所到”,而非规矩形似,同时也不必被客观现实中的常态、常理所拘束,就像苏轼所说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宣和画谱》总结说,李公麟的画作“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14]。李公麟在传世作品《五马图》中绘制了由西域进贡给北宋宫廷的五匹名马。五匹马的面前都有一位牵引的奚官、圉夫。画面主要用白描形式展现,仅在局部略施淡彩。李氏用笔遒劲,使转处极富变化,如马的臀背处用笔圆劲而富有弹性,马的腿部和腹部仅凭墨线的浓淡、干湿、粗细、方圆等差异,就将骨肉间微妙的穿插、起伏变化展现出来,可见李氏对马的结构有精准的理解和把握,如此才能将其中的力度感和丰润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便是李公麟画作的独到、精妙之处。
在继承了顾恺之高古游丝描、吴道子莼菜描的基础上,李氏更为明确地加强了线的顿挫感和方折感,形成了劲爽飘逸的铁线描。铁线描即通过线条的枯湿浓淡和方折圆转来准确概括人物、鞍马、亭台楼阁、山水花鸟等形态特征的用笔方法。[15] 寂音禅师惠洪在观李氏所画《阿弥陀像》时,感其画“大率顾、陆之意,意不尽态,故不施五色,而伯时知之耳……余谛视其笔迹,非今辈所能为,其为伯时之笔审矣”[16]。可见,李公麟在继承顾恺之与陆探微“笔迹周密”“意存笔先,画尽意在”[17]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变革。李氏作画并不依附于着色,而是仅凭几根线条就将整幅画把控得恰到好处。可以说,李公麟作品中的线条已不仅服务于造型,而是更多地用来表达意趣和情怀。
以铁线描为基础,李氏最终创立了“白描画”这一艺术形式。虽然在此之前曾出现过吴道子的“白画”,但吴道子的“白画”仅用于画壁画的粉本,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表现方式。直到李公麟“白描画”的出现,线条才完全脱离于色彩而得到了“独立身份”。邓椿对此评价道:“(李公麟)平时所画不作对,多以澄心堂纸为之,不用缣素,不施丹粉,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18] 刘克庄亦言:“前世名画如顾、陆、吴道子辈,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画家。至龙眠始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高雅超谊,譬如幽人胜士褐衣草履,居然简远,固不假衮绣蝉冕为重也。于乎,亦可谓天下之绝艺矣。 ”[19] 可以说,李公麟这种以墨线勾勒,省去色彩、洗练简朴的白描形式,成为具有宋画风韵的文人画,且能与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相比肩。
在中国画中,线条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种跃动的“生命”,白描更是将线条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其洗去浮华,把中国画提升到一个表“意”的新境界。李公麟是北宋时期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专业画家。相对来说,苏轼、米芾的绘画更倾向于抒发个人情趣,而在造型技法上略有缺失。李公麟却将院体画的逼真、工巧与文人写意精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李氏所画鞍马相比于唐代膘肥的鞍马形态,更注重表现马的“骨气”与“神气”,能够一展名马的文秀和神骏之风。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则趣事:“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20] 事虽巧合,但却足以说明李公麟的艺术表现做到了“有道有艺”。苏轼曾对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21]
这段话中,苏轼再一次肯定了李公麟在繪画技艺和意趣上的神妙之处,并声明李公麟不仅做到了“有道有艺”,还达到了“有道而不艺”的境界。其中的“不艺”并非指李氏不懂绘画技法,而是指其不受技法的束缚,使画面“不留于一物”、尽显天真。李氏的绘画在院体画和文人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其实,院体画和文人画在本质上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李公麟将文人意趣与技法表现相融合,使作品如同“天机之所合”,颇具欣赏价值。
这种意趣和技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传统“形神观” 的具体体现。魏晋时期, 中国美学已经注意到“形”“神”关系,如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观点,将形态、个性与精神气韵放到同等地位来看待。到了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在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基础上,又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22] 等观点,进一步认为画家作画单纯追求形似是没有意义的,更应追求言外之意、画外之韵。
这时,“形”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以“神”为主、“形”为从,“形”的价值和意义是为了凸显“神”的存在,并以实现“神”为终极目标。同时代的欧阳修说:“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23] 作诗和作画都应以展现物之神韵、人之心境为首务。长期以来,苏轼等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元代汤垕便秉承这种看法。汤氏在《画鉴》中指出:“今之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盖其妙处在笔法,气韵、神采,形似末也。”[24] 可见,其认为作画时虽要以“形”为基础,却不能拘泥于“形”,而要做到以形达意、以形畅神。
在实践层面上,李公麟很好地将“形”“神”关系落实到作品之中。其画作不仅形似工巧,还展现了一定的诗意。按照苏轼的评价,“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25]。黄庭坚赞他:“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26]《宣和画谱》称赞其“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入画”。李公麟自称:“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凡此种种,皆可视作文人画“吟咏性情”“所画皆其胸中所蕴”的表现。
三、禅学影响下的绘画风格
李公麟所处的北宋时代,儒、释、道三教已经高度融合。[27] 在这种风气下,宋代文人喜禅、参禅现象十分普遍,如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等都同禅僧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耽禅恋道,对儒、释、道三教经典进行过深入研究,且颇有造诣。这种现象在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莲社图》中可以窥见。《西园雅集图》绘制了当时的文坛精英共22 人,其中有身穿“乌帽黄道服”的苏轼、“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的圆通大师、着“道巾素衣”[28] 的郑靖老等人。在雅集宴饮之时,他们常常谈诗论道。《莲社图》描绘的是东晋元兴年间(402—404)中国佛教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即慧远法师与18 位贤士于庐山东林寺创立白莲社的场景。
北宋时期此类题材的诗画作品层出不穷,这足以证明文人士大夫们喜禅、参禅现象的普遍性。
后世禅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其修持方式的泛化和生活化。早在唐代六祖慧能生活的时代,禅修方式就已由早先的洞穴中打坐转变为担柴运水,即禅僧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悟禅的神通妙理。《坛经》指出:“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心清浄,即是自性西方。”[29] 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维摩诘居士便是如此,即“忘家所以懒出家”。受禅学影响,在李公麟所处的时代,出家已经不再作为修行的必要条件,在家修行的地位甚至高于出家修行。文人士大夫身处红尘即可感悟道法,在日常生活中便能修身、修心。特别是宦途失意时,参禅成了他们抚慰心灵、调节心理的手段。他们从禅理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将忧愁苦恼转为平静喜乐,从而把当下的生活视作世外桃源。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30] 李公麟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他“访名园荫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山林,故所画皆其胸中所蕴”[31]。
佛法认为,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都是佛性的显现,都是般若智慧的流露。古德说:“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32] 由此,一花一草也好,生活琐事也罢,都获得了形而上的光辉,进入到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正如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虽然韦偃的原作已不在,但通过李公麟的临摹可以想见当时唐代御苑牧马的恢宏景象。李氏希望北宋同唐朝一样,能兵强马壮,具备抵御外辱、收复失地的军事实力,并拥有辽阔的疆域和雄厚的国力。画面中,圉官和良驷都以挺拔遒劲的墨线勾勒,人马的色泽相比坡石背景来讲较为浓重,坡石略带皴擦后以赭石渲染,加强了画面整体的气氛。山石草木处,尤可见李公麟的笔墨妙趣。青草牧场、河岸坡地以侧锋虚笔勾勒,加以石绿淡染,与人马相呼应。画面整体虚实相生,表现出淡雅含蓄的文人画意趣,同时墨色变化丰富,行笔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有起倒”[33],无笔笔照摹的痕迹。
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因为接受了禅的熏陶,所以很容易同自然万物形成联系,因而笔下的作品更显得格调高远、意味深长,所画的物象也成了自我心性和情感表达的载体。他们画中的物象超越了物象本身的价值,不再受视觉感官的限制,成为画家心灵和精神活动的延续。
由此,艺术作品便成为画家对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内在思考的一种外在展露。在这一方面,李公麟的作品《阳关图》颇具代表性。[34《] 阳关图》创作于元祐二年(1087),是李公麟为送友人远行而绘。《宣和画谱》有过这样的评价:“公麟作《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关其意。其他种种类此,唯揽者得之。”[35] 作为远行送别之所,阳关自古以来便是诗人、画家描绘的重点。然而,李公麟没有画送别的场面和络绎不绝的人流等常见景象,而是画了一位河边的垂钓者。垂钓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代指隐士、高人,如商末周初曾言“愿者上钩”的姜子牙、东汉垂钓于富春江的严子陵等,皆展现了超越尘世的心性和胸怀,拥有为后人所称道的才学、品行。因此,画中的垂钓者并非凡夫俗子。《宣和画谱》中所讲的“忘形块坐”便指忘却自身的存在,神游物外,与宇宙精神相统一,达到“道”的高度。这同庄子讲的“坐忘”“唯道集虚”“块坐”“心斋”以及荀子所讲的“虚一而静”“闲居静思则通”等观念基本一致,即皆是要人摒除虚妄,保持内心虚静、澄明的状态。而且,垂钓者不只要“忘形”,还要“忘情”,这样才可达到“哀乐不关其意”的境界,进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状态,保持“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36] 的开阔心境。这便是画外之意。由此观之,李公麟具有禅意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文人画的内在本质和精神要义。
朱良志在《传统文人画的人文价值》一文中写道:“(文人意识)是一种性灵的自由意识,是一种重视生命自省的意识,一种远离外在目的,追求生命真实价值的意识。”[37] 李公麟就是将这种意识融入了自己的绘画里。比如,宋代禅师了元曾请李氏为其画像。画成后,了元赞曰:“李公天上石麒麟,传得云居道者真。不为拈华明人事,等闲开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风前嗅,枯木无端雪里春。对现堂堂俱不识,太平时代自由身。”[38]了元的赞语意在表明李公麟的才情及其绘画技艺之高超。其提到的“自由身”说明李公麟把握了了元如如不动、清明自在的内心状态,刻画出了了元最本真的形象。
李氏作画并不执着于外在表相,而更注重表达人物的内在心性,因而当人们观看李公麟的释道题材作品时,便会发现:“其佛像每务出奇立异,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胜绝处。嘗作《长带观音》,其绅甚长,过一身有半。
又为吕吉甫作《石上卧观音》,盖前此所未见者。又画《自在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39] 黄休复品评绘画时,把“逸格”放在“四格”之首。[40] 郭若虚也曾言及“气韵非师”[41]。从中可以看出,绘画创作极其重视“心”“意”“神”“气韵”等不可言明的内在要素。
北宋时期形成的文人画便是要达到这种“自在在心,不在相也”的高妙境界。
如前文所述,禅是儒、释、道交流、融合的产物,受到老庄、易学的影响,而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了北宋时期的艺术作品当中。关于“道”,《周易》解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照此来说,“道”即指“阴阳”。大千世界皆由阴阳组成,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转换,从而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因此,万事万物都表现着“道”、遵循着“道”。
中国画受此影响,画家多认为线条的粗细、浓淡、虚实、轻重、刚柔、曲直、枯湿等诸多变化皆属于“阴阳”的范畴。就李公麟的绘画来讲,其画面尽量省去颜色,删繁就简,轻毫淡墨,在极简中展现了“道”的丰富。
相较易学的阴阳观,佛教主要讲“色与空”之间的关系。早期,中国人把“色与空”的关系理解为道家的“有与无”。《金刚经》中说:“不应住色于心。”“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42] 这里提到的“色”就是相,即“有”。只有不执着于“有”,达到“无相”“无色”,进入“空”“无”的状态时,才能超然物外,不受主客观因素的支配,达至无系无缚、无桎无梏的境界。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李公麟的线条中。
当其线条不再受制于客观形体与外在色彩时,也就成为一种禅思佛理的延续。因此,线条中原本就暗含着“色与空”“有与无”的关系。
李公麟的《孝经图》便是通过白描形式将儒家经典与文人意趣进行了有机结合。苏轼评价道:“观此图者,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笔迹之妙,不减顾、陆。至第十八章,人之所不忍者,独寄其仿佛,非有道君子不能为,殆非顾、陆之所及。”[43] 能得到苏轼如此称赞的第十八章是“丧亲章”。李氏没有用惯常的手法解经,其画中没有一个因痛失亲人而哀戚的人物,也没有去表现厚葬的队伍和场面,仅绘制了邈邈云山下于苍茫水面上的一叶扁舟。李氏以含蓄、隐喻的手法,借漂泊的孤舟来象征孝子心无所依、孤寂彷徨、茫然凄凉的愁情。
他将文人审美和真挚情感寄托于线条的枯湿、浓淡、粗细等变化中,在没有任何色彩的烘托下,令观者感同身受。《宣和画谱》强调,李公麟的绘画以“立意为先”,并在“率略简易处”着力,仅用草草几笔就凝聚了画家的神韵与情思,尤其像《孝经图》这样以白描语言呈现的绘画,更是至率至简。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李公麟在研读儒家经典、佛道义理之后,注重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执着于表象,而是将禅心体悟寄寓于画面之中,使画面承载了画家的心性、品德与高远的情怀,因而画面也显得更加深邃隽永、余韵绵长。
四、结语
李公麟一生都对绘画用情至深,并将自己对禅学的体悟贯穿于绘画实践之中。据说,李公麟在晚年生病时还常在被子上以手比划,[44] 可见绘画早已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亦是他“吟咏性情”的途径。李氏所画《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45],深藏着他的心性与文人情怀,也透露出他希望通过淡然、平和的生活状态来达到睿智、澄明的禅意画境。关于李氏所作“罗汉像”,世称“龙眠样”,是他深刻领悟了“佛性”“如来藏”以及禅学由“证”转“悟”等思想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绘画是李公麟参禅悟道的修持方式。黄庭坚在李公麟《五马图》后的题跋中说道:“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书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倘来之轩冕,殊不汲汲也。”[46] 黄氏所言更加印证了李氏一生所追求的正是高远的出世情怀。李公麟在朝为官,但心中仍不忘丘壑,这便是禅学提倡的“无住”“无念”,即一种既不完全出世,又不被入世所束缚的状态。
李公麟将这种心境融入绘画里,最终达到了汤垕所说的“作画苍古,字亦老成”的境界。汤氏还说:“余尝见《徐神翁像》,笔墨草草,神气炯然。上有二绝句,亦老笔所書,甚佳。”[47] 李公麟这种洗练、简率的艺术形式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梁楷、赵孟、陈洪绶、石涛等名家皆师法于他。他的作品也被后世文人、名士竞相收藏。据载,李公麟在世时就有“都城黄金易得,而伯时马不可得”的说法。宋徽宗时,内府收藏他的作品多达107 件,足见官方对他的肯定。李公麟是文人画真正的开创者。相较于苏轼在文人画理论上的建树,李公麟在文人画的实践层面取得了更加卓越的成就,为中国绘画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1] 元末明初画家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就正式提出李公麟“当为宋画中第一”。
[2] 邓椿. 画继· 卷三· 轩冕才贤· 李公麟[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63.
[3] 参见金维诺《李公麟的绘画》,刊载于《文物》1961 年第6 期。
[4] 徐邦达. 李公麟[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
[5] 单国强. 摹中有创独出机杼——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J]. 中华遗产,2004(2):76-83.
[6] 参见班宗华《李公麟与孝经图》,普林斯顿大学。
[7] 参见板仓圣哲《李公麟〈五马图〉》,日本羽鸟书店出版社。
[8] 何劲松. 关于禅意书画的几点思考[J]. 世界宗教文化,2017(5):74-80.
[9] 关于李公麟的籍贯,元代末年宰相脱脱主持编修的《宋史·李公麟传》记载为“舒州人”,而历史上舒州并不包括舒城,舒城属于庐州、庐州府。对此问题,后代很多史学家认为,《宋史》修撰的时间仓促,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问题和纰漏,对某些人物、事件的评述亦存在失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明确指出:“文臣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也。”李公麟同时代的好友黄庭坚的诗文、邓椿的《画继》、李公麟外甥舒城张澄之的《画录广遗》以及王称的《东都事略》、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钦定四库全书》、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等均言李公麟为舒城人,并有李公麟在摹阎立本《诸夷朝贡图》时的款识为证:“熙宁十年九月上浣舒城李公麟识。”这些都多方印证了李公麟为庐州舒城人。
[10] 宣和画谱· 卷七· 李公麟[M]. 俞剑华, 注.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176.
[11] 李公麟主要活跃在宋神宗赵顼(1067—1085)到宋哲宗赵煦(1085—1100)时期。此时,宋朝与北方的辽、夏相互对峙,外部受到少数民族的威胁,内部又长期采取重文抑武、文人治国的政策,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些政策使朝廷的战斗力低下、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同时,“三冗”问题的出现以及多次变法的失败引发了激烈的新旧党争。
[12] 同注[10],174 页。
[13] 苏轼《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记载,元祐元年(1086)正月十二日,苏轼与李公麟曾为柳仲远画《松石图》和《憩寂图》,其弟苏辙题诗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诗。”在苏轼这篇短文的最后还收录了黄庭坚的题跋:“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由此可看出李公麟绘画艺术上的全面性。其创作题材并不仅限于鞍马、道释人物,对山水画的艺术造诣同样不容忽视。
[14] 同注[10],173 页。
[15] 参见《宣和画谱· 卷七· 李公麟》。
[16] 陈高华, 编. 宋辽金画家史料[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474.
[17]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卷二· 论顾陆张吴用笔[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68.
[18] 同注[2]。
[19] 同注[16],511 页。
[20] 周密. 云烟过眼录[M] 杨瑞,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506.
[21] 同注[16],458 页。
[22] 苏轼. 东坡画论[M]. 王其和, 校注.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114.
[23] 沈括. 梦溪笔谈· 卷十七[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4] 汤垕. 画鉴[M]// 周积寅, 编著. 中国画论辑要.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164.
[25] 苏轼选集[M]. 王水照,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12.
[26] 黄庭坚. 山谷诗注续补[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08.
[27] 杜继文, 主编. 佛教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09.
[28] 米芾. 西园雅集图记[M]// 米芾, 著, 水赉佑, 编. 米芾书法史料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109.
[29] 李申, 合校. 敦煌坛经合校简注[M]. 方广锠, 简注.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1.
[30]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王瑞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3:322.
[31] 同注[12]。
[32] 杜继文, 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15.
[33] 汤垕《画鉴》记载李公麟“惟临摹古画用绢素著色,笔法如行云流水,有起倒”,其中“如行云流水”是指绘画笔法如飘浮之云、流动之水一样飘逸自然、无拘无束,而“有起倒”是指落笔知轻重,自有其变化。
[34] 传世作品《阳关图》虽然并非是李公麟的真迹,但依据后世的记载与相关评价,皆能彰显李氏绘画创作的立意与构思,可作为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35] 同注[12]。
[36] 陈眉公, 小窗幽记· 卷六· 集景[J]. 工会信息,2019(14):35.
[37] 朱良志. 传统文人画的人文价值[J]. 中国美术,2015(3):78.
[38] 释惠洪. 禅林僧宝传[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39] 邓椿. 画继· 卷三· 轩冕才贤· 李公麟[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288.
[40] 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M]// 周积寅, 编著. 中国画论辑要.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143.
[41]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周积寅, 编著. 中国画论辑要.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212.
[42] 鸠摩罗什, 经译. 金刚波若波罗蜜经讲义[M]. 江味农, 讲义. 上海佛学书局,2000:181.
[43] 苏轼. 东坡画论[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82.
[44] 宣和画谱· 卷七· 李公麟[M]. 俞剑华, 注.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174.
[45] 同注[10],173 页。
[46] 周密. 云烟过眼录· 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23.
[47] 汤垕. 画鉴[M]// 中国书画全书· 第2 册.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