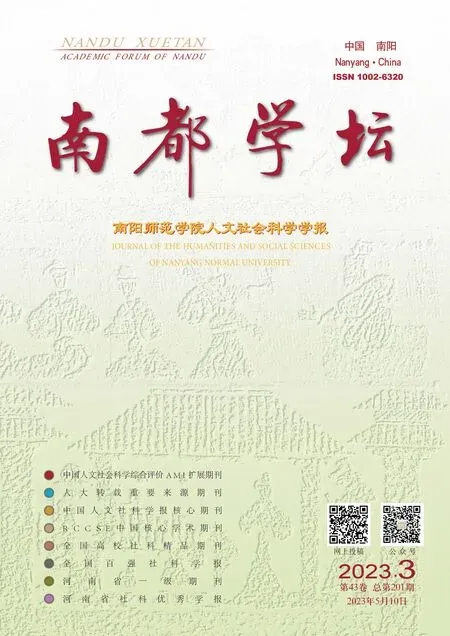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及影响
张 艳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又名苏岭、共山、百门山。因环境优美、文化意蕴独特而成为历代“龙蟠虎踞凤翔”之地。西周共伯和在此封国;魏晋时孙登、“竹林七贤”在此隐居;唐代贾岛、朱湾等曾来此凭吊游览;宋时苏轼来此题咏、易学大师邵雍在此讲学。元朝初期,这里成为北方一个大的学术中心。《宋元学案》所载元代第一学案《鲁斋学案》记载许衡等成员,就以此为基地讲习与传播学术,逐渐形成了以赵复、姚枢、许衡、窦默、王磐等名臣鸿儒为代表,包括其四方弟子、学侣友朋在内的苏门学派。这一群体与其他文人一道,将苏门山文学及文化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影响明清两代。目前学界对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及文化影响关注并不多见。本文遂以此为论题,对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游历、研学与雅集唱和
元代的苏门山文人活动,主要有卜居或游历者的登临题咏、苏门学派的探研问学及雅集唱和等。清代大儒孙奇逢言“元人以苏门为归,既众且贤。可谓人与山水相值矣”[1]399。苏门山浓厚的文化渊源与山水之美吸引了元代众多达官显贵、名士雅客来此寓居或游历。比较著名的如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等。耶律楚材地位显赫,官中书令、赠太师,封广宁王,在元代诗史具有“接宋金之续,开元诗之端”的重要地位。这位元初的第一位诗人,晚年曾在辉县梅溪卜居,“植梅数株,建琴亭月榭,吟诵其中”。其《梅溪十咏》中有“冷落梅溪二十年,今日天教属玉泉”[1]476,可见其与这里结缘时间之长。
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与苏门山渊源深厚,是游历苏门次数较多且影响较大的名士代表。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考,元好问曾四次到辉州,有三次与苏门山有关,且有诗作。第一次是元太宗九年(1237),元好问经卫州,作《卫州感事二首》,过辉县,作《望苏门》诗,这次或许是行程匆匆,没有直接登山,才有《望苏门》。因遇道士萧道辅,作诗《萧炼师公弼》,萧道辅即居住苏门山。第二次是元太宗十年(1238),元好问至卫州,作《再到新卫诗》[2]225,此次辉州之行未见苏门之作。第三次是元太宗十三年(1241),元好问过辉州,与姚枢见面,元好问作《答公茂》[2]244,是年,姚枢初到苏门山安家,元好问诗句“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应许驻金鞍”有宽慰之意。第四次是在元定宗二年(1247),此年九月,与杜仲梁(即杜仁杰)、杜紫薇、王赞等在游黄华山、宝严寺之后,又南游苏门山,作《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啸台感遇》等诗。从元好问四次辉州之行来看,元好问对辉州较为熟悉,当地友人较多,其与姚枢的交往,因资料散佚,至今未引起学界注意。元好问四次游历卫州,三次有苏门诗作,由此可看出其在苏门山诗歌创作兴致之高。除以上诗作外,他还留下《石门庙二首》《竹林寺》等。
其他的如元好问著名弟子郝经曾于元宪宗四年(1254)游河南,过卫州时,游览了苏门百泉并写有《苏门八咏》组诗。另外,一些在辉州任职的官员也多有对苏门山的题咏,如魏必复任辉州知州时作有《卫源清晖》,彭始奋经苏门留下《苏门遥望》,卫恒任职辉县留下《百泉漫步》,都堪称苏门题咏佳作。陈祐任职卫辉府总管时,有《卫源怀归》,其中“一身自觉妨贤路,万事宜收入醉乡。尘满缨冠思一濯,苏门山下有沧浪”[3]214,表达了苏门隐居的愿望。据许衡弟子白栋《思亲亭记》载:“今之富贵利达,位至宰执三公,往往置别业于兹,预为他日徜徉之计,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王祠,因而游赏以醉归者盖千万计,实河朔之丽境,中土之奇观也。”[4]542可见当时苏门山一带人气之盛及由此所形成的文人好雅之风。
苏门学派的探研问学及其雅集唱酬,成为元代苏门山文人活动的时代亮点。元初,苏门山成为著名的讲学基地,以姚枢、许衡、窦默等及其弟子组成的苏门学派在此探研问学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一般而言,人们多将姚枢、许衡等视为理学大家,至于文学方面,则多被忽略,事实上,以他们为首的苏门山文人及其后学的学术和文学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元太宗十一年(1239),姚枢携家归苏门,在此“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5]。讲学的同时,姚枢也有诗文创作,如上述元好问的《答公茂》,可知姚枢与元好问是有作品往来的,而姚枢原作今不存。明何巧新在《椒邱文集》卷九《重刊黄杨集序》曾言“有元一代,俗淳政庞,无足言者,而其诗矫宋季之萎靡,追盛唐之雅丽,则有可取者。盖自郝伯常、姚公茂鸣于北方”[6],将姚枢与郝经并论,称其为元初北方诗坛开一代文学之风气者,由此可见其诗坛地位。姚枢能文,许有壬肯定其首倡道学之时,赞其“气运昌隆,文章尔雅,推回波澜障之功,论者谓文献公不在禹下”[7]。清人孙用正《书院志序》评:“姚文献深嗜邵学,与赵汉江偕隐百泉,辟太极书院,讲明濂洛之旨。一时文风四起。许鲁斋来自覃怀,窦子声来自肥乡,多士景从,担簦负笈,德星快聚,几与鹅湖、鹿洞并传。”[1]399指出苏门学派学术贡献的同时,也说明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元海迷失后二年(1250),也就是在讲学苏门的第十年,姚枢随赵璧应召忽必烈潜邸,作《论救时之弊三十条》,这篇文章分为“修身、力学、尊贤、亲民、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八目,这是他结合时局,在苏门探研程朱之学的结晶,彰显了义理学者学以致用的本色。从广义的文学角度讲,这也是苏门山文学的一部分。
苏门学派的核心人物许衡于乃马真后壬寅元年(1242)始至苏门,结识姚枢,“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及《或问》《小学》等书”[4]32。自此往返辉、魏之间,探研程朱理学。元海迷失后二年(1250),许衡42岁时“移家苏门,与姚枢、窦默日事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星历、兵刑、食货之类,糜不研精,慨然以斯道为己任”[4]33。元宪宗四年(1254),离开苏门,征为京兆教授。许衡在此期间,学术方面著有《小学大义》,诗文方面也留下不少作品。诗歌如古风《送姚敬斋》《别西山》,绝句《宿卓水》《紫薇观》(组诗),律诗《偶成》《赠窦先生行》《喜晴》。文章如《祭李生文炳文》《辞免京兆提学状》《与人》《与子声仪之》《与左丞张仲谦》等。据白栋《思亲亭记》载:“鲁斋先生之寓是邑也,时与门生弟子一至泉上,吟风咏月,悠然而归。”[4]542这种吟咏自娱的生活常态,在许衡自己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其《紫薇观》四首所反映的游历、留宿、谈玄、明志,可以说是在苏门山活动的真实写照。
苏门学派弟子辈如王恽、姚燧、白栋等人的成长经历,与苏门山一带的学术及文学活动也是分不开的。王恽早年在苏门山随王磐求学,后成为姚枢的席上门生。王恽有关苏门山的诗文作品较多,内容广泛。直接写苏门景观的如《涌金游并序》《咏百门》《搠刀泉》等诗;写苏门一带周边景观古迹,有诗《题竹林寺》《白云古寺》《过山阳县题七贤祠》《题山阳七贤祠》《七贤祠下》等;涉及苏门山交游唱酬往来的,有《谢道人惠竹》《送司毅夫之任共城》《山行杂诗》《山阳早发》。涉及苏门趣事的,有文《纪风异》;与苏门望族交往的,有文《乐泉老人说》等。姚燧、白栋等都曾有苏门山求学经历,也曾受邀为此地文化活动等重大事件撰文。如白栋有《思亲亭记》《大元国辉州请佃户灵隐观记》,姚燧有《三贤堂记》等。王复、王博文与王恽同窗苏门。王恽、王复、王博文因文名并称“淇上三王”,可见他们在当时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也是苏门山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文人苏门山文学活动的另一重要形式是雅集唱和,比较著名的如筠溪轩雅集。筠溪轩临共城之西八九里许的卓水,由道士李重元耗费4年时间,于1241年建成。王磐《筠溪轩记》提到李重元建此轩之初衷:“吾平生学道、于世无求,惟喜延接士大夫。”[8]252同时也赞美筠溪轩环境优美:“林壑之深邃,云烟之萧爽,鱼鸟之闲逸,木植之芳馨,每至其上,使人神情洒然,如践异境。”[8]252轩之落成,自然也会助推苏门山文人的雅集活动。今读王恽《筠溪轩诗卷补亡》可知当年筠溪轩雅集盛况:
筠溪旧有亭,甚雅,往年为秋潦所圮,亭与诗卷俱波荡不存。今岁冬来游,紫薇道者丐余诗,将与补亡,且致重构之意。仍为赋此。中间饮客盖廿八年前同游者,侍臣陈季渊、奉使覃焕然、河平牧今右丞史晋明、礼部尚书王子勉、侍御史雷彦正与不肖。紫薇道者威仪杜大用也。时乙酉十月廿一日。
重到筠溪二十年,眼中风物颇潇然。双旌尚忆经行处,八客同来作饮仙。
露湿云梢回晓翠,月明瑶圃澹秋烟。道人说是潜珍客,更看飞檐插碧渊。[9]849-850
乙酉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此年王恽以左司郎中召,不赴。诗中所补记,应是28年前的一次雅集活动。本次雅集活动参与者至少有7人,从参与者身份来看,不乏文坛名流,如陈季渊、雷彦正、王子勉(王博文)等。其中杜紫薇即杜大用,应是当年陪同元好问游涌金亭者。今存陈季渊《筠溪题诗》一首,“千顷□□□□□,□□虽小尽婆娑。筼筜列阵□□□,蝌蚪成书篆籀讹。物外刳心临逝水,人间抗节振颓波。骑鲸未去三韩远,且放沧浪入浩歌”[10]。该诗也可作为苏门筠溪雅集的例证。王恽与苏门紫薇道人关系密切,交往时间长达2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王恽在安仁西里建春露堂,紫薇道人曾赠竹,王恽作《谢道人惠竹》,有“长稍来觅筠溪种,祥祉思凭道荫功”[11]。也正是有紫薇观道人所请,才有其《筠溪轩诗卷补亡》之作。
一些在辉任职的官员也多与苏门文人有雅集唱和,如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陈祐授卫辉路总管,其间王恽多与之游览苏门一带,“日夕得游从燕处,为文章往复,时或持论古今,倾底里无间。至于振衰砺懦,长予志殊锐,四载间犹一日也”[9]2773。王恽《至元四年岁在丁卯暮春之初陪陈王二郡侯泛舟清水兼携妓乐》中的陈王即陈祐、王复二人。这些文人的题咏唱酬雅集活动成为苏门山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苏门山文学活动的兴盛除与书院兴起、名人荟萃有关之外,离不开当地安定的政治环境。元太宗二年(1230)史天泽率兵收复卫州,史天泽以王昌龄为执事,治理卫州。王昌龄好学善诗,寓居期间,得益于金源文士之助,治赋税,修水利,劝农桑,修学舍,经过八年治理,卫州成“熙然而春,郁乎有文”[9]2270的礼乐之邦。这些文人包括王磐、徒单公履、曹居一等。王恽求学苏门及其成长经历,正是卫州文风大兴的时期。在此较为安定的政治背景下,苏门学派呈现向文派转型的态势,文人游历题咏、雅集胜过以往,自然也理在其中。
二、元代苏门山文学创作
元代苏门山文学创作,从题材看,主要有写景、怀古和抒怀等。风格上,以雄健见长,又不乏平淡理趣之美。从创作主题看,崇尚先贤,充满爱民情怀。
写景之作多侧重于苏门山形貌、百泉泉涌之盛及苏门山周边景观等。元代较早咏苏门山之景且影响较大的诗人,首推元好问,其《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影响甚广,白栋在《思亲亭记》中描绘了一番苏门美景后又引用该诗,言“遗山所谓‘烟景独觉苏门多’者即此地也”[4]542。许衡《别西山》也堪称佳作。这首诗以大手笔、全镜头展现苏门之景,“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4]359,可谓全景式的空间回放。“烟岚郁苍翠,远近互吞吐”[4]359是对山色青翠浓郁近距离的感知。如果说“如蹲龙”“如踞虎”是由想象起笔的话,“烟岚郁苍翠”则是由眼前取景,续以山之概貌,接下来“我来苏门居,遨游成乐土”[4]359点出畅游其间,怡然自乐的心态。王恽《涌金亭》《搠刀泉》将视线引向百泉之水。王恽重游苏门,以平民的视角和体验,来写个人真实感受,如“去时兰佩惹春烟,归日羸骖跨败鞯。赖有百门山下水,疗饥犹可度终年”[3]194。言百门山下水,在饥荒之年可依靠度日,虽说有些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从老百姓的立场说的真话呢?其 “六月渴能解,三冬泉更温”[3]20,语言质朴,更接地气。写百泉水的佳作还有郝经的《百泉》诗:“碧玉山前玉镜明,乱山倒影睡龙惊。蹴翻贝阙光零乱,万斛明珠尽一倾。”[12]222用“睡龙惊”来突出山之倒影入湖之势,“万斛明珠尽一倾”描绘百泉水涌之盛,全诗富于想象,语言明快。
元前诗人所写苏门山水诗歌多着眼于眼前之景,如贾岛《阮籍啸台》“地接苏门山近远,荒台突兀抵高峰”、宋人刘豫《登苏门山百泉》“太行雄伟赤霄逼,分支苏门为肘腋。孕奇产秀气蟠郁,涌作琉璃千顷碧”、金人赵摅《苏门漫成》“苏门山水山南奇,我闻旧矣今访之”。这些都是就眼前山水而引发感慨。然元人写苏门山水则有所不同。如元好问“济源盘古非不佳,烟景独觉苏门多”。刘赓“寄语爱梅林处士,苏门风景胜西湖”,则将苏门山水与其他名胜比较。韩准的“谁谓江南好,苏门第一流”,赞苏门山水之美更是精练简洁。
题咏苏门一带的名胜古迹,元代之前,大都落笔于啸台,如晋代庾阐的《啸台》,唐代朱湾的《游苏门登啸台》、贾岛的《阮籍啸台》等,苏轼的《啸台》诗既有前贤的怀古,也有对苏门全景式的概览,如“峰峦相掩映,松柏共阴森”,以点带面,形容苏门草木苍翠浓郁。元代郝经《啸台》:“肉薄群狐尾血腥,一天自作凤凰鸣。阆风吹断无消息,老树遗台万古情。”[12]222与唐宋啸台怀古诗有相通之处,都是赞孙登吹箫隐居品行高洁,千古流传,但写法与前人迥异。前两句用《晋书·隐逸列传》“文帝使阮籍往观”及葛洪《神仙传》所言太傅杨骏召留孙登事。即指晋文帝等仰慕孙登成仙之名召留,而孙登厌恶血雨腥风般险恶政治环境而避祸一事,起笔不俗,风格豪放,可谓名篇。元人题咏怀古,并不局限于啸台,如王恽将题咏目光聚焦到苏门山外,如竹林寺、七贤祠、紫薇观、白云寺、石门等。其《题竹林寺》(四首)、《白云古寺》都是苏门山下景观。《竹林二首》(其二)言“竹林高卧世称贤,隐放看来未中权。千古归潜书法在,一回来读一翛然”[1]480。全诗对嵇康的态度,虽认同其贤,但其对隐逸并不热衷仰慕。
元人在苏门山的诗歌创作,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的抒怀之作。典型的如许衡,其《赠窦先生行》言:“莫厌风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愿推往古明伦学,用沃吾君济世心。”[4]379表明其济世之心。其《病中杂言》(其一)云:“人人都畏死来催,我道人生死是归。但使墙阴无隐匿,不忧心外有危机。得生本自神先宅,未死谁知鬼已依。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须相顺莫相违。”[4]374可谓豁达洒脱,参透人间生死。“花为可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世间巧拙俱相伴,不许区区智力争。”[4]374看淡人间百态名利之争。其在病中渴望归隐,但始终担忧着朝政。许衡从国子监退居苏门,“自怜孤力膺邪议,常欲幽居远市尘”[4]374。诗人在这里该是慨叹岁月已老而功业未成,难抵朝臣邪议,无奈要远离喧嚣,居于苏门。这无疑是将身世之感融入诗中。许衡有长达10年的苏门生活,其镜头记录涉及苏门山多处景点,如《晚步西溪》《宿卓水》将目光指向涓涓西溪,《啸竹庐》是将视线锁在竹庐,而《紫薇观》是将脚步停留在道观,多是有感而发,其内心独白,较多的是与怀古题咏及生活的融合,且具有诗歌日常化、生活化倾向。
从作品风格看,雄健、平淡兼具。一方面,元代的苏门山诗歌体现了中州诗之元气,具有雄健之美。如元好问的《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或直接提到“元气”,如“太行元气老不死”“太古元气同胚胎”;或描绘山水苍翠气盛,如“太行千里青如染”。郝经诗在此表现更加突出,如其《共山行》,全诗如下:
吾生嗜奇能讨幽,足迹径欲穷九州。会稽未得探禹穴,太行先作共山游。是时天地方闭塞,固阴冱涸山灵愁。谁知真宰为我起蛰窟,喜气奕奕山光浮?云容烟影变态出,脉络尽露峰峦稠。宏富屹天造,峭截穷雕锼。峨峨鳌脊一翠万里壮,绾出元气直入东海头。中间膏腴甲天下,匮奇孕秀无与侔。云根涨玻璃,宝藏划不收。玉镜面寒莹,烁烁明珠流。泓澄百丈底,锦石埋黄虬。老蟾喷彩忽荡动,万山破碎翻神湫。竹间老树挂山骨,绿玉葱错风飕飑。不见孙公和,荒台等陵丘。万籁喑不鸣,邃古空悠悠。何时无名公,说破先天由?一笑碧山下,弄月凌虚舟。举手谢浮世,醉卧三千秋。卷藏神纽入化府,从渠菌蠢还蜉蝣。[12]149-150
共山,也就是苏门山。在郝经眼里,与太行作整体观,树木茂盛,一翠万里,元气盛大,玉容烟影千变万化,山峰脉络尽露。“中间膏腴甲天下,匮奇孕秀无与侔。”表达对共山的极度赞美之情,非心胸浩大者难出此语,非眼界大开者难览此貌。郝经此诗充分体现了其语言瑰丽,气大格高的特点。其《太行望》有“今年恰得到苏门,百泉亭上更峥嵘。千岩万壑入绝壁,落日倒衔山尽赤。玉立万仞磔鲸牙,金翠千层拥鳌脊。天沈影重看不足,云净烟虚晚尤碧”[12]150。语言绮丽,想象奇特。郝经有关苏门的诸多诗作,目前重视不够。明清两代《辉县志》及今人编著的《历代名人咏百泉》一书,也未收录其作品,实乃遗憾。
另一方面,作为学者型的苏门山文人,作品风格平淡且富有理趣。以许衡为例,其《宿卓水》(其二):“寒釭挑尽火重生,竹有清声月自明。一夜客窗眠不稳,却听山犬吠柴荆。”[4]365将世间万象都化于寒夜,在清冷明月夜,客宿不眠,忽听一声犬吠,将个人处于寂静空寂与繁杂喧嚣转换之间,全诗充满理趣,引人遐思。其《晚步西溪》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有味,道出晚年归隐之志:“拉友西溪往步联,西溪佳景丽秋天,日回林影苍烟外,风转滩声白鸟前。迅走双轮看磨巧,连安独木讶桥偏,老年活计寻幽隐,须拟冈头置一廛。”[4]380“日回林影苍烟外,风转滩声白鸟前”一句质朴自然,淡语有致,流露出秋景的苍然萧瑟之感。而“迅走双轮看磨巧,连安独木讶桥偏”又透露着一定的理趣。最后作者朴实无华地表露心声:“老年活计寻幽隐,须拟冈头置一廛。”整首诗平实自然,流露着隐逸之士的散淡清逸。其《宿卓水》(其四)云:“水有清声竹有风,我来端欲豁尘蒙。明朝杖履西城路,怅望家山翠霭中。”[4]366其他的如:“千里烟霞山障晓,一竿风月野桥春”[4]374、“晓日烟霞明涧壑,霁天霏霭散林皋”[4]374,向往清风明月的自在生活,言辞晓畅,意境清新恬淡。另外,在元代以前文人的苏门山诗歌作品中,很少看到“我”“吾”等第一人称的字眼。元人则不同,诗中第一人称字眼较为普遍,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如许衡的诗,“笑我羁孤成蹙蹙,于今衰落复骎骎”[4]380,是山中年迈生活的自嘲,另如“都笑谋生我最迂,我思犹恐不能愚”[4]380的心灵独白,正是以自居者观物抒怀,所以在语言上更加细腻、精工、自然平淡。
从创作主题看,充满尚贤意识与爱民情怀,这是元代以前苏门山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在元人的努力下,苏门山不仅仅是山水胜地,更是文化名山,贤哲文化为苏门山注入了新的内涵。登山观水,思念名贤的主题,在诗歌创作中逐渐强化。苏门山文人强烈的尚贤意识,使得他们的创作充满爱民情怀。如许衡诗歌不仅表现为以此为家,与共城百姓毫无隔膜,更衍化为苏门民生之忧。诗人自己已处境艰难,仍保持着一贯的淑世情怀,一如既往关心民生疾苦。如《送姚敬斋》“一祈仁政苏民疲,一祈善政凋民饥”[4]361;又如《和吴行甫雨雹韵》“默知嘉禾半漂没,坐看积潦横穿窬”[4]363。刘赓重游苏门山,虽然也有抒发寄情山水、歌咏美景之笔,但较多的还是直面现实疮痍的勇气以及济苍生之念。如:“客来讵敢濯尘缨?萍藻区区效寸诚。愿乞一杯亭下水,散为霖雨济苍生。”[1]481吴安持任都运转运使,借京都转运粮草之便,曾溯流而上游览百泉,其《苏门徘徊》(其一)“咫尺苏门路,徘徊显圣祠”[3]207就提到凭吊先贤,对这里的先贤表达憧憬之情。
关于元初苏门山文人的学术及文学活动,王公仪《重建圣庙外门记》言:“苏门山水明秀,甲于天下。自昔贤士,多来卜居。如姚雪斋、许鲁斋、王鹿庵诸大儒,相继教授于斯;其受业之徒,如王西溪、雷苦斋、王春山、白素庵、先考秋涧公,尤其特达者也。礼仪由贤者出,人才因教养成。故我辉文风,视他郡为独盛。”[1]312-313充分肯定了苏门学派对辉州文化发展及文坛的贡献。
三、明清认同及文学、文化承传
元代苏门山文人的研学倡道、交友唱和、题咏抒怀等文学活动,对明清文人产生的积极影响,一是文学方面,如苏门文学景观题咏的进一步兴盛;二是名贤文化的发扬光大。
明清苏门文学景观题咏唱和进一步兴盛,多受元人影响,典型如题咏涌金亭。因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诗的影响,涌金亭在明清进一步受到文人的关注和题咏,成为苏门文学景观一大亮点。明代陈璚《游百泉读遗山诗次韵》、秦金《涌金亭元遗山次韵》两首,仅从诗题看,可知都与元好问诗相关。另如明代赵智、金鱼、褚宁等在涌金亭的唱和诗作,更是元好问诗影响力广的又一例证。赵智《题涌金亭》中的“万斛珠玑望眼迷”与元好问诗“水妃簸弄明月玑”相和。金鱼《题涌金亭赵君次韵》有“水面珠玑光错落”,褚宁《题涌金亭赵君次韵》有“散乱金珠入望迷”都是如此。当然,影响明清的苏门山文人作品,并不只是元好问所题涌金亭,其他如马光裕《清晖阁步许鲁斋韵》“山色随望远,峦隐如伏虎”[1]507,纪云鹤《梅溪吟》“月榭题冰句,孤清肖楚材”,从中可见许衡、耶律楚材诗歌的影响。
明清两代,苏门山贤哲文化进一步得以承传。当然,这种贤哲文化,与晋以孙登为代表的隐逸文化、宋以邵雍为代表的隐逸文化不同,具有拯救时弊、解民倒悬的担当精神,为苏门贤哲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因姚枢、许衡、窦默等人对理学的传播及影响,元朝为之修建三贤堂,姚燧曾为此撰写有《三贤堂记》。他们的事迹也对明清两代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刘健《百泉书院记》载:“初议专祀邵子,既而更议祀宋濂溪周子、邵子、司马温公,明道伊川两程子、横渠张子、晦庵朱子,南轩张氏、东莱吕氏,元鲁斋许氏,凡十贤;以姚枢、窦默二氏配。”[1]318明清文人有关苏门山的诗歌流露出对元代大儒的思念敬仰之情,如刘玉“廊庙江海心更切,欲追姚许愧非贤”[3]227诗句,就是怀念姚枢、许衡。“邵子另传周曲礼,姚公堪继汉文章”[3]230赞美姚枢治学精神,也含有对苏门山文人崇尚质实的文章赞美之意。思念先贤不只是感怀先贤事迹,而是要有所担当,有所继承。明王应鹏发出“许子姚窦时丁艰,讲明正道扶危颠。诸贤已矣不可作,往事遗迹竟荒落。里俗循循格古风,不知士者谁承学”[3]267,赞许衡、姚枢、窦默等人为讲学正道、拯救世心所做的努力。贤哲文化所蕴含的担当精神也影响着清代士大夫,吴伟业在《苏门高士图赠孙征士钟元》曾言:“后来姚许开榛芜,斯文不坠斯吾徒。谁传此图来江湖,使我一见心踟蹰。即今绝学谁能扶?屈指耆旧堪嗟吁。”[1]507可谓与王应鹏同呼共应。清孙用正《苏门山赋》:“因之周程夫子,姚许诸公,或师或友,负笈担簦,建太极书院,辟大道之蚕丛。自宋迄明,人文代起,希圣希贤,渊源济美。属在后起者,孰不溯活水之源头,向高山而钦仰止?然则斯山也,直可谓尼丘分体,邹鲁钟灵;斯文借以不坠,学术赖以振兴,岂犹夫一丘一壑,徒以供骚人墨客游赏而无关重轻者哉!”[1]465游历苏门诗从游赏到尚贤的觉醒,元代文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元代苏门山一带的文人活动兴盛,游历者的题诗抒怀、苏门学派的探研问学、文人之间的雅集唱酬为苏门山文学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创作不只是将苏门山水之美推向新的高度,更可贵的是弘扬了名贤文化,丰富了苏门山的文化内涵。探讨元代文人的苏门山文学活动,对进一步认识元代北方文坛、充实河南文学史以及对当下苏门山百泉景区的内涵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