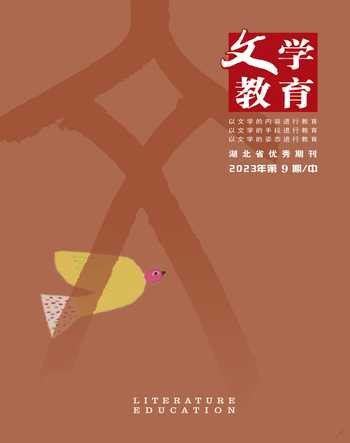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及其审美意义
王子彦
内容摘要:晋唐楷书是书法史上楷书的两个高峰,它们本来一脉相承,但从技法到审美旨趣上又都具有显著的区别。本文先整体概述晋唐楷书的特征,而后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提按顿挫之差异、顾盼关系之差异、节奏多元性与单一性之差异;再根据三种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分别探讨其审美意义。
关键词:晋唐楷书 提按顿挫 顾盼关系 审美意义 萧散飘逸
晋代和唐代书法是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唐代书法素来以楷书闻名于世,名家辈出,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皆为楷书大家。晋代书法虽以羲献父子的行草书手札最负盛名,但其时的楷书亦不容忽视,传世有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等诸多著名作品。
晋代和唐代虽然都是书法盛世,但我们需要知道晋法和唐法是不尽相同的,东晋书法崇尚自然,用笔简雅细腻,尤其是起收笔的顿挫,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没有任何痕迹。后来学者经常感叹:“学晋无门”,实际上就是晋代书法在起笔和收笔位置的提按过于隐秘所导致的。书法到了唐代,尤其是唐中晚期,以颜真卿柳公权为首的书家用笔多提按,绞转笔法已鲜而有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抄书、写经等方面的需求,例如唐代敦煌写经体,在书写时既要保证字体的装饰性、美观性,又要保证书写的快捷,故多用以提按为主的用笔方法;另一方面,提按笔法较绞转笔法在运用思路上更加清晰,法度更加明确,因此比较容易上手,略加训练便可写出像样的字。
晋法和唐法的不同,也有时代的因素。与晋代几乎同时代的北魏发展了独特的魏碑风格,但其与钟、王楷书依然具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字形结构较为自由,不拘一格,每个字的中心离中宫相对较远,且通篇字的大小不尽相同,只有垂直地排列才能将每个字的重心聚集在同一垂直线上,使之有序,换言之,他们在书写时还处于一种有行无距的状态;虽然唐楷也可以写成有行无距的形式,例如颜真卿《自书告身帖》,但唐楷法度森严的结构使其重心靠近于中宫,因此画格而书是唐楷的普遍特征。另外,如果把魏晋楷书单字取出来看,其字形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倾倒与失重,而唐楷则每个字皆成规矩,这也表明唐代较之魏晋是一个楷书书体更成熟的时期。
关于晋代与唐代书法的差异性,近年来研究甚少,大抵都是将晋唐书法视为一体进行其他方面的阐述,例如上海师范大学赵象震在其硕士论文中阐述了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这些日本书家对于晋唐书法的继承;又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杨家伟在博士毕业论文中从书法鉴藏角度对宋末元初杭州法书鉴藏进行了探究,他认为:“大批喜好鉴藏的南北方官吏和宋金遗民聚集于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孟頫、鲜于枢为核心的庞大鉴藏群体。他们通过雅集、互访、交游、买卖等活动方式,促进了晋唐法书的流通与鉴藏风气的兴起,开启了宗唐溯晋复古思潮的先声。”[1]这里的“宗唐溯晋”依然将晋唐书法视为一体进行研究。有时在一些期刊上可以看到对晋唐书法差异性有研究的,但大都是从社会文化、时代风尚、士大夫心理活动等形而上的角度进行阐释,没有具体而微的分析研究。基于此,笔者在本文将从最直观的美术视角去探究晋唐书法的差异,为保证比较的单一变量性,本文将选取两个朝代的同一书体——“楷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先整体概述晋唐楷书的特征,而后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提按顿挫之差异、顾盼关系之差异、节奏多元性与单一性之差异;再根据三种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分别探讨其审美意义,力求从书法美学角度探究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性。
一.晋唐楷书整体特征概述
晋代楷书起于曹魏钟繇,成熟于二王。钟繇楷书有《贺捷表》、《宣示表》等刻帖存世,结体宽博朴茂、中宮开张,对比后世楷书有较为浓重的隶意,卫夫人师承钟繇,又下启王羲之一脉。晋楷至羲献父子,风貌已由朴拙转为秀美,脱去隶意,但较之唐楷又缺少了提按顿挫的修饰。
受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等魏晋遗风的影响,唐初欧、虞、褚、薛等诸家楷书皆具魏晋特色:
欧阳询初习梁朝时风,得大令展感之秘;复师北齐刘珉,笔力为之瘦挺;其后参学章草,领悟索靖用笔三味,终于综合六朝精华。[2]
直至中唐时期,唐楷风貌才渐趋成熟,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中唐书家,在汲取魏晋风骨的基础上,强化了起收笔的提顿,使用笔更具有装饰意味,较之晋楷更加讲究法度,结构更加严谨规范,体势更加端庄。
二.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差异
1.提按顿挫——起伏节奏之差异
与晋代楷书相比,唐代楷书在用笔上提按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起收笔顿挫的强化,而在晋代楷书中则没有这么强的提按表现。提按的差异导致一根线条之内的起伏节奏之差异,即唐楷线条顿挫感强,起伏节奏明显,而晋代楷书顿挫感较弱,起伏节奏较隐蔽。
同样是一字,唐代楷书的起止两端顿挫感十分明显,褚遂良的“一”字更是由于顿挫而使直线条变形为两头重中间轻的“扁担状”线条;而反观晋代王羲之的一字,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起止两端的顿挫,但它的起伏节奏相较而言是微弱的、不易察觉的。
2.顾盼关系——回护连带笔势之差异
晋代楷书线条与线条间的连贯节奏较强,笔画间的回护、连贯的笔势较为明显;而唐代楷书则更注重单个笔画起止的回护,即“藏头护尾”,很少有笔画间的连带笔势。对于“藏头护尾”,蔡邕在《九势》中提到:
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3]
由此可知,唐楷的用笔方法与篆隶用笔相近,都注重线条头与尾的呼应,而“圆笔属纸”“力收之”则更加强调了一根笔画当中的互回互抱,唐楷用笔在节奏表达上正是如此特征。
以“四点底”为例。王羲之楷书四点之间笔势的连贯性强,尤其是第三点与第四点,具有明显的连带顾盼关系,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王羲之书写时笔是如何行走的;而柳楷中四点之间的连带笔意并不强,但每一点的起笔与收笔都处理得很完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晋唐楷书之间回护笔势的差异性。
实际上,如果线条与线条之间的回护连带作用表现明显的话,那么一根线条内的起止两端回护作用就相对减弱,反之亦然。陈振濂老师在《书法美学》中就曾提及:“一般而言,单一线条的回护律运用得越明确,则线条的开放性格就越弱。因为每一线条的自我完整能力强了,它对相邻线条的呼应能力就越不愿意明了地显示出来,而线条之间互相依赖的可能性也就越小。”[4]
3.节奏的多元性与单一性之差异
就用笔而言,晋代楷书笔法较为丰富,中侧并用,时有绞转,而且起收笔姿态多种多样,不拘一格;而唐代用笔则是加强了“顿”的动作,省略很多用笔细节。魏晋时的笔法在唐代变得规范,并被视觉概括和简化了。
以宝盖头中的“横勾”划为例,王羲之在书写横勾时先是向右下侧锋入笔,之后随着线条的书写,轻微地转动笔杆使笔锋逐渐调正,行笔至横划末端时,向右下方轻顿,再慢慢调锋出勾;而柳公权的“横勾”则是逆锋起笔后直接中锋拉至横划末端,随后加强了向右下方的顿笔动作,并直接提笔出锋。
对比发现,唐楷的细节动作没有晋代楷书那么丰富,这是由于唐代楷书笔法对晋代楷书笔法进行简洁化处理。总之,晋代楷书用笔的多样性导致其书写节奏的多元性,而唐楷用笔的简洁性则导致其书写节奏的单一性。
就结字而言,晋代楷书结字大小不一,错落有致,节奏较为复杂;而唐代楷书的结构较为统一,严整,节奏较为单一。米芾曾在《海岳名言》中道:
石曼卿作佛号,都無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5]
米芾认为,唐代楷书使“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伤害了文字原有的结构和大小。诚然,相较于晋代楷书而言,唐代楷书规范了文字本身大小参差错落的节奏,使整体章法的节奏更加统一。
《黄庭经》结字大小参差错落,自然质朴;而《多宝塔碑》结字严谨整饬,大小相称。从中可以看出晋唐楷书的结字在节奏多元性与单一性方面的差异。
三.审美意义
1.起伏节奏的差异导致审美旨趣的不同
提按节奏的轻重会导致两种不同风格的审美:唐代楷书由于提按加重,线条的起伏节奏较为明显,导致刻意成分较多,追求线条装饰感;而晋代楷书用笔提按较轻,追求自然、简洁、朴素的风貌。
2.回护笔势的差异导致审美倾向的差异
晋代楷书由于笔画间的回护与连贯性很强,从而使整幅字飘逸灵动,体现出魏晋文人独有的潇洒自由、逍遥飘逸的情怀;而唐代楷书隐匿了线条与线条之间的顾盼关系,因此表现出严整、规范的法度,这也使我们感受到在唐代大一统历史格局下自由意识的收敛和社会法度的森严。
对于晋唐笔法,苏东坡对此曾有评论,他说:
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6]
苏轼认为以钟、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他们的基本美感和风格是“萧散简远”,求“意外之韵”。晋人的“韵”是晋法对连带笔势的强化造成的;相反,颜、柳之书则隐藏了笔画之间的顾盼关系,从而化萧散飘逸为严整规范。
3.节奏的多元性与单一性对审美的影响
晋代楷书结体用笔较为丰富,节奏律动较为多样,使书作变化多端,让人意犹未尽。唐代楷书则因节奏较为单一,故整体看来较为规范整饬。
如果从唐代楷书“规范整饬”的审美思路再延伸发展下去,便会出现一个问题:学书者一味追求法度与严整,使结字趋于程式化,导致死板,从而极大地丧失了其审美价值。例如明清时期的馆阁体,虽然这种书体规范了书法公用文字的标准,使文字更加便于识读,但“馆阁体”在用笔上千篇一律,缺乏笔法上的变化和章法上的排布,看不到书法家的真情实感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只是为了写字而写字,字体和印刷体一样标准,在艺术审美价值上几乎等于零。这种“死板”与“程式化”的审美表达是对唐代楷法的误解造成的,孙过庭《书谱》中云:
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情楷则。[7]
可见唐法并不是一味地寻求规正,在熟练地掌握法度的同时也要不为法所拘,注重书家个人情感的表达。
一切事物都要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唐代楷书虽然具有程式化的倾向,但正是由于线条节奏的较为单一性和重复性,使得唐代楷书在气势上远胜于魏晋楷书,重复线形的叠加更容易产生气势感。我们在观赏唐碑的时候,不难感受到唐人气势之磅礴,这种视觉冲击力一方面是由于碑身的巨大,但更重要的应是唐代楷书线条节奏的表达所带来的美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晋唐楷书节奏表达的三点差异:第一是提按节奏的差异:晋楷轻而唐楷重;第二是回护连带笔势的差异:晋楷强调点画间的连带性,而唐楷强调单个线条起止的回护动作;第三是节奏复杂性的差异:晋楷节奏表达更为多元而唐楷节奏表达更为单一。
另外,在审美旨趣上,晋楷的节奏表达使其灵动多变,萧散简远,更为朴素;唐楷的节奏表达则使其严整规范而又气势恢宏。
参考文献
[1]杨家伟:《宗唐溯晋》[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0.
[2]朱关田:《唐代书法号评》,江苏教有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3]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4]陈振濂:《书法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5]米芾著,洪丕谟评注:《海岳名言评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6]陈韵如,吴佳伦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选·苏轼文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7]徐利明:《孙过庭·书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95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