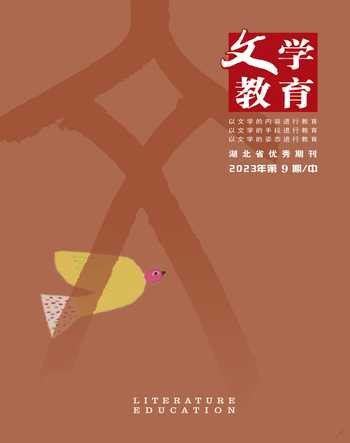母语眷恋和语文感情
周日安 茹丽凡

内容摘要:社会或集团对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心理评价,叫语言态度,包括语言感情、语言忠诚、语言忧患、语言歧视、语言背叛等等,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母语眷恋是人们对自己最早学会的民族语言怀有深深的依恋和无比的忠诚,表现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语言感情。母语有不同的层次,母语教育在中小学里集中表现为语文教育。语文是一种言语学习,语言感情也就相应表现为语文感情——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及其所记录的文学、文化、文史的态度评价。在语文教学领域,确立语文感情这一概念,比较它与语言感情的异同,明确其内涵,界定其范围,然后加以推广与使用,如引导学生将人类普遍存在的母语眷恋这类情感,转化为对语文的热爱,养成深厚的语文感情,进而形成忠于并维护民族共同语的自觉和自律等等,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这将对语文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母语眷恋 语言态度 语文感情
态度是个体对对象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由认知、情感、行为方向融合而成。社会或集团对使用某种语言变体的心理评价,即“对待某种语言的基本意见、主张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倾向和言语行为”[1],叫语言态度,包括语言感情、语言忠诚、语言特权、语言忧患、语言歧视、语言背叛等等,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怀着一份梦牵魂绕的热爱之情,叫故土眷恋;同样,人们对自幼咿呀习得的家乡土语,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叫母语眷恋。王希杰认为:“对于自己母语的深沉真挚的热爱之情,是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们都有的一种感情,这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亲人、乡土、民族和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深沉浓厚的爱的感情的一种反映和体现……”[2]。人们对母语的依恋,自古而然。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小离家,出外谋生,年老而归,乡音无改。乡音刻录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不可抹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母语情结”,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就是一种爱国情怀。
语言是文化的围墙,操相同的方言土语,彼此距离近,有相同根源,容易产生亲近感、归属感;说不同的方言土语,彼此距离远,有异质的根源,容易形成陌生感、排斥感。恩格斯在爱尔兰看到一个杂耍老头,同他用乡音交谈,那老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笔者老家社港,是湖南浏阳北乡的一个小镇,依偎在美丽的捞刀河旁,土话里有个词“打声”,发音很像普通话的“打伤”。从家乡出来的人,碰到老乡或回到老家而不说家乡话,是要被鄙夷和嘲笑的,叫做“打(叽咯)声”,言外之意就是忘了祖宗断了根脉。广东客家人,特别看重自己的方言,视为民系文化的根基,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3]的民谚。与之相当的,是闽南人的祖训“宁卖厅,不变音”[4]。王希杰在《语言感情和语言歧视》里也写道:“在南京我见到一个淮安老乡——一口淮安土话,他说他小时候说了两句南京话,被他老子打了一个大耳光,大骂:‘学驴子叫!”不说乡音,淮安人斥为“学驴子叫”,可见对家乡母语无比忠诚。社会语言学家郭熙也举了一个方言岛的例子,江苏宜兴张渚,是个河南人聚集的村子,外来人身处方言岛的特有文化心态,决定了他们维护方言的坚定态度:不能在乡亲面前“撇洋腔”。当兵复员回来不讲家乡话,别人就会取笑:“你当了几天兵,舌头就歪了嘛!”撇洋腔、舌头歪了,都是乡亲们十分鄙视的事情。战士孔柱是江苏宿千人,当兵三年后回家探亲,当着乡亲的面说“爸爸,您好”。第二天就传出笑话:“老东家的三小子,才吃了几天皇粮,就学会了一嘴洋话。见了他大,叫什么‘八八拧好。真是要饭的吃糖球——穷酸!”宿千人把变异了的口音,讥为“洋话”。打声、学驴子叫、撇洋腔、舌头歪了、说洋话、不忘祖宗言……,方言土语里的这类词语和民谚,是乡音眷恋最为直观的注脚。
热爱并忠于自己的民族语言、地域或社会方言并竭力加以维护的一種情感和行为,叫语言忠诚。荆永鸣的短篇《口音》,就讲了一个母语忠诚的小故事。一群进京打工的老乡,在“我”开设的小餐馆聚会,酒桌上,刘老乡鄙视林老乡口音变了,竟染上京腔了;林老乡委屈得不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出来还不到一年,要是变了口音,我成了什么鸡巴人了我……”平日里文静礼貌的林老乡,满口粗话,冲着刘老乡大声吼道:“谁再说我口音变了,我操他祖宗!”两人产生了激烈冲突,然而事实上,他俩态度高度一致:口音不能变,对乡音应该怀有无限的忠诚。作者“我”于是深有感触:“乡音是你的根,是你的魂儿啊。人在他乡,还是带着自己的魂儿走吧。出门在外,茫茫人海,有了口音,你就有了标签了。”这标签,就是口音所刻录的文化身份。“You are what you say”,正如雷可夫(Lakoff)所言,你一张口,或许就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作品结尾处,“我”突然觉得,口音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绝不像《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挺微妙的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观念与文化。我甚至想,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还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哩!”[5]言语共同体,又称言语社团或言语社区,指在某种语言运用上持有某种共同准则的人员的集合。口音,当然是一个语音、语调问题,是语言问题。但同时,乡音无改,意味着遵循着某种准则,跟自己的言语社团保持了一致;口音变了,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等内涵已经变了,亦即背叛,走出了自己的言语社团,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不再是原来的自我啦:因而,它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语言是民族形成与存在的重要标志,包含着民族文化的根脉与基因。在外族入侵,侵略者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同化被侵略民族时,语言忠诚表现得异常突出。都德小说《最后一课》就反映了这种热爱祖国,忠于民族语言的深厚情感。小说中韩麦尔先生就是一个对法语抱有语言忠诚的人,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小说动人的语言钥匙之喻告诉人们:语言是民族的生命之根,语言不死,民族不亡!作品表达了在民族危难之际,韩麦尔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悲壮地播种、种子在小弗郎士等心田生根发芽,共同重孕民族希望的爱国主题。小学课本里《难忘的一课》也同样表达了这种爱国情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高雄郊外的一所乡村小学里,听了最难忘的一课:台湾光复后,刚刚实现了语言更换,由日语回归到中文,一位年轻的台湾老师,先用闽南语,然后又用还不太熟练的国语上的一堂课——教孩子们学习祖国的文字“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简短的几个字,包含着“多么强烈的民族精神,多么浓厚的爱国情意啊!”
严格意义上说,母语是人们最早学会的民族语言。因语言有丰富的变体,母语也就对应着不同层级。它最初可能表现为人们出生后,所学会的家乡小地方的土语。无论是打声、学驴子叫,还是舌头歪了、说洋话、口音变了……都是在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的对立中,获得了语言的认同和感情。土语是人们获得的第一张文化标签,是个体告别童蒙、成为智人的标记。随后,人们慢慢成长,活动的范围逐渐变大,于是与更大范围里的人们集合在一起,说一种大致相同的话语,叫方言。方言成为了人们的第二张标签,它是民系身份的一种标记。比方说,广州话就是广府民系的母语。而如果走出方言区或国门,与其他方言区的人或是外族人交往,多使用汉民族共同语言即普通话。普通话同样也是我们的母语,标记着汉民族一员的文化身份。例如1929年,民国功勋蒋作宾在出席国际联盟于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裁军会议上,打破惯例,改用中文发言,为的就是要凸显民族身份,用华语之声向全球庄严传达本族的诉求。虽然事实上,直到1945年汉语才成为了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因此,讨论母语眷恋这个话题,不能只看到土语、方言跟普通话对立的一面,更应看到其统一、融合的另一面:方言土语是普通话的地域变体,同样属于民族语的序列。也就是说,人们对母语的深厚感情,既表现在土语上、也表现在方言上,更是集中表现在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上。
语言教育与言语教育,学习路径恰好相反。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声音形式与意义内容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语言的投射。编码人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就形成言语。简言之,言语就是注入了自我的语言形式。在大学里,一些文科专业开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将语音(物质外壳)、文字(书写符号)、词汇(建筑材料)、语法(结构规律)和修辞(运用技巧)等系统知识一一传授给学生,这是一种语言教学。而在中小学或大学的其他专业中,语文是学生习得民族语言的主要途径。作为学科名称,语文虽然歧义丛生,但无可否认它就是一种言语教育:语文教材所选篇目,均为优秀的言语作品(包括些书面化的口语,如话剧),即为口头语和书面语所表达出来的言语。《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确定了课程的性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一方面,通过一篇篇课文的学习,由点到面逐步获得民族共同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和修辞知识,最终融合成为汉语的语言系统,掌握民族的语言,这表现为语文的工具性,即养成乔姆斯基所谓的能用语言进行表达的抽象的“语言能力”。海然热曾在《语言人》中说:“智人首先是作为语言人,即会讲话的人类出现的。”有了这种能力,个体就长成了智人,与其他动物有了界线。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言说是我们的本性”,有了语言,人即能结成集体,形成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学习语文,接受课文所负载的思想情感,使每个个体传承民族文化、涵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成其思想、情感、性格、品格、意志、审美等等均衡发展,强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这表现为语文的人文性。人文性的获得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由自然的生物人逐渐发展演变成充满人性美的社会人。所以,语文学习,是接受文学、文化、文史、人文,吸收营养,发展精神的学科,是塑造民族未来灵魂的工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语文学科的这种双重属性,与历史上的小学、大学有密切的传承关系。语文课本的篇目,均是言语作品,言语生成就是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表达作者思想和感情的过程。其工具性,指的就是语言文字,历史上曾称为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与训诂学,对应汉字的形、音、义。作为交际工具,语言具有全民性而没有阶级性。人文性來自作品的思想内涵,古时称之为教人“明明德”的大学,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就会带上阶级的色彩。通过学习,发展成为大人,亦即君子。可见,使学生能“明明德”,成为新时代的“君子”,也是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小学依附经学,并不独立,属语文学范畴。所以,直到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前,所有的语言研究都能统称为语文学。
既然中小学的语文学习是一种言语学习,语言感情也就相应表现为语文感情。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及其所记录的文学、文化、文明等的态度评价,叫语文感情。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以及人类优秀先进的文学、文化、文明,怀有深深的热爱之情,是学生们养成语感、学好语文的前提条件。当然,语文感情也常常具体表现为对语文学科、课程、教材乃至老师的情感倾向。
语言感情,是人们非常重视十分关注的高频术语;相反,语文感情,在宽广无比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出现频率却很低,与其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语文教学论文里,“语文”和“感情”同现的两个词,常常根本就不是直接成分。将“语文感情”输入知网或百度,得到的大多是“语文情感教育”、“语文感情朗读”之类的短语,所指多为语文课堂中的情感教育,或者带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而不是特指人们对语文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情愫。因而,在语文教学领域,确立语文感情这个概念,比较它与语言感情的异同,明确其内涵,界定其范围,然后加以推广与使用,显得格外重要而迫切,这将对语文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比方说,语文感情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语言感情,它既包含着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即母语眷恋,也包含着对民族文学(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和民族文化(如《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等篇目)的感情,甚至还包含着对世界优秀先进文化(如外国文学篇目)的态度评价。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情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情感”,说的正是语文感情这个核心问题。诚如教育大家于漪所说:“想学好语文?需要先让孩子对语文有感情。”[6]语文感情,也叫语文情感,它是语文素养的核心内涵。欧运波认为:“学生的语文素养包括语文情感、语文习惯、语文积累、语文技能、语文知识等内容。如果要对语文素养的内容进行排序的话,排在第一的应该是语文情感,学生喜欢不喜欢语文,热爱不热爱语文,痴迷不痴迷语文,是衡量学生语文素养高低的首要标志。语文情感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条件。学生对语文有感情了,就会积极地进行语文积累,主动地去建构语文知识,进而形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掌握应有的语文技能。”[7]两位语文大师,都特别强调了语文感情,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母语教育是每一个国家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工程,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石。语文养成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情感。从孩子启蒙开始就着力培养他们热爱母语的情感,让孩子真正在血液里、骨子里爱母语,爱语文,这实在是每位语文人应有的责任。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首先应该是个语文情感丰富的人,是母语的坚定的维护者,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吸引着孩子热爱语文;反之,异化的语文教学,却“构成了对学生与语文之间的纯洁感情的伤害”[8]。
语文感情,一半天成,一半養成。感情的培养,现阶段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兴趣的激发与养成。这远远不够,要培养学生深厚的语文感情,首先要让学生慢慢体会和感受到,语言与个体、与民系、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使学生能产生学好语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张丽均老师所强调的那样:“语文是一种宗教”,它是唯一直接指向“人”的学科。同时,对母语的深厚感情,是每一个个体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愫,带有遗传机制的特征。《口音》中的两位老乡,作为社会的底层,对语言忠诚尚有如此强烈的自觉,这正说明语言感情有自然获得性与天然遗传性。民族共同语,是最高层级的母语,如何引导学生将人类普遍存在的母语眷恋这类情感,转化为对语文的热爱,养成深厚的语文感情,进而形成忠于并维护民族共同语的自觉和自律,这是语文人面临的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现阶段,对语文感情展开理论研讨,加深社会对语文感情的认知,由此形成正面的舆论导向,给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推动语文教学向前发展,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冯广艺.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J].语言研究,2013(2).
[2]王希杰.语言感情和语言歧视[J].语文建设,1993(3).
[3]罗康宁.客家人不忘祖宗言探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1).
[4]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74.
[5]荆永鸣.口音[J].十月,2003(3).
[6]于漪.想学好语文?需要先让孩子对语文有感情[OL].http://www.sohu.com.2017-08-24.
[7]欧运波.如何培养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感情[J].新教育时代,2016(26).
[8]钟世华.谁在伤害学生与语文的纯洁感情[J].语文建设,2013(10).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