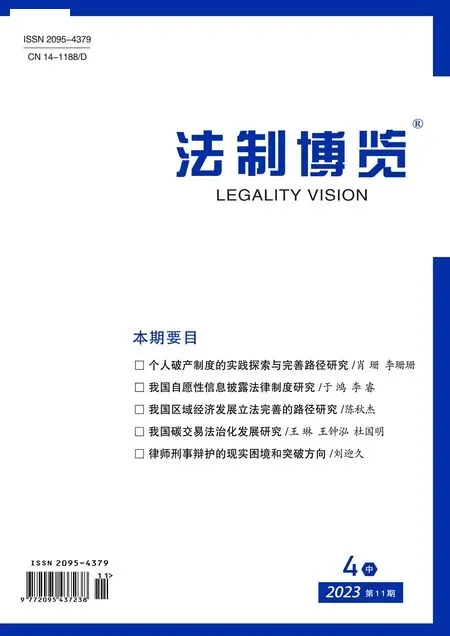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路径研究
刘嘉裕
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检察院,福建 福州 350200
一、问题提出
近几年,我国画圈掀起了一股探索人工智能工具化使用的热潮,而国外也早已用人工智能创作出完整漫画、制作出游戏角色等并投入使用。如日本有团队运用人工智能“复活”漫画之神手冢治虫,通过模仿手冢治虫漫画框架思路、画风创作出一部新漫画作品《斐多》。这里的《斐多》,便是具体的人工智能创作物。
人工能创作物,亦可被称为人工智能创造物、人工智能生成物,是部分学者在探讨人工智能形成的内容是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保护时提出的。当前学界不少学者探讨我国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问题,观点不一。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归人工智能投资者所有,原因是它有利于作品的发展和繁荣;[1]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属于使用者,并将版权视为使用者根据销售合同取得的成果;[2]也有学者认为由设计者享有著作权权益更有利于传播和提高社会文化福祉。[3]众说纷纭,观点不一。
同时我国有关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仍处空白。司法实践中,2019 年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中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该案判决从“著作权主体必须是自然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认为自然人创作完成应该是著作权法判定相关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客体的必要条件,不应对民事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而2020 年,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从“原告内容包含了著作权客体应具备的两个属性”的角度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为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认定用技术生成的内容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且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由此可见,我国司法实践出现没有法律依据而导致同类案件释法不一的问题。因此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以及何种保护路径,仍待研究。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性
(一)现实需要:顺应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趋势
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交易需要,创建了知识产权制度。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们也日渐改变生活理念和法律需求,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逆不可转的时代潮流,因此人工智能创作物在今后将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是在著作权领域,一方面作品的创作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在传播作品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就难免会有免费复制他人作品的情况出现。如果立法缺失、法律空白,将纵容他人恶意或不当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物;二是当人工智能创作物与自然人作品客观上难以明显区分时,人工智能创作物因其零成本而被优先选择。这不仅损害自然人合法权益和打击创作积极性,而且如果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无法受法律保护,将极大降低人工智能研发热情,不利于有关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同时也影响著作权制度发展,这与繁荣社会文化事业相悖。综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作为新技术顺应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已经无法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及时给予法律保护,鼓励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发展。
(二)利益平衡需要:协调分配各方权益
利益平衡是我国《著作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人工智能创作物争议问题本质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在个人利益方面,研发者、投资者、使用者三者开发成本共同构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预估值,但这三者资产、价值占比难以明确。如果缺少《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在利益分成时容易产生分歧。在公共利益方面,得益于《著作权法》保护,前期文化市场可以保持长期稳定,成果也因著作权保护在市场流通赋值。但由于人工智能作品没有得到保护,各方的平衡被打破,没有得到保护的高质量人工智能作品将被免费使用,传统作品的市场平衡将被打破。长久来看,文化市场平衡被打破,人们生产作品积极性被打压,传统作品将因没有市场需求而被淘汰。
(三)独创性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符合独创性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是独立和创造性的。独立指的是单独完成创作,并且不存在侵权行为;创造性指的是作品并不是由已有模式生成。作品中应倾注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形成智慧结晶。人工智能创作物中一方面凝结了人工智能编程人员的智慧结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创作物可能基于模仿人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模式,能够使用独特技术形成有明显特点的作品,因此可以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符合创造性。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著作权性证成
(一)传统著作权归属理论的审视
著作权传统理论上归属于作者。大陆法系中著作权意为作者权,是作者人格的外延。[4]《德国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的前提是个人精神创造,作者的合法权益通过著作权得到保护。[5]即不承认法人为著作权主体。《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将作者权解释为一种知识、精神和财产特征。我国同样在《著作权法》中规定自然人为作品创作者。在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中,以版权对应著作权,不同的是,版权倾向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在《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规定对作品的保护是基于维护作者的利益。综上可见,各国明确规定著作权保护主体为作者,即进行创作的自然人。
在现有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情感和意志的表达环节,缺乏人类生物属性。根据传统的民法二元论,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物为人所用。假设将人工智能赋予法律人格,对传统民法理论和著作权理论而言是突破,是人工智能对著作权主体提出的挑战。因此,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人应当是创作自然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著作权涉及的争议主要有设计者和使用者两方。主张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使用者的观点认为设计者具有创造意图并进行了精神创作,符合著作权对作者的定义。但是一方面这会导致设计者双重获利问题,通常情况下设计者已享受计算机软件的私权保护,如果将创作物著作权归属设计者,设计者就享有两份权利。另一方面,如果设计者享有对创作物的著作权,基于权利保护,使用者的后续使用行为应支付许可费用,这将一定程度上打击使用者对人工智能使用的兴趣和热情,这不利于作品的产生和传播。相比之下,将著作权归属使用者更具合理性。一方面,从创作过程来看,使用者与人工智能的创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6]另一方面,使用者是作者,可以充分激发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热情,这有利于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不断良性循环,充分保障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认定
按照《著作权法》要求,判定是否为作品的标准为是否具有独创性。对独创性的解释,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强调作者原创并且要求情感表达;另一种观点从作品角度认定,认为属于独立创作和创造性表达即构成作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大多从两个方面进行掌握:一是独立创作,这是首要要求。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著作权法》保护个人的智力劳动成果,将智力劳动视为人格延伸过程,维护作者权益以维护公平;二是可以体现创意的个性化表达,即创造性,在表达上不同于公有领域,满足了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要求。
人工智能创作物可否认定为作品,参照传统著作权作品认定标准,应是人工智能创作物具备独创性。从独创性两个要求出发,第一,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实质是独立系统的运行编辑,通过自主选择、优化革新等方式创作表达,此创作符合独创性的独立创作要件;在一些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环境感知和随机运行方式对元素创新生成有差异性的新创作物,亦符合独立创作要件。第二,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发展,高科技带动数据处理、内容运用跃上新台阶,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自主操作,独立创作具有个性化表达、差异性的作品。综上所述,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备独创性,应当结合独立创作和创造性的要求,认定具备独创性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享有与自然人创作的同样作品权益。
四、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选择
(一)确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赋权理念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出现对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新挑战,一定程度上要求加强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约束,并在充分考虑创作物的构成、内容等基础上,结合《著作权法》宗旨,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具备独创性,以此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
(二)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
目前,我国尚未明确规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学术界对具体归属仍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应属于人工智能设计者,理由是人工智能进行创造性活动原因是设计者的编程,包括编辑代码、发出指令等直至生成作品,是核心算法执行创造出人工智能创作物,属于人类创造。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创作的本质是人机合作的智力成果。然而,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工智能设计者享有著作权,市场化程度就会降低,这将削弱研发的积极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应属于拟制法律人格,即人工智能本身。但这忽视了人工智能承担责任的有限性,一旦创作物出现问题产生不良影响则缺少责任主体承担风险。
通过以上两个观点,可以发现将人工智能创作物归属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或实际使用者更符合著作权理论和实践的要求。并且究其本质,最终归属问题是财产利益的归属。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所有者对创作物没有精神上的投入利益,只有获得经济效益的目标。如果所有者或实际使用者拥有著作权,那么将带来更多的财产利益,提高人工智能创作的市场价值,人工智能设计者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将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综上,应明确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或实际使用者享有著作权,并将著作权分配给人工智能所有者,不仅可以促进作品的研究开发和传播,而且可以达到鼓励著作权制度的目的,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规律,从而完善著作权保护制度。
(三)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具备独创性
目前反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物是算法、模板等的结果,不能反映作者的独特个性。但是,人工智能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结果内容,这些符合人工智能本身的独创性和自主性,甚至超出了设计者的涉及范围。
独创性是判断是否为作品的核心要素。作品可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独创性要求。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同的操作时间创建出不同的个性内容。人工智能创作物不仅是人工智能的产物,而且不同于人类大脑的智能成果。它们是由人工智能产生的,也就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他们的创造力表明,世界的智力成果不同于大脑的智力成果,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因此,人工智能的创作物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和自主性。这有利于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文化的多样性,鼓励设计者研发人工智能,创作原创作品,利用人工智能创作作品。
五、结语
确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在于激励创作、创新以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和幸福感。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在高科技发展下衍生的成果,如何选择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路径,不仅需要事实和逻辑判断,还需要价值赋值。纵观眼下,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作者权体系和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版权体系,均界定著作权的制度价值为促进社会文化、科学艺术繁荣发展。如今,科学技术不断完善,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创作物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传统作品。现有的《著作权法》不能契合地区分人工智能创作物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一味排斥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将会影响社会文化传播和发展,这有悖于著作权制度价值。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属、独创性判断、创作过程等问题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研究的核心。我国应综合人工智能创作物特征和著作权法制度价值,尝试构筑完善顺应时代发展的著作权法体系。从长远来看,将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将独立创作和创造性结合起来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能够有效解决纠纷、保障合法权益、平衡各方利益,具有可行性。
时代在不断前进发展,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不断发展,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有关研究远未结束,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保护、著作权判断、著作权归属等问题仍待研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