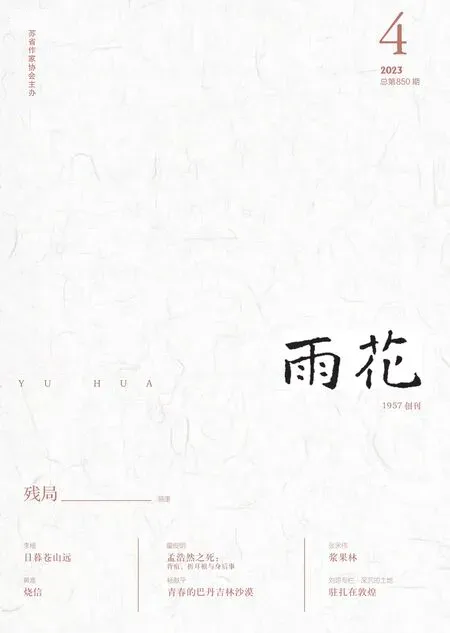驻扎在敦煌
刘 琼
全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玉米种子,都出自河西走廊。
黄河上游的流域面积要占整个黄河流域面积总量的一半以上。黄河上游,河水清澈,含沙量极少。黄河是在流经黄土高原之后,从中游开始成为“黄”河的。黄河上游水质虽然好,但附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基本上都是依赖祁连山的冰雪融水。一方面是因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之故,另一方面也与这段黄河的特点有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从青海出发,经川北,到达甘肃境内时,正处于巨大的“几”字型左下那一撇逐渐向北转弯处,属于黄河上游的峡谷段:河道比降大,水流湍急。这个特点适合建水力发电站。上游峡谷段也是黄河流域水电站的重要基地,比如位于永靖炳灵寺旁边的刘家峡水库。“天下黄河富宁夏”,整个六月,真正能利用黄河水进行灌溉业生产的,只有位于“几”字型最平缓地段的宁夏和河套平原。宁夏也因此有“塞上江南”之誉,宁夏出产的大米曾一度与天津“小站米”媲美。
而河西走廊上绿洲的水源,基本上来自南边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了疏勒河等水系,这些水系覆盖了整个绿洲。比如,玉门、瓜州、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水系,张掖、高台、酒泉平原大部分属黑河水系,小部分属北大河水系,而武威、民勤平原则属石羊河水系。在武威、永昌等地出土了大量石磨、石铲等农业工具,在民乐灰山遗址还发现了碳化的小麦、大麦、高粱等种子……这些考古发掘表明,河西走廊灌溉水源稳定、光热资源充足、土地面积开阔,定居农业等生产活动在四五千年前就开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处于中国西北角、依靠灌溉发展农业生产的河西走廊,一直都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虽然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水源涵养和利用控制,河西走廊绿洲农业不再占优势,但制种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河西走廊被称为“河西走廊绿洲”,并非夸张之类修辞手法。从高空俯瞰,在广大灰黄的戈壁滩上,一条绿意葱茏的廊道从西到东,持续不断。黄河虽然就在不远处,但此时的黄河还处于清澈的幼年时期,再往下走,到了中游,逐渐丰沛起来,成为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的重要灌溉水源。唐代诗人李白有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天山”即指祁连山。从祁连山发源的河流往下形成了石羊河、黑河、北大河、疏勒河和党河等五条水系。绿意开始浓郁并形成规模的地方是绿洲,绿洲附近必定会有河流。沿着河流开垦绿洲,河流断了,绿洲也散了。在依靠采集和渔猎维持基本生存的人类早期,“逐水草而居”的习惯颠扑不破—今天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大片绿洲出现的地方,人烟开始密集,城市出现了。河西四郡作为河西走廊上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既是汉唐时期的边防要道,也是当时大一统国家的经济特区,活跃、热闹、繁华,许多历史的传奇曾经在此上演。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此处的“雪山”即指祁连山。“祁连”在匈奴语里,是“天山”之意,祁连山也称南山、雪山、白山等。雪山和白山之名,盖因祁连山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是名副其实的雪山。冷湿气候有利于牧草生长,在海拔两千八百米以上的地带,分布有大片草原,为发展牧业提供了良好场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首叫《匈奴歌》的两汉时期的诗歌,是匈奴失去祁连山和焉支山后所作。大约五六年前去张掖,张掖古时曾叫甘州,甘肃的“甘”从此而来。张掖,除了丹霞地貌和闹市区的大佛寺,让我记挂了很久的是马蹄寺。它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境内。马蹄寺悬挂在百丈悬崖上,拾阶攀爬中,停顿休息,往远处看了一眼,亮晶晶的雪山就在对面,中间隔着水洗般青翠的碧草,雪白的羊群点缀其间,半天才移动一下。张掖借弱水之力,“一行小麦一行玉米”,孕育出无数“吨粮田”,不仅黄河流域常见的粮食品种,比如高粱、玉米这里有,黄河流域不常见的粮食品种,比如水稻,这里也有。“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信然。八月末,我在张掖的甘州区乌江镇看到了曾以为只有江南才有的水稻和烟波浩渺的淡水湖面。张掖在黑河中游。把张掖滋养成“江南”的黑河,古称弱水,也称合黎水、鲜水、张掖水、甘州水。这些个名字,每一个都让我浮想联翩。去马蹄寺的路上,走着走着,路过一条清浅幽静的小河,岸边恣意地生长着红柳。司机师傅调皮地问:“知道吗?这就是弱水。”我有点猝不及防,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这条叫“弱水”的河流由来已久,《水经注》《山海经》均有记载。“昆仑之北有水,其力不能胜芥,故名弱水”,以草芥之轻类比弱水之弱。“大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此处的流沙,就是《西游记》里天蓬元帅的主场,“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从“弱水之渊”,流出“弱水三千”,从甘州张掖穿过,一路奔流向西,到内蒙变成额济纳河,最后在居延海消失。额济纳是西夏语,即“黑水”。
古有弱水是客观事实,虽然“其力不能胜芥”,但弱水泛滥乃可怖之事。黄河和长江这两条长河,经历几千公里的千转万转到达中下游时,或河床上升,或因降水量激增,改道、决堤,给两岸生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灾难。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在黄河上游附近的黑水治水属于罕见,除了见诸文字记录,也曾被竖碑立传。《新修张掖县志·地理志》:“张掖在洪水时代,完全围以大湖,弱水泛滥其中,各水、泉水悉固注之,无所谓大陆也。禹导弱水至于合黎,居民始有耕地。”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有两类人物常常被推举为部落和族群的首领。一类是身强力大者,他们在渔猎和采摘果实时收获多;一类是有治水之能之功者。前一类好理解,身强力大,才能带领大家战胜外力和环境,从自然界获取更多食物。后一类也好理解。当人类从采摘狩猎以获取食物的简单劳动进化到相对复杂的种植业、畜牧业时,水既是生命个体的生存要素,也是农牧灌溉业的重要依托。所以,古籍中记载的水,往往是“神”,如河神、东海龙王。水是生产生存之本,干旱缺水,生产难以为继,“逐水草而居”是迫不得已。水泛滥,洪涝灾害也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时候就产生了各种治水故事。善于治水者,就是当时的时代英雄,比如大禹。
大西北地广人稀,进入河西走廊尤甚。
酒泉是距离敦煌最近的城市,记得从敦煌开车到酒泉,总共四百公里,大约走了五个小时。天高地阔,宽宽敞敞,祁连山在南。向东看,不远处是黄河的上游,即将进入峡谷段。沿途,大片大片的荒漠,除了三三两两奔跑着的车辆,人类活动的显著信息比如农田、房屋,似乎只有阶段性零星分布。
早年读书时,始终搞不清敦煌和酒泉的隶属关系。查找过一些资料,各有说法。比如成书于东汉建初时期的《汉书》距离前朝不到两百年,按说最有权威,遗憾的是,对西汉设置河西四郡这一政治大事,《汉书》虽有记录,但在后人看来这么大的事,不同章节说法已经严重不一致。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是在元狩二年设立酒泉郡、武威郡,元鼎六年设立张掖郡、敦煌郡。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则是西汉于太初元年设立酒泉郡与张掖郡,太初四年设立武威郡,十三年之后又设立敦煌郡。还有一个说法,认为西汉只设置酒泉、敦煌、张掖三郡,并未专设武威郡。这个说法今天的信众也不少。历史的魅力,可能就在于种种悬而难决的疑问。搁置争议不论,根据已知说法,至少有两点基本可以肯定:一是敦煌与酒泉曾经“分而治之”,敦煌被酒泉代管是后来的事;二是在河西走廊上设郡,酒泉是首例。酒泉,又称肃州,甘肃的“肃”即由此而来,酒泉的区域位置优势可证。冷兵器时代,修筑城墙以抵挡外敌,是人类能够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在汉王朝统治者看来,河西不保,江山难安。因此,号称“万里长城”的汉长城是从今天的平壤南部一直修到敦煌以西,用夯土、砂石等筑城,由烽燧、古堡、亭障等组成防御工事,在各枢纽建立要塞,驻扎装备弩机的骑兵巡逻,屯田、养马,“肃靖宁边”。
敦煌和酒泉分治,是西汉中央政府组织有生力量抗击长期在边境骚扰滋事的匈奴等北方强悍民族取得实效之后的事了。为了巩固边防成果,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郡,至少从形制上,把敦煌与酒泉并置、分治。分而治之,设置两个要塞,相当于在边境加编了一道针脚细密的守备力量。分而治之的做法是从酒泉西部拿出一部分土地和人口,划拨给敦煌。敦煌者,盛大之意也。历史上的敦煌,因在甘肃、青海和新疆的交接处,成为“华戎交汇之第一所”。河西走廊“置四郡,列两关”的两关—阳关和玉门关,都在敦煌地界。敦煌战略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
由于中原移民增多,加上流经酒泉的北大河、红水河、疏勒河等南北河道稳定,周边绿洲寥廓,农业生产状况不错,酒泉作为一个城市,人口繁衍数量和区域分布都达到一定规模,具备分流条件。酒泉比敦煌幸运,汉唐乃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人口繁盛,工农业生产基础扎实,甚至成为周边卫星城市的中心,包括代管敦煌。
敦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唐以后,敦煌开始衰落,到了明代,已经退化成单一的边防哨所,人口急剧减少,也不再具备一个完整城市的规制。敦煌衰落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战乱。唐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再度冲击边境,敦煌先后被吐蕃、西夏占领,成为前方战场,河西走廊作为西域与中原的商贸之路因此中断。与此同时,南方海上商贸发展起来,逐渐取代陆地丝绸之路的一些功能。元代,敦煌重归中央政权,西部商贸活动一度试图复兴,敦煌也逐渐有点人气。明代朱氏父子执掌朝政,对西北实行“闭关”政策,将防守重点放在嘉峪关,在嘉峪关以西设立关西七卫,不仅停止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就连莫高窟也基本停止建设。敦煌由此沦为纯军事的边防。公元1524 年,明嘉靖王朝时期,彻底封锁嘉峪关,将嘉峪关以西平民全部迁到关内。关外的敦煌,自此成了“风波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直到清雍正三年,在敦煌重设行政机构,并从关内迁来大量兵民屯兵屯田,发展农业。十年之后,也就是雍正末年,敦煌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十万余亩。
河西四郡的设立,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郡制起源于春秋战国,最终成型和成熟,还是秦汉时期。西汉中央政府在张骞率部打败匈奴余部后,“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实之”。这些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被动移民,移民对象大多是家境穷困潦倒者或犯法犯错被充军发配者,“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西四郡的人口数曾经达到七万多户,总计二十八万多人,主要成分是从关内迁徙而来的汉人。这些汉人在原籍都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农民的特点是趋于稳定和保守。这些因为种种原因被“等而下之”的人,到了边关后,获得新生活,“谷入米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人稀,水草以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这种人与地互促的前后变化,是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力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孟子的“人之初性本恶”论的一种辩驳。
河西走廊设置四郡后,大批次汉人由南而北迁入,不仅丰富了河西走廊的人口成分,最重要的是,向西与天山以南的农业生产方式呼应,形成一条稳固的农业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在改变河西走廊传统畜牧生产方式的同时,客观上形成“防火墙”,有机地隔断了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联络以及向南部不断骚扰侵犯的可能性。曾经战火连天、战马嘶嘶的河西走廊,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引入和发展,粮食供应稳定,农副产品供应丰富。这块土地逐渐有了人气、烟火和商旅活动,很快发展成为一条东西方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往来的交通要津。
以敦煌为例,敦煌设郡后,首先是移民屯垦戍边,在长城以北开垦大片农业区,当时常住人口达一万一千多户近四万人,逐渐成为多民族聚集、商旅往来的重要驿站。
唐宋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文化繁荣,有赖于两汉以来河西走廊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昌盛、积累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兴盛,河西走廊在进行商贸活动的同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对话之地。唐宋以后,商贸活动停止,边关关闭,但当时从朝廷到民间盛行学佛,一些宗教人士比如玄奘,从敦煌玉门关偷渡出境,到印度本土学佛取经,之后又经河西走廊回长安,到内地传教送经。来来往往中,许多僧人经过河西走廊,在此休息,甚至就驻扎下来,开凿石窟、修建寺庙、颂经念佛。从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一路向东,是酒泉的大法幢寺、雷音寺,张掖的大佛寺、马蹄寺,武威泾川大云寺、海藏寺、鸠摩罗什寺,等等。继续往东,还可以看到临夏炳灵寺、天水麦积山。“数不胜数”一词用在此处,再恰当不过了。数量多还不算什么,河西走廊的这些石窟寺庙迥异于内地习见,虽然当时建造它们存在宗教用途,但对于后世之人,它们个个都是瑰丽雄奇的艺术宝库:从雕塑到建筑,从色彩到造型,从艺术虚构到真实记录,望之兴叹,望尘莫及。莫高窟当然是其中最珍贵的那颗明珠。河西走廊既是佛教由西至东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路径,也是佛教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沃土。从东晋开始,敦煌城东南二十五公里处,大泉河谷里开凿了一百多个石窟,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境内的瓜州,与白居易笔下的“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瓜洲古渡同音。取名瓜州,顾名思义,有瓜果的绿洲。河西走廊光照强,昼夜温差大,只要有灌溉水源就能种植瓜果。如果对石窟壁画艺术感兴趣,看完莫高窟,再坐一个多小时车,就到了瓜州。榆林窟和锁阳城都在瓜州。与莫高窟近在咫尺的榆林窟某种程度上被公众低估,其内藏石窟艺术与莫高窟可以“互文”对照。古老的锁阳城现在基本消失了,被传说夸大的一些说法也无法考证。锁阳城和瓜州的最后消失,与河流的改道、干枯有关。有绿洲,就会有人类聚集,出现村庄和城市。河流改道,绿洲也会改道。河流干涸,村庄和城市也会慢慢消失。楼兰、高昌这些古城的消亡,除了战争产生人口折损,也是由于风沙蔓延、水源消失之故。流经敦煌的河流,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党河。它是敦煌的母亲河,属于疏勒河水系。党河还在蜿蜒流淌,瓜州已成往事。几年前的夏天,参加作家叶舟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精装本出版座谈会时顺访瓜州。戈壁荒滩,土筑的高台上竖块界碑,写有“瓜州”二字,徒增怀古之思。
比较而言,位于敦煌东面的酒泉,虽然更接近内地,感觉上却更加遥远。最早对酒泉有一点具体的印象,始自某年中秋。中秋假期过后,好朋友从酒泉家中带回一方沙丘石送我。这方被自然界冲刷出许多沟壑的沙丘石,线条圆润,造型优美,侧平面还埋伏着数条隐而不发的骨棱,像特级车工手下的杰作,却是“天工”。从西到东、从南到北,这块来自酒泉戈壁滩的石头,一直搁在我的书案上。我的这位学生时期的密友,学的是现代物理,“军二代”,虽为女性,却有豪侠之气。三十多年过去了,毕业之后,她仿佛一滴水,消失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记忆中曾经那么清晰美丽的眉眼,如今想起来,也都渐渐地模糊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河西走廊的边贸活动虽然停止,商人足迹减少,但文化的魅影自此降临。
《史记·高祖本纪》里,在汉高祖刘邦生病乃至驾崩这一节,有两处写到燕王卢绾。一是“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另一是“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卢绾叛逃到匈奴,为后来西汉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边境问题埋下伏笔。这是河西走廊设郡开市的前事。
——酒泉晋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