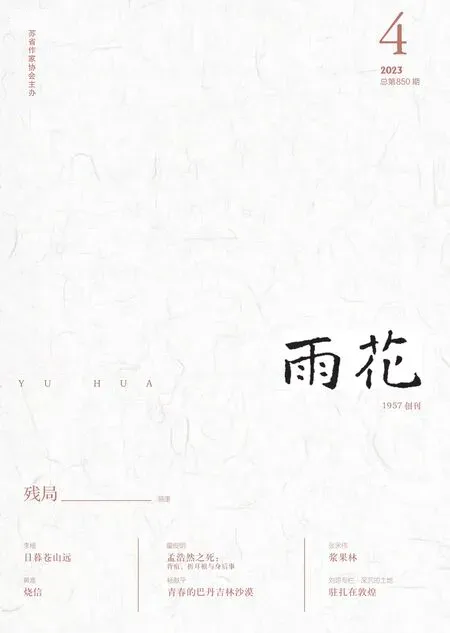去鳗鱼口
小托夫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开着货车在路上跑。有个小伙子站在路边冲我摆手,他想搭我的车。我把车靠路边停下。“上来吧,”我说,“去哪儿?”他踩着脚蹬子爬上来坐到副驾上,关上车门时说:“去鳗鱼口。”我说:“顺路。”从这里到鳗鱼口,大概要五个小时。我是到鳗鱼口送一批货,我觉得路上有个人聊聊天很是不赖,要不我就只能不停地嚼槟榔,听相声或者评书。
“你到鳗鱼口做什么?”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是到鳗鱼口送货。鳗鱼口不产鳗鱼,只产冷水鱼。我不知道为何那地方叫鳗鱼口,我搞不明白那地方跟鳗鱼有什么关系。有次有个人告诉我,给那地方命名的是个打南方来的,爱吃鳗鱼。但我送的货不是鳗鱼。
“我想去鳗鱼口看看。”他把背包放到脚旁,扣上安全带。“我不知道我要去看什么。但就是想去那儿看一看。”
我说:“你不会是以为那儿的鳗鱼做得不错吧?”
他说:“不会,我知道那儿没有鳗鱼。这个我知道。”
我把车重新启动了。“现在不一样了,那地方去年开了一家鳗鱼餐馆,在鳗鱼的吃法上有独门绝技。生意不坏。”
“你尝过?”他问我。
“是的。”我说。我接下他递过来的万宝路香烟,然后点上。老实说,我不爱抽外烟,抽不习惯。他也抽烟,他把车窗摇得更低了,可能嫌烟雾散得太慢。我接着说:“有些游客到了那儿,也会去尝尝。怎么说也到了鳗鱼口了嘛。”我私以为那家馆子大概是从地名上嗅到的商机。
他说:“你车上拉的不会就是鳗鱼吧?”
我说:“不是。”
我想他是不是闻到什么腥味了。我拉的是些别的,是冷冻鸡。其实我不爱干这个工作,完全是为了糊口。我有个女儿寄养在她姑姑那儿,我需要为她挣点钱,不然我不会干这个工作的。之前我跟伙伴合伙开了个客栈,但把钱都赔光了。客栈开在景区,那景区内陆陆续续进驻了太多客栈,同行间倾轧严重,最后搞得大家都没钱赚。我有时候想当动画片编剧,亲自给我女儿编一部,有一天指着电视机一板一眼地告诉她,这是你爸爸编的。想来这多好啊。—但我只是想想。
我告诉小伙子:“是些冷冻鸡,开膛破肚了,毛也退光了。”
他说:“噢。”
他看上去只有二十三四岁,我问他是不是属狗,他说是,他果真比我小了一轮。他穿着破了皮的夹克衫,戴着帽沿略微发白的黑色渔夫帽,脚上是双破旧的浅灰色运动鞋,脏兮兮的鞋带缠成了死结。身材中等偏瘦,相貌普普通通,鼻梁稍稍有点歪斜,颧骨处有点点雀斑,那双单眼皮的眼睛总是向下斜瞟,不大与人对视。“你是哪里人?”他说了个地名,那地方我还从来没去过,可也没少听说过。“那挺远的,”我说,“你跑那么远就为了到鳗鱼口看一看吗?”
他说,“不。在那儿住上一天,还要去下一个地方。”
我说:“那我明白了,你是在搭车旅行。”
他说:“你说对了。”
一阵感觉上有些漫长的静默。期间只听到货车行驶在公路上发出的那种听腻的咔咔嚓嚓声。他不再说什么,那样子好像是把应尽的义务尽到了。说完即止。再多说下去,就不那么情愿了。他将头倚靠在窗框上,垂着眼皮,香烟噙在嘴里,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雾飘到帽檐下熏到眼睛,也不太在意,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多余的动作都没有。可以说是纹丝不动。他那顶渔夫帽下的面部表情显得十分消沉呆板,眼神也很呆滞,愣愣地盯着自己的膝盖发呆。膝盖处的工装裤上有一块灰扑扑的油污和几眼破洞。他整个人看起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还夹带着忧伤和颓废的气息。他不想多说话,想必也与此相关。
他不想说话但我想说话,这是我带上他的主要原因。我们之间隐隐有着这种层面的冲突和矛盾:一来我想说话,二来我好奇他是怎么了。我想搞清楚他是怎么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我开口说话了。我问他:“是不是有心事?”
他把头呆板地摇了一摇,我还是时不时地看他一眼,让他感觉我还在等着他的回复。我料定不管如何他都得回复,不管回复什么。别忘了他是在我车上,他在搭我的车,我有权利随时随地停车让他和他的背包从车里下去。虽然我很少会这么做。想来只有过一次,那家伙堪称一代屁王,自从上车就响屁连连,我得把车窗一直开着,而且得开得很大才行,但是那又是冬天,这地带零下十来度,还飘着雪,再加上车速带起来的风和自然界的风混作一团一股脑涌进来,人体所感受到的温度就更低更低了。我简直冻得要命,手都要握不稳方向盘了。我感觉自己光着身子被扔到南极去了。我一路咬牙切齿坚持着,同时又不得不听着他为了缓和气氛硬生生编造出来的笑话。路边旅馆的招牌一现身我就把他撂下了。
小伙子果然开口了:“你看出来我有心事?”
我说:“一看就能看出来,不一样的。以前搭我车的人,性格一般都很开朗,也就是很放得开,不然怎么好意思去搭车?他们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一坐下就天南海北东扯西扯一通胡侃,有的边说还边往肚里灌酒,甚至忍不住还要亮一嗓子。说是在KTV 里不好意思唱,在这嘛谁也听不到,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五音不全跑调跑完也不要紧。虽然说也遇到过腼腆的,但也不至于像你这样,你现在的状态可不像出来旅行的人应该有的。何况你还是搭车旅行。所以我说你有心事,你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瞅我一眼,把手伸到车窗外弹弹烟灰:“被你看出来了。”听到他这么说,我想我是猜对了。但是,他仍旧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他越是如此,我就越想知道他是到底被怎么了,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等着,直到等得不耐烦了。我说:“有些东西憋在心里不见得多好,说出来的话多少会好点。”
他说:“你真想知道?”
我按了四五下喇叭,告诉前面那辆这地方很常见的十三米长的半挂车我要超车,让它别再像白菜叶子里的绿虫子似的随便乱扭动。“嗯,”我说,“多少想知道点。”我怕这家伙随便拿件事出来搪塞我,就又给他来点心理暗示。“你把我当树洞就行。梁朝伟还需要个树洞呢,看过那部电影吧?你把我当成你的树洞就行了。尽管放心,我干涉不了你的生活。你下车后咱们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了。这个你应该也清楚吧?”
或许是我的心理暗示奏效了,也或许他本来就想说了。总之,他说了出来。说出来之前,他还有些动作,这番动作代表了他最后的犹豫。做完这些动作他就一下大开金口了。就好像太阳冲破了山的遮挡,一下子放射出万道霞光。所以也不能对他的动作视而不见。他的动作大致如下:将香烟再次伸到窗外弹弹,弹到一半,发现只剩烟蒂,烟丝部分已经悉数燃尽,于是,重新点上一根,猛抽两口,放在嘴边叼着,笔直倚靠在座椅上,闭上双眼,又睁开,然后又闭上,其间双手十指交叉握着,搁在腿上。“他们甩下了我。”他说。他的语气听来平淡无奇,可我愣是从中听出了些许失落。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本身的含义令我产生了相关的错觉。只此一句,他只放出了这一句,但我知道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我要做的只是似有若无地引导他把事情讲出来。
“他们是谁?”
“一起出来旅行的伙伴。”他望着前挡风,从中可以看到萧瑟荒凉的大地和戈壁滩上遍布的褐色岩石,还有一条笔直无尽的公路。“他们甩下我走了。”
“为什么?”他们定然不会无缘无故甩下他。
“是这样,”他顿了顿,像是嗓子眼被东西卡住了,蠕动喉结干咽一两下。“我梦游把他们吓到了。”
“就为着这个?”
“对,我想没有别的原因了。”
“你们一共几个人?”
“算上我是四个人。”
“他们跟你是什么关系?”
“是在一家青旅认识的,都是出来旅行的,之前谁都不认识谁。为节省开支我们合伙包了辆车。”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三个撇下你开车走了?”
“是啊。”
“就是因为你梦游?”
“嗯。”
这可真是个倒霉的小伙子,因为梦游而被同伴们抛下了。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怜悯,感同身受般的怜悯,好像我就是他,我经历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不快,我被那几个家伙无情地抛下了。这种程度的怜悯不是随时随地随随便便就能产生的,一次,一个家伙跟我讲他跟妻子婚姻破碎的悲剧,他讲得情真意切潸然泪下,甚至嚎啕大哭,我则继续开着车无动于衷,我没有对他产生应有的同情,更别说怜悯了。我只是从置物台上的纸盒里抽出几片纸巾让他把眼泪揩干净,我所做的只有这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对他的故事产生共鸣,按理说我应该共鸣才是,怎么着我跟他一样都有那么一段失败的婚姻。
“你是怎么梦游的?”
我太想知道他是怎么梦游的了!我把手插进衣兜摸出一根瘪烟,填在嘴里把它点着,我想好好听他怎么说。我记得点烟时我的手微微抖了两下,不得不说这暴露出我多少有点兴奋。其实说白了,何止有点兴奋,我简直感觉到心里万马奔腾。虽然不难从新闻上读到有关梦游症的报道,以及各类奇奇怪怪的梦游方式,但是在生活中我还从没有遇到梦游的人—或许遇到过,只是我不知情罢了。我没想在这个的秋末的下午,在这片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的戈壁滩上,在我百无聊赖地沿着漫漫长路跑运输的途中,遇到了这个小伙子,这个有着特别遭遇的小伙子。
“我们开着车出发后,”小伙子开始坦露事情的缘由,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我差不多始终保持着侧耳倾听的姿态,极少发言。“第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我下床在房间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们中有个人被我吵醒了,迷迷糊糊地睁着眼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看着我,是后来他自己说的。他说见我游魂野鬼似的走来走去,他一下就没睡意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还感到很害怕,他不敢叫醒我,把另外两个叫醒了。当晚我们住的是客栈的四人间,两个上下铺的床。我睡在其中一个上铺。他们醒来后,就一起坐在那儿看着我。看着我时而走在黑影里,时而走在打窗棂那儿照进来的月光下,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脸色被月光照得苍白。另一个睡在上铺的就大着胆子喊我名字,一连几声喊不醒我。其中一个就说,打开灯!另一个睡得离灯近,抬手就把灯打开了。灯亮后,他们就不怕了。又喊几声,还是没喊醒我,就走过来把我拍醒了。我对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他们说,你经常这样吗?我说,我不知道。据我所知那是第一次,到底是不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没叫醒我没发现我,我走累了就躺回床上继续睡了?我不知道。”
“又一个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起来撒尿,发现我的床铺空了,也就是我没在床铺上睡着,他以为我在厕所里,就等着我出来,不知等了多久始终不见我出来,他就推门去了厕所,我不在里面。他把另外两个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不见了。他们都很纳闷,因为前一晚见到我梦游了,所以他们判断我应该梦游着从房间里走出去了。一检查门锁,发现门只是虚掩着,并没有闩上。他们想看看我去哪儿了,穿上衣服到处找我。客栈里每个可以藏人的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其中有个人望着院门说,八成出去了。一检查院门,院门也是虚掩的,也没有闩上。他们就打着手电筒出去找我,外面是乌漆麻黑的荒山野岭,想找个人可太难了,他们只找了一小时不到,就回来了。那天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了。要不是他们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出去了。凌晨四点一刻,我推开房间的门,径直朝自己的床铺走去,我抓着扶手踩着脚蹬爬到上铺若无其事地躺了下来。他们那天晚上整宿都没有睡好觉,觉得我像个游荡的幽灵一样神出鬼没,太吓人了。
“为了防范起见,再到晚上时他们就提议说要把我的手脚捆住,以防我再梦游吓人。我其实不想同意,一想到被人捆住手脚扔在床上那类画面,就让我有一种深受侮辱的感觉,并且也睡不舒畅,试想你的手脚被人用绳子捆住,动也不好动,翻个身抓个痒都成问题,你能睡得舒畅吗?但为了安抚他们,让他们睡觉时不再提心吊胆,我只得同意了。”
听到此处我忍不住插嘴说:“为什么他们还让你跟他们睡一间房?”他们既然害怕,就应该让他单独开间房睡才对。
“那天我们没有睡在房间里,我们是在湖边露营。那个地方太好了,白天可以看湖水,晚上可以看星星,清晨和傍晚都可以看到日照金山。我们到那时已经傍晚,所以就想在那里住上一晚。我们各睡各的帐篷,但是他们害怕我晚上跑到他们帐篷里去吓到他们,就提议把我的手脚捆住。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篝火旁喝完最后一瓶酒后,有个人打了呵欠,说不早了,该睡觉了,明天还得早点起来看日照金山呢!另一个人拿出绳子对我说,走吧,去你帐篷。他钻到我的帐篷里把我捆住了。另外两个人进来检查了一下,然后他们很放心地去睡了。他们睡了安稳的一觉。到了清早,其中一个人先起的床,他刚扯开帐篷,就发现帐篷外满地都是鱼,都是硬邦邦的死鱼,鱼眼发白,鱼鳞干枯。他套件衣服从帐篷里跑出来,伸着食指边走边大致数了一数,大大小小足有几十条之多。真是咄咄怪事啊!他嘴里念叨着走到另外两个人的帐篷边,先后把他们喊醒了。他喊他们时我也被吵醒了。我也从帐篷里走出来了。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谁给你解开的?然后他们又互相去看对方,他看他,他看他,他又看他,他们全都摇着头说,别看我,不是我。他们又一起看向我,问道,谁给你解开的?我也像他们那样摇头,我说,我不知道。
“鱼哪来的?他们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觉得地上的死鱼应该与我有关,但是又没有确凿的依据。他们昨晚都睡得太死了,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们根据之前发生的事情,又根据我手脚的绳子被解开了,就怀疑是我干的。他们进而又怀疑,我是在装作梦游,其实是成心在作弄他们。他们很生气,一个个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盯着我。正当他们为这件事气急败坏时,其中有个人突然大喊了一句,糟了!我们的车呢?
“我们的车不见了。那辆汽车原本停在我们帐篷附近,现在四处都看不到它了。另一个人跑到帐篷里拎着裤子出来,他挥着裤子说,车钥匙也不见了,我本来把它放在这个裤兜里的。他们分头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我也去找了,也没有找到。他们把责任归咎于我,说我偷了那辆车,要我交出来。我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啊!他们说我说谎,说我没有老实交代。我说我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我要是知道什么我就说了,我是真不知道。有个人上来踹我一脚,说,就是你搞的鬼,整天装神弄鬼的,就是你干的。另外两个也上来踢我,一脚又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又接着踢。他们踢累了,手撑在膝盖上弯下腰喘着气说,听着,那辆车是你偷走的,跟我们几个无关,到时给老板赔钱,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出的!然后我又听到有人说,真是倒霉透了,出来旅个行还他妈要赔辆车!听到这句话时我手还抱在头上,蜷着身子躺在草地上。”
“那辆车后来找到没?”
“找到了。他们打完我,歇了一阵儿,情绪也慢慢稳定下来了。他们中有个人对另外两个人说,八成他昨晚又梦游了,把车开到哪儿去了。咱们不如去找找看,说不定还能找到。另外两个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点头同意再次去找。他们就又带上我一起去找车了。他们试图让我回忆我昨晚都到过哪儿,我说,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们走到那条南北走向的公路上,分作两队分头去找,一队往南一队往北。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拦路搭车。这样比走着快多了。车子是另外一队找到的,他们在十多公里外的公路上发现了那辆车,钥匙也在车上。他们绕着车子检查一遍,发现完好无损,坐在车上拧动钥匙也能打着火,后备箱里的物品也一样没少。于是他们开着车来接我和另外那个同伴,我们又一起回到湖边把帐篷装到车上。但是他们不愿带上我了。他们不想接下来的行程里再出什么差错。当天中午,我们在路边餐馆吃午饭,吃罢饭,我们每人又喝了几瓶汽水,我问他们要不要去个厕所,他们说不去,我就自己去了。当我从厕所里出来时,他们连人带车都没了。”
小伙子讲完后,我也终于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抛下他了。他们抛下他这件事,从道义上来说虽然不应该,但也情有可原。就和我那次把那个一路响屁的家伙半途抛下一个道理。怎么说呢,毕竟不是谁都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这种情况的。
“那么,车是不是你开到公路上去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
“那你现在,去鳗鱼口,”我说,“是在继续自己的旅行吗?”
“不,我这是在回去。”他说,“其实鳗鱼口我已经去过了。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我现在是在回去的路上。你这是我搭的第三辆车,是今天的第二辆,上午我还搭了一辆。我从没搭过车,但现在我不搭车就没办法了。我得回去。这边连汽车站都没有见到。”
“鳗鱼口有汽车站。”
“是的,所以我要到鳗鱼口去。我知道过了鳗鱼口,再过了羚羊镇,就有个火车站。我要到那儿去乘火车。”
“你放弃自己的旅行了?不多玩几天了?”
“我现在哪还有心情去玩!”
如果有谁遇到了跟他一样的遭遇,十有八九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就是没有玩的心情了。我相当同情他。也深为理解他。他还那么小,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小弟弟,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坐在副驾上低头抠着裤子上的破洞,要不是开着车不方便,我真想好好拥抱他一番。我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真的想带他坐到酒馆里好好聊聊,好好喝上一顿。要是现在路边就有酒馆的话,我会毫不犹豫把车停下。耽误了送货也算不了什么,比起我跟小伙子的相遇来,那能算得了什么?屁都不算!
“现在你好受点没?心情好些没?”我想问的是,他把事情讲出来后,对着我这么一个树洞讲出来后,有没有那么点效果。
“好点了。”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说真的还是只是在敷衍我。我无法确断定这一点,我个人偏向于他说的是真心话。也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好受点了。
虽然他没再说什么,可我越来越激动了,越想越激动。我把着方向盘的手和踩着油门的脚都不那么稳准了,车也就被我开得忽快忽慢,一晃一晃的。对于自己无法把控的情绪,我一点招儿都没有。我动了真情实意,直直望着他说:“小伙子,说真的,我真是想狠狠地拥抱你一下。”我的声音里肯定充满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小伙子那双闪动着特殊眼神的双眼朝我盯来,他的身子动了动往车窗那边靠了靠。我猜他误会我的意思了。不过说真的,如果真的是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对他做点什么,估计他也一点招儿都没有,除了跑,还是跑。我是真想拥抱他,没有任何不良的想法,只是出于感同身受和真真切切的同情怜悯,当然还有还有,那就是,他跟我一样,都是同一类人,说白了,我们都梦游。
“小伙子,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说,“坦白说,我有着跟你相同的遭遇,我也梦游。”
“你也梦游?”小伙子瞪大双眼。他不再紧张了。我看出来了。他更想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是的。”我说。
第一次知道自己梦游是在跟妻子结婚三年后。“那天晚上睡下不久,”我对小伙子说,“我披件衣服起床,踩着软底拖鞋,径直来到厨房,翻出一块牛肉和一把水芹。我把水芹切成段,把肉片成片,往锅里添勺油,放入生姜丝、胡椒、蒜瓣儿,就开始炒了。等妻子被厨房里的动静惊醒时,我已经把一道水芹炒肉炒好盛盘了。她从卧室走出来时我正双手端着这盘菜规规矩矩地往饭桌上放。我妻子说,大半夜你干什么呢?你饿了?我不吭一声,你知道吗,我转个身又去厨房拿筷子,看也没看她一眼。妻子更大声地说,你干什么呢?倒是说话啊!这时我醒了,我看着手中的筷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手里拿着筷子。”
“你直接在厨房里做了道菜?”小伙子忍不住笑了。这还是他第一次笑,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咧得很大。
我说:“谁也别说谁,就像你,把车开到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撂在那儿,自己走回来。还有那一地死鱼是怎么搞的?”
他说:“别问我,鱼的事我真不知道。车的事我也完全不知道。说是我开的,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说:“要是没被我妻子看到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一道菜。”
他说:“你认为那些鱼是哪来的?”
我说:“这个可不好猜测。但我觉得应该跟你有关。”
他说:“我让它们从湖里跳出来,它们就傻乎乎地跳出来了?”
我说:“也有可能是你到湖里抓的?”
他说:“我怎么抓,徒手抓吗?可我根本就不会游泳啊!”
我说:“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他说:“还是说说你吧,后来你又梦游没?”
“梦游了,”我回忆着对他说,“那次之后,大概又过去一个月吧,我又半夜去了厨房,从冰箱的冷藏室拿出一条鳜鱼,放在案板上,使着菜刀“咔咔咔”地剁。这次我连厨房的灯都没开,这次,我在月光下剁一条鱼。”
“这次你可能想做条鱼吧?”
“不,我没有做鱼。”我说,“我只是剁它,把它剁碎,仅仅如此。”
“只是剁?”
“对,没有别的。”
“那挺奇怪的。”
“是的,我妻子因为这件事受不了我了。她不久就跟我离婚了,她说她怕我杀了她,就像剁那条鳜鱼一样。她说从新闻上看到过了,有个美国男人梦游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她说她一想到我也梦游,就害怕得整宿睡不好。其实,”我对小伙子说,“在她发现我梦游之前,我就发现了她有相好的,只是我没说出来罢了。我从头到尾都没说出来。她现在也不知道我知道她背着我干的事儿。她把孩子撇下走了。她不想养我们的孩子,她想跟那个相好的再生一个。虽然她没这么对我说,但我是能感觉得到。”
“她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
“现在你还梦游吗?”
“不知道,”我对小伙子说,“现在我是一个人住的。”我还真是不知道。
“我突然想撒泡尿。”小伙子说。
我说:“走,一块吧。”
我们相继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戈壁滩上。一片萧瑟荒凉的大地。
晚上八点半,我们到了鳗鱼口。
我把货车开到那家闪烁着霓虹灯牌的鳗鱼馆门口停下,准备带小伙子尝尝鳗鱼口的鳗鱼。我们肩并着肩就像友谊深厚的把兄弟一样走进馆子,异口同声地对迎面走来的那个风韵犹存的老板娘说:“来条鳗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