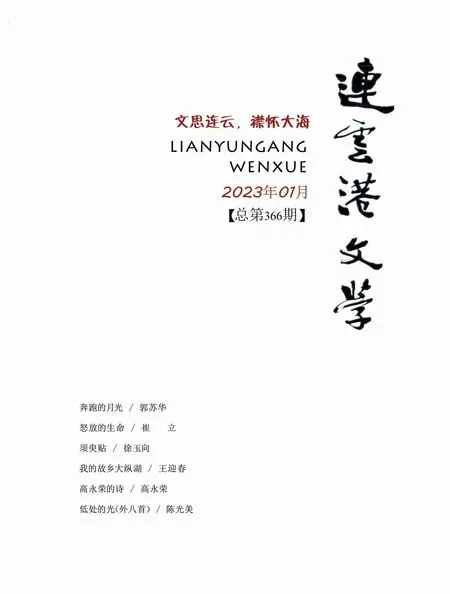我的故乡大纵湖
王迎春
我的故乡在大纵湖,老家就在湖边的村庄——北宋庄。
北宋庄,在多少年前的哪一天诞生,不得而知,但我能清晰地勾勒出我爷爷从兴化一路飘摇过来的情形。
大纵湖,不只是湖
年少时,父亲就曾经讲过,若有机会,三件事值得去做:一是在平原上堆一座哪怕不是十分高大的山;二是造一条通向远方的高等级的马路;三是下大力气开挖一条彰显里下河特色的河道。这与现代化的梦想似乎离得太远,堆山、筑路、治水,都是祖祖辈辈农耕情结、文人寄情山水观念的映照,既过了自己豪情满怀的瘾,也为这方水土留下一抹痕迹。
事实上,现实中这样的机会与我的梦想相去甚远。家乡的湖、河、道,而今皆呈现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美,特别是这方湖,已然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一座美丽自在且富有诗意灵气的东方水城,流连于此,养身、养气、养心,这必然归功于更有情怀值得致敬的主事者。而我想到的是办报办刊,办一份我自己理想中的报纸和杂志。
《大纵湖》杂志,便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场约会。
没有深尝办杂志的艰辛时,我对一本杂志之于一座城市的潜移默化而深远悠久的影响,早从《读者》杂志之于兰州身上有了某种感知。很多读者并未到过兰州却对这座城市充满好感,多是因为《读者》杂志温暖而人性的光芒。在兰州有读者大道、读者出版集团。一本杂志与一座城市共生共荣,提高了城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造就了一段佳话。
盐都人杰地灵,自古文人荟萃。把《大纵湖》杂志办成一本立足盐都、面向省内外,致力于涵养盐都文脉、提升特色品牌、滋润读者心灵、扶掖后起之秀,以文学艺术为主、兼具人文特质的文化综合期刊,并极力彰显独特的文学性、乡土性和实用性,这是传承地域文化,繁荣一方文艺,亦关涉乡土、时代、生存和风俗等方面的一个深刻命题。
我们瞄着《读者》的高度去办《大纵湖》杂志,眼高手低某种意义上说一点都不是缺点。在诸多方面的关心支持下,《大纵湖》——无须盛装,无须张扬,也无须鞭炮和礼花,只是迈着稳健的脚步,低调而又自信地走下“流水线”,摆上我们的案头,至今已经是第三十五期了。
杂志,一定是“杂”而有“志”。对于一本杂志来说,“杂”指的是用细分栏目来吸引更多数量的读者和潜在受众群体,而“志”才是一本杂志的灵魂所在。《大纵湖》杂志根植盐都大地,她必然透着这方水土的自然芬芳,她必然是为这方水土上的人状物言情,她必然是真善美的旗帜,她必然透着包容开放温润人性的湿地之美、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我们正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迈进,一期比一期接近。
崇尚软实力的时代,文化就是最大的实力。转念一想,只要是能为盐都文化建设添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只要是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盐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益于盐都外塑形象和内聚力量,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大纵湖》杂志何尝不是耸立在平原上的山,流淌在乡间的河,铺展在大地上的道。于我则是圆梦,于我们的内心则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大纵湖,不只是湖!大纵湖既是初心、使命、责任,更是岁月、自在、美好。
丁马港
丁马港村位于盐都楼王镇的西北,离大纵湖十华里左右,和一般的乡村民居不同,这里的民居有不少是建于清末时期的。
其实我幼时生长成长的杨港庄,与丁马港近在咫尺,一个水系,同属一方水土,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纯属一个模样。车停在村口的一片空地上,向南径直走20 米距离,迈上明显高出的平地,一米宽却十分悠长的丁马港小街就呈现在前面。小街更像是一个个小胡同,没有城市的繁华,市井也有些凋敝,街边的店面往往和住家连在一起。走进一家住户,77 岁的朱大爷热情地迎了出来,带领我们参观自家的老宅。朱大爷说,他家的房子建了起码有100 多年了,为了保留以前的风格,没有对房子进行大的装修。朱大爷还说,村里一二百年的老房子多呢,与他家连着的一户房子就建了有约200 年光景了。
看着朱家的房子,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古朴,虽年代久远,房梁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但房梁的五柱还是很坚固,牢牢支撑着整座房子。地上铺的都是青砖,既防滑又美观。在屋内,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铁环状的东西,显得很是突兀,询问之下才得知,这是过去为防土匪用的,一旦有土匪来,村民就把大门关上,插上门栓,最后再用两个铁环把门加固。站在天井里,就能看到封火墙,既有防火功能,又彰显大户人家的气派。在村里,这样的房子还真不少,房子的整体构造和建筑细节,处处都有讲究。砖木结构的楼房,分上下两层,有些是阁楼式建筑,木质楼梯通往阁楼,阁楼顶上还有窗户。
村里几位老人介绍,明代洪武年间,一批人从苏州阊门来到千户沟,也就是现在丁马港再向西的一块洼地,插草为标,原先这里叫定马,因为马车到这里就走不进去了,只能把马拴在柱子上,即把马定在这里,时间长了,就传成了丁马,后来逐渐形成了丁马港镇。过去村里有四大家族,分别姓顾、凌、姚、陈。顾家是地主出身,田多,放租;凌家经商;姚家开船厂;陈家是书香门第。四大家族中又以顾姓族人最多,据说顾家以前可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村里原来的2 间串街楼都是他家所有。一位顾姓的顾灿芝大爷介绍,2 间串街楼是9 进建筑,是一个叫顾黑宝的人家建的,传说房连房,廊连廊,除了天井,不见天日。小楼目前还剩一栋,位于小街东西向巷子里。这座两上两下的小楼,看上去基本上还是完好的,雕花的窗户,屋檐的防水檐,墙上的铁圈,带有青苔的砖墙,无不诉说着岁月的久远。
绕过一个杂货店,村里人说,前面就是两间串街楼的最后一栋,原先的主人叫顾宛清,在老人去世后,儿女都到城里寻发展,宅子就破败荒废了。不过做工典雅的古宅,还是让我们窥见一丝昔日的风韵。院子里铺的是一色的小青砖,前庭的雕花格扇门有近四米高,还有门槛,想来当年很是气派。走进宅内,虽然有一角屋顶已然塌陷,但绛红色的房梁没有大的损坏,支撑着飞檐高脊的屋面。在锅灶的旁边,支着一把破落的摇桨的橹,证明这里水乡的繁华。谈起这个古宅,村里几位老人都很是惋惜,说这里的木头都是铁梨木,是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才有能力置办的,就这样毁了太可惜了。在一片荒芜中,依稀能辨别出客厅、厨房等,墙面、横梁都有浮雕纹饰,十分精致。
丁马港西面通兴化,北面接建湖,南面连宝应,过去学校、商店、邮局、粮店等设施齐全,且水运十分发达,滨海、阜宁一带水产品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几十年前,这里不少的人家早上四五点钟起,挑着鱼虾到盐城鱼市口,早市后,又回到家中做中饭。
今天的丁马港村,是2001 年2 月由丁马、丁西、水产三个村合并成的,在作物种植的同时,有水产养殖面积300 亩,主要养鱼虾之类的水产,还包括甲鱼等特种水产养殖300 亩。另外,还做些砂石运输的行当。小街上有老人做鞋子,是那种老式用锥子、鞋楦的布鞋,也有过去老灶蒸馒头的店铺,以及理发店,还有人家提供租被子的服务,两元一条,供家里来客的村民租用。
在和村里人交谈的过程中,老一辈的村民希望能修整这些古建筑,恢复老街的风采。如何保护好乡村的一些古村落、古建筑,发挥应有的地理、人文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可喜的是,2020 年春,江苏认定并公布了首批107 个省级传统村落,丁马港村丁马位列其中。
时光在这里雕刻着一切,从丁马回大纵湖,一路上风轻云淡水茫茫。今天盐城东向出海,自古就是西乡出彩。大纵湖和丁马港一样,散发着更加蓬勃迷人的魅力。
大纵湖的西瓜
大纵湖的西瓜一般都不长在大田里。你看,高高的圩堤上那个巍然耸立的瓜棚,在阳光下格外令人生畏,绿油油的瓜秧下,星星点点大小不一的西瓜一下子填满了少年所有的想象。
童年的西瓜,少年印象最深的还不是生活中真实的西瓜,而是银幕上的。记得电影《小兵张嘎》,路边一堆青皮西瓜,旁边那个胖翻译官双手捧着一个硕大的西瓜,吃一半,撂一半,啃得满脸瓜汁,让人在痛恨胖翻译官的同时,好不眼馋嘴馋那西瓜,简直垂涎欲滴。童年时每看一遍《小兵张嘎》,就似饱餐了一顿甜甜的西瓜。《小兵张嘎》是黑白电影,但直到现在脑海里存留的不是斗争的残酷,却是那西瓜诱人的色彩——青皮花纹,乌籽红瓤。
西瓜在少年的心目中神圣高贵。大纵湖大堤瓜农的女儿就更感水灵,瓜贩的千金更感金贵。班上那个姓杨的女同学家里长瓜,少年就认定她是学校最洋气的孩子,这没办法。邻人啖瓜,便神不做主般过去相食,实在执拗不过少年的馋样,这时候递上薄薄一片瓜的那个主家,就是少年心目中的菩萨,一辈子感恩不尽,那一片甜甜回忆弥足珍贵。
偶见一空地,少年直呼:这地方种上西瓜多好啊。曾经多少次向校长建议:操场的空地上应该种西瓜。每年都央求父母:咱家也腾出一块责任田种上西瓜吧。爷爷总是笑着说:口粮都留不足,西瓜能当饭吃啊?!少年不理解,怎么也不理解:吃饱西瓜就不吃饭,还不行吗?!想想现在的孩子,在琳琅满目的水果堆里,西瓜在他们心目中不仅大众而且土气。
少年对西瓜的特殊情结解不开。就是现在,走在小区的花园里,仍不由感慨:一半长花供观赏,一半种西瓜享口福,那该多好。闲来,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圆,信笔而来,看着纸上的圈就如一只只秀色可餐的西瓜。每每少年的家人便说:你这是得了西瓜综合征。唉,这其实是童年嘴馋落下的病根,根本无良药根治。
那时候少年西瓜见得不多,吃得更少。在大纵湖畔的村庄上,花钱买西瓜吃的机会真的很少。买一只大西瓜,觉得挺奢侈的,也为难父母。但买一次,吃一回西瓜,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从瓜摊上或瓜船上左挑右拣一只西瓜,兄弟们抢着往回搬,生怕半路上有个闪失,弟抱一段路,哥再抱过桥,一段一段的,像是接力赛。对了,如奥运火炬接力,捧着西瓜的少年此时就是一个光荣的火炬手,引得路边的一群看客们不是欢呼,却是眼馋,有些怕半路上有人出来抢断,兄弟们就这样一路虔诚地抱回一只大大的西瓜。
把西瓜护送回家,清水洗净,猴急猴急地一刀下去,随着一声清脆悦耳的咔嚓声,瓜一分为二;再一刀下去,二分为四,再一刀,三分为六,一刀又一刀,西瓜被劈成一道道细细的弯月,人手一片分而食之。那就叫爽啊,一口又一口,不到青皮哪肯罢休。那时候的西瓜计量单位除了只,用得最多的应该是片,摊头上除了论只卖,还有论片卖,大片1 元,小片5 毛。这是多么人性化的销售方式,不知解了多少买不起整瓜人的馋呢。按片卖的西瓜一定比论只卖的珍贵可口,容易让人记得住。
贫穷饥馑的年代,卖瓜者的智慧、邻人递片瓜的淳厚,在少年记忆中是一道令人满足而又绚烂的风景,和美丽的大纵湖一样,在少年心中成为一种永恒。
大纵湖的夏日
都说是苦夏,孩子多半是没有苦夏这个概念的,盛夏是大纵湖孩子奢侈的盛宴。
在大纵湖,再漫长的暑假也好混,混得大汗淋漓,混得痛快淋漓。在大纵湖,每一个暑天更多是泡在水里的,河水里、雨水里、露水里、汗水里……最迷恋出没在芦荡里,最惬意埋伏在棉花和西瓜套种的大田里,最憧憬垂钓在鱼塘边,最刺激莫过于在杨港闸口逆流而上,最惊险还是在排涝站下口摸鱼。湖畔,那一片生机盎然的野地处处有孩子们玩闹的身影。以至东东上个星期偶然到城南某个小区转悠,竟然被纯原生态的景观吸引了,那不就是大纵湖杨格港的野外吗?东东决定在此买房,因为东东找到了童年的梦想和根。什么户型不户型的,从前杨格港砖墙草盖的低矮房子还不一样住人?!
东东对大纵湖最美好的回忆都在夏天。偶尔起个大早跟大奶奶一起下棉花田,说是除草打公枝抹碎芽,其实田里长着小瓜、番茄等吃物才是东东真正向往的。东东饿着肚皮走过清晨的田间,钻进迷人的青纱帐,沾上满身的露水,在这里都能找到填饱肚子的食物,一条带毛的黄瓜,或是一只清脆的菜瓜。走进庄稼地,东东没有一次是空肚而归的。
晌午的时光是百无聊赖的。一觉睡到太阳八丈高,兴许是让肚子饿醒了,桌上盆里凉凉的稀饭,省了碗具,搬起来便喝个底朝天。坐在阴凉处闲着也是闲着,顺手帮奶奶剥起蚕豆米子,剥到半碗够一顿冬瓜汤便罢手,坐久了也没了精气神。
见奶奶要到河边淘米,东东顺势从奶奶手里抢过淘米篮子,直奔东头大河边。一条米把长的挑板码头,与乡村所有的大小河流一样,河水清澈见底,顺着淘米水的米香,成群的鱼儿聚集过来,闹腾起阵阵水花,东东眼馋得很,脱下小裤头藏匿在桥下墙洞里,跳下河,与鱼儿同嬉起来,乐得忘归。半个小时过去,不见人和米的小脚奶奶便颤巍巍地赶到河边。
“你个细猴子,管不住你,明天让你老子把你带上街去。”奶奶把东东叫上岸,直往家撵。东东竟也忘了是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
丝瓜架吊瓜藤搭起的凉棚下,东东躺在小木桌上,听知了鸣叫,数头顶大小不一的丝瓜吊瓜,瘪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想到昨日棉田摘得的几只青番茄,一骨碌爬起来,跑进厨房,不等洗净便啃起来,三下五除二就下肚了,舒坦!
邻里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凑到一起玩几把扑克牌,扑克牌一律玩得皱巴巴、脏兮兮的。少年游戏就如夏日的天,说变就变,玩得好好的,说不准为一张牌就闹得不欢而散,厉害些互打得死活不依。不长记性,过不了几日,便又玩耍在一起了。
不一会儿,正午的上空便弥漫着阵阵人间烟火和饭菜的幽香。丝瓜汤,青椒炒丝瓜皮,炒自己昨天挖的螺。冬瓜汤,炒冬瓜皮,小葱炖蛋,还有番茄蛋汤,炒韭菜,炒茄子,饭锅头上炖茄子,这样的菜蔬就是暑期的下饭菜肴了,典型地道的里下河农家风味。这便是东东童年大纵湖生活最原始的底色,直到今天,这样自然纯美的记忆仍常常让东东感怀。那天盐城工学院陆庆龙教授画展上几幅故乡背景的画让东东深深感动,教授的画不张扬无半点雕饰之感,纯粹的原汁原味,一下子击中东东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就是存放童年故乡的味蕾。
中饭过后,大纵湖的狗热得吐着舌头喘着粗气,蹲在大树下打盹,而这时候大纵湖孩子就属于河水了,一泡就是半天。浪里白条,在水里玩捉迷藏,在高桥上跳水,有柴油机船经过,往翻滚起的水花里扎猛子最刺激最令人兴奋了。那年,一位少年玩伴就因为玩过了头,不小心钻进船肚里再也没有出来,等捞上来便断了气。少年父母肝肠寸断的哭声感染了邻近的村庄,都在悲伤着这个夭折的少年。因为有了这样痛楚的教训,大人孩子多了一份警惕,这个暑期的后半程,整个村庄便再也没有上演过少年溺水身亡的事件。但这样的事件,在乡村直到现在从来都未停止过。
听老人们讲故事,听大人们拉家常,夏日晚夜的时光多半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下河图凉快,晚上火烧心。没有电扇空调,无风的日子,奶奶手不离的芭蕉扇是东东童年最温馨的记忆。还有夏日夜晚那闪闪的萤火虫,照亮了乡村少年的童年梦想。其实现在想来,夏日里手持一把芭蕉扇真正是一种优雅的文化,一种文明。
进入8 月,离9 月1 日正式开学的日子渐近了,一天,两天,时光过得陡然快速起来。东东一天天掰着手指头,惶惶然。湖荡里杨格港的孩子们,哪个愿意进学校的笼子?二十天,十五天,十天,九、八、七、六、五、四……小东东就欣喜地发现,七月大、八月大是老祖宗给我等顽童的恩赐,没有日子可捱了,才定下心来把未完成的暑假作业补上。
盛夏收场,墙头上的丝瓜、扁豆快下架,地头的芋头、山芋也可以刨了,杨格港的暑假时光就这样几乎在自由散漫、无拘无束中一天一天过去,天渐次添了些许凉意,等小裤头换成长裤长褂,9 月1 日开学的日子也到了,东东开始了新一个学年。从9 月1 日始,就是收获的秋了,对于读书的孩子,学业年轮里又升了一级。
一壶老酒大纵湖
城市是村庄的天空,从村庄出来的人是天上的星星么。小时候我就认为城里的二姑奶奶是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她不只是星星,二姑分明就是我们的太阳。小学读完便离开了大纵湖畔的村庄,一晃荡,举家进城整整30 年过去了,渐行渐远的村庄成了城市里的我时常仰望的天空。
一岁一枯荣。30 年间,村庄上的人们进进出出生生死死。清明,穿过一处处杂草丛生中的墓穴,默读着墓碑上一个个庄户人的名字,有看到名字脑海里立即闪现出记忆中的那个长者,也有恍惚半晌才把名字和从前的那个人对得上的,更有几个似乎名字很熟但就是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具体的人了。
那年那月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如今他们的名字都镌刻在石碑上,今天无一例外都活灵活现复活在我的记忆里。而村庄正以另一种距离的美呈现在我的眼前。
今天我回到了村庄,回到了旧时光。
从来都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人人都会成为旧时光里的那个人。那天去村庄中心寻访一位长者,探身进屋子,老式宅子里堆着各类杂杂拉拉的旧物,旧书报、老家什、老笔筒、旧藤椅、旧挂历等等,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顿时旧式时光的生活氤氲而来,简朴、安详、优雅、高贵。
老酒,这时候是最有意味的。那天,中饭时分老人非留下我陪他小饮几杯,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弯下身,朝着略显昏暗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带出来的是一瓶不知哪年的老酒了。看那已然斑驳的招牌,我一眼认出就是我童年在乡下曾经见过的“大肚子”洋河,飞天敦煌图案虽已不再鲜艳,仍一下子勾起了我陈年往事的怀想,这陈年的老酒啊,还有身边从旧时光里走来的老人呢。
大纵湖的曾经岁月在这里变成了经年陈酿,我怎舍得打开?但又忍不住品味一口的冲动,拧开经久岁月的瓶塞,顿时满湖酒香,不醉自醉。
又见炊烟升起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听到《又见炊烟》,我内心总会升腾起莫名的感动,一种久违的、沉淀于心中的某种感怀会怦然抒发,难以抑制。
炊烟不在今天的灯红酒绿中,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也许个个会哼唱,但炊烟不是人人意会得了的。炊烟属于乡村,炊烟下站立的是祖母,是外婆,是母亲。炊烟颂歌的是延绵不绝的生命。
故乡在大纵湖畔,在我的印象里最美的是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清晨和黄昏,湖边村庄时常笼罩在薄薄的雾气和淡淡的青烟中,身在其中似曾不觉。从远处归来,对着家的方向望去,由远渐近,看烟气青纱般包裹着老屋、树木,团团不解,是雾、是烟、是气;非雾、非烟、非气,温暖地牵引着归人。那是一幅绝美的水粉画,写意、迷离、真切、变幻,观者沉静坦然,心驰神往。
春来了,农户的瓦屋插着杨柳,远远地看孩子们在湖堤上跑:“开了春,赤脚奔,挑荠菜呀,擢茅针!”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朝他们漫过来!染得他们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沾满了花粉。大人们嗔怪:“看把你们开心的!”孩子们一路笑,又扑向了田野。
村庄上的人越来越少,村庄的点名簿越来越薄。一个个村庄被现代文明蒸发,升华成一幢幢都市楼宇。故乡和炊烟注定被定格在久远的梦中。消失不都总是件坏事。消失有时是一种升华,我有着深刻的感受。
初秋的午后,我站在城南公寓,俯瞰楼房林立的新村,远眺城郊高高矗立的塔吊。看,在水一方——村庄原来的地平线上,定格着新的风景。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炊烟随时可以断,但人间烟火却从来没有消逝过。
大纵湖,既是一处游不尽的湿地公园,也是一壶品不完的文化茗茶,更是一部读不完的文学长卷。她不仅闪烁着千百年来的沧桑和沉浮,更丛生着新春的力量。
我的故乡在大纵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