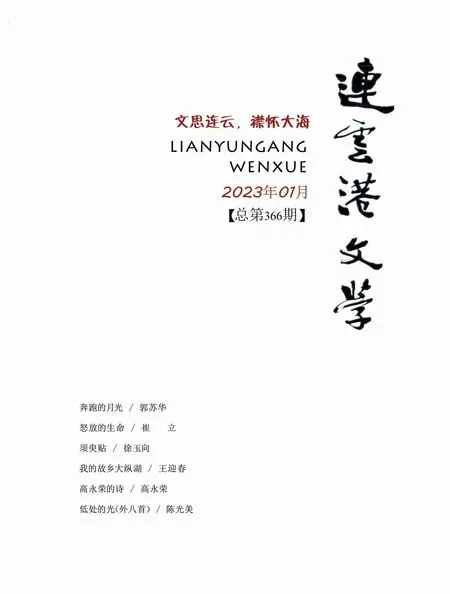野船
倪月友
但凡江河渡口,都有一艘野船,它不会轻易让人看见,徐鬼对我这样说。
徐鬼在阿蓬江边的梯子洞长大,从没去过城市,连县城都没去过。从十六岁开始,他就在梯子洞摇着一艘木船渡来往行人。梯子洞水面平稳,往前往后都有激流险滩和诡异的漩涡。往前的右岸是壁立千仞的鲤鱼岩,白色的崖面被四周葱茏的树林围出一条鲤鱼形状。鲤鱼长约4 千米,宽约1 千米。站在左岸的小店村看鲤鱼,背鳍、尾巴、鱼眼、鱼嘴无不生动,连鱼鳞都很分明。只是鱼鳃上有条绳子穿出来,将鲤鱼牢牢地拴在了一个巨大的石柱上,使它挣脱不得。虽然这条鲤鱼被拴住,但它的神性还在,小店村的村民能通过早雾在鲤鱼上停留的位置判断晴雨,比天气预报还准,你说神不神?
梯子洞上游是阿蓬江湿地公园最美的景段,下游是二十四个望娘滩。传说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变成了龙,沿着这江水去往大海,可是他不舍娘亲,频频回首,每次回头就形成一个险滩。从小店村看,那龙真的栩栩如生,兀立江中的两尊巨石是龙眼,鱼眼后面蜿蜒奔腾的江水就是龙身了,这是一条很有气势的龙,也是一条很悲情的龙。
每次去梯子洞,我都要站在小店村的卡子上静静观赏一会儿望娘滩和鲤鱼岩,由衷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徐鬼只要见到我,就会给我反复讲述鲤鱼岩和望娘滩的传说。他语速缓慢,仿佛每个字都是用力挤出来的。他的每次讲述都一样,连叹词使用的位置和高低都相同。可每次听他讲这两个传说,我都不觉得枯燥。他讲得太感人了,好像他不仅仅是在讲神话故事,而是在进行艺术表演。虽然他没手舞足蹈,但能通过神态、语气和身体语言让人自然联想到。他冷静舒缓的语言就是那样有魔力。这次去小店村找到徐鬼,徐鬼没有讲神话传说,而是讲起了野船。
徐鬼有近四十年没有正儿八经地渡过行人了。因为修酉彭公路时,梯子洞的下游在1987 年架上了石柱门大桥。过河的人基本都从桥上过,没有谁愿意拄着石鼻子下一坡去乘木船过河后,再拄着石鼻子上一坡。从桥上过,不用下一大坡再上一大坡,也不怕涨水了船不敢渡,更不用小心谨慎地喊船家摇船。
渡河的人少了,但徐鬼还是经常到梯子洞的江边看看,看亮花花的阳光从峡谷的高空照下来,铺在碧绿的水面上,看着两岸半没在江水中的奇诡洞穴。想象着这洞穴究竟如何曲折幽深,会通往何处,出口在何处,梯子洞的野船会泊在哪一处洞穴。
梯子洞渡河的人越来越少。岁月荏苒,下梯子洞渡口的大路也越来越荒僻。大路两边的茅草放肆起来,开始向大路侵占,任意倒伏向大路,甚至还在大路中间长出了新芽。徐鬼受不了,仿佛心里也在长荒草。他会情不自禁想起自己摆渡的岁月。
四十年前,从庙溪去苍岭,去酉阳,去岭口都得经过梯子洞渡口,往来的行人多,很热闹。刚刚学摆渡的徐鬼坐在岸边,慢条斯理地裹了旱烟,点燃,衔在嘴里,学着他祖父的样子摇着两片木桨渡人过河。梯子洞渡口在很深的峡谷里,下了船,总得爬两千多米的长坡,上到湘河或者小店。行人们并不消极苦闷,累了就停下来嘶啸两声,声音尖利,在峡谷里撞来撞去,顺着河谷传得老远。一声嘶啸往往会引来两岸行人的跟仿,于是此起彼伏的嘶啸声让野渡热闹起来,撩得林中的猿群在山崖间兴奋地跳跃攀爬,也发出啸厉的啼叫。
徐鬼刚刚掌握木桨,划船运送行人的时候,他爷爷并不放心,抽着旱烟坐在岸边山洞里看着他。爷爷不担心他的水性,他能与险滩拼搏,能在滩上的激流里抓鱼。爷爷是担心他灵机应变的能力,怕他慌张,把一木船的人交待到江里。船上乘客多数是盖上下来的旱鸭子,不识水性,入水就往水底沉,一个人救不过来。在梯子洞渡人过河,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两三分钟就横渡了水面,所以宁愿多几个来回,每船必须少装几人,这是规矩。爷爷只对他说过一次这规矩,他就记得牢牢的,他知道孰轻孰重,有些规矩是半点都不能违背的。爷爷在梯子洞摇船渡人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事。
徐鬼说,他十一岁就晓得梯子洞的江面上有野船,野船神出鬼没,来去无影。掌船的是一位高人,两片木桨横在木船上,高人躺卧船中,木船任意往来,不为风浪和水势所拘,而是随心所欲,想去哪里便去哪里,甚至还能在滩头的浪尖上旋转舞蹈。
那是农历四月间,早晨天气晴好。徐鬼和爷爷在岸边的岩洞里吃了早饭出来,坐在木船上晒太阳。才一支烟工夫,江面雾气蒸腾起来,越来越浓,两边山上也罩了厚重的黑云。阳光消失,到处黑沉沉的,好像立马就要下大雨。徐鬼和爷爷把木船拴在岸边的石鼻上,准备进石洞躲雨。天空已飘起了零星的雨点,江风肆虐,把江两岸的树木荒草摇得前倒后伏,哗啦啦响。
正要进洞,从湘河方向下来一个面若桃花的女子。女子要过河,说是回娘家有急事,希望船家渡她。爷爷仔细打量了那女子,摇摇头说:“江上风大,摇桨危险,船已拴,不再横渡!”那女子不听解释,软磨硬缠,要爷爷将她摇到对岸。她说:“一两分钟就过了江,老船家为什么难?与这渡口打交道几十年,难道还怕这点风浪?”爷爷绷着脸,不理睬她,只顾引着徐鬼往石洞走。大滴大滴的雨点砸下来,接着就是大雨倾盆。他和爷爷躲进了石洞。那女子见说不动爷爷,也不进洞躲雨,转身就往坡上走。爷爷不留她躲躲雨,由她任性。徐鬼看不过去,招呼她留下来躲躲雨,等大雨过去了再走。那美如桃花的女子根本不听他劝,头也不回。透过磅礴的大雨,他看见女子的衣服紧贴着身子,使她更加美丽撩人。很快,她就消失在了雨帘中,没了影儿。
雨点滴落江面,绽开密密麻麻的波纹,波纹间升起乳白的水汽儿。徐鬼问爷爷:“为什么不把女子摇过河?即使摇过河了,大雨也还没下来!”爷爷看了他一眼说:“大风大雨不摇人过河,这是规矩!再说,那女子不一定是要过河,她是故意为难我们!”
徐鬼听了爷爷的话,觉得很难理解,明明人家说要过河,怎么是为难我们?爷爷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继续说起来:“一个人要过河,会选择晴好天气,不是晴好天气,也会选择无风无浪、没涨大水的时间过河,谁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看那女子,面若桃花,美丽得很,却要在风雨中过河,过不了河,也宁愿冒着大雨离开,雨也不躲,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爷爷正说着,一道刺眼的闪电过后,猛烈的炸雷在对面半坡炸响,一棵大杉树被拦腰截断。炸雷让徐鬼和爷爷都沉默了。江面变得诡异起来,白雾纠集在一起到处乱窜。风在暴雨中发出呜呜的声音。爷爷说,每个江河渡口都有一艘野船,它来无影去无踪,那些在风雨中和江水泛滥时要求过河的,都是想去坐野船,坐野船不是为了上岸,而是为了把自己藏起来,让人找不见,去安静的世界洗自己的眼睛和内心,洗尘世遭受的冷漠和辛酸。
江面波涛越发汹涌起来,江面上有一艘鼓满风的白帆船,在浪尖上颠簸,帆与雾融为一体,船舷紧贴水面。爷爷点燃旱烟,吐出一大口浓烟说:“看,梯子洞的野船出来了,出来洗寂寞了!”白帆船顺着望娘滩漂下去,消失不见。很快,天又再次放晴。
我说:“徐鬼,你说野船原来是白色的啊,是不是死亡之船?”
徐鬼说:“乱说,野船不一定是白色的,也不是死亡之船,只是来去无影,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野船。”徐鬼静静地说起了当年他和爷爷的对话。
天晴了,江水依然碧绿,并没涨起来。爷爷说野船的颜色是变幻的,就像一个人的心情一样,不仅颜色是变幻的,就连大小和形状也是不确定的,有时候是帆船,有时候是舢板船,有时候甚至是竹筏或木筏。
“那天是我第一次看见野船,也是我第一次听说野船的诡异和神奇!”徐鬼不疾不徐地说,好像他讲的根本就是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故事。
我问徐鬼:“那艘野船不是沿着望娘滩远去了吗,怎么还会回来?”徐鬼说:“是啊,当时我也这样想,野船不是消失了吗?这渡口应该再也没有野船了啊。”
爷爷看出了徐鬼的疑问,吐出一大口蓝烟,烟像一道墙遮住了他的脸。不要以为野船走了就不再回来,不管野船下没下望娘滩,漂没漂过二十四个望娘滩,它都会回到属于它的渡口。爷爷还告诉他,在梯子洞边消失的人,有可能都坐着野船走了,野船把他们运送到了宁静的地方,又安安静静地回来了。
徐鬼疑惑地望着爷爷,百思不得其解。爷爷说,他曾亲眼看见两个放竹排的年轻人在望娘滩上消失,那是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后来,年轻人的父母们很伤心,请了水尒子沿江打捞了十多天,结果一无所获。爷爷说,那些执着的父母,不晓得这对夫妻是坐野船走了,将不再回来,他们已厌烦或是害怕了俗世的辛劳。爷爷还说,他自己也要哪一天坐着野船离开,去过一段清净日子。
就在石柱门大桥修好的第二年,基本没人乘船渡河后,徐鬼失了摆渡的职业。他只好把木板船用桐油漆过的绳子拴在岸边的石鼻上,把桨搁在船里,落寞地上坡,在小店村耕种土地为业。
爷爷早就不摇桨渡人了,不过每年热天他都要去梯子洞洗澡,顺便摸两条鲤鱼,用野藤穿了提回家。徐鬼的父母经常埋怨爷爷,要他别再下河洗澡,更不要潜水摸鱼,怕他年龄大了出事故。可爷爷根本不听,说他们根本就不懂他和梯子洞的关系,连热天都不下河去洗两把,还不如死了。
徐鬼的父母根本不会水,更不会摇桨摆渡,是十足的旱鸭子,他们怎能体会爷爷和梯子洞的关系呢?徐鬼晓得爷爷不光夏天下河洗澡摸鱼,连冬天也想下河洗澡摸鱼。爷爷天生就是和水融为一体的,他的皮肤硬得发光,肌肉一片一片有序地排列着,简直像鱼鳞!爷爷忍住冬天没下河洗澡摸鱼,真是怕儿子媳妇担心,他必须考虑他们的感受。
徐鬼也想劝爷爷别再下河洗澡摸鱼了,但他说不出口,他知道爷爷要从洗澡摸鱼中找到宁静的快乐。
后来,村子里的年轻人纷纷飞了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挣钱,徐鬼已经结婚生子。很多人都邀徐鬼出去打工,还把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迷人。徐鬼摇摇头说不去,相信在老家也能赚到钱。徐鬼明白,自己不愿出去是惦记梯子洞的那个渡口。即使他现在不再摇着木船渡人过河,也依然忘不了那里。他有事没事要借故到梯子洞的岸边走一走,看看存放在岸上洞穴里的木船。
徐鬼太爱梯子洞了,老是找借口下河脚去。他婆娘心知肚明,却不点破他,怕他落寞,怕他受气。自从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后,除了徐鬼和爷爷,基本没人下过梯子洞河脚了。
徐鬼没想到父母比爷爷先离开人世。爷爷九十多岁了,还耳不聋,眼不花,看上去格外硬朗。人们说老头子不但身体硬,心也硬,儿子儿媳都走了,还没心没肺地活在世上。夏天,九十多岁的爷爷依然要到梯子洞河脚洗澡和潜水摸鱼。有了鱼,他不与徐鬼搭伙,独自用柴火烧一锅鲜鱼汤,倒二两白酒看着橘红的夕晖不言不语地慢饮慢酌。徐鬼和媳妇都想劝爷爷别再下河洗澡摸鱼,要喝鱼汤,徐鬼下河去捞。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都知道劝也是白劝,爷爷会坚持我行我素。
“江河边的人是不是都知道每个渡口都有一艘野船?”我问徐鬼。
“不,不是,我们周围几个寨子就只有我和爷爷知道,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有一次,我问父亲听没听说过野船。父亲说从没听说过。母亲就更不用说了,她是大盖上嫁过来的,从小离江河远得很,哪晓得野船呢!”徐鬼点了根毛草烟,悠悠地吐了口蓝烟说。
听爷爷讲野船后,徐鬼经常留意梯子洞江面的动静。他多么希望再一次看见野船在江面上出现,有几次他还冒险从隐没在江水中的奇诡洞穴凫进去,希望在洞穴里找到野船。每次凫进去两里水程他就再也不能向前,洞里的水寒彻入骨,再不回凫,会四肢抽筋,冻死在水洞里。徐鬼一直留意和寻找野船,但没再看见过野船。直到有一天爷爷突然消失不见,在寻找爷爷的途中,他才再次看见野船。
爷爷是在九十六岁生日那天不见的。徐鬼和媳妇在许家盖薅完花生回家时,天色已晚,血红色的夕阳照着吊脚楼,无数紫红色的蜻蜓在空气中噗噗飞舞。徐鬼吩咐婆娘煮夜饭,他要先到梯子洞河脚洗澡。媳妇本想说下梯子洞来回要一个半时辰,还是不去了吧。她张了几次嘴没说出来,她知道徐鬼太爱梯子洞,早就想下江里去洗澡。她说也是白说。
媳妇刚把饭菜舀上桌,摆好筷子,徐鬼就回来了。徐鬼怕媳妇等自己,只在江面上囫囵地洗了澡。媳妇问,爷爷呢,你没遇见他?徐鬼说没看见。媳妇说回家来还一直没看见爷爷,是不是去谁家串门了。徐鬼在寨子里打听起来,喊起来。可根本不见爷爷的影儿。
徐鬼慌了,胡乱吞了一碗饭就沿着下梯子洞的路上找起来,喊起来。媳妇也开始到处找爷爷。到处都没爷爷的影儿。
徐鬼没回家,在梯子洞岸边蹲了整整一晚上。江风顺着峡谷吹出来,呜呜地响。月亮洒下溶溶清辉,落在江面上。有鱼儿耐不住寂寞跃起来,拍在江面上发出啪啪的响声。徐鬼静静地蹲着。他多么希望爷爷突然举着一条鱼从水底下冒起来,或者从某个半没在江水中的洞子里钻出来,呼噜呼噜地游上岸。
这些都是徐鬼一厢情愿的想法,爷爷一直没露面。爷爷去了哪里,是不是乘着渡口的野船走了?对,爷爷一定是摇着野船去了安静的地方,独自清洗满耳的嘈杂。近几年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太吵了,先是各式各样的录音机,后来又装上了高音喇叭,再后来是电视,然后是哗啦哗啦的大票子和钢筋水泥房。爷爷曾说,这寨子怎么一入冬就特别张狂啊,多想清清静静过个年!
江面撕开一层亮色时,徐鬼去看了存放在山洞里的木船,木船还在,还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心里说,嘿,木船还在,老家伙一定是乘坐野船去远处藏起来了。
太阳还没从许家盖升起来,橘黄的朝霞却染红了大半个天空。徐鬼从梯子洞一口气跑回家。他找出斧子、墨斗、锯子、曲尺、凿子等工具,掀出堂屋里的一截老杉木,开始斫、凿、刨、镶起来。一天工夫,他造好了一艘小木船。那真是一艘小木船,小得恰够躺下他的身体,再装不下任何东西。
媳妇没和他说话,也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心里却明白要做什么。木船造好时,她已把饭菜舀上了桌。徐鬼看了一眼媳妇,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吃完饭,他揣上一支手电,扛着那艘精致的木船出门了,甚至都没和媳妇打一声招呼。
徐鬼把小木船平放在梯子洞渡口的江面上,和衣躺进去,又把手电夹在腋窝下。太阳已上了中天,金黄色的光暖暖地照着江面,照着他黧黑的肌肤。他感觉有些晃眼,他不管,微闭着眼睛开始划水,把小木船划向半没在江水中的奇诡洞穴。
徐鬼现在讲起这事时,脸上还透出一股决绝的狠劲。
我说:“你把小船划向那些半没在水中的洞穴,究竟要干什么?”
“我要找到那艘野船,看看它究竟隐藏在哪里,是一位什么样的高人在驾驶它。”徐鬼说。
徐鬼满怀信心地朝一个洞穴划了进去。开始,他的眼前全是黑暗,是恐怖的黑暗。他根本不管,放任小船自由行进,在小船停止不前时,才摁亮手电筒看看是什么情况。
起初的黑暗过去,他看到船舷边有些通体发亮的小鱼儿游来游去。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明白了,原来在黑暗的核心也能感知光亮,只要用心体会,光亮无处不在。
小木船荡啊荡啊。他果真在一处宽阔的水域看到了艘破烂的舢板船。他划水靠近舢板船。那船破破烂烂的,只差没沉入水底了,船上有支发乌的木桨。他摇了摇舢板船,有吱吱呀呀的响声,仿佛立即就要垮掉。他又掂了掂木桨,有点沉重,也许是浸透了水的缘故。这样一艘舢板船,怎么可能是梯子洞渡口传说中的野船。就算这是野船,哪有高手驾驶得了?他有些失望,划着水继续往前漂行。
徐鬼说,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从黑暗的洞穴中出来了。
他往前划啊划,再没遇见一艘船,也没碰上什么高人。后来,他发现发亮的鱼儿少了,又陷入一片密密麻麻的黑暗,他以为是要进入了高人和野船禁地。正在紧张时,前方出现了亮光,小木船驶入了更开阔的水域,眼前哗啦一下亮堂开,简直要把他眼睛给晃瞎了。好一阵子,他才适应过来。小木船原来漂进了更加广阔的江面,江面上有他从没见过的大船在往来。江右岸,连悬崖上都修了房屋,码头上也到处是人。徐鬼把小木船在江边靠了,起身下船来,打听这是哪里。有个好心的老人家对他说这是龚滩。
徐鬼很羞愧,其实龚滩离梯子洞并不远,不过是半天的路程,可他竟然没来过。他不想再待下去了,弃了小木船,来到龚滩街,找一家小店说明情况后,讨得一碗面条吃了,沿着乌江支流阿蓬江走回了梯子洞。
徐鬼给我讲到这里戛然而止。
说实话,我根本没听明白徐鬼讲的是什么意思。我问他:“这次你究竟找到野船没有啊?”
徐鬼慢悠悠地说“既然野船那么神秘,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我相信爷爷的话,但凡江河渡口都有一艘野船,它不会轻易让人看见。爷爷就是驾着野船去了某个安静的地方,独自洗涤内心的尘垢。我其实用不着找他,既然他是驾着野船离去,会让我找到吗?”
我说“老徐,这只是你的个人说法,没有其他人听说过野船的故事!”
对,没有其他人听说过野船的故事,因为峡谷太高,阿蓬江水落得太深,对这里的水都不了解,怎么会知道野船的传说?我一辈子不愿出门,总有事没事下到江边。我爱这隐藏在峡谷里的水,我相信不常去看看,水也会荒芜,我和它的关系就像兄弟,像夫妻,我能在这片水域里找到自己,即使孤独也不怕,或许更好!假如有一天我烦了,我也会在江边偶遇那艘野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