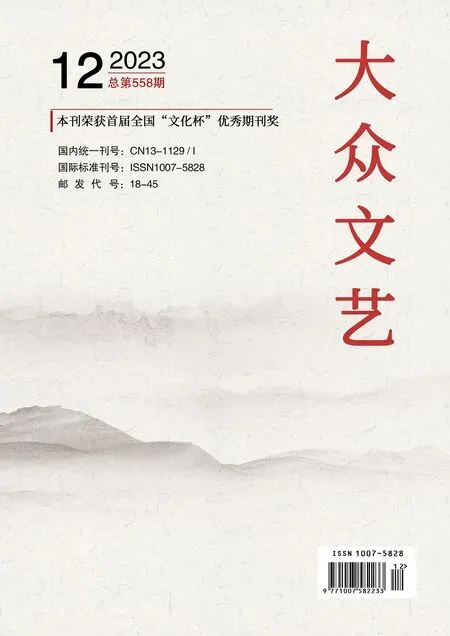符号隐喻下的身份丢失
——以残疾文学中“残疾”身份丧失为例
刘泓柏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7)
残疾人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类群体,在文学文本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残疾文学包含残疾人作家所写作品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残疾形象,涉及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等多个方面。受宗教影响,十九世纪初残疾人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国内的残疾文学则发轫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末。西方残疾文学起步较早,独特的社会环境、平权运动推动了残疾理论的发展与更新。国内残疾文学创作受此影响较深,在长期的理论演变中,残疾文学分化出众多分支,主题复杂多样。
符号隐喻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技法,它将文本中某一身份符号化,成为某种意象,从而通过隐喻的方式达成文本概念的主旨书写。在残疾文学的众多主题中,符号隐喻被运用在大多数人物形象中,实现了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或战火飘零下的国家韧性,或美丑对照下的罪恶之证,或精神荒芜下的理性启蒙,皆是残疾文学中符号隐喻的主旨探寻。
一、身份模糊与丢失:残疾文学中的“残疾”缺位
在早期的残疾文学中,残疾形象几乎都是以扁平人物出现。残疾在文本中被符号化,通过隐喻达成某种写作目的,然后被遗弃。久而久之,残疾文学中的“残疾”开始出现缺位现象。
在残疾文学创作初期,西方对于这一角色的构建大多与邪恶、凶残、丑陋等负面词汇挂钩。十九世纪,宗教的教化集中体现为触犯禁忌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则以各种身体残疾为具体表现。因而,在这一时期,身体的残疾被视为邪恶的象征,残疾人相应就是为非作歹之徒。再加以十九世纪功利主义盛行,物欲成为人们的贪恋,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于是,“残疾”这一概念被提出,用来作为宗教中“罪与罚”的象征,清教主义为了重新稳定伦理道德,加强教化功能,在文学创作中就大肆刻画凶恶的残疾人形象。《红字》里的驼背齐灵沃斯在自己的妻子出轨后,变得敏感、疯魔、凶狠。“我生来畸形,何以还要欺骗自己,认为聪明才智在一个青年女子的心目中可以用来掩饰生理上的缺陷!”[1]畸形的自卑让他逐渐恶化,成为一个以折磨人为乐趣的疯子。《白鲸》里的亚哈船长因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而变得残疾,从此他满怀复仇之恨,为了追杀白鲸置船员安全于不顾,成了固执疯癫的复仇者,最后与白鲸一同葬身于深海。这一时期的“残疾”被符号化为“恶”,残疾只是角色“恶化”的跳板。“残疾”形象被符号化处理后,文本常因“恶”的原因淡化处理“残疾”形象的描写,以“罪有应得”等动机漠视“残疾”相关的文学表达;“残疾”及其相关描写因而在作品中大量缺位。
发展至十九世纪末,残疾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战、二战导致大量士兵变残,战争中的人们开始精神颓丧。西方出现“迷惘”的一代,中国也因受战争威胁,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刻。这些因素不断影响下,西方渐渐减少对残疾人的仇视,中国也关注到残疾群体。残疾人在文本中被塑造为弱小、可怜的群体,人们在其身上灌输了同情的情感色彩。《包法利夫人》中的伊波利特是跛足,“他的马蹄足的确也和马蹄差不多一样大,皮肤粗糙,筋腱僵硬,脚趾粗大,指甲黑得像铁钉。”[2]尽管他的脚与他人相异,但是他从未因跛足而影响自身的生活,甚至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然而周围人却以“看到生厌”“体现自己的善良”等理由强迫伊波利特进行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失败了,伊波利特不得不进行截肢,虽然获得了人们的同情,融入了大家的生活,但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周围人击碎,处境更加困窘。表面上看,“残疾”被符号化为“战争”,文本通过塑造残疾形象,将对残疾的去除视为对战争的成功反抗,从而激励了无数在战争中受伤的年轻人。但实则,“残疾”成为一种烙印,是常人对残疾人的凝视。“残疾”本身被视作一种原罪,对残疾的去除即是歧视视角下的矫枉过正。人们“可怜”“同情”的假象下蕴藏的是对“残疾”的歧视,不利于残疾人的平权。“残疾”或被“战争”替代,或在歧视下被刻意消解,残疾文学中出现“残疾缺位”的现象。
从上述两个时期看,“残疾”在文学作品中是以工具性元素存在的。正如大卫•米切尔与莎伦•斯奈德提出的“叙事假肢”概念,在文学书写中,残疾这一元素并不是“叙事假肢”的重点概念,而是以主题的跳板内容出现,当主旨目的达成,残疾便被遗弃,它不再出现在读者的视角之内,身份消隐。
除此之外,符号化的定义重合,也使得“残疾”概念模糊、特性减弱,逐渐从文学作品里消隐。例如萧红的《手》中,有一位来自乡下求学的少女王亚明,她的双手因为帮家里染布而沾上了各种难以洗去的颜色,变得黑黑的。因此她遭到了同学、校役和校长的歧视与排挤。当“残疾”被符号化为“不正常”“孤立”“罪恶”等,同时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象具有相同的符号化定义。王亚明的双手只是被染料染黑而和其他同学不同,但它在符号化定义上和残疾达成了一致。这就导致,王亚明虽不是残疾,但也符合了残疾在文学上的特征与定义,从而被视作一种残疾。于是,人人皆残疾,残疾概念的严肃性降低,界定变得模糊。再加以当时社会对“残疾”这一概念的厌恶与漠视,“残疾”逐渐被其他意象取代,残疾意义被消解,从而在文学作品中缺位。
从以上维度来看,符号隐喻隐藏了残疾文学中的“残疾”特性,致使“残疾”在部分残疾文学中缺席,不利于大众对残疾的认识以及残疾群体的平权。
二、残疾、作家、社会:残疾缺位的现象探究
残疾理论是时代对残疾观念的投影,残疾文学依托于残疾理论的发展,其背后隐藏的“残疾”缺位现象也与之有较大的关联性。
早期,残疾被单纯定义为医学概念,指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不正常,以至丧失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被视作个人的内在问题,是与常人相异的病态。这种理论认为残疾是残疾者的内在局限,是其自身导致的融入社会的障碍。在此框架下,残疾者因残疾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被视作一种异端,是与正常社会背离的,以此残疾者被抛弃,成为天生被放逐的群体。残疾理论影响着社会心理,渗透进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对“残疾”的情感倾向。这种理论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为早期“罪与罚”的符号化。这是人群仇视致使的“残疾”丧失,人们对罪恶抱有反感情绪,残疾作为罪恶的具化象征,在文学作品里同样被漠视,成为服务于主旨的牺牲品。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残疾理论的构建,西方逐渐将重点放在有关残疾的深层内涵上,即将残疾与社会状况相联系,认为是社会的凝视与平常的标准造成了“残疾”这一结果。在这一约定俗成的标准下,残疾人因自身的缺陷而有着某一方面的能力缺憾,沦为弱势群体,无法融入社会。这一理论为残疾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残疾被置于社会语境下,脱离了被歧视的个人内在缺陷说。但社会模式下的残疾理论同样存在问题,残疾的特殊性被消解,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此情景下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残疾,理论上做到了平等。这就造成了后期文学作品中残疾另一种意义上的缺位,残疾人与正常人差异被消除,文学作品里更是将二者做了艺术上的处理,体现为残疾人通过救助融入了社会,成为主流群体中的一分子。一方面这对应“战争”的符号化,残疾成为人们凝视的烙印。另一方面,更多地以社会弱势群体冠名的与残疾对等的符号出现,残疾的独特性丧失,被更多的概念取代,在文学作品中缺位。
然而文学作品和残疾理论中的平等并没有真正推动残疾人的平权进程。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痛苦、不适与功能受限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以另一种维度的地位卑下——能力不足,继续受到来自能力强者的歧视。人们以绝对公平为准则,实际仍在无形中压迫着残疾群体。在这样的公平原则下,诞生了一批非残疾身份的残疾文学作家,他们以与残疾人平等的身份地位进行文学创作。然而缺少正确的生活体验使得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残疾的困境,心目中的残疾人形象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为了追求特色性,他们对之进行艺术加工,在隐喻意义上进行拔高。残疾退位,反之“英雄”“理性”“思想启蒙者”等形象出现。残疾群体既失去了身份上的特殊关注,同时还要接受相比先前更苛责的能力标准。
以此观之,在早期和中期的残疾理论影响下,残疾文学实然出现了“残疾”的缺位现象,这体现了社会对残疾理解的偏颇与错误。社会心理投射进文学作品中,残疾人群体陷入困境。
三、残疾回归:经验本位与社会平权
残疾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残疾”缺位,残疾人群体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开始出现残疾人平权。众多残疾人作家涌现,以自身经历为蓝本,进行残疾文学创作。残疾文学中“残疾”开始回归,残疾理论随之更新,社会对残疾的概念逐渐步入正轨。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脊髓上长了肿瘤而下肢瘫痪,后天残疾使他几近崩溃。他把自己的心绪全都写进了文学,在《秋天的怀念》里,他会乱砸乱扔东西,“其余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3]在《我与地坛》里,他经常一个人待在地坛,就坐着不说话,一去就是一下午。然而他并未颓废许久,残疾带给他的除了打击,还有对亲情的探寻,对生命的思考。他敏感地捕捉到一直跟在身后,担忧地望着他的母亲。那是无论残疾与否,一直跟随着他的东西。他把握了生命的本质,谁都无时无刻不处于残疾之中。残疾并没有从他身上离开,但爱与生命给了他与残疾相处的勇气。涅玛特35岁时因脊椎管肿瘤高位截瘫,他在自传《永不言弃》塑造了“叶尔江”这个角色,实则是自己的缩影。他对死亡恐惧、害怕手术,但仍会因为家人的深情而对生命充满希望与热爱,“只有当一个人身陷黑暗,在黑暗中直面死神,在恐惧与希望中苦苦等待黎明的曙光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太阳带来的无限希冀。”[4]残疾人作家本身有切身的残疾体验,他们的作品中“残疾”作为主要叙事元素,从始至终都保有极高的存在感。从对“残疾”的怨恨与恐惧到与“残疾”和解,残疾文学中“残疾”回归,成为人们正视的命题。这是独属于残疾人作家的经验叙述,他们向大众近乎残忍地揭露自己的心理,让大众走入残疾人的世界,体会残缺的艺术。
残疾理论因此有了更新,交互式定义对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下的残疾定义进行了批判。它既肯定了残疾属于个人的内在属性,也认同了残疾需要在与社会的复杂交际中才能呈现其本质特征。残疾也许无法被完全消解,但阻碍残疾获得基本权利的行径更该被解决。由此,残疾从被歧视、被逃避的地位推至大众视线之前,成为热门的话题。残疾平权开始兴起,社会开始积极寻找合理且有效的方式。残疾文学的发展滋生了一批对残疾有深入理解的作家,加入高质量残疾文学的创作行列中。
大江健三郎因自身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从而对残疾有了独特的体验。他用心灵与这个孩子产生了共鸣,在残疾中看到了生命的盎然与美丽。于是他提出了“再生”与“共生”的命题,“残疾”成为生命的另一种状态。同样的还有美国作家迈克尔•贝鲁贝,他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小儿子杰米,他撰写的《杰米了解的生活:一个特殊儿童的成长》记叙了一个智力残障小孩的成长。他逐步了解的世界以及他在某些方面展现的并不残障的智力。杰米能记得他们以前生活的所有点滴,并把这些都讲给贝鲁贝听。这就像是一本日记,人们得以从日记里刻画出一个智力障碍的小孩,了解他感知世界的方式。毕飞宇的小说《推拿》以盲人的视角平淡地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毕飞宇没有在里面掺杂任何的同情与可怜,几乎将他们当作常人来写。在文本中,我们体会到都红在活动上演奏完钢琴,主持人哽咽着讲出她的励志故事是多么的荒诞与可笑。没有人为她的演奏技术鼓掌,他们在意的只是两只看不见的眼睛,和这样的她竟然会弹钢琴这件事。我们能够体会到王大夫发的毒誓为何是“如果我说了瞎话,一出门我的两只眼睛就什么都能看见。”[5]当我们看完整本书,“看见”与“看不见”不再是表面的定义,而成为心灵的描写。
当作家对残疾进行去特殊化处理,以近乎白描的笔触去展现残疾人的世界。残疾人才真正走进大众的视线,“残疾”才真正在残疾文学中归位。残疾理论趋于完善,残疾平权也开始走上正轨。对于文学而言,促进一个群体的平权反而需要追求平实化叙述,需要不加掩饰的直观描写。在平权面前,文学要暂时性地服从于生活,先向大众展示真实的生活,再进行艺术创作,使文学高于生活。
结语
本文以残疾文学中的“残疾”缺位为主题,探究了缺位现象与成因。残疾文学发展的背后体现的是残疾平权的进程,“残疾”缺位体现的是社会性仇视与漠视,理论与文学作品中的平等实则也蕴藏着大众对“残疾”根深蒂固的歧视。当平权兴起,残疾人作家出现,以自身经历为蓝本进行经验创作后,“残疾”才真正回归。于是,越来越多的非残疾作家投入高质量残疾文学创作中,促进了大众对真实残疾世界的认识,加速平权进展。以此,社会心理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符号隐喻的技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残疾”在残疾文学中缺位,但无论什么时期的残疾文学,作为对残疾运动的纪实,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理念总是在运动中更新与完善,文学作品作为对一个时代的记载,始终表现出留声机与传声筒的作用。残疾理论仍未完善,残疾文学也将在时代中摸索,构建全新的残疾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