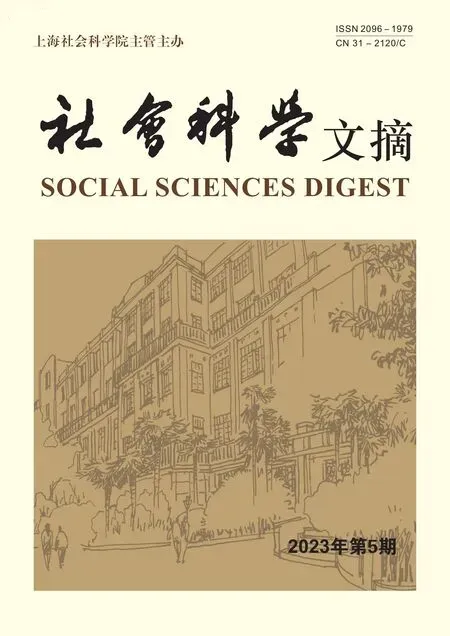现代国家的双重身份与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的建构原则
——一个纯理论的分析与猜想
文/黄裕生
国家是理解国际体系的原点。如果我们能澄清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那么,我们将看到现有的国际体系是基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普遍性的那些原则建立的,这些高级版本的普遍原则构成了我们理解、想象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的基点。那么,如何理解、确定现有国际体系的成员主体的身份呢?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深究的首要问题。
一
在现有国际体系里,国家这个成员主体实际上有双重身份。但是,人们今天通常只强调国家的民族身份,并且只根据这一身份去理解、分析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对“民族”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讨论,从而澄清国家的民族身份。
在这里,重要的是澄清促使民族共同体形成并被标识出来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看,这些核心要素包括特定的文化、基于血缘关系而显现于外部的族群特征、族群的共同利益。基于这些要素的认同而自我确立起来或者被确立起来的族群,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民族既可以是一个个人的身份,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当人们把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单位作为一个国家单位来理解与认同时,我们把这种国家称为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于民族所包含的核心要素是特殊的,当国家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身份出现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特殊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性并非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唯一基础,民族国家从其诞生起,就带着民族性与强力这双重向度,一个民族实体的强力使这一民族的民族性成为这个民族实体被确立、被承认为一个国家的理由——确切说,是一个物理原因也即一个实然原因才使民族性成为一个民族自立为国的理由,而不是出于应然的正当性理由。
因此,如果国际体系仅仅是由只有民族身份的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关系就必定只遵循着近乎丛林法则的实力法则。每个国家都有理由完全从自己的民族性与民族利益出发规定与他国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理由把自己的民族性与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国际体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期待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每个以自己为优先的国家都必以实力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尽可能损害他国的利益。这一方面必使得民族国家之间陷入不断纷争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必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结盟永远都是短暂与临时的。其次,每一个民族国家出于自己优先的利益考量,既可以随时加入全球合作与全球分工,推动全球化,也可以随时退出合作而反全球化。
二
由于民族性和实力都不能给一个民族共同体提供使之成为主权共同体的正当性理由,民族国家自它产生开始就面临正当性上的困境。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民族国家必须以某种客观化的合理程序接受自己的人民——所有自由而平等的契约者的授权洗礼。这个洗礼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成为“人民国家”(people’s state)或公民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据此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也是人民国家。在这里,民族与人民开始重叠:民族就是所有拥有普遍意志的契约者个体构成的一个全体,而所有契约者组成的全体就是完全被普遍意志规定的人民。因此,当民族与这样的人民重叠的时候,民族才有正当性成为一个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也就不再是基于其民族性与实力的民族国家,它已成为一个基于所有成员以某种理性程序参与契约、授权的人民国家。
一个民族国家获得人民国家这个身份在根本上有三重意味:
第一,国家主权的获得与行使需要以某种合理的程序得到国民的授权,国民的普遍意志,也即人民的意志,既是国家主权的唯一正当性源泉,也是国家主权行使的目的的唯一准绳。这里,有必要对“国民的普遍意志”这一最根本也最难理解的概念做出说明。这个普遍意志不是契约的产物,相反,它是契约的基础。这个普遍意志的普遍性首先就普遍在它内在于每个人身上,其次,普遍在它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意志。普遍意志的这种双重普遍性使每个人的意志成为自由的意志,因为人们能够突破受必然性支配的私人意志而接受普遍意志的双重普遍性的约束性要求,从而接受自身的要求,因而接受一种独立于外在必然性的自主—自动的要求。只有当契约者把普遍意志当作最高法则并接受其约束时,他的所有行动才是应当被允许与尊重的,每个契约者这种应当被允许与尊重的一切可能行动,构成了每个契约者的自主行动空间,也即一个人外在的普遍自由权。
第二,国家主权行使的目的首先是捍卫人民也即所有个体公民那些不可让渡的普遍自由权,维护与促进每个公民基于这些权利的相应利益以及公共福利。任何人既不得再仅以国民之外的哪怕神圣的事物作为行使国家主权的目的,也不得再仅以任何个人或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作为行使国家主权的目的。
第三,国家要保持为正当的国家,它必须依普遍意志进行治理,出于这种普遍意志与至少符合这种普遍意志的法律应成为治理国家的根基,具有这种双重普遍性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普遍法,依此普遍法治理的国家才是法治国家。因此,国家主权一方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有界限的。对一个人民国家主权的侵犯就是对这种普遍权利的侵犯,因而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侵犯。一个以普遍权利之外的理由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国家,也必会以同样的理由侵犯自己国家人民的普遍权利。当且仅当在承认、尊重并维护每个国民个体的那些普遍权利这一前提下,一个国家的主权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如果让渡部分甚至全部主权有益于更好维护或捍卫公民的普遍权利以及相应利益,那么这种让渡是可以接受的。
三
国家一旦获得人民国家身份而走上向人民国家转变的过程,那么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刻改变国际关系体系:
首先使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与相互尊重成为可能。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承认、尊重自己国民的权利时,必须同时承认、尊重所有其他主权国家国民同样的权利,因此,它必须承认与尊重其他人民国家的主权。
其次,人民国家不仅首先有职责捍卫自己国民的普遍权利,而且也有国际义务尊重与维护其他主权国家国民同样的普遍权利,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人民之普遍权利的损害,就是对所有人的权利的否定与冒犯,包括对人的普遍尊严的冒犯。这也意味着人民国家的主权受到国际限制:不得损害、侵犯人类的普遍权利,否则他国有纠正的理由。
最后,财产权成为人民国家要保障与捍卫的权利,每个公民对自己财产的占有和支配应当获得国家普遍法的确认与保障,据此,建立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市场、展开相互开放的公平国际贸易是一项正当的要求。
四
不过,直到今天,人们误以为这三百多年来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完全是基于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国际体系里,民族国家是每个国家的首要身份,也是首要载体。但是,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性误解。导致这种误解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在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上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国家民族身份;另一个原因则是一种观念上的双重混淆与误解,首先是把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民主事业也即契约立国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而把民族直接混同于人民。
这种普遍的误解与混淆带来了两个严重的世界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谓是世界性灾难。原来只是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民族或族群产生了政治共同体的诉求,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大分裂与大冲突,为了民族性不惜大规模牺牲人类个体之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第二个问题是,导致人们看不到民族国家在接受契约论确立起来的原则与机制洗礼之后获得的人民国家这一身份,以致仍然坚持只以民族国家的身份与立场去理解、确定国际关系,这在实践上导致国际体系变得非常脆弱。
五
为了思考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我们在理论上一方面有必要从现代国家的双重身份这一现实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基于人民国家这一更具普遍性的国家身份来想象。根据这两点,我们可引导出构成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每个主权国家都应尽可能完成向人民国家的转换而成为实质的人民国家,并捍卫这样的国家。成为人民国家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应然方向,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人民性水平,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普遍性水平。这个过程也是促成最初基于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国际体系转化为由人民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的过程。
原则二:基于构成所有人民国家主权正当性来源的普遍意志之上的普遍原则将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优先原则,而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的特殊原则将靠后。每个国家忠于其人民,就是忠于一个普遍性使命——维护与捍卫其成员个体基于普遍意志而拥有的普遍权利与相关利益。因此,基于普遍意志而确立起来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乃是每个人民国家履行其忠于人民的使命。这种世界体系要求所有现代国家把民族国家的特殊诉求置于普遍原则之下,而不得把民族国家置于普遍法之上。
原则三:遵循有限的多元原则。对体现人类之差异性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尊重与维护,不仅是人民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与相互尊重这一原则的要求,而且也是人民国家维护与捍卫人类成员个体的普遍自由这一使命的要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原则,不过,这条原则是有界限的,任何多元与差异本身不能否定其前提也即人的自由本质,否则,多元与差异将否定自身。
原则四:对内有别于外,对外无别于内的原则。所谓对内有别于外是指,在内政上,基于国家的民族性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殊性而制定或采取适合于这种特殊性的政策或法律,既不应把这样的政策与法律推向世界,也不必照搬其他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所谓对外无别于内则是指,用以处理、对待国际关系的原则不应被限制在国际关系领域,而是应该也能够适用于国内关系。
原则五:拒斥一切“世界尺度”的原则,唯以人民为原则。所有号称以世界为尺度的原则在本质上都是非整全性原则,是非世界性的,都只是基于有限知识确立起来的视角性原则。当人们以这种被误以为以世界为尺度的视角性原则作为建构世界体系的完备性原则时,所建立的必定是一种基于“先知”式权威的体系和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且仅当人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基本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才有可能进行契约活动,所以,国家与世界体系就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性关系基础上。这种相互性关系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为人类个体被置入了自由之中而是能自由(Freiheit koennen zu sein)的,也就是能不断自我打开,能够自我差异化自身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成员个体的自由构成了伦理社会的基础,因而也构成了国家与一切可能的世界共同体的基础。如果说人民就是依内在于每个人的普遍意志共同契约出一部普遍法而联合在一起的所有契约者全体,那么,人民就是被置入自由的那种自由者的联合体,人民原则在根本上就是自由原则。由人民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应当,也只能够首先以自由原则作为建构与确立其秩序体系的原则。
原则六:所有国家都应当最大程度去肉身化。国家作为一个承担着委托与代表的人格(person),它有自己的肉身,那就是由一系列强力组成的一个有机体,其中最强壮部分就是军队、警察。就民族国家而言,它必须尽可能拥有强大的肉身,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利益。人民国家的产生则为人类告别依靠肉身力量来寻求和平的时代提供了可能性。人民国家没有内部敌人,只有需要防患的非社会性力量。它也没有外部敌人,因为如果国家保持为人民国家,那么国家之间将没有理由进行侵害性的敌对行为。因此,人民国家可以也应当尽可能去肉身化,把自己的物理强力限制在最低需要的限度内。
原则七:如果让渡部分主权,以便形成一个人类共同体,从而更有利于维护与实现成员个体的普遍权利以及相关福利,那么,为了忠于自己的使命,人民国家没有理由拒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不断走向“共—和”的历史,全球共—和是人民国家最有可能迈向,也最合乎理性的一个世界体系。
附论
从长时段看,未来的国际体系只能是一个世界体系,也就是在人民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体系。这样的国际体系将演进为一个依普遍法行事的世界体系:经济上将统一为一个全球性的自由市场;政治上将形成一个基于普遍法进行管理与监督的世界性法治联盟。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所有宗教、所有文化传统都将得到接纳与容忍,但是,任何宗教或传统都被要求接受普遍法的制约。在这个法治的世界体系里,没有任何特殊性能被置于普遍法之上。相应地,没有任何特殊组织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正如马克思曾经预言的,社会将还给社会本身。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社会将还给人民,也即还给社会存在于其中的自由人。人民不是民粹主义者,人民不受为所欲为的众意的支配,真正的人民是把自己的意志置于自己的普遍意志之下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