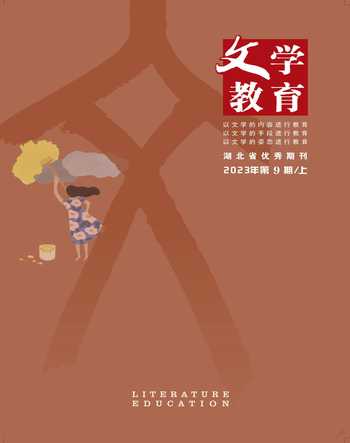钱锺书《谈艺录》对袁枚论诗的批评
杨芳菁
内容摘要:袁枚是钱锺书在论述清代诗学时着力最多的诗人,他在《谈艺录》中对袁枚其人及“性灵说”都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指出其论诗的独到之处及其在清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重点集中于对其论诗缺失和误解上的“批却攻隙”,目的是使袁枚诗论以更为真实、清晰的面貌示于后人,为后世学袁论者提供新颖的、全面的研究视角。本文对钱锺书对袁枚论诗的批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同时针对批评中有待商榷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利用文献分析法、社会历史批评法等研究方法,旨在完善现有研究成果、对后来研究者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谈艺录》 袁枚 《随园诗话》 文学批评
清代诗学发展至乾嘉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作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诗学观点,以此消彼长的形式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着,成为清代诗坛一盛象。最终“性灵派”主将袁枚以其深刻的学识和诗论逐渐压倒另外两家,取代沈德潜成为乾隆时期诗坛盟主,主导乾隆诗坛三十余年。袁枚逝世后,后世批评家对其人、其论都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规模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毁誉参半——历代研究者对袁枚的批评回顾
与袁枚同时稍后,章学诚、朱庭珍的批评最为激烈,二人对袁枚的诗论、作品和为人几乎全面否定。章学诚的批评集中在《章氏遗书》中,对袁枚反叛传统,鄙弃礼教,不顾舆论大收女弟子等行为都进行了严厉谴责,甚至到了痛斥的地步:“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 …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1]“近有倾邪小人,专以纤佻浮薄诗词,倡道末俗,造言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壸。”[2]可见,章学诚是完全以“卫道者”的立场批评袁枚的。而朱庭珍则将更多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性灵派其他诗人如赵翼、张问陶,主张“宗正法”,否定性灵派末流创作中显示出的轻佻流俗的倾向,同样是站在正统诗学的立场指责其违背封建礼教、破坏诗坛正统秩序,而朱庭珍却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全部归咎于袁枚。①章、朱二人的批评言辞过于激烈、刻薄,也多被后来研究者诟病。
继沈德潜之后的“格调派”领袖王昶对袁枚诗论的批评要温和得多,王昶并未将矛头集中于否定、批判袁枚诗论上,而是重在表达与袁枚论诗的差别,强调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主张“先贵学问博,次尚才气优。”[3]在学古上继承沈德潜宗唐,强调学习唐代诗歌的“雅正”传统,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
钱锺书之后的学者王英志对袁枚及性灵说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直接批评不同,他是通过点校、整理袁枚论著,实地考证袁枚的住所、交游经历②等实证的方式,达到对袁枚生平及诗论作出了更为真实的整理和评价,其研究较少受前代批评家的影响,可以视为当下研究袁枚较为全面、深刻的成果。
综上所述,嘉庆朝可以说是对袁枚批评的风水岭,乾隆年间的批评人数相对较少,且基本上都为恪守封建礼教、理学的卫道者持有保守观念所致。嘉庆朝由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忧国忧民之士回归传统、以儒学挽救衰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自然成为被视为异端,他们只看到性灵派发展到末期显示出的轻佻流俗的倾向,却忽视了性灵派同样不乏批判和讽喻精神的佳作。
二.褒而不崇——《談艺录》对袁枚的总体评价简述
钱锺书对袁枚论诗的总体态度在《谈艺录》“随园诗话”一则已十分明确:“良以此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话,无可比伦。故为之批却攻隙”。[4]500可见,钱锺书充分肯定袁枚《诗话》的价值,但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批评。首先,钱锺书认为袁枚受人讥弹主要是出于“门户之见”和“妒忌之心”:“子才佻达放肆,荡检踰闲,盛名之下,佔尽韵事,宜同时诸君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4]498认为是妒忌之心所致。的确,较之大多数批评者,袁枚一生都过得十分自在,作为家中的长孙受尽爱护,幼年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仕途虽不是平步青云但也算一帆风顺,又常得至交、显贵的帮助,归隐后的生活也轻松惬意。因此,如今研究者多认为袁枚遭人如此非议的背后不免有妒忌、羡慕的原因。
钱锺书对袁枚的批评也集中在为人和诗话两方面,称:“自有谈艺以来,称引无如随园此书之滥者。”[4]498批评《诗话》收取太滥,也同样批评其选诗缺少客观标准,顾念旧情,又为名利左右,“利名扇荡,取舍标准,不能自高。重以念旧情深,爱才心切……若乃比论诗如选色,而实托风雅为狭邪,评头论足,狭语媟言。”[4]498批评其人有失风雅。钱锺书的批评,其实在袁枚主持诗坛时已经有人指出,袁枚也一一进行反驳,针对收取太滥的问题,他在《诗话》中说明自己的选诗态度:“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5]针对被诟病结交权贵、顾念旧情,《诗话》中归纳的选诗七病:“选家选人之诗,有七病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七病也。末一条,余作《诗话》,亦不能免。”[6]可见,袁枚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论诗之不足。
总而言之,钱锺书充分肯定了袁枚在我国古典诗话史上的价值,同时为他受到的片面批评正名,但因为其诗论确有不少缺失,因此并不推崇,以秉笔直书的态度对袁枚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貌异心同——袁枚论诗与各家有暗合
“性灵说”是袁枚为反驳当时主导诗坛的几家主要诗论提出的,但钱锺书认为几家其实并非判若水火,相反,在比较几家诗论后他得出结论:袁枚诗论其实与各家都有暗合,《谈艺录》便用大量篇幅考证了几家诗论的相似处,主要集中在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禛“神韵说”以及章学诚的批评上。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单列一则论述袁枚评价严羽,《诗话》中谓:“沧浪借禅喻诗,不过诗中一格。”[6]而钱锺书指出袁枚虽批评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实际其诗论亦与严羽多有相通处,如二人都强调“悟”:严羽论诗主张“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消纳”说,强调作诗以有言外之意为佳,主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而后人多不理解其“消纳”,正如屠倬作《菽原堂集序》记载查梅史论诗主“消纳”,谓:“沧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纳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为野狐禅。”袁枚正是因为不解严羽之“消纳”,才导致单以篇幅长短评判诗之优劣,且不知“悟”并非禅所独有,其实袁枚论诗时也曾借禅论诗,如其《诗话》卷四中论及“灵性”时引云窦禅师语:“‘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灵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与严羽之论相合。
袁枚与严羽诗论相通还表现在二人重“多识”,《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7]《诗话》亦有:“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5]②“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6]与沧浪诗论也不谋而合。
王士禛“神韵说”是袁枚的主要批评对象,袁枚认为王士禛“才力薄”[8]③,作诗短于气魄,缺乏意境和力量,指出作诗虽应以有神韵可贵,但不应“首首如是”,同时批评其为文造情,说道:“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不真矣。”[6]但钱锺书考证二人诗论也并非截然对立,比如袁枚在《再答李少鹤》中提及“神韵”的重要性:“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体格是后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9]又与“神韵说”有暗合处。此外,二人都反对诗中强加格律,如袁枚强调诗作“都是性灵,不关堆垛。”[6]王士禛自述作诗“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联句,不叠韵,不合古人韵。”[6]此论也颇得袁枚欣赏。
除以上两家袁枚主动发起的批评外,《谈艺录》第八十六则专门论述章学诚对袁枚的指摘,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已经成为古典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而《谈艺录》同样说明了观点:章学诚诗论与袁枚貌异而心同。举章学诚同样重“性灵”、重“识力”,强调“绝学孤诣,性灵独至。”[10]“文词犹三军,志识其将帅。文词犹财货,志识其工师。”[10]同样贬斥作诗“权门托足”的行为:“王公之仆圉,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学问不求自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之仆圉之类也。”[10]与袁枚立论都十分相似,再次证明他对袁枚不遗余力的痛斥多是“出于头巾气盛,门户见深”[4]656。
由此可见,《谈艺录》将袁枚诗论和他家诗论进行比较,指出其诗论与各家相通之处,使读者在研究袁枚的过程中对清代诗论发展具有更为深刻、细致的认识,这种批评角度在袁枚批评史上是别开生面的。
四.批却攻隙——纠正袁枚论诗不足之处
1.袁枚论诗之自相矛盾处
钱锺书对袁枚的“批却攻隙”首先集中在批驳其“诗分唐宋”论的前后矛盾上。《随园诗话》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6]说明袁枚深非诗以朝代定优劣,即主张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此论显然是针对当时主导诗坛的沈德潜“尊唐抑宋”及学习沈德潜的明前后七子而发,对当时诗坛这种错误的发展倾向起到了纠正作用。但《谈艺录》考证袁枚论诗论及诗分朝代时却有自相矛盾之说,如在同卷云:“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6]又有: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李、杜、韩、苏音节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6]则认为宋元、中晚唐又优于盛唐。又云:“唐以前无有不熟选理者……宋人以八代为衰,遂一笔抹杀,而诗文从此平弱矣。”[6]却又有尊唐抑宋之意。再观其诗论亦可见他对唐宋诗的不同态度,他十分赞赏杜甫、白居易诗歌,而对宋代大家如苏轼、黄庭坚的批评十分苛刻,认为宋诗少韵味与情思,有何尝不是以朝代论诗之优劣?钱锺书指出袁枚此论与其前说已有矛盾,同时表明自己观点: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重情韵、宋诗重思理,重表现丰神情韵的诗归入唐诗,重表现筋骨思理的诗便可归入宋诗,二者并无好坏之分。
2.袁枚对各家批评有失偏颇
袁枚的诗学批评集中在宋、清两代,其中对清代诗学批评以沈德潜为首,这点在《诗话》中已经十分明确:抱杜韩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之韵者,谓之木偶演戏。[6]便是针对沈德潜“格调说”而发。而《谈艺录》中则考证袁枚对沈德潜的批评其实多片面之见,如袁枚主张作诗贵有理趣,认为诗有理语为上乘,这一观点即是与沈德潜的发难之语,而事实是沈德潜也未尝言诗不可明理,其诗中也不乏理趣之语,如其《说诗晬语》中引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11]《清诗别裁集》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12]都表明沈德潜并不排斥以“理”入诗,由此可见袁枚对沈德潜的诘难有失偏颇。
除沈德潜外,袁枚对宋诗也颇多微词,首先体现在他虽反对“诗分唐宋”,但在评价唐宋诗时又时常以时代区分优劣。再如袁枚不喜宋代儒学和理学,便对严羽等人大加批驳,其实其立论与严羽多有相通,以上前文已经说明;此外,袁枚批判宋人“以八代为衰”,认为因宋人不治《文选》遂使其诗文较唐卑弱。针对以上诘难,《谈艺录》通过大量实例进行辩驳,举欧阳修驳李徳裕语:“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侯家不置《文选》,盖其恶不根艺实。”[4]544为“偏议”之语,说明不重《文选》的现象自唐代便有,并非由宋人始,由此可知袁枚对宋人的批驳也有失偏颇;再如《谈艺录》举袁枚对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评价,仅根据王安石“近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一联便评其诗“凿险缒幽,自堕魔障”,没有读其全集便妄肆诋毁,不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而袁枚论诗甚推杨万里,甚至视其为“性灵之宗”[6],其实亦多为未全面了解的片面之见,如他称赞杨万里“但愿君王诛宰否,不愁宫里有西施。”[13]一联其实是王安石诗中原句,《谈艺录》批评袁枚推举杨万里,就将天下溢美尽归于他,甚至夺他人佳句[4]535,可见袁枚对宋人的批评过于片面。钱锺书对袁枚论诗偏颇处一一矫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后人学袁时的人云亦云。
3.補充袁枚论证无力处
《诗话》卷三引毛西河批苏轼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袁枚认为毛西河诋之太过,而反问毛西河《关雎》中为何是雎鸠“在河之洲”而非斑鸠?《绵蛮》中为何是黄鸟“止于邱隅”而非白鸟、黑鸟?[6]可见袁枚是以“性灵”出发,以借景抒情的角度加以批驳,虽有说服力,但钱锺书认为袁枚论证未能扼要,《谈艺录》中补充道: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物,故诗中遂遍及之。[4]551又引《苕溪渔隐业话》中谓河豚必须与蒌蒿、荻芽同煮,证明苏轼是因见画中有蒌蒿才想到河豚,蒌蒿是诗人眼中所见,河豚是诗人心中所有。批驳毛西河是因不知题画诗特征才有此诡辩,研究者称钱锺书此处的批评是“重新塑造过去的艺术作品,使之面目一新,使过去保存下来的经验重新得到理解。”[14]如此反驳,既较袁枚有力,又未负题画诗作者之苦心。
《谈艺录》补充袁枚论证还集中在第六十九则对“理”的认识上。《诗话》反驳沈德潜“诗无理语”论,云:“《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咏怀》云:‘疏因随事直,忠故有时愚亦皆理语。何尝非诗家上乘。”[6]强调诗有理语为上,而钱锺书认为袁枚混淆了世事人情之“理”和“诗”中之理,所举诗例所言之“理”都仅是世间普通人情道理,且所引诗句也并非都为诗家“上乘”,因此对沈德潜的批驳便显得无力。在表明观点后,钱锺书举各家对“理”的论述,如《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理也。”[7]南宋道学之“性理”、沈德潜所论“禅理禅趣”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写景言情诗和说理诗具有不同的体式,即写景言情诗为景、情——景、情,写景、言情的目的在表现言外之景、情。说理诗则为景——理,写景的目的在表现言外之理;理趣诗的精髓在于“理语必精”,要执简御繁,以小见大,做到“著语不多,而至理全赅。”[4]562强调理趣诗重在举一反三。此外,钱锺书认为直接地说理只能成为理语而不能为诗,因此作诗要“状物态以明理”[4]563,将理蕴于能引起人审美享受的事物、景物中,方可成为“理趣诗”。钱锺书此论,从理论上解决了诗中“理语”和“理趣”的问题,又较袁枚更进一步。
五.简评钱锺书对袁枚的诘难
袁枚主张作诗首倡“性灵”,强调“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6]以天分为主而辅以学力,同时重视“灵机”的作用,崇尚“诗人之笔,列子之风,离之愈远,即之弥空。”[15]的“空行”说,认为必须要有天分和灵机方能作出好诗,这也是性灵派的普遍追求。但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并未忽视后天学力的作用,相反,他同样重视博学以辅助天分、灵机的发挥。而后世批评家却多以此批判袁枚,可见是没有完整地研究他的诗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指出了这一点,说道:“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粗浮浅率,自信能诗。”[4]520与袁枚相反,钱锺书更重后天学力,认为只有“性情”不可为诗,只有“才学”亦不能成诗,诗之所以为艺术是因为它有规则禁忌,需要有打磨、有取舍,作诗想要“得心”,必须先“应手”,心中所想与笔下之句必然会有差距,这差距只有多读、多学方可弥补,笔者认为钱锺书此论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袁枚诗论不足,但他自述之所以不推崇袁枚是认为他的《诗话》“无补诗心,却添诗胆……惟其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4]520跟随他的性灵派诗人误将作诗当做极简单之事,于是引来更多无知无学之人也学“作诗”,这些人将袁枚推上了神坛,因此袁枚此论有损诗之正宗,这里又将学袁者不重学问归咎于袁枚,似乎前后矛盾。笔者认为钱锺书此论虽有可取之处,因为“性灵派”末流确实有许多低俗之作,但只因此就将袁枚诗论一概否定似乎过于绝对,且“性灵派”发展到后期袁枚已经逝世,已不能主导流派诗人的创作走向,所以如果因此就否定袁枚诗论及《诗话》等著作的作用显得过于极端,且钱锺书将清代著名书法家钱泳《履园丛话》所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多;自宗伯三种《别裁》出,诗人日渐少。”[16]理解为钱泳对袁枚的批评也欠妥当,首先,笔者认为在清代文坛汉宋之学针锋相对的现实中,“随园独标性灵”为乾嘉诗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清中叶这样一个较为平和、安居的时代,参与创作的人增多并不是一件坏事。
《谈艺录》被视为中国古典诗话研究集大成之作,它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批评观点,也是袁枚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钱锺书以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才思对袁枚论诗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又给了诗歌中的“理趣”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对袁枚论诗不足之处予以完善,使读者对袁枚有了更完整、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1.
[2]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45.
[3]王昶.清代诗文集汇编·春融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58.
[4]分别出自钱锺书.谈艺录·随园诗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袁枚著,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补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65-773.[6]袁枚著,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488.
[7]嚴羽著,郭绍虞点校.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6.
[8]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七·仿元遗山论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88.
[9]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十·再答李少鹤[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208.
[10]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M].上海:上海书店,1988:1-7.
[11]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52.
[1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
[13]王安石.四库全书荟要·集部·临川集·卷三十四[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5.
[14]李洪岩、毕务芳.论钱钟书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与贡献[J].文学遗产,1990(02):17-26+143.
[15]袁枚著,刘衍文、刘永翔点校.续诗品·空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22.
[15]钱泳.履园丛话·卷八[M].北京: 中华书局,1979:204.
注 释
①王英志点校了《袁枚全集》《子不语》,出版了《袁枚评传》《袁枚诗选》《随园十种》《性灵派研究》等专著,有《袁枚年谱简编》专题论文,是当代性灵派研究的重要学者,且对袁枚对各家诗学流派的批评、交游史皆有专题论述,十分丰富。
②此处所引袁枚《诗话》原句为:“李玉州先生曰:‘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说明袁枚并非提倡性灵而不重学问,而是以性灵为首学问为辅助,如今有不少研究对袁枚此论有误解。
③此处所论袁枚评价王士禛诗“才力薄”原句为“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为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