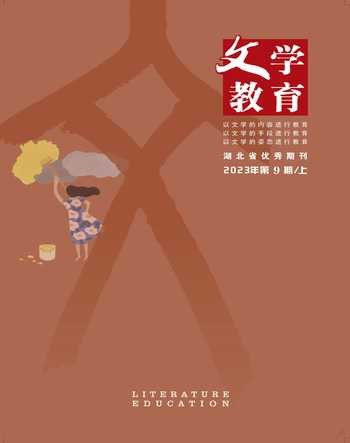谷崎润一郎早期创作的失落与转型缘起
刘聪
内容摘要:“官能美”是成就谷崎润一郎早期创作所遵从的重要审美观念之一,在时代与传统因素的多重影响下,他以一位叛逆的官能主义者的姿态登上文坛并成为一颗新星。但谷崎并没有将这样的审美追求贯彻到他的中后期创作中,他在这样的官能式写作中遇到了令他难以脱离的困惑与失落。《春琴抄》中所融入的对于明与暗、男女等双重关系的探讨成了他自我反拨的一个起点,但此时他仍致力于极尽官能性的展现;及至小说《痴人之爱》创作内外的多重失落,则让他对官能主义与西洋崇拜彻底失去了兴趣,从而正式开始了他复归古典的转型之路。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 官能崇拜 失落 转型
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年对“官能美”的崇拜令他初登文坛便大放异彩,也成就了他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审美风格。年轻的谷崎对官能美的追求是他早年西洋崇拜的直接产物,又与其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事实上,谷崎润一郎早期异色的官能写作并没有长期延续,而是很快走向了失落与转变。谷崎为何以这样惊世骇俗的异类姿态进入文学创作的世界、开启他的作家生涯?他又缘何在这条官能主义之路上开拓女性崇拜与虐恋之美的极限,最终却在失落中放弃官能书写的?通过考察谷崎所处的时代状况、文学传统,我们可以发现他内心的诸多矛盾与碰撞,进而探询他在创作中期走上古典转型之路的缘由。
一.谷崎润一郎的时代与传统
1910年,在发表了《刺青》、《麒麟》等短篇小说后,谷崎润一郎以新人的姿态打破了被沉闷的自然主义之风笼罩着的明治文坛。本是为了师法欧美、创设新风的现代日本文学为何会发展到这样的境地?谷崎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而对文坛产生冲击的?我们首先需要对传统与时代状况进行考察。
所谓官能的体验,即人通过身体感官所获得的快感。谷崎润一郎创作早期所呈现出的耀眼的官能美,显然受到了明治、大正年代时兴的西洋崇拜风气的直接影响。但不难发现,这种官能体验在传统文学中早有体现。在随笔《恋爱与色情》中,谷崎润一郎对日本传统的恋爱观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日本民族的传统是耻于表达恋爱之情的,人们的感情欲望都相当淡薄。谷崎由日本茶道中挂在茶几前的卷轴出发,他发现,只有以恋爱为题材的卷轴不能挂在茶几之前作为茶道艺术的装饰,书法或其他山石画卷则无恙,原因是人们认为“恋情违反茶道的精神”[1](p154)。所谓“茶道的精神”,则是指“侘寂”的审美形态,这是通过俳谐、茶道等具体艺术样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理念。在茶道的世界中得到显著表现的“侘寂”观念,有着禅宗佛法所带来的感情克制之理,意在施行一种舍弃浮华修饰、细细体会枯淡之味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生活状态与恋爱和情欲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在禅宗观念的影响下,古代写作者们的情感表达是受到许多克制的。但禅宗思想毕竟是外来之物,已经存在的“土著的世界观”[3](p24)并未消亡,反而以一种功利的状态与佛家共存,滋生了大量优秀的创作。与佛家对恋爱情感避而不谈所表现出的“高洁”的世界观相反,古代诗歌与散文创作者们对于世事与人情的丰富描写,则体现出本土世界观的世俗化色彩。传统文人们将佛家思想作为自己形而上的寄托,在创作时却大都沿袭着土著观念的传统,例如在《万叶集》中便收录有“朝亦镇我魂,暮亦收我魄;我心乃忶忶,繁思不得霍”[4](p217-218)这类坦率地表达如火般思恋之情的诗句;《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中的背德故事数不胜数。可见,正因为有占据统治地位的佛教世界观对恋爱与性的压抑,才会滋生出“背德”的传统。
及至近代日本,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1885)中一反传统的文学风气,提倡“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所谓人情即人的情欲”[5](p47)。在逍遥所开启的先河下,以往被认为是有悖伦常的欲望情爱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产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逍遥的理论以及二叶亭四迷的小说实践中逐渐形成。二十世纪初发展得声势浩大的日本自然主義文学直接继承了逍遥的理论,如实描写人的生活经验、情感欲望。不过,自然主义作家们沉浸于描写人物表面的忧郁与苦闷,但却没有对于人类心理的深度挖掘与深刻洞察,这种如实的自我剖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真诚的,实际却显得浮于形式、单薄无力。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初,大范围接受西方思想移植的近代日本的矛盾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朝着帝国主义的方向迈进,明治维新后急速进入现代化的日本社会,在二十世纪初期出乎意料地陷入了停滞。石川啄木愤懑地写了《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来批评以后期自然主义为首的那些与国家强权同流合污的作家们,称自然主义为“披露现实但不解决、单调地描写、统一的态度”[7](p164)的文学,社会与思想陷入困境,文学发展也陷入了凝滞之中。这便是截至谷崎开始以作家的身份在文坛活跃之前,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样貌——由接纳西方文学思潮、大力宣扬西方的小说观,到逐渐走向闭塞,亟需新的活力源泉。
生长在这样剧变年代的谷崎润一郎,无疑也接受了不同文化的影响。谷崎在小学就开始阅读《太平记》、《雨月物语》这类古典文学著作,青年时期又投身于西方哲学的世界中。成长于明治、大正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影响,但一方面又有着怀疑和反思。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谷崎润一郎,不知不觉中拥有了丰厚的知识储备与宽阔的文化视野。
1910年,《新思潮》杂志刊载了年仅24岁的谷崎润一郎的处女作《刺青》。这部题材异类、文笔浓艳的官能小说如同投入死水中的一块石头,在文坛之中溅起了不小的浪花。当时远离自然主义文学、以独特的唯美风格自居的名家永井荷风写下评论谷崎的文章,赞誉他“成功开拓了还未曾有任何人着手或试图着手开拓的艺术的另一面”[9](173)。在日本自然主义风潮的统领之下变得沉闷且凝滞的时代里,谷崎以这样一篇小说登上文坛,无疑表明了自己的反叛与创新姿态;但谷崎的反叛又与前所提及的古典传统和维新后的西洋崇拜脱不开关系。在谷崎早期的创作探索中,我们能发现他的诸多矛盾与转变,亦能隐约窥见他在创作中后期进行转型的倾向。
二.虐恋之美的高扬与自我反拨
在传统与时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谷崎润一郎形成了叛逆的精神特质和主张官能美的创作态度,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他早期对虐恋故事的偏爱,他的首部短篇《刺青》便是其中代表。
《刺青》讲述的是一位叫清吉的年轻刺青师追求完美的女性肌肤、进而在上面“刺入自己的灵魂”的故事。这部小说奠定了谷崎润一郎早期创作的整体风格,包含了许多在之后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官能性因素,例如施虐与受虐、女性崇拜、知觉上的异乎寻常之感,以及对特殊癖好的追求等等。这些官能性因素最早也是最主要地表现为“受虐”的体验。在《刺青》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刺青的过程,对于被刺的人而言,是极为痛苦的。而对于刺青师清吉而言,这种如同施虐一般的过程却是愉快且享受的,这是他剑走偏锋的艺术追求,他渴望在这种追求极致的痛苦与华丽的过程中到达感官与艺术的顶峰。
在清吉终于遇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女人时,他将一幅画着古代纣王之宠妃妹喜的画呈现在姑娘面前。刺青是将针尖刺入皮肤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清吉对人知觉感受上的刺探;而将恶人的画像展示在姑娘面前,则是对姑娘内心真实面貌的试探。姑娘是清吉内心的“完美”女性,但对于清吉而言,“完美”并非道德品行高尚纯洁、行为举止优雅端庄,相反,清吉追求的是恶和欲望。在清吉心中,完美的女人是一个能够盛下他的刺青作品的完美容器。这个容器承载的不仅是刺青作品,也是清吉的灵魂。在快要天亮时,清吉完成了他的刺青作品:一只巨大的蜘蛛如同活了过来,盘踞在姑娘的脊背上,抱住姑娘的身体。清吉告诉姑娘,有了他的刺青,姑娘将成为最完美的女人。姑娘则褪下恐惧与怯懦的面目,回应了清吉的邪恶欲望。至此,施虐、受虐的两个灵魂之间得到了相交,对于极致的痛苦与华丽的追求,在清吉与姑娘身上达到了融合。
在这部处女作中,谷崎润一郎就以如此异类且高调的方式,把他对于“灵魂的艺术”之追求以及男女间隐蔽的情欲展现出来。谷崎这一展现的过程极尽官能与背德之事,这是在极端唯美的领域完成自己求异的内心表达。
在谷崎润一郎早期的虐恋小说中,“虐”占据了绝对的地位,而“恋”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谷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种求异的、反叛式的表现,故而他急不可耐地在自己的早期创作中穷尽了虐恋的种种官能体验,并辅之以最为华丽香艳的语言。这种书写,既满足了他自己的表现欲,也满足了大众读者的窥淫心理。或许是由于谷崎对异类官能表现得过早且过于详尽,这种以追寻极致快感为目的的表现力没有持续几年,很快就在他的创作中退场。之后,官能体验在谷崎的脑海中逐渐复杂起来,他认识到人的情欲与感官体验的异常丰富。十多年后,当他再次回到虐恋题材时,“虐恋”中的“恋”逐渐在小说中得到展开,这也让他的虐恋小说走向了更高的层次,成就了他的官能小说代表作:《春琴抄》。
故事中,春琴是一个才艺兼备、面容姣好的天才少女,却失去了视力而成为了一名盲人琴师,弟子佐助则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从仰慕春琴逐步发展到对被春琴施虐的享受,直至愿意为春琴刺瞎双眼、付出一切。谷崎润一郎在短短数万字的故事中将一种“受虐式情欲”的快感展现得酣畅淋漓。刺瞎自己双眼的佐助,其行为是出于他对春琴的近乎痴癫的爱欲;佐助在伺候春琴时,面对个性阴晴不定的春琴的刁難并不感到厌烦,而是将春琴的刁难与责罚当成了一种娇宠,这是在性格上对春琴的体贴与服从;接着他又从春琴在教导学徒弹琴时的严格责罚中体会到了一种生理上的微妙快感,这便是佐助感受到“兴奋”的开端。春琴因意外致使自己容颜受损,佐助在刺瞎双眼后欣喜若狂,“以骤然失明之异常步伐走到春琴面前,狂喜高呼曰:‘师傅!佐助已经失明,可终生不见恩师尊颜之微瑕矣。岂非恰在最佳时刻成为盲者乎?定是天意也。”[10](p263)他既能与自己仰慕的师父春琴成为同一类人,也能做到无视春琴脸上的伤痕,而用纯粹的触觉来感受春琴的施虐,在这里,“色情”最终演变成了对虐恋情欲的享受,谷崎润一郎通过对二人言行举止的细致描绘,将两位主人公的虐恋演变的阶段性过程详尽地呈现了出来。
从《刺青》到《春琴抄》,谷崎润一郎完成的不是对时代文学之风的改造,而是进行了一次对于自我官能主义的失望与反拨。在他的脑海中正逐渐形成一个朦胧的美的目标,这个目标早已不仅仅只停留于纯粹官能式的表现主义,而开始向着更深远、更复杂的审美世界出发。从《刺青》到《春琴抄》的变化过程中,谷崎由纯粹对“虐”的展现逐渐向“虐恋”之“恋”这一方面倾斜,完成了一个对早期纯粹官能主义风格的跨越,这是他从声色、知觉逐步向情绪、情感跨越的过程。这是他的官能崇拜的第一次失落,也是他文学转型的一个起点。
三.西洋崇拜与官能幻想的失落
在谷崎润一郎早期创作里对官能美的幻想中,施虐、受虐的行为主体,大多都是女性。这一阶段的谷崎通常将女性塑造成一个恶魔般的形象:或妖艳迷人,或神秘莫测。这一类女性形象往往略显单薄,且谷崎对她们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官能色彩的描绘上,前所提及的《刺青》即是典型。关于自己的女性观,谷崎曾在《雪后庵夜话》中直言不讳,说自己“视女性为高于自身之人,总是从自己一方仰望女性。非为我崇仰者,皆不作女子视也”[8]P269。在《刺青》之后很久,谷崎都在不断挖掘着自己心中女性崇拜的要素,但这种盲目且狂热的女性崇拜在谷崎的小说中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这一方面是因为谷崎自己已经对这种刺激性的官能感受感到了厌倦,一方面也与谷崎的西洋幻想走向失落息息相关。
谷崎润一郎的西洋崇拜观念是很浓厚的,这在他小时候偏爱西洋料理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年少的谷崎家道中落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有到了祖父的忌日,谷崎和弟弟才有机会开开洋荤,尝到从高级饭店订购来供奉祖父的火腿蛋卷[8](p166),西洋料理给年幼的谷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尽管成年后的谷崎已经不再钟爱西洋料理,但儿时的味觉记忆多少左右了他的思维观念的形成。
成年后,谷崎润一郎的西洋崇拜观念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年轻的谷崎看来,明治维新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日本文明根本比不过成熟的西欧文化,同样也够不着自古便深受其影响的中国与印度文明那般高度。这种自觉流露出的西洋崇拜观进入了他的早期作品之中,成为了他生动的异国幻想。在《玄奘三藏》和《哈桑·罕的妖术》中,谷崎书写了幻想中的印度世界,充满了宗教氛围下的神秘美,但说不清道不明。在《哈桑·罕的妖术》中,谷崎同样借人物之口简单传达了自己的创作意图:“虽然憧憬印度,但还没有机会去漫游,所以希望凭借想象力,来描述一下这个国家”[11](p88-89)。能发现,“想象”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谷崎审视异域文明的手段。对于谷崎润一郎而言,与其说中国、印度是他幻想的乐园,倒不如说是他通过自己的想象构筑了一个贴合自身审美情趣的空幻世界。
至此,谷崎早期的作品中的问题已显而易见:信奉表现主义、有着浓烈西洋崇拜观念的他,更倾向于官能体验这一层面的表现,这种表现能对感官造成极大的震慑,但他却忽略了人的精神与外部世界的细腻的联结关系。彼时的谷崎笔下的女性与西洋一样,都是他透过一层有色眼镜,将其当做一种异域景观式的“他者”来进行书写的,其中所描绘的那些极其异色的人与事物,都缺乏真实性。这些缺陷也是导致谷崎逐渐对当前的审美观念感到失落、并思索转型的重要原因。在创作出了他的西洋崇拜小说中的代表作品《痴人之爱》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西洋崇拜,转而沉浸到古典文化当中去了。在这段创作经历中,谷崎对女性与西洋的崇拜观经历了一个迅捷但复杂的认识转变的过程。
《痴人之爱》创作于1924年,讲述了工程师让治与年仅十五岁的Naomi同住,将她培养成自己理想的女子之后与她结婚,却最终无法控制Naomi的故事。在Naomi的反复引诱与精神折磨之下,让治变得老实而又温顺,彻底成为了Naomi的玩物。《痴人之爱》蕴含着很丰富的西洋韵味:让治在生活兴致上偏爱模仿西方、追求时尚;让治遇见Naomi是在咖啡店,在培养过程中,他送Naomi去学钢琴和英文,他们的生活方式全部是西式的;就连两位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如此:让治名字的日文发音,与英文名“George”几乎一样①,Naomi的日本原名叫“奈绪美”,但在小说中始终以用来表示外来语的片假名来表述②,且与《圣经》中的人物拿俄米(Naomi)重名,如此一来,便更增添了Naomi这一人物形象的西洋风味。谷崎润一郎在《痴人之爱》中寄托了自己全部的女性与官能的幻想,亦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于女性以及西洋崇拜的问题所在。让治本想将Naomi当做自己的高级玩物,但Naomi却把握住了他对她的痴迷与崇拜,反过来控制了让治的精神,令让治想要将Naomi作为神圣一样供奉起来享用的希望彻底幻灭。谷崎对神圣的女性的追求与崇拜在结局宣告破灭,这一结局体现了谷崎对于女性、官能幻想的失落,也暗含着其西洋崇拜的失落。
尽管永井荷风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评价谷崎润一郎的小说艺术“并不是受到了明治文坛哪位前人的影响,也没有受文坛上所风行的艺术规律或主张的影响,而完全是来自于他自身深刻精神生命的神秘冲动”[9](p173),但很明显,荷风这段话是为了给初登文坛的新人谷崎助力而有意忽略了他与外界的影响关系。事实上,谷崎在文学创作早期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来自于荷风本人,其中最明显之处就在于二人对西洋的迷恋与尊崇这方面。不过,荷风的西洋观到了谷崎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荷风有过在法国和美国生活的经历,切实受到过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学艺术的浸染,而谷崎一生除了到过两次中国,并没有涉足其他国家。所以,从对于西洋文化的接受程度来看,荷风所感受到的法国文化“是被古老文化渗透到每个角落的诗一般感觉的风土”[3](p384),而谷崎润一郎则始终在依凭着自己大正年间的中国旅行留下的印象思维和文学阅读经验,在幻想中构筑着其他国度的精神风物。学者中村光夫在《谷崎润一郎论》中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谷崎所痴迷的西洋不是真正的西洋,而本质上是西洋文化在东方的文化殖民之下所呈现出的表象[13](p143)。这种间接性的、东方主义式的文化接受之下所产生的幻想,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根据,最终只能在想象中化为泡影,并被谷崎放弃。
谷崎润一郎早期创作中的官能崇拜,从《刺青》、《麒麟》中纯粹的感官体验,到《春琴抄》、《痴人之爱》中对男女关系的异类探寻,这其间包含着他对官能书写的反拨与思索。这种知觉上的刺激体验究竟能够留存多久?这样的小说写作模式还能为自己带来多少有价值的新故事?对于当时的谷崎润一郎而言,这是一个令他困惑不已的难题。他的女性与西洋幻想在《痴人之爱》中遭到破灭与失落,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在经历着婚变的苦恼,他的第一任妻子千代子被同为文坛名家的好友佐藤春夫夺走,此事一跃成为头条新闻,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历经了艺术创想和生活体验的双重失落之后,1923年的关东地震,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谷崎在震后迁居关西,开始了他复归古典美的艺术转变之路。在对他早期作品中的官能书写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官能崇拜成就了初登文坛的谷崎润一郎,而谷崎对于官能崇拜这一令他扬名万里的早期审美风格的失落与背离,也是他创作上的必然转变。
参考文献
[1]谷崎润一郎.饶舌录[M].汪正球,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2]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M].王向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3]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4]万叶集精选[M].钱稻孙,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5]坪内逍遥.小说神髓[M].刘振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正宗白鳥.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M].王憶雲,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7]千葉俊二、坪内祐三編.日本近代文學評論選明治·大正篇[M].東京:岩波書店,2003.
[8]谷崎润一郎.雪后庵夜话[M].陈德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
[9]永井荷風.冬の蠅:永井荷風随筆[M].東京:丸善株式会社,1935.
[10]谷崎润一郎.恶魔[M].于雷,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11]谷崎润一郎.异国绮谈[M].陈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12]谷崎润一郎.痴人之爱[M].郑民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13]中村光夫.谷崎潤一郎論[M].東京:講談社,2015.
注 释
①“让治”在日语中写作『譲治』,假名标注为『じょうじ』,罗马音标注为“Jiōji”。
②小说原文的写法为『ナオ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