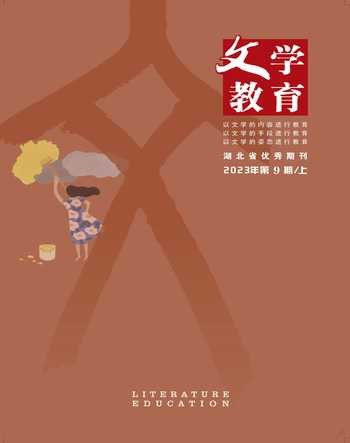挑战与局限:《缅甸岁月》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贾钰祺
内容摘要:《缅甸岁月》是乔治·奥威尔根据他1922-1927年在缅甸的经历写成的一部小说,传达了他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思想。小说聚焦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吸纳新成员的过程和主人公弗洛里的命运,揭示了大英帝国衰落背景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关系。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缅甸岁月》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且已受到挑战,但挑战中也存在着局限,这体现了奥威尔对权力关系和人性本质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缅甸岁月》 后殖民主义批评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两部政治讽喻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让他一举成名,从此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坛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回顾奥威尔的写作生涯,我们不能忽视他小说创作的起点:《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它被认为是继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1900)和福斯特(E.M.Foster)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之后最优秀的英国殖民地小说[1]21。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作者本人1922-1927年在缅甸作为帝国警察的经历,日后奥威尔回忆这份工作使他“痛恨帝国主义”[2]110,《缅甸岁月》也成为他反帝反殖民主义思想的早期表现。小说情节聚焦两条线索:一是英国人弗洛里在殖民地缅甸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又追求白人女性伊丽莎白受挫,最终痛苦自杀;二是土著官员吴波金为了进入凯奥克他达俱乐部,不择手段地陷害与他有竞争关系的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甚至将矛头转向其好友弗洛里,最终得偿所愿。这两条线索由弗洛里和维拉斯瓦米之间的友谊联系起来。通过这两条线索,《缅甸岁月》既展现了大英帝国的衰落背景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又反映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语境下的身份认同的反思。
以海外殖民地为题材的小说是英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缅甸岁月》作为其中之一,以其独特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外评论界已从多个视角解读《缅甸岁月》,其中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义的角度上。由于《缅甸岁月》是基于奥威尔在缅甸的生活经历而创作的,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传性质,因此关于奥威尔在小说中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态度的分析和讨论成为研究的主流之一。约翰·哈蒙德(J.R.Hammond)指出《缅甸岁月》反映了奥威尔对帝国的专制统治下国家与个人之间矛盾关系的反思和批判[3];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则认为奥威尔虽然在小说中表达了反帝反殖民思想,但仍然透露出了反对社会变革的保守主义倾向[4]。同时,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东西方互动中所产生的对殖民话语的挑战与颠覆,例如黄绍栋将情妇马拉美对“白人老爷”的复仇视作东方试图与西方建立平等关系的象征[5];王艳红以通过揣摩白人心理而上位成功的土著官员吴波金为例,论证了大英帝国殖民话语的虚伪与荒谬[6]。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缅甸岁月》中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吸纳新成员的复杂过程,从后殖民视角探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认为小说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被殖民者能够通过对殖民话语的模拟挑战这一界限;但同时这种模拟存在着局限性,尚未真正撼动殖民帝国的根基。
一.俱乐部:抵抗与接受
《缅甸岁月》以小镇凯奥克他达的治安官吴波金为了进入当地的俱乐部,策划陷害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为开始,引出之后一系列的情节纠纷。凯奥克他达俱乐部是当地的一座殖民者的精神堡垒和白人群体的聚集场所,“一座破旧的独层木制建筑”被描述为“全城的真正中心”[7]14,远离周围的缅甸社会。它不仅是娱乐场所,还是种族身份的象征,白人至上的中心,“是不列颠权力的真实所在,是土著官员和百万富翁徒然向往的极乐世界……在全缅甸所有的俱乐部当中,它几乎是唯一一家从不接纳东方人会员的”[7]14。事实上,所有位于殖民地的俱乐部,起初都是殖民者为维护其白人特权而建立的一个“庇护所”。约翰·廷布斯(John Timbs)曾分析认为“club”(俱乐部)的词源来自于“cleave”,而“cleave”这一单词同时具有“分裂(to split)”和“坚守(to adhere)”的含义[8]2。《缅甸岁月》中的凯奥克他达俱乐部也正是如此:它是殖民者彰显自己所“坚守”的“白人身份”的特定场所,俱乐部中的白人通过默认的、不成文的条例拒绝东方人的进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限在此划开。
然而,在殖民帝国逐渐衰落、民族独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俱乐部不可能一直孤立于东方人之外,它们被迫面临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缅甸也不例外,这在《缅甸岁月》中也有反映:宣传反抗思想的报纸、各地的抗税斗争、村民们围攻俱乐部的行动等等,都展现了那个英缅关系的紧张时期。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逐渐转变为防御型,对殖民地的控制也逐渐减弱,警长韦斯特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现如今这些狗娘养的土著都进了各个俱乐部了。我听说连佩谷俱乐部也是……我们可能是全缅甸最后一个抵制他们的俱乐部了。”[7]19面对缅甸其他地区的欧洲俱乐部逐渐向土著开放的新局面,主人公弗洛里作为一个偏向于同情土著人的俱乐部成员,直接推荐自己的好友、当地医生维拉斯瓦米进入还只有白人的凯奥克他达俱乐部:“由于本俱乐部内尚未有东方人会员,而允许公职官员获得大多数欧洲人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如今已经成为惯常之事,无论其为土著抑或是歐洲人,因此我们应考虑在凯奥克他达地区遵循此惯例。”[7]19作为《缅甸岁月》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弗洛里与缅甸许多忠实拥护大英帝国的西方人不同,他痛恨帝国主义,同情在殖民主义苦难中挣扎的缅甸人,愿意与他们交往并了解他们的文化,也获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因此,弗洛里主动推荐维拉斯瓦米进入凯奥克他达俱乐部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所厌恶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反抗。
但俱乐部的另一位成员埃利斯作为极端的种族主义者,语气激烈地反对俱乐部接受东方人的进入,并发表了一连串的种族歧视言论,以贬低土著的身份地位来“捍卫”白人统治的“合法性”,声称“大家必须合伙起来,一起说‘我们是主人,你们是要饭的——你们这些要饭的要安分守己”[7]29。他表现得正如法农比喻的那样:“殖民主义者是一个裸露症患者(exhibitionist),对安全的关注(preoccupation)使他不断地‘大声提醒当地人,只有他才是主人。”[9]42他甚至以弗洛里脸上的胎记为由,怀疑他白人血统的“纯正性”:“我可受不了谁成天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脸上有块黑斑的原因。花斑一块,而且瞧他那黑色的头发、柠檬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个欧亚混血。”[7]32弗洛里就此被白人同胞贴上“有色人种”的标签,受到种族主义话语的不公正对待。在以埃利斯为代表的殖民者看来,弗洛里不那么“白”的外表、与土著人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对土著文化的欣赏使他具有了一种“打破了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10]116的身份,动摇了殖民主义的权威,弗洛里也就在殖民主义的“承认规则”(rules of recognition)下被排斥和另眼相待。弗洛里曾一度在反对维拉斯瓦米加入凯奥克他达俱乐部的通知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举动不仅是因为他害怕吵架,还因为他意识到胎记带来的歧视让他无法与其他白人成员平等交流:“啊,他可实在是厌烦吵架呀!那些嫌言怨语、奚落辱骂!一想到这儿,他就有些畏缩;他觉得脸上的胎记清晰可感,不知喉咙里有什么东西,让自己嗓音变低、心里发虚。”[7]64胎记使他在偶尔放弃自身作为“白人老爷”高高在上的地位時,就会被定义为“低白人一等”的“混血儿”、“非我族类”的“他者”,让他在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环境中无法正常发声。与生俱来的白人身份将弗洛里禁锢在了种族主义的囹圄之中,他虽然发自内心地厌恶殖民主义话语对人性的扭曲,但切身的利益关系又让他无法完全从中挣脱,这导致弗洛里在遭受俱乐部其他成员的质疑之后,面对是否要继续帮助自己的朋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进入俱乐部时一度退缩犹疑,变动立场。正如奥威尔在一篇关于缅甸的随笔《射象》中所说:“一旦白人开始变成一个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2]73作为殖民者和“白人老爷”的弗洛里虽然试图挑战殖民主义的陈规,却又无法完全跳出自身的局限,复杂而矛盾的身份认同是他悲剧结局的导火索之一。
起初,主要由于以旧成员埃利斯为首的强烈反对,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未能进入俱乐部。但在当地缅甸人民一系列激烈的反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后,俱乐部成员不得不直面英缅关系不复从前的现实,终于招募了新成员吴波金。吴波金的加入并没有引起不愉快的动荡,双方都很高兴:吴波金实现了他最大的梦想,欧洲人“对选了他很是满意,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新成员”[7]302。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就此打破了“只有白人”的旧规。随着英缅关系的不断变化,殖民者不得不做出调整,他们希望将俱乐部建立为远离东方人的“庇护所”的期望也最终会破灭。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对新成员的接纳,反映了当时的大英帝国为了缓和英缅民族冲突,不得不放弃一部分白人特权。在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英国殖民帝国衰落的背景下,殖民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政策,而这也是多元文化协商的产物。
二.缅甸社会:模拟与矛盾
《缅甸岁月》中描绘的缅甸是一个炎热、贫穷、落后和原始的国家,这里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东方人:缅甸人、中国人、印度人,还有一些东西方混血儿,他们与英国殖民者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断存在着对立和联系的复杂情况。作为殖民者,英国人用他们的军队和警察控制着缅甸,以更好地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英国人在缅甸还宣传白人种族优越论。这一观念给被殖民者注入了一种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植根于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使其在种族主义视角的凝视下不断自我贬低,逐渐厌弃本民族的文化,并主动向殖民者所谓的“优越”文化靠拢。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中提出“模拟”(mimicry)概念作为“混杂性”(hybridity)概念的具体化,并以此来描述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文化的仿效,而这种仿效将产生“几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10]86的主体。巴巴以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模拟人”(mimic man)概念为例,认为这一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吉卜林、福斯特、奥威尔、奈保尔的作品”,他们是“有缺陷的殖民模拟的产物”,“被英国化,却绝不是(真正)英国的”[10]87。麦考利的“模拟人”概念原意指在殖民地“形成一个‘翻译者(interpreter)的阶层,他们有着印度血统和肤色,但在品位、思想、道德和才智方面英国化”[11]116。在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中,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可以看作这一阶层的代表之一,他是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的典型,思维方式展现出明显的西方化倾向。维拉斯瓦米和他的朋友弗洛里经常围绕大英帝国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他们的立场往往正好相反。作为“白人老爷”,弗洛里言辞尖锐地揭露大英帝国主义的本质,包括白人的种族歧视、对缅甸环境的破坏和剥削压榨的殖民政策。但维拉斯瓦米却称赞英国,忠实地崇拜作为白人的英国人,即便面对弗洛里的冷嘲热讽,他依然热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在反驳弗洛里时,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您为什么总是辱骂您所谓的那些白人老爷呢?他们是世上的精英啊。想想他们的丰功伟绩吧——就说那些把大英帝国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伟大行政官们……英国绅士也是非常高尚的典范啊!他们彼此之间忠诚磊落!伟大的公学精神!即使是那些举止令人遗憾的人——我承认某些英国人很傲慢——也具有我们东方人所欠缺的那种伟大而纯正的品质。但在他们粗犷的外表下面,是一颗金子做的心。”[7]36
显而易见,维拉斯瓦米的身份认同与他的种族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他身为被殖民者,却为殖民者的所作所为辩护,因为他已经内化了大英帝国一直以来宣扬的殖民话语。他热衷于赞美那些英国绅士,试图用这种赞美所带来的身份归属感和优越感来掩饰对自己种族的自卑感。“他表面上表现得高尚而得体,但这与他内在的畸形形成了对比。”[12]60维拉斯瓦米的处境反映了作为弱势群体的被殖民者在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主动抛弃自身与固有文化传统的联系,以白人文化为先导并进行模拟,力求来自西方文化的认同。因此,加入凯奥克他达俱乐部对他而言,代表着被“欧洲绅士们”认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凯奥克他达分区的治安官吴波金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服务和奉承英国人,剥削和压迫缅甸人,为了获得欧洲俱乐部的资格竭尽所能,而那对他来说是“比天堂还要难登的至圣之所”[7]149。他对进入俱乐部的执着追求同样来源于殖民话语下被殖民者对自身种族与文化的强烈自卑,和对白人“精英”文化的狂热崇拜。吴波金厌倦了仅仅局限在缅甸人的社交圈中,进入俱乐部在他看来正是摆脱原有种族和阶级身份并融入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一件真正伟大的事情,高尚、光荣”[7]148。为此,他甚至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打击作为维拉斯瓦米的朋友和支持者、身为白人的弗洛里,并承认为了自己的利益,之前也曾“整过白人”。不知不觉中,他在为殖民帝国效力、模拟殖民话语的同时,也挑战了殖民者的权威。在殖民体系中浸淫许久的吴波金对白人的心理已然十分熟稔,并从中发现了他们的软肋:“对白人不用指责;你得当场抓住他才行。让他在大庭广众下丢脸,就在现场。”[7]227因此,他指使弗洛里曾经的缅甸情妇马拉美大闹众人集聚的教堂,颜面尽失的弗洛里向伊丽莎白寻求和解失败,最终绝望自杀;吴波金也最终实现了他进入俱乐部的梦想。讽刺的是,弗洛里曾经在收到吴波金暗含威胁的匿名信之后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觉得,一个东方人真能对自己造成什么危险”[7]80,而他的结局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由东方人吴波金的阴谋导致。凯奥克他达俱乐部曾经制定白人老爷的“五大主要美德”,其中有一条即强调“我们白人必须团结在一起”[7]201,但吴波金一手策划的阴谋的成功,却向我们展示了白人群体的不团结:为了是否接纳东方人进入俱乐部争吵不休,对流言蜚语的将信将疑,对弗洛里的另眼相看,等等。正如弗洛里本人所说,“我们的传统就是一起饮酒作乐、共享美味、装作是朋友,尽管彼此都深恶痛绝。我们所谓的团结一致,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7]37殖民者将俱乐部构建为“白人的中心”,吸引模拟殖民文化的被殖民者以进入俱乐部为目标而努力;换而言之,英国殖民者为被殖民者提供了机会来模拟宗主国文化,但被殖民者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了解殖民者的种种问题——因为殖民者经常会在许多判断上产生误差和错失”[13]103,揭露了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乃至殖民体系本身的缺陷,从而出人意料地挑战了白人的权威。
维拉斯瓦米和吴波金的模拟产生于殖民地的混杂之中,然而他们的模拟只是为了摆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而没有对殖民话语进行怀疑与否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殖民话语的权威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模拟既是相似也是威胁”[10]86,它对殖民权威进行了扰乱。李锋曾以《缅甸岁月》中的埃利斯为例,通过他对“英语讲得太好了”的缅甸管家和进入教堂的土著基督教徒的咒骂这两个例子,指出被殖民者的模拟会引起殖民者“心中的恐惧”,因为这将模糊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14]98。而从《缅甸岁月》的结局来看,这一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被打破:模拟殖民话语的吴波金看穿了殖民者的软肋,并据此击败了白人弗洛里,最终成为了俱乐部首位来自东方的成员。
综上所述,在《缅甸岁月》中,模拟引发的后果无疑是矛盾的:对于殖民者来说,本意在于强化权威却最终暴露了自身的虚伪,试图捍卫“五大美德”却最终不得不让步;对于被殖民者来说,努力靠近西方文化却令自己陷入身份困境,孤悬于同胞之外,也并未真正被西方所接受——执着于与“英国绅士”交流的维拉斯瓦米最终遭排挤成为边缘人物,“功成名就”的吴波金也未真正进入俱乐部的核心,出于对大英帝国和个人权力的极度崇拜,他在进入俱乐部之后满足于现状,重新变回了一味奉承英国人的模样。奥威尔以其冷静锐利的笔触,深入描绘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在揭露殖民话语对人的扭曲的同时,也思考着复杂的人性。
乔治·奥威尔根据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深刻反思写下的《缅甸岁月》反映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属缅甸的境况,书中欧洲俱乐部试图维持种族主义的陈规而最终失败的结局,以及缅甸社会中复杂的矛盾状态,为我们提供了探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关系的视角,以及对构建身份认同的思考。在《缅甸岁月》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英国人弗洛里厌恶并试图反抗殖民话语,东方人吴波金则能够通过对殖民话语的“模拟”挑战并冲击了殖民者的权威,小说结尾更是通过吴波金阴谋的成功与弗洛里的死亡扭转了两者之间的地位关系。但无论是弗洛里还是吴波金都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作为东方人的吴波金,他挑战权威后又止步于个人利益,重又回到奉承白人和服務殖民帝国的位置上。这启示我们:只有对殖民话语进行彻底的反思,构建起正确的身份认同,才能找到摆脱压迫的新出路。
参考文献
[1]Brander,Lawrence. George Orwell[M].Longmans,1956.
[2][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Hammond, J.R. A George Orwell Companion[M].Macmillan Press, 1982.
[4]Boehmer, Ellek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黄绍栋.弗洛里之死:《缅甸岁月》中的男性气质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
[6]王艳红.他者如镜——论乔治?奥威尔东方之旅激荡的文明反思[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7][英]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M].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Timbs,John.Club life of London[M].R.Bentley,1866.
[9]Fanon,Frantz.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M].Penguin,1965.
[10]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Routledge,1994.
[11]Sharp,H.Bureau of Education.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M].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0.
[12]Lieskounig,Jürgen.“The Power of Distortion:George Orwell's ‘Burmese Days”[J].Journal of the Australas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7(2012): 49-68.
[13]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李锋.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中的种族政治[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2):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