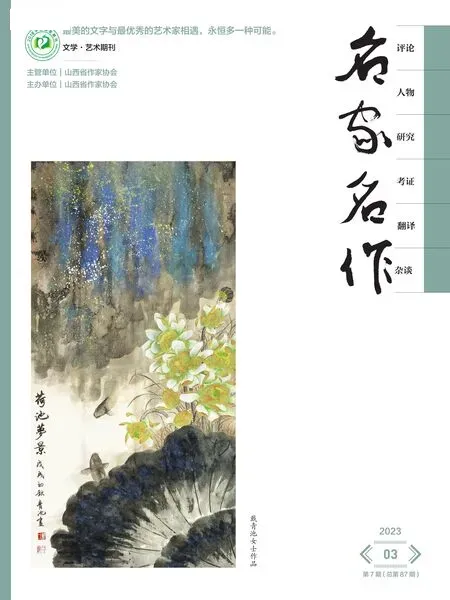旧体诗词的当代命运
——以《诗刊》为例
祝 欢
一、引言
近年来,旧体诗词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研究成果硕果累累。众多研究成果之中,个案研究与旧体诗词入史问题研究较多,回到历史现场,在报刊上从传播视角研究旧体诗词文体命运的成果还比较少。受语言工具所限,旧体诗词自现代文学开端就被打上“旧”的标签驱逐出新文学的行列,旧体诗的“非法”性甚至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然而随着《诗刊》创办与领导人旧体诗词的发表,区分新旧文学的标准由只看形式扩大到兼顾内容,旧体诗词在此背景下才获得呼吸,取得了本该有的“合法性”地位。本文试图从《诗刊》(1956—1964)创刊情况谈起,分析这一权威性刊物是如何为旧体诗词争取“合法性”地位,《诗刊》对旧体诗词在当代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说明语言问题是限制传统诗词在当代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诗刊》的双重属性
《诗刊》的创刊经过,目前有两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一是臧克家的争取。“大家都说,诗歌需要一个阵地,应该搞个刊物才好……我把这些事情向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同志谈了……不久,刘白羽同志到我笔管胡同的宿舍来了,说:领导已经同意诗刊出版。”[1]二是说《诗刊》的创立是徐迟的积极倡导,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二次理事会议快要闭幕的时候,“他举手从坐席台上站起来发言:中国是个泱泱诗国,建议创办一个专门发表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刊物,就叫《诗刊》好了。”[2]不论《诗刊》具体的创刊情况是哪一个,我们都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发现,从一开始《诗刊》就带有官方与民间双重性质。
不论具体的创刊情况怎么样,“党的关怀”是回忆录中着重强调的一点。强调这点说明的不仅仅是《诗刊》的合法性地位,更强调的是《诗刊》是全国性的权威诗歌刊物。
第一,在诗人群体选择上,应“双[1]百”方针的倡导,《诗刊》编辑部团结老中青三代作家并积极挖掘新人,繁荣诗歌创作,广泛邀请各派诗人参与。艾青在《诗刊》上发表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代表了早期诗风的回归,抽象、新颖、独特,给诗坛带来了从只注重思想到也注重艺术性的新变化。甚至《诗刊》还请已经在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陈梦家在刊物上谈谈其人其诗在很长时间都是禁区的徐志摩的诗。不仅如此,《诗刊》同时还邀请公刘发表了《迟开的蔷薇》,敢在刊物上发表爱情诗,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第二,《诗刊》个性的是主编与副主编的政治身份。在强调阶级成分的年代,臧克家是地主阶级出身,从政治面貌来说,臧克家是民盟成员。《诗刊》副主编的徐迟也非党员身份,但最能体现《诗刊》独创性与个性的大胆举措是公开刊登旧体诗词。
这个时期人们普遍认识到新诗的发展仍然存在不足,苏联文学的前车之鉴使大家认识到,民族化发展才是新诗发展的出路,新诗发展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这个时期关于如何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李煜词、陶渊明诗、山水诗、李清照词、李白杜甫的诗都曾是20 世纪50 年代文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讨论并不在于就旧体诗论、旧体诗,讨论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是在如何借鉴古代的优秀遗产蓬勃当下的创作。这些讨论最后形成的共识是,新诗应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大众一系列的关于如何借鉴与继承古代遗产以及关于新旧诗歌的讨论,正是立足于如何蓬勃新诗发展,一系列关于古典文学遗产的讨论,使得诗歌与旧体诗又重新活跃了起来。正是在此背景下,《诗刊》发表旧体诗词不仅仅是合乎风气的做法,同时也有敢为人先、引领示范的勇气。正是《诗刊》既具有官方的权威专业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的双重性,才可能会有发表并开创旧体诗栏目的自主性。
三、旧体诗“合法性”地位的获得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文言为语言工具的传统诗词被冠以“旧”的标签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白话文为语言工具的现代文学。以追求现代性为旨归的现代文学抛弃了在他们看来束缚现代人思想的古代汉语,进而给一切文言作品贴上落后的标签,自此传统诗词在文学史上一直被压抑,其“非法性”地位甚至延续到了当代文学时期。但《诗刊》从创刊开始就为“非法”的旧体诗保留了位置,在《诗刊》的引领下旧体诗词“合法性”地位最终得到确认。
1957 年创刊之前,毛泽东诗词广泛流传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诗刊》编辑部提议请毛主席在《诗刊》上发表一个定本。于是编辑部去信希望得到毛主席的回复与肯定,很快毛主席回信包括十八首旧体诗词和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发表在《诗刊》创刊号头条,引起了诗界巨大的反响。在1957—1964 年这八年中《诗刊》又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共十九首旧体诗词作。除此之外,《诗刊》还发表朱德、陈毅、董必武、李济深等人的旧体诗词共约四十首。领导人旧体诗词的广泛刊登,对于提高旧体诗的“合法”地位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自从毛主席诗词发表后,旧诗渐渐多起来了,并且也神气起来了。”[3]许多作家和写新诗的诗人开始写作旧体诗词,既写新诗也写旧诗的“两栖”文人逐渐增多,例如茅盾、老舍、沈从文等新文学家都是在1957 年前后又开始写作旧体诗词的。
旧体诗能在当代取得“合法”性地位,领导人公开刊登旧体诗词是根本原因,但《诗刊》煞费苦心创办并保留旧体诗栏目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然而“旧体诗页”开辟出来后,要巩固这个栏目绝非易事。虽然毛主席同意刊发其旧体诗鼓励了旧体诗创作,但同时刊登的《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4]编辑部成员为巩固旧体诗栏目,开始向社会各界诗人约稿。据《诗刊》原常务副主编杨金亭回忆,臧克家及《诗刊》社的同志们为了巩固和坚守旧体诗这个栏目,动了不少脑筋“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文坛名家之作的不定期栏目,向诗人词家乃至一般诗词作家的每期两页的固定栏目过渡。”[5]从而摆脱了“旧体诗页”只能借用领导人和名家名作维持的局面,使得“旧体诗页”成为广大诗人都能平等发表的栏目。由此,旧体诗才最终由“非法”性走上了“合法”的地位。
四、旧体诗复兴的艰难
自《诗刊》刊登旧体诗词后,最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公开发表旧体诗词的刊物增多。各个杂志放开了手脚竞相发表旧体诗,“而1957年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人民文学》《诗刊》等中央和省市报刊上纷纷发表旧体诗词作品,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其中,《光明日报》自1958 年1 月1 日起创办了《东风》副刊,发表名家旧体诗词是其特色之一。”[6]《诗刊》的成功示范后众多刊物纷纷效仿,扩大了旧体诗的传播途径与生存空间。
其次是刺激了旧体词创作。“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旧诗,甚至有些新诗人也写起旧诗来,青年人也竞相效仿。”[7]旧体诗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加之旧体诗词作为中国古典遗产其自身魅力自不待言等因素,共同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既写新诗又作旧诗的“两栖”文人越来越多,许多新文学家“勒马回缰作旧诗”,如沈从文、茅盾等人,甚至五四时期竭力批判排斥旧体诗、提倡新诗的先驱者们,都开始写作旧体诗,如叶圣陶等。旧体诗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数量不断增多,这是旧体诗生命在当代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影响是改变了人们对旧体诗的看法,相比于仅仅是从形式上区分新旧,在《诗刊》发表旧体诗后,区分新旧文学的标准有所扩大,不仅仅是从形式上区分旧体诗,注意内容才是区分新旧文学的重点。1962 年郭沫若在《诗刊》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主席的诗词不能说是旧的。应该从内容、思想、情感、词汇上来判断新旧。”[3]陈梦家在《诗刊》上说:“从形式上来看诗,是不妥当的。”[8]陈毅在诗刊社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也说:“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3]在《诗刊》发表旧体诗以后,改变了人们传统对立的新旧诗歌观念,新诗与旧诗的界限被重新定义。如上面所分析过的,由于新诗发展不足使大家意识到传统的旧体诗词可以作为新诗发展所需的养料。新旧体诗歌之间的界限被重新定义,新旧对立的思维才被打破,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虽然《诗刊》发表旧体诗、保留旧体诗栏目使得旧体诗的地位上升,为旧体诗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是旧体诗词仍然没有与新诗或者说旧文学仍然没有与新文学取得同等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语言。语言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在创造语言的过程中人有很大的能动性,但一旦语言被确定下来,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根深蒂固性,如果没有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在自我变革的强烈需求,转型是非常困难的,更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从现代语言哲学看来,以语言的新旧来区分新旧文学是合理的。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符号还是思维思想本体。高玉认为,虽然提倡“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没充分意识到语言不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思想思维本身,但由于提倡改革的他们本来留学欧美,受西方现代文化浸染,无意却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将文学带到了现代,引起了思想界的巨大变革。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也是思维本身,运用不同的语言写作,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自白话文运动以后,白话文成为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文言被贬低被边缘化,白话成为文学正宗,是不可逆的潮流。即使是领导人以及名家的示范与倡导,即使是官方权威刊物刊登旧体诗词,从语言角度说来,以文言为工具的旧体诗在当代已经不可能与新诗平分秋色。
从创作者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旧体诗创作相对新诗来说更需要门槛。传统诗词是文言的产物,能写会读旧体诗至少需要有文言的功底,但自从白话成为文学正宗以及教育部规定在教学中使用白话以来,文言已经与普通读者渐行渐远,创作与欣赏旧体诗词必须具备的文学或者说文化修养如今普遍不足,也导致了旧体诗词在当代复兴的艰难。
五、结语
《诗刊》虽为新诗的代表刊物,但实际上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诗刊》为例,运用现代传播视角在《诗刊》中考察旧体诗词当代的文体命运。探究旧体诗是如何重新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如何由“非法”地位走向合法地位。但这种“合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力的,在现代汉语背景下,旧体诗词创作虽然一直延续,但旧体诗词入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五四”后被打上“非法”标签的旧体诗词,虽然在《诗刊》的引领示范下,在当代获得了“合法”地位,但“落后”的语言形式,一直是阻碍旧体诗词合法进入在“现代性”焦虑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要原因。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