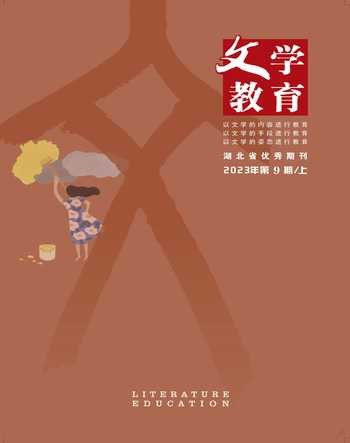文学地理视域下的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化研究
杨静静
内容摘要:汪曾祺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具备极高的文学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是在众多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汪曾祺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一份子的创作所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本文将汪曾祺创作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的形式,分别从里下河地区的地域文化风貌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以及汪氏小说对里下河文学内涵的发展等方面来展开,为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学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切入视角。
关键词:汪曾祺 地域文化 里下河文学流派 短篇小说
近年来,随着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乡土文学也重新盛行起来。里下河文学作为乡土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围绕着汪曾祺、毕飞宇等在文界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里下河作家而开展的。尤其是对汪曾祺研究较多,成果主要围绕着汪氏小说所产生的意义等方面。但作为文学现象出现的里下河作家群与该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地域文化影响作家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还作用于着他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方式,这便引发我们对里下河文化和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次的思考。
因此,本文以汪曾祺的生活背景、具体创作环境等为例来分析“里下河文学”的特征,将作家和文本结合起来,更能完整梳理出来该流派文化内涵受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首先,论述里下河文学产生的背景: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其次,文学产生的背景决定了汪曾祺笔下的里下河地域文化品格。最后,汪曾祺在继承里下河地域文化的同时,为里下河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一.里下河文学的发展背景
存在无疑决定意识。一定的文学现象可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绝不仅仅是偶然,它是多种因素在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结果。“作家的文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自然、社会的客观实在在他的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某种形式的认识。”[1]一个文学流派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必然与该地的地域环境以及人文风情密不可分。
(一)独特的地质地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里下河文学的产生、成长与繁荣必定离不开里下河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里下河”这个名字乍一听,你会以为这仅仅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河流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四条水系流经此处,在水流的冲击作用下,一个平原成为了人群聚集之地的最优之选。古代人称之为“登堤而望,内若釜底,外若建瓴”[2]里下河这个区域是江苏境内长江至淮河这一段中最低洼的地方,是实实在在的水乡,正是这独特的地质地貌为里下河人民的繁衍生息和文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家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被水源富足、气候适宜、泥土相对肥饶这些因素所满足。同时这些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对作家的气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写作中大多以里下河地区的地域风景和人情特色为主要的写作对象,透露出了自然而又清爽的格调。
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在早年创作的作品《鸡鸭名家》中通过描写风俗人物的种种事迹,体现出作者对俗世里万事万物的欣赏和对普通小人物的关心。文中讲到鸭子们所活动的地点白莲湖:“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湖邊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3]这里通过对湖的描写,将一个气候温和湿润、景致优美的苏中里下河地区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湖泊众多、水源充沛使万物得以滋润生长,盛产鱼米使人们过着自足自乐的生活。常年生活在水边使得作家的写作风格清新、自然,笔下的人物也如同流动的河水一样灵动。
同时,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能保证当地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也使得他们性格爽朗却不乏心思细腻心思细致。《晚饭花》中,作家借李小龙的视角对王玉英的相貌进行了一番描述:“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4]这样的少女给人的印象就是天真朴实、开朗豁达,这与作家长期所生活在开阔的水乡是密切相关的。
(二)浓厚的文化氛围
“里下河”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带着浓厚人文气息的文化符号。自古而今,里下河地区这片沃土上出现过一大批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人物,包括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等,这与当地的深厚历史文化氛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里下河地区接受着两种文化底蕴的浇灌,它既领略到了独到的“楚汉韵味”,又是“维扬风骚”的集成者。而且,里下河地区历史上曾经聚集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明朝曾经施行过 “洪武赶散”的政策引得了江南的文人向苏北一带迁移,而到了明末清初,本土文学和外域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对里下河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通过考察便可以发现,“无论是汪曾祺还是毕飞宇、朱辉、刘仁前、庞余亮,我们可以从他们很多作品中看到《水浒传》,明清笔记小说的神髓以及流淌在骨子里的一种崇文精神,这都是里下河古典文脉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5]但如果仅仅依靠文人墨客的传播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里下河文学恐怕很难呈现出像如今这样的景象。其次,在里下河这片土地上,所任职的历代官府都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重视教育,致力于将这片沃土改造得带有文化气息。因此,在这里不管是城市还是民间,老百姓都逐渐养成了追求风雅的性格,久而久之,民间也一直存在着清新、淳朴的民风。该地区是沿河而立,当地居民依河而活,商业文明因河而兴。在这里,听着评书、喝着茶不仅是文人雅士的爱好,也是一般平民所喜爱的。最后,一个地区有着一种地域性格,里下河地区的地域性格中不单单包含着尊道贵德的良好品质,又有潇洒自在的人格魅力。人的精神和气质就是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的集中表现。汪老笔下的人物虽然各有特点,但是总的来说,不管何种人物都不会带给读者一种压抑和沉闷之感。相反,各色人物有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识,这些便得益于汪曾祺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的感染以及汪曾祺对家乡民间文化的信任。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及历代作家的努力,才推动了里下河文学的蓬勃发展。
二.汪曾祺笔下的里下河地域文化品格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改革、民族关系、人口迁移、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6]地域文化等因素会对作家自身性格气质的形成、价值取向的确立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作用到作家所创作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存、地方传说等显性文化,还是社会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等隐性文化,无一不渗透着浓郁的地域色彩。”[7]几千年来,里下河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特质——它既具有“水”的细腻和灵动;又有着“土”一样的朴实、顽强,在两者的交融中呈现出了细腻、温柔、内敛、和谐的文化品格。里下河地区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对当代里下河作家流派产生的影响,这在他们的创作中得以窥见。
(一)泱泱流水的“柔”情结
汪曾祺的作品中所讲到的水意象,既指的是自然界中人们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物质的水,又代表着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里下河文学中也透着泱泱水气,这种水气和水的实体有关。汪曾祺多次谈论过自己和水结下的不解之缘,自小生活在这水乡之中,所触所感无一处不与水有关。他也曾在书中写道:“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8]通过了解汪曾祺的成长环境和生平经历以及里下河文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我们便会发现水意象作为研究汪曾祺作品和里下河文学的切入点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选择水意象是作者本人时常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他所接触的都是和水有关的。另一方面,是作者在心理上进行的自主选择。
在《大淖记事》中,作者首先带我们见到的便是一望无际的河水:“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9]这篇小说的背景就是一片浩淼的大水,而在这片水中,妇女们敢脱光衣服在水里嬉戏,十一子和巧云可以在沙洲上的草丛中进行幽会。这些对水的描写,都来自于作者每日的所见所闻。那些与水相伴的日子都印在了汪曾祺的内心深处,在脑海中聚集,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同时,流动着的水又与活跃灵动的生命形态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水是流动的,象征着江南人的活泼、富有生命力。可是江南的水,少有汹涌奔放的气势,只是长年潺潺汩汩地流淌着,培育出了江南人特有的温和柔美的性情。”[10]《受戒》中描写了这样一个豆蔻少女:“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11]这个灵动的少女就是小英子,她天真烂漫,活泼伶俐,丝毫不受俗世尘烟的浸染。她家所居住的房子在大淖这个地方是少有的:“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12]我们可以设想,正是这样开阔的水乡才培育出了这样一个豁达、开朗、豪爽的少女。同样长时间在水乡居住,水的柔软和坚韧浸润出了汪曾祺的宽容和乐观,致使其文学作品不写过分悲伤的故事,创作总是含蓄而不直露,留有余地。
水情结使得汪曾祺在创作中经常将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有着充分水气的地方,更赋予笔下人物以充盈的“水气”,正如他自己所说:“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13]汪曾祺笔下的带着“水气”的水乡人就是在汩汩流水的滋养下,肆意挥洒这生命的活力。
(二)土生土长的“刚”文化
里下河地区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造就了里下河地域独特的文化特质,同时也赋予了文学品质中既带有水一样的流动着的柔和之感,又夹杂着土地的朴实和坚毅,在两种文化特质的交织下呈现出和谐、细腻的艺术风格。里下河地势四周高、中间低,看起来就像一口锅。正是因为这看似封闭的“锅底洼”地形,把里下河地区包围成封闭的区域,为这里的文化蒙上了一层保守的色彩,将在苦难面前不畏惧、不退缩的土生土长的刚毅品格保留并传承了下来。
这种“刚文化”也体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女性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温柔和贤淑的代表。但是,更多的时候,她们压抑了心中的欲望和情感,而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刚强。在里下河文化内蕴的熏染下,这里的女子既不是足不出户、受到道德伦理制约的封建女子,也不同于一般作者笔下的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女性,而是在乡村土生土长,不受外界干扰,保持着最自然模样的女性。[14]这些女性具有水一般的灵动,但是所不同的是,在天真烂漫之外,身上还自带着人生智慧。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或许没有出生于富贵之家庭,也没有特别好的生活氛围,甚至父母都不在了。但是这些女性从不会去埋怨生活带给自己的苦难,而是用一种勇敢、认真、踏实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在《侯银匠》中侯菊就是具有这样的“土”一样内敛而又刚强的女性。侯菊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缺少了母亲的爱护却依然能精明巧干,早早就学着大人的模样帮父亲侯银匠料理内外的事务。就算没有得到生活的善待,她却仍能够安天乐命,用“土”一样顽强精神来面对生活的风浪。
“刚文化”也和汪曾祺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汪曾祺一生虽算不上传奇的一生,但却算得上足够坎坷。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划分为革命右派,必须经历各种改造,如关进牛棚自省。可是他并没有像别人想的那样,因为政治对他的改造而喪气。反而看淡了,并与苦难进行斗争,坚守自己的内心,把这段往事看作一次值得回忆的生活经历。汪曾祺故事中的人物也有着这样豁达、通透的性格。《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历经了一系列的人生起伏之后,面对一个人要照顾两个男人的局面,没有绝望,也没有逃避,勇敢地承担起生活的责任,完成了生命的蜕变。当然这种朴实和刚毅也体现在当地老百姓的身上。巧云没有了清白,并没有任何人对她进行嘲笑和歧视,反而为她打抱不平,赶走了刘号长。是这片土地赋予了他们的朴实和热心,虽然经历了困难,也少不了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但总是会用热情乐观的心来应对,并一直对自由保持着不懈的追求。而全部的这些都离不开里下河这片丰饶大地的滋养。
三.汪曾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帜[15]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壮大,不仅是受益于里下河地区的自然和文化氛围的影响,更离不开作为中坚力量的旗手——汪曾祺的贡献。汪曾祺在继承里下河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使得里下河文学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特色。
(一)俗世里的温情
汪曾祺小说中常构造出了一片纯然安乐、与世隔绝的乐土。汪曾祺自己觉得,生活是很好玩的。他的作品中虽有悲苦,但在这悲苦的背后有着柔和的人情来支撑。这份温情使得这平凡的俗世近乎仙境。作为一个抒情式的大家,汪曾棋对故乡和人民的叙述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对平民生活中,风俗人物的描写和对温爱和谐人性的赞扬上,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相当的笔墨去书写那隐藏于这美丽人性风景背后的人的生存艰难和在此艰难下散发的温情光辉。
这俗世的柔情中,一种是单纯的爱恋之情。《受戒》构造了一个充满自由空气、远离现世斗争的世外桃源,通过描写从小一起长大的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纯纯的感情,流露出了美好、纯真的人性。和我们所了解到的严格遵守条条框框的寺庙所不一样的是,“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他们经常打牌。”“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16]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淋漓尽致地将一个充满了浓郁温情的人性世界展现在读者眼前。正是在这种俗世中,明海与小英子才可以自由呼吸与成长,他们之间的单纯的爱情才没有被误解、玷污和阻挠,并得以继续自由发展。
另一种则是,热烈的邻里之情。平日里,大淖里的乡亲们性格比较开放、大大咧咧、在处理事务上也不拘小节。可当有人遇到不幸时,都会得到乡亲们的援助。《大淖记事》中,在十一子被刘号长一行人打得半死不活时,锡匠们把钱凑起来,将人参买来,熬成参汤给他喝,并向县政府伸冤,县政府没有做出实际行动后又纷纷上街游行,顶香请愿,将号长赶出了大淖。从中可见乡亲们的淳朴和义气还有大淖和谐的氛围。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大淖里的人们最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他们在物质上相互帮助,精神上彼此理解,正是在面对这个俗世时所留下的柔情。
而在特殊时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许会表达得隐晦,但是会一直存在。《寂寞与温暖》一文中,受尽文革批斗和侮辱的技术员沈沅在几经磨难后,精神接近于崩溃。在这种精神紧张,人人自危的时期,一位老工友王栓却在安慰他一定要好好地挺过去。其实,主人公的悲惨经历也是作家本人在回忆文革中自己的境遇。但他与其他作家所展开的角度不同的是,他并未对主人公被打成右派的来龙去脉多加赘述,只是简单说了下他的经历是与他的日记言论和对领导的批评有关。
汪曾祺一直以“一定要把这样一些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把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17]这是他笔下的人物是充满着温情而又立体、社会充满着柔情与爱的重要原因。
(二)困境中的人道主义
文艺复兴期间,欧洲大地上兴盛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它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本性解放,重视维护人类的尊严。起初是以人文主义的形式存在着,后发展为一种世界观。这便是人道主义。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8]。他曾说:“我不了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19]汪曾祺将这种人道主义丰富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化内涵,它在汪曾祺的笔下主要体现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宽容博大的仁爱思想。
汪曾棋以写人物为目的,他是“贴着人物来写人物”。然而你若是常读他的作品,你就会清晰地见到一群善良、朴实、宽容而又不乏生活的韧性的人们。这些人们的行为和内心是相契合的,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做的一切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在这里“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这看似“随便”的婚嫁习俗,实质上是对人性最大的尊重。它从未强调所谓的伦理道德、女性的贞洁,而是充分尊重和释放人性,提倡追求真正的情爱和个性解放。大淖人身上所带着的一股韧劲和由此散发的魅力也正是对人性尊重的体现。汪曾祺笔下塑造的多为小人物,正是因为身份的平凡才使他们更容易被生活所带来的重负所拖累,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这困苦的生活而因此堕落下去,而是在绝望中重拾希望,有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大淖记事》中,巧云面对着自己被欺辱,十一子被刘號长打伤,不知何时才能好,自己还有一个残废的爹需要照顾的局面,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承担家中的重担,像个男人一样挣钱养家,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在小说的结尾,当他人问巧云,小锡匠的身体能否好起来,她笃定地答复到会好,这个答案包含着巧云对未来的信心以及不轻易屈服的韧劲。她对爱情自由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热情,都体现出了人情的光辉。
汪曾祺小说总体所要呈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儒家博大的仁爱思想。他在《自报家门》里说:“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20]这体现出了汪曾祺是极其推崇儒家的宽容的“讲人情”的仁爱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也可见端倪。只是,汪曾祺并不是在直接强调仁爱,而是采用了一种通俗的方式,将“仁爱”融化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和风俗事件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岁寒三友》以竹、松、梅的别号来命名,对应着小说中讲的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21]:画师靳彝甫、开绒线铺的王瘦吾和做爆竹的陶虎臣。这三人虽然职业不同,但是为人处世上却有着太多的相似点。他们的经济状况虽不是特别富裕,但也不是穷苦潦倒,都属于这平凡人生中的普通一员。但他们又不是最普通的,他们比平凡人更多了些美好的品格。他们善良而热心,在帮助别人之时,倾尽所能。这三个人物凝聚着汪曾祺对世间万物的仁爱思想。
(三)原始自然的“民俗情”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22]汪曾祺出生于一个沿海的经商而又带有文人气息的家庭,故能经常接触到各行各业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市井生活和民间习俗颇为了解,故其小说对民俗的描写非常细致。汪曾祺小说大多取材于家乡农村和周边地区,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家乡景致、风俗,故被称誉为“风俗画”作家。
《大淖记事》里描写到了不少当地的习俗,其中最为热闹的莫过于过节滚钱这个娱乐活动:“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就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就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到多少取多少。”[23]作品中对滚钱的细节描写看似平常,其实充分渲染了过年时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热闹气氛,让人读了以后仿佛身临其境。
在汪曾祺作品中,我们时常能通过迎娶婚嫁、衣食礼仪等现象来感受当地的民风民俗。风情习俗这些在传统文学中被视为只起衬托、渲染作用的事物被作者提高到了与人物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审美关注的主体对象。作者将风情习俗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可以详尽展现人物的生活的全部和性格态度。而有的风俗的插入,可以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引出作者接下来要讲述的事物。总之,民俗的存在一定自有用处。《受戒》中,不管是对水乡万物的描写还是对庙宇节日的概述,无论是大淖里常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小英子和明海的嬉戏,都显得那样淳朴、真实,都没有一丝丝的扭捏作态。相信如果缺少了独特民俗风情的展现,小说不会有那样的审美效果。
风俗民情高度浓缩着千百年来的民族地域文化,全面展现了这个地区的人们从生活到文化上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是作家传达作品的内涵的一种凭借。里下河作家对家乡风俗的各种描述,赋予作品一种强烈的地域特色,彰显了该文学流派的独特内涵。
悠悠岁月沉积下地域文化,孕育了里下河文学流派,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乡土文学增添了新的一笔色彩。它的审美地表达日常生活,透露着节制、中庸与和谐的古典美学追求以及自叙传的特点都是为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路径。汪曾祺在继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又为里下河文化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里下河文学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打破宏大叙事,表达人间的“小温”也会使得文学的视野越发狭窄。里下河文学的创作既要走出去,也要不忘初心,只有具备了为新兴的时代发声的能力,里下河文学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文化作用。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2]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曹诗图.社会·文化·环境[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
[4]孟繁华.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5]卢军汪.曾褀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贾轸,唐文起主编.江苏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1978-200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0]杨学民.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写作,1995(1).
[12]雷鸣.诗意乡土书写的“同向歧异”——沈从文、汪曾祺乡土小说比较[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
[13]肖莉.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14]石兴泽.汪曾棋论[J]文艺争鸣,2007(4).
[15]邓玉久.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J].中国文学研究,2008(4).
[16]郜元宝.汪曾祺论[J]文艺争鸣,2009(8).
[17]季红真.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汪曾祺小论[J].文艺争鸣,2009(8).
[18]张雯雯,王春林.里下河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略论[J].小说评论,2015(05).
[19]孙建国.里下河文学的童年叙事[J].文艺报,2017(07).
[20]鄭润良.里下河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女性形象[J].文艺报,2017(005).
[21]温潘亚.里下河文学流派及其“域内”作家创作风格概述——读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J].雨花,2017(14).
[22]王干.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J].大家,2019(06).
[23]柳应明.论里下河小说的人物塑造特征[J].名作欣赏,2020(03).
[24]李芳.诗意的栖居——论汪曾祺小说的文化意蕴[D].长春:吉林大学,2004.
[25]彭接燕.漂泊的水手与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汪曾祺比较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26]张懿红.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27]孙玉珍.论当代里下河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28]朱毓瑶.江苏里下河作家群创作的民间性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29]常伦军.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0.
[30]胡迟.迷惘·沉溺·升华——从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与苇岸的乡土文学创作看“诗性家园”的演变[D].安徽大学.2003.
[31]周卫彬.“里下河文学流派”初探[N].文艺报,2013-10-18(007).
[32]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几个关键点[N].文艺报,2016-07-22(006).
[33]郑润良.抒写俗世的温情[N].文艺报,2016-06-29(006).
[34]舒晋瑜.里下河文学流派能否进入中国文学史[N].中华读书报,2013-10-
16(006).
[35]舒晉瑜.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N].中华读书报,2015-11-18(012).
注 释
[1]曹诗图.社会·文化·环境[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243-244.
[2]贾轸,唐文起主编.江苏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1978-200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192.
[3]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53.
[4]汪曾祺.晚饭花集[M].杭州: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3.
[5]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几个关键点[N].文艺报,2016-07-22(6).
[6]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写作,1995(1):1.
[7]陈大路、将晓红:地域文化基本特征的新审视[J].学术交流,2007:11
[8]汪曾祺.浮生杂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
[9]汪曾祺.大淖记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
[10]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62.
[11]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16.
[1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15.
[1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第五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13.
[14]裴蕾,缪军荣《受戒》:用风情抒写人情[J].汉字文化,2019(04):71-72.
[15]杨学民.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4.
[16]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14.
[17]汪曾棋美学情感的需要和社会效果[J]文谭,1983:(1).
[1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1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91.
[20]汪曾棋.自报家门,汪曾褀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0.
[21]汪曾祺.受戒[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249.
[2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
[23]汪曾祺.浮生杂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