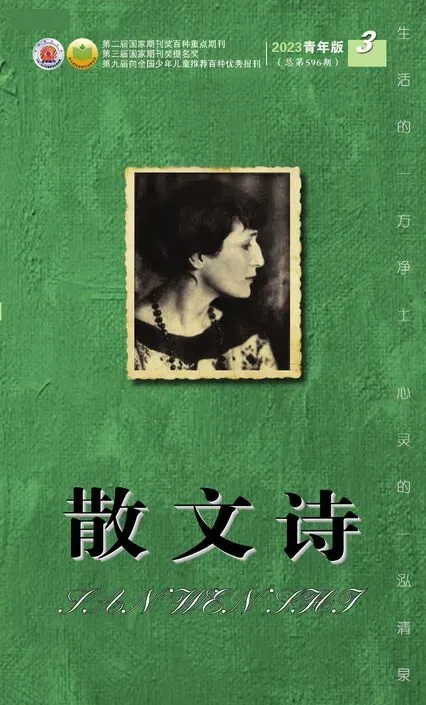在一座堙灭的都城里怀念先祖
◎赵凯云
履迹坪怀姜嫄
走过的人请把脚步放轻点, 飞过的鸟儿请把羽毛压低点, 游过的鱼儿请把鳍划慢一些。
时光独立, 地气与历史的身影对峙。
在平凡和神性之间, 在灰色和绚丽之间, 几千年的风雨, 我们怀抱谁的名字取暖, 怀抱谁羞花落雁的容颜, 把奔驰的岁月迷醉? 谁让我们在奔跑的地平线上窃取呼吸, 窃取植进胸膛的阳光?
站立寂静发丝间, 悬空的星子, 让我想起爬满树枝的火, 想起埋藏地下的灯, 想起隘巷、 履迹坪、 狼乳沟, 如何绽放出安静的生命之光?
是谁在古城墙上说: 万山成峰人最高, 万木成林火最红, 人心比御面通透。 是谁倾尽一生把梅花开在阴凉的峭壁上, 把一粒麦穗推进燃烧的谷仓中; 是谁掰开石头的心事, 把草木沉默的火熄灭?
群山望着我, 我无力回望, 越靠近, 就越陷落, 沉睡不起的城。 隔着光影的沟壑, 双手凌空一握, 掌心的温柔便绿满梦里河山。
废墟上, 没人知道光阴的鲜美, 草原一样辽阔。
凭借头顶的缝隙承接月色, 大雾四起的精美里, 一根稻草顺流而下, 抱紧你的肩头, 借清明的雨, 倾泻一场不易示人的泪水。 它的童年和垂暮一样孤独、 高远。
无畏的人间, 还有什么比传说更美, 更忧伤; 还有什么比时光更亮, 更悠长; 还有什么比水北的水更蜜, 更甜。
虚幻的时光流逝, 一座死火山喷发。
安睡的人, 紧贴岩石, 把脸翻转过来, 盈盈一笑的唇齿间,鲜花盛开, 烟花一样夺目璀璨。
注: 姜嫄, 一作姜原。 后世尊称姜嫄为圣母。 今彬州市炭店乡水北村有姜嫄墓。
永世魂存兮, 后稷
风劲雪疾, 天空像倒倾的鼓风机。
细密的白, 覆盖龌龊的世界, 盘根错节的爱恨, 福荫天下五谷。 融于大野, 隐于嘹亮的素洁。
就这样, 在隘巷, 在二郎坡, 在狼乳沟的冰面上, 用马蹄逃生, 用颤抖的鸟羽点火。 彻骨的冷, 在豳水的河面上嚎叫, 抱紧娘的肩头, 仍觉得疼。
麦子是泥土鲜活的孩子, 它催开所有的花朵, 打开所有坚硬的骨头, 在阳光下储备能量, 在布谷鸟高唱的喉音里抽穗、 拔节, 在滚烫的汗滴上算黄算割。
一把锋利的镰刀把饱暖深入二十四节气, 夜以继日地收割头顶的金黄。
在夯实的场院碾场、 脱粒、 戗麦, 把圆润闪亮的麦粒运进粮仓。 十指翻飞, 憨实的脸上开出古铜色的花。
这位种禾粟、 植桑麻的老者, 起垄播种、 扶犁而行的老者,在节气里“舂、 簸、 淘、 蒸、 烤、 熏” 的老者。 他清瘦的颧骨、皴裂的双手, 在走漏的风声里, 透露内心所有的秘密。
他负重前行的身影, 代表了华夏大地上所有春风、 夏日、 秋雨、 冬雪一生的表情。
在豳国的天空下, 他活出了一个豳国男人, 在农事给养中所应体现的饱满、 沧桑、 英勇、 无畏, 锃亮的锄头也比不过他骨头中的脆响。
从邰到豳, 从豳到邰, 疑惑而多艰的路上, 一路风霜, 一路雷电。 用犁铧唤醒庄稼破土拔节时的第一声啼哭。
泾河两岸炊烟缥缈, 山径的野花疯狂地开, 摸黑回家的人,狂风暴雨一涨再涨, 一升再升, 也淹没不了急切的脚步。
千百年后的今天, 作为他遗世的子嗣, 作为他遗落当世的儿孙, 却无法在众生的喧嚣里, 匍匐平原古朴的冻土上, 集齐历史零落的碎片, 无法在明亮起来的天地间追溯史书里的水声泱泱。
昨日, 在豳山砍柴, 生火取暖煮饭。
今日, 在断泾激流的船舷上极目远望, 对酒当歌。
明日, 有谁会在远去的驼铃声里与他对和?
这寂寞、 眼泪、 悲哀、 苍白横淌的心啊, 火怎可点燃——谁还会陪他下河捉鱼逮虾、 捡拾草丛间的野鸭蛋? 谁还会在纯粹的夜色里, 静立柴门沉默地为他守候孤独? 谁又会在窑洞的庭院,养花种草, 吃百合做成的玉面, 喝露水熬制的大麦茶? 门前小溪流过, 风一吹, 少女的笑声环佩一样脆响。
后稷, 豳人心中的第一伟男子, 有谁的歌唱能比他的胸膛更开阔辽远, 有谁的生命比他的骨灰更富于灵性和尊严?
人心无边, 有人会在无边的人世里祈祷忏悔, 放下或忘记;抑或在后人的泥土里翻晒记忆, 种下忠言逆耳和醒世良言。
当高粱的香, 绽满渭北平原的时候, 泾河水生出的闪电, 能将乌云和铁击得粉碎。
旷日持久的风, 吹着。 豳国的露珠, 经年明亮着。
祖坟的光, 失踪于远离和荒芜。 抱愧和荣耀。 这颗粒饱满的粟米, 在一路踉跄的悲壮歌里起伏。
人生越是走向终点, 越是对母腹充满敬畏; 愈是接近生命的墓碑, 愈是对儿时记忆盈满温暖。 永世照耀的光里, 斑驳的墙壁,我一脉相承的子孙, 在他的遗训里站成万古风流。
注: 后稷, 古代周族的始祖。 传说为姜嫄之子, 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 舜时为稷官, 主管农事, 教民耕种。 有“中华农业之父” 之称。
在一座堙灭的都城里怀念先祖
在豳州, 事无巨细, 一串串凋零的脚印, 铺满绵软的泥土。
枯叶, 在自己的枝头迁移和飘落。 东去的泾水在明亮的夜色里欲言又止, 快速遁去, 只有勤劳和忍辱负重在山野田间回荡。
一簇簇含苞的桃花, 在太极湾, 在七星台, 在龟蛇山, 在人迹可至的沟壑穿越和荡漾。 麻桑中的豕, 你要识好歹, 手捧的家谱在岁月的流水中夺目而朴素。
洪荒后的苍黄, 一尾鱼带着象形文字, 着粗衣, 戴斗篷, 在泾水北岸, 筑豳地, 封豳公, 播五谷, 栽桑麻, 饲畜禽, 身先士卒, 蓬勃如圆润的日。
“行者有资, 居者有蓄积”, 农夫们像等待收割的庄稼一字排开, 女人们学刺绣会纺织。
只要天性本真, 识一字足够。 入洞穴, 学烹饪, 养育后代。
在豳州, 我学会早起, 和着茶叶, 用诗文把天色煨明。 豳人性本善, 怪不得你——古公亶父自有妙法: “举国扶老携幼, 尽复归古公于歧下”。 在去西歧的路上, 用凤鸣酿酒: 仁厚三两,良善三分, 见地三斗, 还有一分坚韧看家护院。
移居岐山, 傍山而居的先祖, 在渭水之畔的炊烟里, 用古铜色的双手, 抱紧异乡的每一寸土地, 用强劲的生命之根隐植于丰润空旷的泥土。 我这个四千年后的臣民, 却在与时间交锋的途中, 行走在无法存活和延续的旱土上。
在豳州, 我怀想一座隐没的都城, 我看见那么多寻根的身影,泪流满面, 跪伏在公刘始祖陵园的晨光里。 面对此, 我不敢言及枝繁叶茂的血脉, 更不敢言及血性、 刀光剑影以及农事。
无法理顺几千年来先祖们在延续香火的霞光中, 种下过多少汗水和希冀, 历经过多少开创家园的欢娱和疲惫, 流落过多少舟车劳顿四处迁徙的哀愁。 又是如何不舍地离开豳地, 辗转入岐,扎根在西府凤鸣, 继续我们血脉的奔驰。 有气力便可砸出个锦绣好河山! 他们如何从踉跄的步履里走出周王朝的雏形?
在豳州, 古公教会了我吟诗饮酒, 教会了诗经中歌唱的鸟如何展翅, 教会了后世人如何泼墨挥毫。 毫是风吹草不动, 毫发无损的毫。 生是犯我境之剑, 我要你不得安生的生。
在豳州, 我学会了锻打, 学会了耕种, 学会了在温热的水面上植下钢铁。
豳州, 我要紧守你, 你教会我们如何救活那枚叫做故乡的稻谷, 教会我们生于斯也要死于斯, 做粮食的亲随。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称彼兕觥, 万寿无疆。” 在《诗经·豳风》 的千古名句里, 我满含热泪, 以子孙的形式, 把世代相传的烟火抱于胸前, 深深膜拜和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