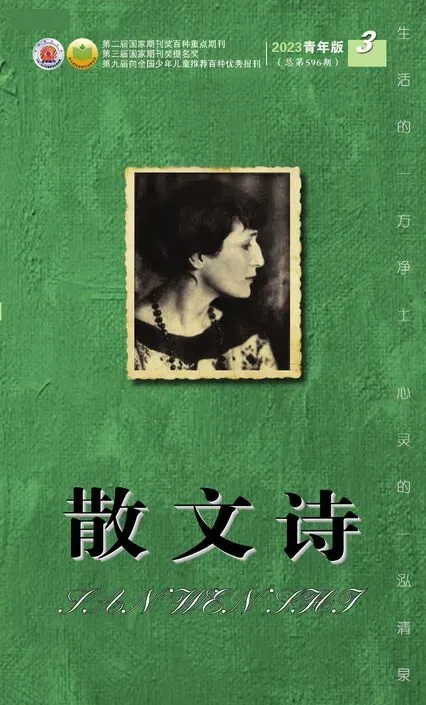事物偏离了几公里
◎叶 耳
我们当初无法理解的, 事后你再去想, 就想通了, 也能理解。许多人沿着这样的路, 往山的上面攀登, 他们在找寻一份生命的印痕。 归途的姓名, 籍贯, 以及编码, 它们都属于生命的风景。你说, 你无法理解的初恋, 她不过是一朵映山红的颜色, 她不过在枝叶的细节里隐藏了无与伦比的想象。 我还是喜欢羊台山的羊, 而不是阳光的阳, 羊在奔跑, 激活了一地的草木与露水。
九岁的她也是草丛里的羊。 家里喂了几只羊, 她可喜欢它们了, 经常写完作业就跟我去山里放羊。 她爱把心里的一些话说给羊听, 羊一边听她说话, 一边漫不经心地吃草。 她和羊在一起,她们都是大地上的诗。 她有时会唱歌给羊听。 她唱得很动情时,我会忍不住喊一声, 悦宝。 她会停顿一下微笑着回应我, 哎。 然后, 继续又清唱起来, 每倾听一次, 都将我深深打动。
她模仿羊的咩咩声, 可以引来山里另外的羊。 我喜欢乡村的她, 野生的植物与自然给了她无穷的想象力。 其时, 她在山下小学念三年级, 作业之余, 她喜欢在草稿本上写奇思妙想的句子。我把这些句子拆开来, 分成行, 就成了她的每一首诗。 她和羊站在那里,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生活的真, 一种自然的真, 一种朴素的真。 这些真, 散发出诗意的光亮与美感。
我们总是在慢一拍的抒情中遇见自己。 也许等到春天就好了,这不过是个愿望, 也是一种不错的想法。 让晨雾弥漫一会儿, 让蹲在竹子之间的刷牙声再持续一会儿——叮当作响的杯子, 你摘下眼镜若有所思, 嗯, 若有所思的视力也大不如从前了。 这是生活的境况, 你看见她漱了漱口, 世间之美, 一只打鸣的公鸡和一只嘎嘎的鸭同时在杨梅树下出现。 我几乎不提周围的事物, 关于粮食与蔬菜的常识, 故乡从来都充满了宁静的哲学。 水的稀少让人担忧, 这是一个问题。 它们在一点点缺陷, 他们在一个个沉默。 打破常规的是一副字牌, 个别的猫叫有些离奇, 不过慢慢适应了的柴火, 干湿都能燃烧。 真实偏离了几公里的想象, 马路上的毛毛细雨, 狗尾巴草满坡都在摇晃。 赶场的集市有些走光, 声响和米酒荡出了一碗方言。
入药的话也有不同的药效。 同样一款药, 同一个制药厂出品,同款包装版本, 同样规格数量等。 感冒让我问了三家药店, 三家药店的费用不同, 第二家多了一块钱, 第三家贵了八块钱。 有些老歌听起来也是药, 可以反复听, 每听一遍, 都能想起一些丢失的时光与往事。
一日的春光, 有时是我们一生中找寻的开始。 疼痛与爱, 孤独与梦, 热爱与美, 等等, 就像春水拂过你的眼睛, 你的星辰。你伤口的眼睛里有流浪的影子, 那是大地上行走的孩子, 那是温泉般圣洁的母爱, 那是万物无限的柔情。 就这么轻轻地读你, 读你玻璃窗外的喜悦, 读你的名字, 读我们生命里永远的春天。 这样的城市, 再没有什么声音, 比你的微笑更动人。 谁在倾听纯粹的语言? 谁是做梦的孩子? 醒来, 我们怎样在你宽大的手里长成气候? 我们怎样接近一张明媚的脸庞? 答案在闪烁, 闪烁的答案。
潮湿的双眼, 感动的心灵, 觉醒的人。 春天的动词在走动,觉醒的想象在走动, 青春的姑娘在走动。 当然, 很多人知晓你的姓名, 你是在一个女人的勇气里, 拿起了心爱的笔。 她不会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 我们又怎么能忘了呢? 还记得你曾说过的一句话: 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 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如果从后院远远看去, 就会看见有一个人, 有一只爬墙的猫。
绕口令的游戏你还记得吧? 每个季节的狗尾草的后院, 都是一本小说的山。 在山里, 呆得再久也无法说出她, 尘世的树从未离开。 她们, 像年轻时的母亲经历爱情。 你看见了那只睡在黑夜的翅膀吗? 它们不小心惊落了我的月光, 我的月光。 月光光, 天黑黑。 返乡的姑娘与一匹遗失的马, 下落不明。 她们, 用记忆割开了我的伤口。 这后劲着实不轻啊, 这多年的烧酒, 在一个人的路途醉得不轻。 因为一次猜谜, 我把手里的柴草抛进了正在燃烧的昨夜。 昨夜, 在客里山醉上一晚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难道没有在客里山醉过么? 哪怕是你擦肩而过的回忆。
醉过的还有在偏房的瓦檐上的炊烟。
你看看, 它们千锤百炼的舞蹈, 你已多久没有关注这舞蹈?
手里捧着煮熟的玉米, 我想起昨日黄昏, 我想起邻家阿妹在细雨中走过的咳嗽。 挑担的红薯, 隐姓埋名的红薯, 结实如琴的柴堆, 每一块都在点燃。 此刻, 十二个片断的怀念, 是十二个月农历的手稿。 你突然想起了一只鹅, 是屋门前的那只麻鹅还是白鹅呢? 你知道一只鹅要拨动多少清波吗? 这其实并不是数学题,但大雪应该已经在来临的路上, 它们有鹅毛一样的大方, 大雪要怎样地扬长避短才肯降落在你的眼前? 沸腾的水在鼎锅里热爱一生, 热爱是一个发烫的词。 我们还是继续烤火吧, 让成群的家禽们再次练习, 我都差不多忘记了这苍茫的记忆, 今日已是立春。
院子中间的凸塘已虚构了每个人的想法。 也包括诗人与农人的想法。 梧桐树和柏树之间的距离, 我听见他们的声响, 我也听见翻山越岭的水。 翻山越岭的泥, 水泥马路上的翻山越岭。 翻山越岭的, 还有树上的鸟在咕咕噜噜。 穿睡衣的雪花, 想象赋予她们溪流, 只有这次。 此刻的铜月亮, 它的熟悉也使我伤感。 看来, 我有必要停下来透口气。 一个路口。 另一个乡村, 山上的植物让人陌生。 你也让我感到了陌生, 那种熟悉的陌生。
禾荡里的几个小孩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可别小看了他们。 这小家伙们, 每一锄都触及它们, 被阳光照见的泥土和石块, 我无法辨认这事物的坚韧。 好奇的猫和狗, 它们和植物一样在几米处探望, 我看见羞于启齿的杂草被一一排除。 在乡下, 有些呵斥的确习以为常。 除了发声, 只剩下了这句: 这又是谁家的孩子呢?对啊, 这又是谁家的孩子呢?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有些事情你如果想做就去做好了, 有些人想见就去见好了。 我经常没事时就与一些母亲聊起孩子, 描述或浓郁或温柔。 她们是我的乡村课。 我记得有一天, 山很安静。停电以后, 我想转转, 边走边想。 我掩饰不住忽略的倾诉与交谈。远远地, 我看见女儿捧着通知书和三好学生奖状走来。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挑着一担白菜刚从地里回来。 她们都是持续不断的构想, 就像心里的酒, 也是可以慢慢陶醉我的。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试着去回忆与构想。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大雪需要持续一个冬季。
此时, 我通常很想喝一杯茶。 我端起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油菜花点燃了自己。 本地鸡与饲养鸡的不同比较, 嗑瓜子的大娘随手扔下一地农事, 字牌的生活夹杂在撰写的家谱中, 还有人驱赶着牛羊去山里吗? 这些生活的百事, 数学不断从泥土里生长。你说的立春第二日, 我说的三日又立春, 它们其实没什么两样。没有两样的日常, 在客里山, 摘菜做饭的妇人鼓动热气, 她们每个都在家长里短之间鲜活。 其实别的什么已不再重要, 这是真的。
有个小伙伴在喊着另一个小伙伴的名字。 剪裁的手工与一把豆子磨砺, 比我们还迫不及待。 磨砺的日子想知道这一生的事情确实需要花点工夫。 磨一份豆腐需要花费的工夫, 打一副字牌需要花费的工夫。 推磨的人推动了整个青春期的自己, 也推动了一朵乡村的民谣。 浸染的金黄是一朵民谣, 热爱的手艺也是一朵民谣。多少爱人的肩膀有扁担的印痕, 我们的心里就有多少烟火的歌唱。
下午, 我在马路上散步时想, 路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亲戚。 你这么想时, 再认真去看他们, 还真像。 生活像锅铲在此时此刻翻炒, 姐弟一样的句子被数次涂改。 山是山。 树是树。 如果有条小河从客里山的对门岭流过, 那些经年流淌的一定是自然的深情岁月。站在一面清澈的镜子前, 我无意间想到的, 是时候要刮刮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