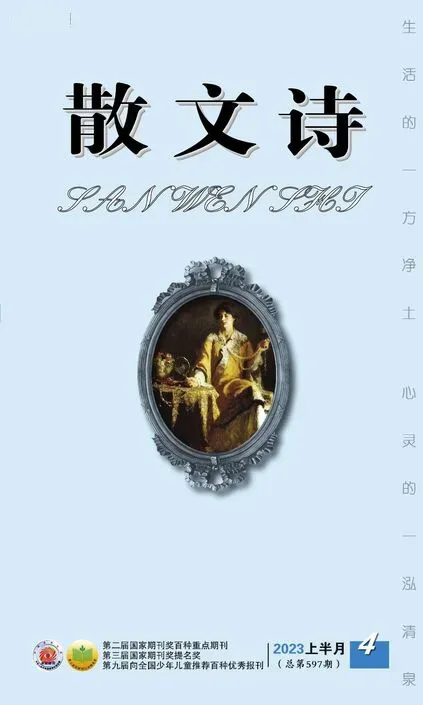在雨水跌宕的地方
◎何瑶兰
在雨水跌宕的地方
在雨水跌宕的地方——
吊兰依旧无精打采地挂在墙上, 像这个安静的世界。
她迷茫地抱着娃娃沉睡。它闭着眼睛, 蝴蝶飞来, 也不理睬。
它想:
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已经很少有人想起玫瑰, 和黑暗中失去裙摆的女人。缄默的雨淋湿每一个角落, 把人影淋成苍白的碎片, 然后组装成令人心悸的蓝。
今年的雨水特别多。第二天, 她向孩子们叮嘱, 上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无声之地
扭曲的各种机器房, 从四野之外向她涌来。
月光下, 一块块可爱的橘瓣, 带着冷兵器的寒, 规规矩矩地制造声音。
在这无声之地。
她依靠这些尖锐的房子所产生的节奏来聆听世界。形形色色的云与风, 都是被加工的材料。不过, 她依旧无法听清棕榈树坠落的声音。
她欣然接受, 在这无声之地, 能被定义的都已远离。
当捡起落在沙滩上的贝壳, 另一种生命的褶皱与脉搏隐隐跳动, 她不禁徘徊与犹疑:
是夜归有月, 还是岸有潮水?
落日之地
一只猫, 从铃兰跳到观音竹。
蚯蚓乘着快艇, 从电线缠绕处奔向落日。
无聊的时候, 他和同伴们谈起养老院年前的那场雨, 和雨中滑落的山坡与墓碑。
声音越来越大, 盖过衣冠楚楚、几片荒诞的、叶的恭维。
为了显示安详与幸福——
他们争先恐后地在棋盘上落子。棋盘上映着沟壑, 沟壑里望不见未来。
偶尔, 他也读诗, 端详松针的沉默。
如同某日院里阳光灿烂时, 有人闭上双眼, 又趁着夜色不知所踪。
行走之地
在缺口处、缝隙处、漏洞处, 他辗转了许多城市, 身上许多部位也开始漏风。他有时是一个人, 有时夹杂在同类中, 被石头推着走。
今年冬天格外冷, 暗河流动时, 他站立在桥上看人间大雪,洋洋洒洒覆盖神的耳垂。不止一次, 那红薯的香味攻城略地, 紧紧地包裹他。
无人关心他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
他自己也是。
他日复一日看着行人的裤脚, 绿色的、粉红的、黑色的……那些缤纷的独角兽, 在各自的琴弦上彳亍而行。
什么都与他无关。
他偶尔想起家乡的橘子树, 金黄金黄的。许多次, 他眯着眼,伸手去拿, 都会听见“咔嚓”一声。
哦, 是摄影师——
人间最关爱他的人。
失去之地
村前的流水枯了。
河里的老虎们还在。
多年前, 大雨滂沱, 老虎的故事在河堤处展开。祖父背着我,踩着它们光滑的头颅过河。
东边的树林消失了, 矮小的庙堂还在。失去母亲庇护的幼崽,现在, 只能抵达我的膝盖骨。
南面的花生地杂草丛生, 那个最爱数花生的胖女人, 后来到底还是数丢了自己。
面对语言的蜜剑, 我越来越少语。
来到这个地方后, 人必须会失去什么。
比如我抬头看到的, 始终是狮子山。它, 始终是沉默地端坐在云边。
沉寂的, 还有许多, 漂泊的心呀, 如同四散的花椒, 再也挂不到高高的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