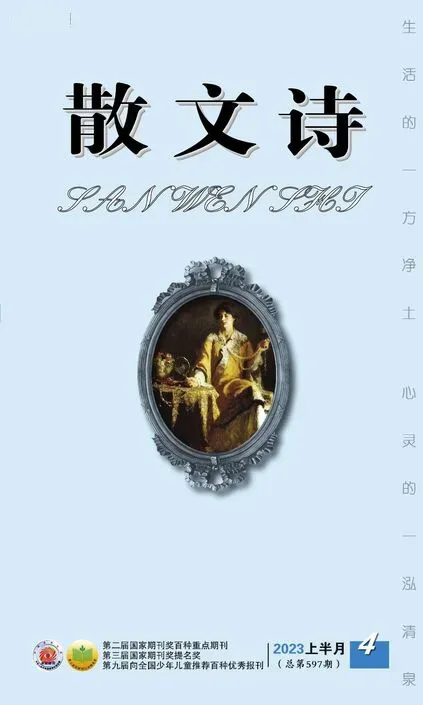铜瓦厢寻幽
◎雷黑子
柏树:百树之长
萜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柏, 走进铜瓦厢的梦。
梦, 是小白兔最爱吃的叶子。
铜瓦厢的小白兔, 不是从黄河里飞出来的浪花儿, 便是从天空飞下来不再随风流转的云卷儿。不管是水做的小海棠, 还是云撮的大耳白, 都是爱柏的品茗者, 它们最舍不得品的, 就是仙贝样的柏树叶, 铜瓦厢独有的仙女柏。
伴着英雄的赞歌, 仙女柏漫卷起舞, 从千年之外不朽的高洁里来到碑林。
道义口含芳馨的柏叶, 吹奏着柏树籽最爱听的祥符调。柏树籽兴奋之余打开了包裹, 释放出气体维生素连绵不绝的独特幽香。
当时, 小狐狸和几条搁浅的船, 一起在河边的柏林里野炊;几条晒干的鱼, 趴在柏木船舷上, 正好狐狸跳起来也够不着的地方, 哄太阳。
河水从一个坑跑到另一个坑, 再游逛到下一个坑。
每到一处, 河水都会从兜里掏出一些生命力顽强的柏树苗留守, 所以, 它并不在乎野兔, 抑或毒蛇, 包括唱着歌的猫头鹰,是否乘坐柏树航行五千年那么远的里程的头等舱。
铜瓦墙漏风了, 可以捡几个还能喘气的脚印贴上。
铜瓦房漏了, 可以借几个女儿家嫣然的笑容盖上。
如果铜瓦坝有了纰漏, 若是没有百树之长的柏树护佑, 想赶走气势汹汹的洪水, 恐怕捍卫会在小白兔的焦灼中日复一日地失眠。
无论哀悼在柏树下丢下何等强硬的长寿, 它们都永远没有菘萜耐沤, 那些焗黑的头发, 和没必要焗的, 有如日头掉进河里,天刹那间就被染黑了。
柏壳衣犹如火焰纯净的礼服, 稳定着情绪无常的白发。
榆树:勇士粮
铜瓦厢是榆树的道场, 是爱心开花结果的村庄。
一棵棵肌肤全无, 裸露着骨骼的老榆树, 在一场大雪里打着喷嚏, 咳嗽着长眠仙逝。
不去责怪, 饥饿在谎言中蔓延后诞生的死亡。
榆树, 自觉地成为一个已逝时代里最后的食粮。
悲壮的不是榆树流着血, 还在与钻进骨头里的蛀虫殊死搏斗,而是晚霞把榆树根仅有的心血, 都给了洪水碎掉的石头。
或许它知道, 每道坝的石头, 都肩负着更沉重的使命。
每一棵成熟的榆树, 都是一位忍耐力超常的勇士。
它的身体就是与灾难搏击的战场。
尽管凶残钻进了仁爱的心眼里, 它都流着血泪, 仍然与无法参悟的睿哲, 进行着持久的善恶搏击, 且从来没有屈服过。宛如铜瓦厢的儿女, 面对水患蝗灾, 从来没有放弃过倔强的安澜。
性格坚韧的小榆树, 同样遭受着手臂蠹枯的蚀心之痛。
但它仍旧向过家家的孩子们, 奉献着甜嫩晶莹的想象。仿佛人世间的童贞, 都是小沙弥从铜瓦厢的榆钱里开启的。幼小的榆苗并未了解父辈们的经历, 只是童心未泯地模仿着长辈。
把冬天的积蓄, 倾囊挂上铜瓦厢的枝头。
把花不完的榆钱, 精心调制, 蒸熟一锅又一锅春愁。
杨树:抒写者
铜瓦厢的杨树是出了名的一根筋, 一门心思地登高望远。
把蒸蒸日上的铜瓦厢, 推送到往事记得最清楚的云册上;把地图上删掉的路线, 逐一复原;让仰之弥高却迷了路的云彩, 沉淀凝聚, 找到家乡。
天天向上的杨树, 总是趁着春色, 书写漫天皎白的文字, 字字珠玑, 向人们揭示着上苍玄妙的轮回密码。
但是, 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
无奈的杨树, 只好把大地身临的苦楚, 向天空倾诉。它的叶,被误作鬼手, 却日日夜夜地劳作, 拍落了多少藏匿的污垢;当更多的惊叹, 拍落月光, 更多的疑惑, 也就被修缮成雨做的掌声。
每一串杨絮, 都是铜瓦厢的孩子, 一个纳闷的神情, 聚集了洁白的迷惑和纯洁的不解。
它们一直等着能有人回答, 直等到同样迷惘的风, 吹散了烦懑的羊群, 所有问题扎上了翅膀, 飞满了天空, 迷糊了孩子们的眼睛。
孩子们闹不清, 为何父辈们不想让杨树提问, 不想让疑虑飞越天际寻找答案, 甚至认为杨树是染病在身, 才漫天追问, 就给它吃药打针。
性格直爽的杨树, 再也没有提过一个问题。
沉默后的杨树, 成为令人仰视的抒写者。
餐风饮露, 从远古倜傥到今世, 俯视着黄土地的枯与荣, 倾听着黄河的呼吸。杨树并不是不知道答案, 而是在用另一种表达, 为尘世敲着警钟。
桑树:故乡果
一只蚕穿越很多册日历, 回到铜瓦厢阔别已久的桑园。
十道坝并不是女娲柔软的十指, 却抽出一丝丝河击石面般的绝世铿锵之音。桑树既不在房前站岗, 也不在房后探望, 它要去河堤, 把一颗颗红心献给至死不渝的禹。
其实, 桑叶一直就在蒲松龄的枕边, 淑卿当然知道桑葚就是为清退骨热特地赶来的。一个人出生不如一个人离去, 那些荒芜怪诞的日子里, 桑树穷其一生, 翩翩成魅丽的红头花, 等待颤颤巍巍的蒲公, 把它戴上聊斋的门头。
沉默并不是金子, 它是紫葚最初的呐喊。
桑林间, 金雀喙吮着满腹经纶的桑葚, 完成着红宝石上古的约定。它们和睦徜徉, 它们摇曳安详, 它们让幸福一次次河水样打湿了绿掌, 一次次被血液密集了千百颗奇异的故事。
那是千丝万缕的故乡果。
面对盐碱地, 更多的桑树会选择疗伤, 而不是仇恨。小桑果会彼此相互搂抱, 簇拥着, 闪着光, 跟随着阳光的手势, 低声合吟一曲浪涛坚强的呜咽, 协力为黄河缝纫一件大禹的衣衫。
待到秋后的月圆之夜, 桑树会把婆婆们的心愿和祷告, 结成蚕茧, 交到最有恻隐心的那阵风手里, 带到未来的夜空提前缫上。
还有许多红透的梦想, 并非遥不可及的清高, 而是富裕后对扶贫者的感恩。所以, 它们私下里恳请小桑叶, 把它们捂在淑卿贴心的树杈下, 只结交执著的蚕。
松树:岁寒精神
松树把照过自己的每一寸阳光, 都储蓄起来, 留给雪在冬天取用。松叶按照光芒的身材, 做好了四射的准备。
一切就绪。深思熟虑的铜瓦厢, 果断地把招待客人的体面事儿, 交给了发型帅气蓬松的松树。
把黄河的每一滴黄, 都滤出松花;把麦地曾经放出的卫星,都击落成秋后休闲的松果;把那些年前心贴着的后心, 都编织成励志的纪念。
一枚松针串出了那么多可以忘记的日子, 一张渔网打捞了那么多可以期冀的日头, 为什么不让逃荒多年的小松鼠, 重新回到松林间修复欢迎的手势?
就让松枝捡起一片片阳光遗漏的金叶, 让松根掬起一滴滴河水弥散的松香, 打造一种经得起时光荏苒的长寿松。
如果你会修春光, 那就劳烦别让铜瓦厢的笑颜过于明媚;如果你能把春光修剪得含蓄, 且善解人意, 那就把春天的铜瓦湖裁缝得无比得体。
让冬天的天堂, 羡慕得飘落遍地的后悔;让不老松脑海里扎得最深的那条根, 不但记录铜瓦厢曾经的苦楚, 也记录一下老来乐正在经历的富足。
身不由己的悲极之乐, 吹响了松节坚定的雪夜。
凄冷的松涛, 在铜瓦湖结成厚厚的冰。很多松粉喂过的小鲤鱼, 用嘴撞击着冰层, 为松风打着极其缓慢的节拍。
松仁不愿意离开铜瓦湖的冰清玉洁, 不忍心松树在数九寒天,翘首等候着岁寒二友赴约。
楸树:活化石
楸独自从冰川世纪彳亍到今天, 只为做一件让世间更纯净的事儿。而世间, 并不知道它为此受到的伤害和委屈。
如果有一天, 一棵小苗毫无征兆, 忽地从大坝的怀里探出头来, 那栈道的桥梁, 一定是从铜瓦厢迁徙出去的, 可以原谅任何一轮夕阳的楸树。
顺其自然的楸树。无论让它蹲守在冰冷的酸雨, 还是让它驻扎在碱性的沙堆;无论让它穿梭于巧匠的琴弦, 还是让它潜伏于红木的阴影, 它都是在为铜瓦厢演绎优美的舞姿和奇妙的乐声。
楸树纹理通直的愿望, 在法则里打磨光滑了的月亮。
铜瓦厢已不止是温暖的别称, 楸树也不再做红木的替身。历经沧桑巨变守护了铜瓦厢世世代代的活化石, 比谁都懂得慈悲的成本。
要穿过清朝一溃千里的沼泽, 民国伤痕累累的沙滩, 最好请新世纪的蝴蝶, 落进沙堆和丘陵, 用十二种生肖的英勇隐喻, 把所有脆弱的火苗, 都长到铜瓦厢的脊梁上。
所以, 楸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烦恼和往事, 都以最直接的表述打动棕眼, 使自己最大可能地亲近卑微, 拒绝欲念的聒噪, 保护铜瓦厢恬静的呼吸。
沙堆里熟睡着的奶奶, 是第一个发现楸树为王的人。
所以, 每到夜晚来临, 铜瓦厢的孩子都会从她头上掐一朵神秘的紫楸花, 聆听她讲述木王最新的故事。
槐树:膏药扎针
面对槐树的提问, 锈铁锚蹲在渡口, 一阵哽噎。
一天进嘴二两沙, 确实是一幅铜瓦厢当年的老照片。
面对槐树的讲述, 张庄跑进梦里抽泣。膏药扎针, 确是一个人用生命挖来胶泥, 盖住沙堆, 栽上槐树, 治愈了铜瓦厢的风沙病。
一页槐叶, 就是一封来自远古深宫的信笺, 注释着皇家三公的角码, 只有心有灵犀的人, 放在舌尖, 儒雅地吹奏, 才能演绎出黄河号子对未来的描绘。
冰心是如何善待明月的, 槐树最为清楚。
月底收回来的都是下弦月, 月初要发给黑夜的必须是上弦月,这需要槐根翻来覆去地折叠。
能擂响的, 都是国槐温雅的眼。能擎起的, 都是刺槐绽开的美。能飘落的, 都是槐树剔透的情。
一阵涛声跑过来, 汉子们为它抬出了千尺的号子;一串槐花落下来, 冰清了女儿们娴静的粉黛时光。
槐树虽然一身刺, 却并非是生就的银针。
它每一针都灸在流沙的要穴, 治疗着铜瓦厢曾经生病的滩地,曾经鸟兽回头风沙漫天的下马台, 如今已是幸福成林, 欢笑声声。
槐叶作诗, 槐花做梦。
——致秋天的花楸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