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的理论价值
钱激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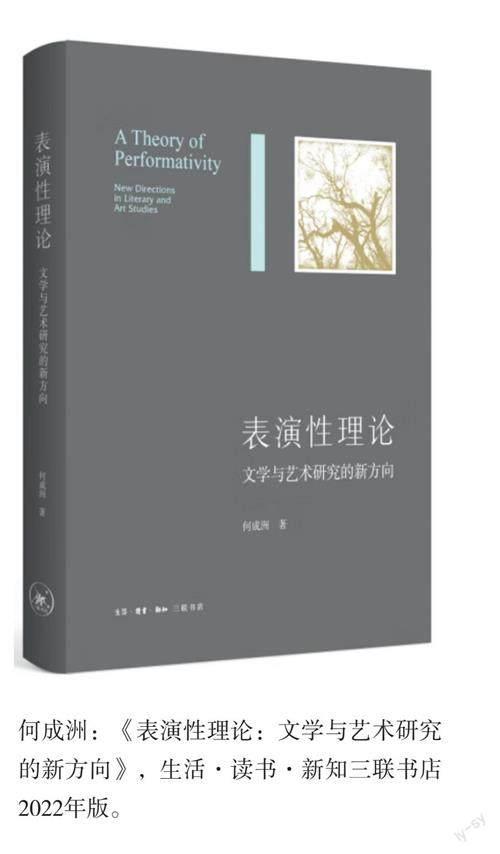


【摘 要】 何成洲的论著《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梳理、阐释了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西方批评话语中一系列与表演性理论相关的、重要的跨学科成果,该书的出版为国内的文学与艺术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野,其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和使用例证的跨文化性都显示出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意识和将本土与世界密切结合的眼光。以表演性理论为依据和方法,对英国剧作家卡里·丘吉尔的剧作《爱与信息》进行批评,可以印证文学表演性理论的施行性、事件性和干预性特征及其广泛的应用性。
【关键词】 表演性理论;何成洲;《爱与信息》
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围绕对表演性理论的认识与应用,西方批评话语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学术史发展的跨學科成果。何成洲的论著《表演性理论:文学与艺术研究的新方向》(以下简称《表演性理论》)是在梳理、阐释与这些理论相关的经典论著、批评家思想和概念演变轨迹的基础上诞生的,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性别表演理论、哲学的事件性理论、表演人类学理论、剧场美学理论和跨媒介理论等。该书体现了文学表演性理论在中国经典文学、戏曲表演、跨媒介艺术、西方跨文化戏剧、当代电影与电视文化等各领域的应用。该书的出版为国内的文学与艺术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野,其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和使用例证的跨文化性,都显示出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意识和将本土与世界密切结合的眼光。本文将运用书中所提出的文学表演性理论,从理论资源、戏剧文本和戏剧制作三个角度,说明文学表演性理论的施行性、事件性和干预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并以英国剧作家卡里·丘吉尔(Caryl Churchill)的剧作《爱与信息》(Love and Information)为例,运用文学表演性理论展开评论,从而体现该理论在戏剧评论中的重要作用。
一、建立文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
什么是文学的表演性?何成洲在《表演性理论》中明确指出:“文学是审美的,也是施行性的;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是言语叙事的,也是行为动作的。”[1]该书为这一观点的确立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者首先溯源了语言的施动力:从维特根斯坦、J. L.奥斯汀(J. L. Austin)到德里达,“表演性”概念均被用以描述语言的施行性和对现实的参与性,这说明语言既是描述世界的表达工具,也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德里达提出的语言“可重复性”和“可引用性”概念,更使语言的施行力量进入文学领域,从而打破了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的主从关系,揭示了文学语言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作者继而考证了当代剧场表演性美学的事件性特征。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Erika Fischer-Lichte)的表演性美学和汉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的后戏剧剧场理论在当代剧场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剧场表演性美学理念一方面彻底颠覆了戏剧创作和批评话语中的既有等级制度,赋予剧场里的一切元素与作家和导演平起平坐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深入挖掘了表演与观众的互动关系。无论是费舍尔—李希特提出的观演关系“反馈循环自生系统”[2],还是雷曼所强调的后戏剧剧场里观演者“自我问询、自我探究、自我意识”[3]的体验性,都证实了当代剧场的“表演性”概念所强调的是具有“互动、生成、创造力与干预”[4]等特征的表演事件。
在考察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理论时, 何成洲同样十分注意挖掘性别表演与事件性的密切关系。虽然巴特勒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前期论著中冷落甚至放弃了对身体的物质性分析,但性别表演理论突出的性别述行性和操演性始终具有鲜明的事件特征。何成洲指出,巴特勒从话语和行动两方面揭示性别的操演性、虚构性、群体性和裂变特征,不仅与奥斯汀的言语施行性、德里达的言语引用性特征形成了呼应和印证,而且开启了表演性理论在身份、族裔、阶级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路径。这里的裂变是固有身份规范与实际身份形成二者碰撞和突变的结果。显然,性别表演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其缠绕、新生、干预等事件性特性。
在对事件的创新力量的描述中,作者从德勒兹和齐泽克的理论出发,说明无论是德勒兹所提出的流溢和阈限等概念,还是齐泽克所提出的断裂、堕入和撤销等概念,其实都在提醒人们发现与认识艺术作品和真实社会中事件发生的当下性、生成性和改造力,亦即都关注到了事件的表演性。何成洲认为,既然文学构成本身就是一个事件,那么事件性也必然是文学和艺术研究的表演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通过阐述《人物:文学研究的三种探究》(Character: Three Inquires in Literary Studies)[1],特别是根据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后批评阅读、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约瑟夫·诺斯(Joseph North)的第三种范式等,从西方批评话语的角度指出文学和艺术研究推动表演性转向的必要性。
这些阐述表演性理论的代表性理论家们从方方面面证实,“文学不仅指具有文学性的文本,而也应该被看作是行动和表达”[2]。何成洲由此在其著作中将文学和艺术的表演性概括为具有施为性、事件性和干预力量的行动,这一理论建构与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话语形成呼应。首先,它顺应了当代社会表达媒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当代文学创作者往往借助语言之外的媒介去表达思想并介入社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从单一的语言文本研究转向与其他媒介和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因此,文学表演性理论的提出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其次,文学自身一旦具有了行动力,它就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它与被接受者的关系变得模糊与不确定。这样的视角十分契合当下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物转向”潮流。在后人类主义理论引导下,21世纪的文学创作十分关注人类身体与其他有机物、非有机物和非人类物质的依存关系,形成了后人类文学转向“物”的想象性推演。文学作品一方面试图表现技术参与人类身份和主体塑造时的具身认知反应,另一方面试图表现文学行动由人类与数字工具联合完成时所发生的离身认知。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提出的“动能实在论”更是将文学批评的目光指向被话语遮蔽的自然、肉身和物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表演性理论将文学本身当作具有施为能力的“物”,显然也加入了后人类批评的潮流,颠覆了文学认知中的因果链条。借用巴拉德的话,文学与人类构成的关系体将“不先于关系存在,而在现象内部通过具体的内在—行动出现”[3]。可以想象由此带来的革命:文学研究将不再只以作者、读者和作品为中心,而以文学生产过程和环境为导向,以文学与真实世界的内在—互动为切入点,寻找其动态的、裂变的、撤销的和流溢的施动力。
最后,何成洲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文学至少包含三个层次:文本、文学的网络和社会集合中的文字。这就将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语言文字之外,这样的思路与认知叙事学所提出的“过程范式”类似。“过程范式”强调的是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反应批评,但与以往的“主题进路范式”和“比较范式”不同,它更关注“文学如何参与和表现心智功能”[4]。如果说参与和表现读者心智的功能是文学认知叙事学的任务,那么文学表演学的目标则远大于此,它要与艺术作品产生前、中、后发生的所有事件形成互看、互渗、互助的视角,并试图在作者与读者、生产与接受、文学世界与社会现实、语言文字与其他媒介、本土与世界等各种与文学事件生产相关的元素互动中,建立文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这样的网格状过程范式必將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性理论建构,开启具有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学研究方法。
总之,《表演性理论》一书为文学与艺术研究方法的表演性转向进行了理论基础坚实的、理论与例证密切结合的、系统全面的论证,充分体现了文学研究的过程性、包容性和可塑性。它所引领的文学和艺术批评方法论不仅能为本土文学与文化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打开切口,还可为当代文学与艺术阐释提供新的方法和路径。
二、《爱与信息》中的文字表演性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奠定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其中包含的生活与艺术的不对等性引发了各时代西方文学思潮中现实主义概念的延伸与演变。从19世纪末开始,经典摹仿说不断受到挑战:从象征主义戏剧到表现主义戏剧,从荒诞派戏剧到残酷戏剧,从史诗剧的陌生化手法到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的“贫困戏剧”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空的空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实是无法被摹仿的,他们从再现手段中“砍掉”摹仿,“摘除”其中的虚假、复制和相似性,通过隐喻、象征、存现的方式接近真相。文学表演性理论的提出,为考察当代戏剧摒弃摹仿、贴近现实的创作手法提供了作品与读者、导演、观众共谋合作的路径。
以当代英国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的《爱与信息》(2012)为例,这部表现媒介技术高度发达时代人类情感结构发生变形的戏剧,在上演之初就因其语言和结构的别出心裁而备受瞩目。R.达伦·戈伯特(R. Darren Gobert)认为,在这部剧中,作家邀约观众与演员共同生产意义的空间[1]。在后结构主义尽力回避意识形态探讨并宣告“作家已死”的语境下,《爱与信息》却以饱满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鲜活的剧场性和实践性宣布:新型剧场同样可以介入现实。该剧通过小说形式与生活现场感密切结合的感染力,证明文学本身不再是静态的、被动的和等待被发现的客体,而是具有施为力、自主性和干预力的主体。
在文学表演性理论视阈下,小说是“毫不知情或共谋合作的事例”[2],而戏剧文学更有促成文字与读者合作的潜质。丘吉尔笔下的《爱与信息》以能动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随机叙事的可能。首先,戏剧结构仿佛随机森林算法的分类器,如何分类和回归问题全凭读者想象。全剧由57个短小精悍的场景组成,以不连贯的叙事方式呈现了7个内容迥异的部分。通常用于戏剧分段叙事的幕与场被省略,只剩下7个数字和标题,作家允许“场景的顺序根据需要在每一小节内被任意安排”,且“每一场的人物不重复”。文本末尾还提供了“任意场景”[3]。这种随机性极强的叙事设计为读者与文字的合作打下基石。其次,戏剧基本元素如角色、对话、行动等统统消失,代之以长短不一的诗句和简约、诗意的语言表达,这样的开放文本[4]、无角色表演和散文风格显然在鼓励合作的、非等级制的制作模式,为文字的施为留下了丰富空间。最后,既然作家有意避免将读者代入任何有历史时段的瞬间,文本叙事也断然拒绝任何可能的因果关联,为什么副导演凯特林·麦克里德却认为,这是一部与英国息息相关的国情剧[1]?显然,文本的现实指涉感来自台词的自然主义风格,以“粉丝”为例:
太爱他了/比你爱他/我要跳窗/吃火/砍掉我的手/……/只为摸到他/只为告诉他/只为看见他/只为让他看见我。[2]
这些富有诗意且带有讥讽意味的陈述生动描摹出一种偶像崇拜心理。丘吉尔让自然主义式的台词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说话方式,如此一来,台词干预现实的力量就不是通过对现实的复制来实现,而是让偶像文化这一系统成为有意识的主体,使偶像符号与真实肉身纠缠于一处,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理性主体的操控。这是诗意戏剧语言和算法式戏剧结构打造的文学自治力量。
《爱与信息》中包罗万象但又细致入微的场景设计,使读者能够一边想象剧场的物质力量,一边召唤文本所提供的、关乎人人的现实问题,使原本集中于话语层面的思想,走进身体和自然。由于文本内容的包容性、叙事安排的随意性和人物对话的生活性,这部剧就具备了向外与向内两个维度的力量。向内映照每一个观众的日常生活,向外指向广阔的大千世界,细微的心理刻画与宏大的画卷铺陈共同构造了一种新型的剧场模式的抽象现实主义空间,它比任何舞台提供的幻境都更真实。
三、《爱与信息》剧场
与观众的共谋合作
当文学行动由人类与数字工具联合完成时,“分散的施动创造了两个互相竞争的人类视角”,一个是具有具身认知能力的“理性、统一、自治的自我”,另一个是能够产生离身认知的“多重组装、与数字计算机关联的后人类主体”[3]。表演性理论从文学自治视角反映了人类理性主体与文学作为离身认知生产者之间互相影响和彼此竞争的状况。《爱与信息》的跨媒介制作即在不自觉中体现了后人类时代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竞争,操演了人类在多感官通道的融合中形成了怎样的物质—符号形象。
2012年,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版的《爱与信息》用白色盒子作为场景发生地,人物和道具在盒子里随灯光闪动发生魔术般的转换[1]。而2014年的美国纽约版中,一个个片段则在蓝色立方体内闪现,令观众联想到社交应用软件instagram的图片分享功能。方框式的舞台设计类似布鲁克所谓“空的空间”,需要演员的想象力去组装,观众的想象力去填充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多媒介材料组织则揶揄了社交媒体时代人类感知被区隔和数据化的状态。“跨媒介剧场可以更加精确地反映人们通常参与世界的方式,因为剧场里再现的所有变量融合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和世界。”[2]剧中,人工智能、科学实验、视觉编码和DNA序列等各种代表科技进步的媒介都干扰甚至扭曲了人类的感知能力。“虚拟人”里,堕入情网的男子竭力为机器人辩护,“她漂亮聪明善解人意”,“她是唯一倾听我爱我诗歌的人”,她有“思想感情”,“她会爱”,“我从未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3]。“做爱”“孩子”“天气”等单元场景表现出,由于过分依赖数据、材料和分析,人类逐渐丧失了对直觉和感知的信任,而更多依靠算法,但经由算法编辑出来的人类情感交流方式令人不安、焦虑和疲惫。
剧场的情绪调动既凭借立方体/白盒子制造的物质化效果,也利用了色彩、线条、灯光等去肉身性手段。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版的白盒子设计力图“捕捉场景的抽象现实主义、全剧的冷淡和实验感,同时提供无限的可能”[4]。当长短不一的速写在快门声和LED灯闪中转瞬即逝时,舞台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观众会被突然闯入的“真实”弄得不知所措,自然主义竟至如此造作的程度,丝毫不加掩饰地炫耀,告诉观众这是真的。这种让“真身闯入虚构”的行动,在雷曼那里,就是“真实剧场”,因为此时的身体“成了一种自身的真实”,“它们不用姿势来述说这样或那样的情感,而是通过其存现来宣示自身,使自己成了某种集体历史的记录”[1]。作家和导演在回避再现与接近再现的不经意间,将观众带入自己十分熟悉的生活体验,“很滑稽,有心痛,有困惑,有时接近乏味,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儿像数字时代的生活感受”[2]。剧作的批判力量恰恰来自由观众肉身和舞台物质合作构成的“真实”,这一多媒介制作在与后戏剧剧场和后人类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实践了物质的主体性,这种真实感会促使每个人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以自己熟知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
丘吉尔运用贴近生活现场的片段,以多棱镜与显微镜相结合的戏剧视角为剧场施为性打开了通道。一方面,《爱与信息》在贝克特式的极简对话中叙述当代人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观众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场景中立即识别出自己或身边的人;另一方面,它以易普生、契诃夫的方式走向人的内心,释放一种不安的、令人沮丧的进程感,令观众产生一种源自旧有戏剧魔力的“感觉—情状(feeling-state)”[3]。
结语
《爱与信息》对现实的指涉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再现,也不同于史诗剧的陌生化效果,而是通过开放的戏剧结构、无角色人物、无时段场景和多媒介吸纳等手段调动读者、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合作,在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竞争中,在熟悉而陌生的审美体验中,在身体和情感的触动中,不自觉地推动社会介入。剧场构作在打破虚构与真实界限的同时,构建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想象、现实认知和情感纽带,它们能够促使个体采取行动,思考自己在面对世界危机和挑战时的责任。这正是戏剧在与人类感知的内在—行动中施展的行动力。
本文以戏剧《爱与信息》为案例,揭示出《表演性理论》一书所梳理、阐释的文学表演性理论在戏剧批评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表演性理论》一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该书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方法十分突出,在梳理西方表演性理論概念时,作者不仅总结了某位批评者自身思想的流变,而且善于展示不同批评者观点间的继承与发展、质疑与挑战;此外还注重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批评术语的来龙去脉进行归纳,这些都使得西方表演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代表性概念和经典论述以凝练、生动、互动的方式得以彰显,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幅立体的、活动的表演性理论概念图。此外,书中丰富的案例不仅为表演性理论的运用和阐释提供了多元视角,还融入了中国学者的跨文化体验,使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经典作品、中国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在表演性理论的框架下得到呼应。总之,该书在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它引领的跨文化艺术批评实践值得进一步探索,它开拓的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方式值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责任编辑:杨梦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