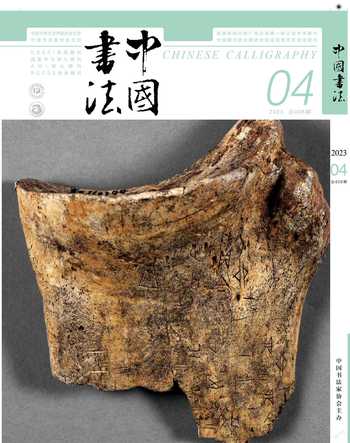“扬州八怪”及其又化资助现象研究
陈传席


摘 要:清代康乾时期,扬州商业大盛,富商巨贾云集于此,诸多商人醉心文化并兴起了一股文化资助之风,商人建学校,撰诗书,举办雅集聚会,推动了扬州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资助之风也影响了扬州画坛,一方面带来书画市场的繁荣。画家为投资助人所好,在绘画风格及题材选择上又常以资助人的喜好为基准;另一方面伴随商业经济发展,市民意识抬头,扬州画家开始主张强调自我,突出个性解放的绘画理念,并因此产生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而随着扬州商业的衰落,扬州画派失去了优渥的生存土壤并逐渐走向寂寥,嘉、道之后画家涌入上海,上海画派开始崛起,影响至今不衰。
关键词:扬州 书画市场 扬州八怪
扬州文化事业的赞助群体
清代康乾以降,商业蓬勃发展,商人更是呈现士人化现象,对此戴震曾云:『贾者,咸近士风』,扬州商业的主力军徽商尤其如此。他们既『拥资巨万』,又能节俭,而把大批的钱财花在赞助文化艺术事业上。如创办书院、学校,培养、教育人才,当时的扬州书院、学校可谓鳞次栉比,据《扬州画舫录》卷三所载,除了原有的资政书院、维扬书院、甘泉山书院外,又新建者『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用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等等。这些书院、学舍的建设和维持,其资金皆来源于盐商,或和盐商有关的盐运使司的运库。两淮总商汪应庚曾捐五万金重修学舍,并以二千金置祭器、乐器,以一万三千余金购买学田一千五百亩,岁入归诸学宫,以待岁修和助乡试资斧。安定书院乃康熙元年两淮商人所建,雍正年间,两淮商人捐资八千缗扩建学舍。梅花书院原为崇雅书院,马曰琯重建堂宇,因其西即梅花岭,故改名曰梅花书院。敬亭书院亦由两淮商人出资建于康熙二十二年。被请到书院讲学的人,据《扬州画舫录》所载,最低亦是进士出身且有一定成就和特长者。担任书院院长者,更是当时著名人物,如王步青、杭世骏、赵翼、陈祖范、蒋士铨、姚鼐、茅元铭等数十人,『皆知名有道之士』。『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1]。书院培养的人才中,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高级官员者比比皆是,如段玉裁、王念孙、裴之仙、管一清、杨开鼎、梁国治、谢溶生、任大椿、汪中等等数十人,皆出于这两个书院。各书院不但培养一大批人才,而且也招来外地一大批人才,这也是扬州文化艺术事业兴盛原因之一。
清代乾嘉时期,扬州出现著名的『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者,皆因盐商的招徕而至,来后多寄寓盐商家中,由盐商资助他们从事学术研究。
盐商大量收书、藏书、收画、藏画,好客尊士,资助和招徕一大批文人,是扬州文化兴盛的另一原因。几乎每一个盐商都有这类『德政』。以下以影响较大,且在研究『扬州八怪』中必须了解的几位大盐商为例加以分析:马曰琯和马曰璐。这两位既是大盐商,又是著名的斯文之士。马曰琯(一六八八—一七五五),字秋玉,号嶰谷,安徽新安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遗迹至今尚可寻),城北西园(天宁寺西,今为扬州最高级的宾馆)尚有他的行庵。《扬州画舫录》卷四记其『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南巡时,赐两御书克食。尝入祝圣母万寿于慈宁宫,荷丰貂宫之赐。归里以诗自娱,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马曰琯著作有《沙河逸老小稿》(《扬州画舫录》误记作《沙河逸老诗集》)。
马曰璐是马曰琯之弟,字佩兮,号半查,工诗,与兄齐名,人称『扬州「二马」』,举博学鸿词不就,著有《南斋集》等。
佩兮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中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2]。乾隆三十八年,下旨采访遗书,马曰璐的儿子马裕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赐给当时『书城巨观,人间罕觏』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此书共五千二百卷,分类三十二典,马裕装成五百二十匣,藏贮十柜。尔后,弘历帝又赐给御制诗以及《得胜图》三十二幅。『二马』藏书为『江北第一』。但他们的书并非用来做摆设,而是给当时的士人提供学习、阅读、欣赏、研究的机会。所有的读书人皆可以到这里阅览,有的还可以借出传抄。卢见曾就经常到这里借书,并题其所寓楼为『借书楼』[3]。马氏小玲珑山馆成为扬州文人的活动、聚会中心,他们经常举行诗会,每到会期,于园中设一案,上置笔二、端砚一、小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即遍城中。现存《韩江雅集》诗十二卷,就是小玲珑山馆中聚会的诗人、画家互相唱和诗录,由马氏出资刻印。
以『扬州八怪』为主的扬州画家更是小玲珑山馆中的常客,马曰琯的《沙河逸老小稿》中经常记到这些画家,汪士慎、金冬心、郑板桥等人的诗文集中也多次提到『二马』招饮、索画以及共同观画、吟诗、赏花、游园的事迹。从诗中可以知道每次小玲珑山馆集会,皆由『二马』设宴招待。汪士慎《嶰谷、半查招飲行庵》诗有云:『韩江诗人觞咏地,吟笺五色鲜如花。林光射酒好风日,老桂香幽时一袭。』由是观之,不但宴饮讲究,写诗用的五色笺也十分讲究。
『二马』对收藏古今绘画作品皆特有兴趣。『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锺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钜观』[4]。『扬州八怪』大部分画家皆为『二马』画过画。郑板桥一时客居马氏行庵隔壁,马曰琯也不放过向他求画扇面的机会。[5]
而且每画必题诗或长款。著名的绘画史论家兼画家张庚(著有《画征录》《浦山论画》)虽不是扬州的常客,马曰璐也特请他为自己画《小玲珑山馆图》,并自书长跋,跋云:『……适弥伽居士张君过此,挽留绘图……』此图至今尚存。
有些画家、文学家就长年寄居在小玲珑山馆中,只要有一定才华,生活贫困者,『二马』都设法请来,不但『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而且,给以医疗、刻集。《扬州画舫录》记著名文学家全祖望『在扬州与主政(马曰琯)友善,寓小玲珑山馆,得恶疾,主政出千金为之励医师』。《南宋院画录》辑者厉鹗生前,马曰琯为他『割宅蓄婢』,死后在家庵中设位致祭。
马家还附设刻印工场,著名学者朱彝尊『归过扬州,安麓村(大盐商)赠以万金,著《经义考》,马秋玉为之刊于扬州』[6]。『尝为朱竹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版﹂』[7]。所以,沈文悫序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中说到,『古人莫不有癖,嶰谷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诗斥淫崇雅,格韵并高,由沐浴于古书者久也。』仅马氏一家,不知吸引资助多少文人、画家。
比马曰琯稍年轻一些的大盐商是江春,歙县人,为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江春居扬州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秋声馆』『康山草堂』等,园中曾有芍药花开并蒂十二枝,枝皆五色,卢见曾为之绘图征诗。江春选时文付梓行世,集为《随月读书楼时文》,并自著《水南花墅吟稿》《深庄秋咏集》。江春世族能诗善画者长年寄居其家者甚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文士画家被江春延至家中,养在秋声馆、康山草堂等处,不可胜记。
据《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所记:『方贞观,字南塘,安徽桐城人……寓秋声馆二十年……』『熊之勋,字清来,江宁人……常居康山草堂。』王步青被江春延至家,师事之,并主安定书院。吴梅村之孙吴献可,通经史,究名法之学,被江春『延于家二十年』等等。『扬州八怪』之一陈撰,字玉几,号楞山,浙江钱塘人。不仅自己寄居在江春家中,其女嫁于南徐(镇江)许滨(画家)后,翁婿都寄居在江春家中。『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不知多少人得到他的资助,所以,『方伯死,泣拜于门下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8]。
再如程梦星和郑侠如两位大盐商(皆新安人)。
程梦星,字伍乔,一字午桥,号洴江,又号香溪。康熙壬辰进士,曾官至翰林编修。为商后居扬州廿四桥旁,置筱园,种芍十余亩,梅八九亩,荷十余亩,架水榭其上,名『今有堂』,又构亭曰『修到亭』,又有『初月沣』『南坡』『来雨阁』『畅余轩』『馆松庵』『藕糜』『桂坪』『小漪南』诸景物。程午桥在这里经常召集文人雅士吟诗作画饮酒,『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榼,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9]。
郑侠如,字士介,号俟庵。其兄弟超宗有影园,赞可有嘉树园,侠如则有休园,园宽有五十亩,住宅前后有含英阁、植槐书屋、碧厂耽佳、止心楼诸胜,园中有空翠山亭、蕊心楼、挹翠山房、琴啸、金鹅书屋、三峰草堂、语石樵、水墨池、湛华卫书轩、含清别墅、定舫、来鹤台、九英书坞、古香斋、逸圃、得月居、花屿、云径绕花源、玉照亭、不波航、枕流、城市山林、园隐、浮青诸胜。[10]
《扬州画舫录》卷八记云:『揚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程、郑二园和小玲珑山馆一样,也是以最优越的条件招待各地文人,『诗成即发刻』,且三园比较,『休园,筱园最盛』。其招引文人来扬之盛状,迨可想见。
再如汪玉枢的『南园之盛』,王躬符曾于是园征《城南燕集诗》,吴泰瞻等三十六人,『各赋七言古诗一首,镛州廖腾煃序其事,一时称为盛游』[11]。汪玉枢并非最大的盐商,南园也非最盛之园,一时『盛游』尚需三十六位有名于时的文人为客,扬州二百多盐商,再加上其他『豪商大贾数十万』,其时扬州吸收全国各地文人之多、文事之盛,亦可以知矣。
研究『扬州八怪』和扬州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卢见曾也是一位不能不知的重要人物。卢见曾(一六九〇—一七六八),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辛卯举人,历官至两淮转运使,卢虽不亲自行商,实为盐商总头目,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燕盛于江南』。『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汪士慎、金冬心、郑板桥、高凤翰、李葂等皆为其座上客。卢自己也工诗文,性度高廓,不拘小节。不仅他自己的诗文集甚丰,同时由他主持编印的扬州文人诗文集更丰,著名的《雅雨堂丛书》《金石三例》《感旧集》等等,皆卢氏出资刻印,对促进扬州文化发展以及保留扬州文化遗产起到过重大作用。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发起的『虹桥修禊』事,其影响又大大超过小玲珑山馆及筱园、休园之会。『虹桥修禊』在扬州曾有几次,孔尚任在扬州时,曾修禊于此,以诗文为时所推崇。总持风雅数十年的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时,曾与部分文人修禊虹桥,互相唱和,亦称一时之盛。但规模最大的乃数卢见曾发起的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修禊虹桥的一次,卢亲自邀请在扬州的名流文人参加,并自作七言律诗四首,和者竟达七千余人,有人竟一和再和,如《郑板桥集》中就有《和雅雨山人虹桥修禊》四首,《再和卢雅雨》四首。一次唱和诗就有数万首,并编成三百余卷,这在世界诗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全唐诗》收有唐一世三百年之诗,也不过二千二百余家,诗四万余首。如果以一斑而窥全豹的话,这次『虹桥修禊』就足以显示当时扬州文化的雄厚力量。而这种雄厚力量,正是建立在盐商的巨富和好客尊士的基础上的。盐商一旦失势,这些文人也就立即散去。
还有扬州商贾大量刻书一事值得重视。扬州刻书业历史悠久,至清康乾时大盛,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皆史无前例。名气最大的当数《全唐诗》。
康熙四十四年皇帝下旨曹寅负责刊刻《全唐诗》,就是因为曹寅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实际上《全唐诗》也是由扬州的盐商出资所刻。曹寅于奉旨当年在扬州天宁寺(遗址至今犹存)开设刊刻《全唐诗》书局,一年多就完成了这一九百卷的浩大工程。从校补、缮写、雕刻到印刷、装潢,无一不精。尤其是缮写,九百卷,不可能由寥寥数人书写,找大批书写家书写,又要字迹相近,如果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城市,并非易事。《全唐诗》刻印成后,康熙皇帝大为赞赏,并形成一种刻画风格,即所谓『康版』。
曹寅在扬州除了刊刻《全唐诗》外,还刊刻了《佩文斋书画谱》《词谱》《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诗余》《全唐诗录》《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题画诗类》《渊鉴类函》《历代赋汇》以及《御制诗》初、二、三集等十种书,近三千卷。所刊刻之书缮写和校刻皆精。[12]
以上是曹寅主持扬州诗局时所刻,属于官刻,但多是盐商出资。曹寅自己还刻有《栋亭五种》和《栋亭十二种》(按曹寅字栋亭)。《栋亭五种》内有《类篇》十五卷、《集韵》十卷、《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重修广韵》五卷、《附释文互助礼部韵略》五卷,《栋亭十二种》有《都城纪胜》、《墨经》、《法书考》八卷、《砚笺》四卷、《琴史》六卷、《梅花》十卷、《禁扁》五卷、《声画集》八卷、《钓矶立谈》、《糖霜谱》、《录鬼簿》二卷以及《后村千家诗》二十二卷等,皆是重要的学术著作。
商人各自刻书,数量更多,前已述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刻板的众多书籍,被人称为『马版』。江春自己刻有《随月读书楼时文》。被称为『四元宝』的大盐商黄氏四兄弟中,『大元宝』黄晟刻有巨著《太平广记》《三才图会》等,『二元宝』黄履暹为苏州名医叶天士刻《叶氏指南》,又刻《圣济总录》等。卢雅雨刻的《雅雨堂丛书》,有古也有今,其中很多颇有价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学者所查阅。现常见的王士祯的《感旧集》,也是卢雅雨为之重刻。
还有『扬州八怪』的诗文集,至今尚可见到的汪士慎、金农、郑板桥、李葂等人的诗文集皆是盐商出资刻印。文学名著《儒林外史》也是得到盐商的资助才刻印出来的。古代刻书绝非易事,每部书『非千金不得』,扬州刻书巨富,既显示了盐商的经济力量,又显示了扬州的文化力量。
由于商人刻书的带动,扬州出现了很多刻书为业的场家,他们自己也刻书赚钱。扬州的刻书业发达,以致形成了『扬帮』刻业艺人,盐商衰败后,『扬帮』中大部分艺人也流落金陵、上海等地。另外,大量刻书,也少不了画家,几乎每一本书都附有图,而且往往有名家为诗文家画的像。
扬州经济对扬州画派画风的影响
新安画派之画风的形成也是受商人影响。比如新安商人特喜购倪云林的画,新安画派的画家则全是以倪云林为法。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扬州八怪』的主流画风形成也和商人有一定关系,前已述,扬州画家作画自由更多一些,因之画家主观情绪更重要。但任何有成就的绘画都必备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师传统,一是师造化,最后是画家精神气质的决定因素。任何商人都不能命令画家朝哪一个方向去努力,但却可客观地不自觉地限制他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徽商在黄山附近兴起,那里的画家师造化就以黄山为主,一时间全国来黄山的画家皆以画黄山为主。为了表现黄山,光学倪云林的画法就不够用,就要创造新的技法。盐商在扬州兴起,全国的画家来扬,师造化就以扬州遍见的花、竹、兰、菊为主,扬州少大山奇峰,山水画便也减少。当然,这不是什么主要问题,主要是绘画的风格问题。
严格地说,扬州并没有一个画派,各家有各家的画风,并不一致。但总的来看,扬州画坛上还有一个主流画风,还有一个大概的精神状态。为了论述上的简便,姑以其主流画风为主进行研究。主流画风即被人称为『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汪士慎、罗聘、高翔、高凤翰等人的画风,虽各具面貌,然皆纵横排奡,飞动疾速,三笔五笔散漫不经。其艺术水平并非太高,但皆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展示出生动活泼和不受绳规的气氛,和当时笼罩画坛的『四王』死气沉沉的画风截然相反。
『四王』画风当时被称为『正宗』,『正宗』相传柔弱萎靡,毫无个性,早已形成模式。八怪的画生机勃勃,反映了十八世纪又一次抬头的市民思想和市民意识,强烈表现自我,突出个性的解放,这是扬州以商业经济为主的市民思想的大显露,和八怪同时,寄居在扬州盐商之家的全祖望、戴震等学者也都是强调个性解放的,做学问也抵抗那种空洞的义理之学。戴震更指斥『义理』障蔽了『人欲』,指出『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公开提倡『彰人欲』,也就是个性解放,强调自我。而商业城市中,突出来的『自我』都有一股强大的活力,所以八怪的畫风,正是扬州这个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之折射,这是八怪画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汪鋆说它『似苏、张之捭阖』,完全正确,『苏、张之捭阖』是商人活动于世的必备手段,艺术是意识形态,又称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态是社会意识形之于『态』上的态。没有扬州商人打开的生动活泼的扬州城市局面,就不会有『扬州八怪』生动活泼的绘画。
『扬州八怪』的画,师传统主要是师近传统,即清初在扬州画坛上的有成就画家的传统。主要是石涛,其次便是查士标。石涛是坚决反对当时泥古不化、死气沉沉画风的主要人物,他的画纵横排奡、生机勃勃。石涛早期画山水,后来兼画竹石、花果,只要把石涛的竹石花卉和『扬州八怪』的竹石花卉画一比较,其师承关系一目了然,尤其是罗聘的竹和石涛的竹几无二致。『扬州八怪』几乎都服膺石涛,金农、李方膺、李鱓、高凤翰、郑板桥等人皆一而再、再而三地称道石涛。郑板桥不但称道石涛,而且还对石涛的美学思想颇有研究,对石涛思想中的『师其心不师其迹』『师其心不在迹象间』等也有更详细的阐述。八怪之一的高翔是石涛的朋友。石涛死后,高翔每年为之扫墓,至死弗辍。[13]
有人说,关系如此深厚,在艺术风格上是不可能没有感染的,这种推理绝对可以成立。石涛的画以及绘画思想对『扬州八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事实。
其次是查士标。查士标晚年居扬州,死于扬州,葬于扬州。查士标的画早期属新安画派,后期,他『故乡乱后莫言家,南北浮踪度岁华』[14],散漫、动居的生活改变了他的画风。他后期的画以动和散为主要特色,史书称其『风神懒散』。他的山水画也有些花鸟画化,山石、林木高度概括,又流动风散,『扬州八怪』提到查士标的人虽然不多(查死于一六九八年,八怪们当时只是孩子),但他的画风『润物细无声』,从『扬州八怪』的画迹中很容易看出来受到査士标的影响。
很多国外学者把石涛、查士标都算作『扬州八怪』,虽不严谨但也似乎有一些道理。查士标、石涛都是从黄山下来的,他们原来都可以说是属于新安画派,迁居扬州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扬州商业开始繁荣,他们到这里可以售卖字画,赚取更丰厚的报酬,一言以蔽之,是盐商把他们吸引到了扬州。他们在扬州扎根、撒种,开出了『扬州八怪』的花。归根到底,『扬州八怪』画风的形成,商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扬州八怪』的画另一个特点是:几乎每一画上都有长题,或诗或文。款题图画,始自苏、米,至元而大盛。到了『扬州八怪』,又产生一大变,如果说『扬州八怪』有突出的成就而高于其他画派,那就是他们的诗。八怪每人都有诗文集遗世,如按十五家论,只有杨法和闵贞无诗集,所以,一般论者也不把这两家列入八怪之中。十三家有诗文集,其中有两家诗文集已佚,至今尚可见有十一家,而且金农一家便有十五集。其中郑板桥、金冬心在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李方膺、李鱓的诗散失甚多,其诗清新自然、生动流丽才气不在郑、金之下。
八怪善诗,画上必题诗,其根源和盐商不无关系。
前已述,盐商大部分是文人且有诗文集行世,他们刻书,出资为文人刻集,和文人唱和,显示了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实际也如此)。中国士人的传统观念:只会画画的不足道,乃至被视为匠人。诗文之余作画才算高雅,所以他们特别讲究画家的文化素养。扬州『二马』,以文会友,凡文人来访,进门须先作诗一首。待审定后,再决定接待等级。据说丁敬初到扬州,投奔马曰琯,马问他一些掌故,丁没答出。马又以扬州风景『青石蓝书黄叶经』为上联,要丁对下联,丁亦未能对出,马认为丁才能平庸,于是待之甚薄。后来丁敬只好跑到杭州去了(扬州绿扬村至今尚有这副对联,上曰『青石蓝书黄叶经』,下曰『红旗白字绿杨村』)。这个故事出处尚不明(丁敬能诗,也许是后来事),但也道出了盐商重士特重诗文修养的事实。还有传说黄慎到扬州卖画,一度失势,请教金农,方知在扬州卖画必须善诗、善书,黄慎回闽后,学诗成,再回扬州,名气方大振。这些传说确否,还待考证,但其基本精神符合扬州画坛之实。
从上述小玲珑山馆、休园、筱园等诗文盛会以及『虹桥修禊』等盛举看来,盐商亦特重诗文,画家如不善诗文,是很难得到盐商青睐的。
绘画作品销售量最大的扬州茶肆酒楼、店铺菜馆,主要为商人而设。商人们坐在茶肆中,读书品诗,方有情趣,加上受风气影响,缺少题诗的画,一般店馆也不大愿意购买。所以,『扬州八怪』的艺术中诗书画印相结合这一显著特色,虽然是画家们努力的结果,但商人所制造的气氛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乃至制约作用,是丝毫不能忽视的。它从内容、形式各方面限制了画家,画家处于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去适应这种由商人无意或有意地限制了的内容和形式。顺之者昌,不顺者去,扬州画坛的大概风格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只要商人能继续保持他们的巨大财富,扬州的繁荣就会继续下去,扬州的画坛就不会衰落,而且将会产生更伟大的画家(最年轻的罗聘艺术成就就超过了很多前辈)。
『扬州八怪』之后,仍会出现新一代的『八怪』『九怪』和『不怪』。可惜好景不长,第一代大商死后,他们的子孙未能保住这个家业乃至于他们自己就未能继续保持這种巨富。
盐商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已开始贫困,财产荡尽,田园充公,乃至『子孙流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想象,盐商家的戏班不论是几百人、几千人,无疑都要另寻主顾,离开扬州。建设园林的人马,无疑也要转移到其他繁华之地。为大商服务的商店、茶肆酒馆、妓院、刻书馆、医药店等等,大部分都要另寻存身之处。所以,嘉庆、道光之后,扬州已完全失去了昔日之繁华。当然,扬州尚不致饿殍满道,但昔日诗酒盛会,书画题咏,风流儒雅之美事已无人再能组织了。所以,嘉庆、道光之时,扬州的文化事业也就跟着衰落下来了。大画家尤要巨商支持,一般人是买不起他们的画,买得起也不会买,一个贫困的城市首先需要的不是绘画,画家居,大不易,大画家居,更不易,充其量不过需要一些画匠而已,或许尚能容纳少数画家,但却很难吸引外地的名画家,更难产生大画家,即使有一些像样的画家产生,也无法保持,他们要向商业繁荣发达的地方去谋求生存,就像当年外地画家跑到扬州来一样。所以,扬州画苑,在嘉庆之后也就没有出现过大画家,而且在罗聘死后,即顿显寂寥。
刘鹗《老残游记》中有一段问答,最是真实之叹,问:『扬州本是名士的聚处,像八怪的人物,现在总还有罢?』答曰:『前几年还有几个,如词章家何莲舫、书画家吴让之,都还下得去,近来就一扫光了。』嘉、道之后,画家又涌到哪里去了呢?
另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正在等待着他们,这就是上海。上海不但有水路运输,有港口,更有铁路运输,世界各国的大商人渐渐云集于此,上海的商业在崛起,可以断言,上海画派也将跟着崛起。事实也正如此——继扬州画派之后,上海画派乃是中国最大一个画派,其影响至今不衰。
——扬州八怪书画精品展
——天津博物馆藏扬州八怪精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