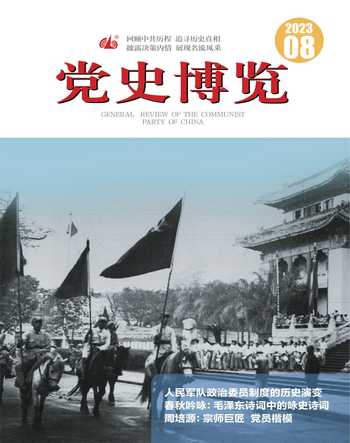周培源:宗师巨匠 党员楷模
胡新民

周培源
周培源是我國近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被誉为20世纪四位世界流体力学巨匠之一。他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两弹一星”元勋大多是他的学生,因此他被称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新中国的诞生,让周培源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于是,他放弃了不问政治的初衷,于195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无论风吹浪打,他都毫不动摇,恪守共产党员准则,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直至生命的最后—刻。
两次拒绝加入美国国籍
1902年,周培源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绅士家庭,16岁时辗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上海一些地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插牌时时刺激着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毫不犹豫地加入游行队伍中,贴标语、喊口号,冲在最前面。他因此事被这所教会中学开除,只得回乡自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上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看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招收插班生的广告,决定参加考试。他成绩最好但录取过程却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来他才知道,那次清华原定在江苏省招5名学生,有关部门已经内定了5名。因周培源考试成绩实在太优异了,有关部门只好与清华交涉,增加了一个名额。

周培源(右三)与家人和学生们合影。左四为钱学森
考入清华学校,成为周培源的人生转折点。一是形成了“科学救国”的理念,二是形成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理念。后面这个理念,鲜明地体现在他对美国的认识上。他的三女儿周如玲后来在纪念其父的文章中写道:“美国同意用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来办学,并非仅为善施,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致——他们害怕将来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精神影响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一言以蔽之,正如父亲所说:他们只不过是想以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办法来进一步控制中国而已。对此,美国人并不隐讳。如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们认为,即使在扩大精神影响上有所花费,但回报将会更高,因为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要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周培源被送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在美国读书期间,周培源仅花3年半时间就拿下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进行短期访问学习。1928年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海森堡,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1929年9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聘请,周培源结束了他的博士后生活,回到清华任教,成为当时清华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也是第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时年27岁。在此期间,他给许多后来成为科学名家的学生讲过课,其中包括钱伟长、林家翘和郭永怀。这三人后来在西南联大时一起考上了公费留学生。周培源把他们三人推荐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
1936年,周培源再次赴美,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研讨班,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了一年。这对他一生的科学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回国后看到日本正在加紧扩大侵华,他立即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回忆:“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周培源受梅贻琦校长之托组织学校南迁,从长沙的临时大学一直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的毕业生中有一半学生都追随周培源开始湍流理论(流体力学中最深奥的领域)的研究,这些人中,林家翘、胡宁、郭永怀等后来成为海内外著名的科学家。
1943年9月,周培源携全家赴美,到加州理工学院做科研。因美国急需科技人才,到达不久,他就收到美国移民局正式邀请他们全家入籍的信函,但他一笑了之。后来,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实验站,请周培源参加。由于这是政府科研单位,只有美国公民才有资格加入,外籍人员必须先加入美国国籍后才能加入。对此,周培源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不加入美国国籍。周培源深知:美国科技发达,应该利用机会去那里好好学习,为实现“科学救国”创造条件。但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他心中有数,科学家是有祖国的。1947年11月18日,周培源在写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和朋友威兰德教授的信中,专门提到美蒋勾结:“国民党政权注定要灭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代,没有一个彻底腐败、官僚、专制的政府可以维持下去,尽管它得到大洋彼岸的朋友的精神和充分的物质支持。”
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与林家翘等当时都在加州理工学院,周末他们经常到周培源家聚会。他们在国内时,都亲眼看见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官吏日益贪污腐化引起的天怒人怨,因此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希望。他们在美国报刊上看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与新四军深入敌后,动员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打击日伪军等伟大成绩,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认识。有件事让周培源印象很深。他曾在美国接待过一名到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他问那名官员国内的形势,那名官员一开头就说,共产党很可怕。周培源对他的回答感到很惊讶,便问道:“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还有美国政府送来的大量飞机大炮,为什么还怕共产党?”那名官员答不出来,只是说:“可怕!可怕!”多年后周培源回忆道:“现在看来,情况就比较清楚了,蒋介石向美国政府索要大量的武器与美元,并不是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为了准备打内战,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并用从美援中贪污来的几十亿美元的赃款养肥了四大家族。”
1947年2月,周培源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全家离开美国返回上海。4月,周培源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周培源和两个女儿,冒着扬沙的寒风骑车进城,欢迎解放军进驻北平。周如玲清楚地记得:“当晚我看到他们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我看见父亲激情难抑。拳拳报国之心,伴着破晓的春色炽烈燃烧起来。没多久,我的二姐如雁,当时年仅14岁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1973年7月17日,周培源(左二)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杨振宁(右一)
忠诚于党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已经出走,学校行政部门工作几近陷于停顿。中共中央和北平市委决定在清华成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叶企孙担任常委会主任,吴晗和周培源担任副主任。由于叶企孙很少管事,而担任了副市长的吴晗工作又很忙,主要工作就都落在同时兼任教务长的周培源肩上。当时北平市委统战部对这位“清华元老派”人物的评价是:工作积极,虚心负责,对党表示钦佩。周培源曾对校党委统战部部长说过:“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也由于解放军仅在短短几年内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击溃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正确、强大和符合民意,这才使我决心留下来,走保卫清华迎接解放的道路。”
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根据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如“反动党团登记”“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每次运动,全校师生都要参加,有时还要停课,这必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周培源一方面认识到在新旧交替期间这些民主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在教学安排中为此让路,积极支持;另一方面认为教学工作也应严格要求,不能放松。他的威信,他的高超管理才能,使这一阶段的毕业生成为清华历史上具有鲜明的又红又专特点的有用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各条战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对消除旧知识分子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提振民族自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周恩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结合他自己经历谈的知识分子立场、态度和为谁服务等七个问题,对全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周培源极其真诚、热情地投入运动中去。他的小女儿周如苹回忆道:“特别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集中反映了当时他的认识和对思想改造的态度。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是有些偏激,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他是真诚的,他的思想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共产党寄予了厚望。他坚信多年的科学救国思想在新中国能够得到实现。通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并开始树立新的世界观,同时清除了他们对院系调整的抵触情绪。”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教育部于1952年开始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当时清华的不少教师想不通,有人甚至说是把“清华五马分尸”。周培源非常理解国家大局,耐心做思想政治工作,在上级党组织和清华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没有发生丝毫风波就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调整任务,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周培源随清华文理学院一起调入北京大学。北大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党委书记是江隆基。马寅初社会活动较多,学校的事情基本不管,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由周培源负责。他和江隆基配合默契,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周培源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这个专业培养的许多人才,后来都成为力学界的领军人物和骨干。

1979年,英国前首相、牛津大学校长麦克米伦访问北京大学时与周培源(右)交谈
1955年,周培源应邀去苏联参加莫斯科大学建校200周年校庆活动。亲身感受到苏联老一代共产党人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发展变化,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了认真的思考,回国后向所在单位北京大学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周恩来亲自提名,任命周培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由于频频出国,入党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直到1959年2月5日,他才被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
自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后,周培源自觉地、始终如一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独立思考,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他熟悉学校的教职员工,只要有交谈的机会,总是仔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有什么困难需要学校帮助,征求他们对系、校工作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前,人们随时可进周培源家聊天,反映情况,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因此,周培源对北大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1957年,针对当时有人炒作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言论,周培源多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予以坚决的驳斥。1958年,有人提出了激进的学制改革计划,周培源认为不符合学校实际,表示不同意。后来这个计划虽然得以通过,但在实际执行中难以落实。1964年的“社教”运动,影响到学校的教学,北大出现了一些复杂问题。为此,周培源专门写了材料呈交给周恩来。
“文革”中反对在《红旗》上刊登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周如苹回忆道:“父亲在运动初期由于有中央明令保护,加之他正在组织世界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另外也许在北大多年人缘较好,所以没有受到冲击。”不久,周培源全身心投入群众运动,一度成为北大一派群众组织的领袖。在北大两大派群众组织举行公开辩论时,周培源作为其中一派的领导坐在台上。当时在台下观看的季羡林对周培源充满敬意,觉得这正是他一身正气的体现。后来,他经历了1967年视察陕西汉中北大653(653工程是周培源在1965年为落实毛泽东“三线建设”要求亲自策划的一个项目)分校时遭部分学生围堵批判,1967年底家被抄,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被监护审查,等等,但总的来说还是有惊无险。
1969年下半年,担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的周培源下到陕西汉中北大653分校。年底,北大领导通知他回北京,参加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1968年,湖南的一名中学教师写了一篇彻底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的支持,陈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文批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相对论,也听过爱因斯坦的演讲,对这种批判实际上心里清楚,经过反复考虑和努力,他先搞了一个内部批判组来应付。作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又身为共产党员的周培源,深知在党刊《红旗》上发表批判相对论文章将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的影响,于是他坚定地对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此后,他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表示过反对意见,有一次甚至当着陈伯达的面表示反对。最后,这场批判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不了了之。
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7月14日,周培源昔日的同事任之恭、学生林家翘等27名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组团回国访问。他们对新中国在科学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但对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杨振宁在1971年夏回国访问时就已经提出过。周恩来在接见任之恭等人时提到了杨振宁,说道:“他讲话实在,毛主席称赞他。”周恩来对陪同会见的周培源说:“请周培源同志提倡一下,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实际上,此前周培源就已经发现并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还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周恩来这次指示之后,周培源将文章进行再次修改整理,于7月20日上书周恩来,认为科学应用和基础理论不可偏废,但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并提出具体意见。周恩来很快作出重要批示。但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一些人的强力阻挠。北大哲学系的一名教师回忆:“我担心他为此挨整,但周培源先生当时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共产党员要有党性,要坚持原则,不怕他们整,整又有什么了不起。如今事过多年,他的这些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他这种为党的科学事业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我深深敬仰。”周培源的文章在排除干扰后于当年10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是新中国外交大突破的时期。1972年,經周恩来建议,周培源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事接待任务骤增。但他对学校科研教育工作并没有放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8月,北大数学系教师王选提出并开始研制激光汉字排版系统后,周培源独具慧眼,从人财物上全力支持。王选在1995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1998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王选后来还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86年1月,粒子物理讨论会在广州举行。前排左起:彭桓武、李政道、周培源、杨振宁、朱洪元等

1992年6月1日,周培源在为他90寿辰而举办的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上发言。前排左起:杨振宁、周培源、吴大猷、李政道等
1978年7月,76岁的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长。10月赴美国访问,就中国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和美国派访问学者来华等问题与美方达成协议。1980年,他带着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赴美国对美21所高等院校进行详细的考察。回国后,从师资水平、人才培养、学术现代化、思想教育和领导管理等五个方面,对我国高校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意见。1980年9月,周培源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年近八旬的他,除了担任北大校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任务相当繁重。他考虑应该让年富力强的人来接北大校长的班,于是在年底写信给中央,请求辞去北大的职务并于1981年3月得到批准。但他仍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仍然未中断带研究生和做科学研究,一直到1993年11月去世。
周培源在科学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赢得了海内外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尊敬和爱戴。1992年,周培源90寿辰,海内外他的学生、友人发起在北京召开“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暨祝贺周培源教授90寿辰纪念会”。海内外著名华人学者几乎全都与会,此次会议成为20世纪第一次中华科学巨星的大聚会。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用“献身科学,教育英才;功在国家,造福将来”的贺词表达了他们对老校长的衷心赞颂。
最崇敬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培源多次见过毛泽东,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次都与物理学有关。一次是1964年谈基本粒子,一次是1973年谈基础理论。
基本粒子是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之一。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回忆:“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国内的粒子物理工作屈指可数,研究工作主要是沿着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方向进行的。毛泽东主席1955年1月15日在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子、质子、电子也是可分的观点。1965年《红旗》杂志刊载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这鼓励了一些国内粒子物理理论研究人员去学习方法论,并用之于分析粒子物理实验结果和探讨粒子物理理论发展。”
坂田昌一是日本理论物理学家。他毕生从事原子核物理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并作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8月,坂田昌一作为团长率60余人的日本科学代表团参加由中国发起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周培源是中国代表团团长。1964年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当周培源向毛泽东介绍了日本坂田昌一时,毛泽东说读过他的文章,这让坂田昌一既惊讶又喜悦。
8月24日,毛泽东请周培源、于光远(周培源的学生,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谈坂田昌一的文章。毛泽东问了不少关于基本粒子的问题,周培源一边介绍,一边把一些要点写在纸上给毛泽东看。后来周培源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文中写道:“毛主席办公,经常不分昼夜,有时通宵达旦,白天休息几个小时,这时(就是在我们到他卧室的那个时候),他刚睡醒,还穿着睡衣(睡裤上还缝有一块补丁,培源师注意到了,离开毛主席那间房子后我们还议论过),又开始了工作。毛主席谈话时,或站,或坐,或来回踱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完全是商量、探讨、研究的口气,使我们毫无拘束,就像在老朋友家里做客。这次一直谈了3个钟头。”括号里的内容为报纸保存者于光远的补充说明。文章还提到毛泽东当时问到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教授讨论过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周培源事后作了调查。他在1978年《毛主席的旗帜是科学的旗帜》一文中写道:“事后我问傅鹰教授,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讲的?他说是在讲义中提到的。可见,毛主席连北京大学化学系发的讲义都看过,真是博览群书。”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杨振宁,周恩来和周培源陪同。接见中,毛泽东对杨振宁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也十分关心我国的科教事业和基础理论研究,再次提出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希望中国的科技成果能够对全人类作出贡献。周培源回忆说:“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生难忘。”
周培源的一名学生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他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事业,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尊重。”“我毕业离校,下乡插队,他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听说你到了北戴河附近下乡插队。北戴河,我还是当年在清华学习、到唐山实习时去过。那时我们是为了成名成家,而你们下乡是与工农结合。“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信中,他还告诉我,他最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
1949年5月,周培源作为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代表人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培源回忆起那天会见的情景时说:“周总理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5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应英国共产党的邀请,中国派出了以刘宁一为团长,周培源、李德全等几位各界著名人士为成员的代表团,赴英国参加庆祝活动。回国后刘宁一因临时有其他任务,代表团即公推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在汇报中,周培源表露出不愿从事外事活动,只想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思想。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励说:“你们这次出国,做了许多工作,做得很好嘛。以后你们出国,不要有思想负担,要大胆放手地去做工作,不要缩手缩脚。凡是对人民有益的工作,都是重要工作,不会做的要在实践中学会,这是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新中国对我们的要求嘛!”
从那以后,周培源把从事外事活动放到同科研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他在外事活动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才能和杰出的能力。和周培源一起参加过几次外事活动的于光远说:“他能坚持我国党和政府的立场,同时又能灵活地运用策略。”“我认为培源师在国际和平事业方面的操劳,是他的一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
1955年,周培源向北京大学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从这件事中,周恩来看到了周培源的思想正在发生质变,对周培源关怀备至。有一次,周恩来见到周培源的二女儿(当时在部队工作),高兴地说:“你爸爸申请入党啦!”接着详细地向周培源的女儿询问了周培源的家庭、生活及思想情况,关怀、鼓励之情溢于言表。
十年内乱期间,周恩来在百忙中一直注意对周培源的保护。当周恩来获悉周培源担任了北大一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后,很快派他的联络员去做工作,劝他退出来。周培源觉得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有错误应该耐心帮助他们。但是,对总理的信任使他很快听从了劝告,退出了群众组织。1967年,周培源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去陕西汉中北大653分校视察工作时,部分学生要批判周培源的某次讲话。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指示当时的陕西省委负责人,让陕西省委采取保护周培源的措施,并且随时汇报情况。周培源在周恩来关照下,平安回到北京。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平静。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玲回忆:“1967年12月21日半夜抄了我们家。大概周总理连夜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翌日清晨,他们又将当夜贴到全北京城的大字报、大标语全撕了下来,没敢对父亲采取进一步行动。”她还回忆在1968年底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周培源被监护的情况。当她到监护的地方看望父亲时,“(父亲)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找人去吧。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强忍着涌到我眼中的泪水,安慰他说,‘别急,都会好的。我们心照不宣,父亲要我去找的人就是周总理。毛主席生日的前一天,没有任何说明,父亲突然被放回家”。
1976年1月8日清晨6点,当北大广播台照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的新闻广播节目时,哀乐传出。周如玲从梦中惊醒,一下从床上跳起来,飞奔到父母的卧房,告诉他们周总理逝世了。周如玲记忆中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不止,很久不能自制。父亲听到我祖父逝世的消息时也没有这么伤心过。”
2001年7月1日前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周如苹撰写了《父亲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文中写道:“父亲和许多老共产党员有着很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他最崇敬的优秀分子,他以他们为楷模。尽管没有人授予过他什么光荣称号,但是我坚信父亲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