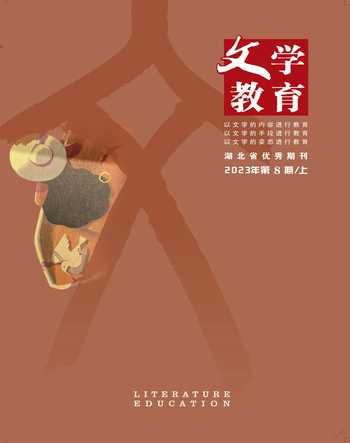国家形象视域下李娟《冬牧场》的“汉写民”解读
田文羽 徐梅
内容摘要:“汉写民”文学是一种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文学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汉写民”文学在建构国家形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过去,人们对于“汉写民”文学的理解仅限于它在传统与现代化碰撞中的缓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以往“汉写民”文学的神秘化、想象化、人物“乌托邦”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汉写民”文学书写形式单一、发展迟缓。而李娟的《冬牧场》作为新时代“汉写民”文学代表作,在用平等展示、生动再现、日常化的书写手法丰富少数民族形象塑造的同时,又对当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进行了增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在文学层面上建构国家形象的创新性表达。
关键词:李娟 《冬牧场》 汉写民 文学话语 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国家行为与活动在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心目中形成的印象与评价”[1]。国家形象是始终是对外展示的一面旗帜,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的达成国家形象的建构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汉写民”文学不断提高自身,成为沟通多民族文化的桥梁,其进步不断增补着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又受当代主流文学话语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发展,进而投身到建构中国形象的“自塑”事业中去。李娟的《冬牧场》作为当代“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描绘了新疆哈萨克族的冬日牧歌,也是“汉写民”在新时代中的尝试与延续。
一.国家形象的建构及“汉写民”文学的发展
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中代表我国地位,展示我国实力的重要依据,实质是在国际上对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但是目前我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尚还存在问题,“孟建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形象建构困难重重,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或困境: 第一,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呈现出令人痛心的“他塑”现象(即被他方掌握主动权);第二,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中(即自我塑造),则存在着诸多问题。”[2]为此,在新时期,中国形象的“自塑”成为了国家形象建构事业中的重中之重。为改善这一现状,需从各方面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3]民族与文化始终是“自塑”国家形象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共同构成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国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备受关注。而文学作为现代社会形象构建的主要载体与跨文化传播最有效的手段,在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汉写民”作为一种文学书写形式,是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化关注的直观体现,是对于少数民族形象在文学层面“他塑”的重要支撑力,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的繁荣,并且在“中华民族共同體意识”的引领下,其内涵不断变化、丰富。
“汉写民”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是从20世纪80年代,彼时的中国处于现代性转型中,传统文化与这股现代性文化潮流碰撞摩擦产生剧烈冲突,由于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法,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崩塌滑坡的现象。“‘礼失而求诸野,每当知识分子的理想在现实环境中受挫、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她们往往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4],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破碎使得一部分作家转而投向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洪流。“面对这一困境,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不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5]120,少数民族文化以其独有的叙事资源融入进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中,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多民族文化史观”的重构,这便是“汉写民”文学最初的意义。
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对民族团结繁荣愈发关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发展迅捷的今天,在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繁荣,现代性转型与传统文化发展达到相对平衡的境况下,“汉写民”的关注重心也应随之转变,转移到少数民族文学形象塑造上来。
二.李娟“汉写民”道路在新时代的突破
(一)多视角“他塑”的进步——以日常化书写解构神秘化
早期的“汉写民”文学实践源泉来自于汉族作家对于边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现实感受,并以此为叙事资源,以期达到文化身心净化的效果。无可否认的是,所谓的“生活体验”与“现实感受”,都离不开边疆地域与民族生活为主的创作温床。以《冬牧场》为代表作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汉写民”文学也依旧遵循着边地实践的传统,其“平等展示”与“如实再现”的书写特点逐步完善着少数民族形象的多视角“他塑”建构。
《冬牧场》以真实打破“想象”,突破了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想象心理,将少数民族文化“去少数化”,以日常化来书写哈萨克牧民文化的地方性。以以往“汉写民”文学的代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其中对于驯鹿鄂温克族的描写偏重于民风民俗的描写,并且着重对于其中的“萨满文化”进行了宏大的书写,这可以理解成为作家想要通过这种庄严肃穆的少数民族文化书写达到一种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效果,但让人震撼的同时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敬畏心理。范稳在《悲悯大地》中通过书写一些胡鬼神蛇的故事情节来衬托雪域高原的神秘色彩。虽然这确实达到了一些文化自救的效果,但是却在潜移默化之间把少数民族文化推向神秘化,产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距离感。
而李娟《冬牧场》的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这种由“想象”而造就的距离感,把日常生活作为书写的重点,从日常中寻取共同点,加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通意识,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由“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他塑”魅力所在。她不再刻意放大民风民俗对于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而是从日常入手,着重日常生活。在她的笔下,没有宏大的民族习俗场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仪式感,有的是平凡但温馨的日常生活,是揭开神秘面纱后深入其中的真实感受。李娟在文中的日常化书写把哈萨克牧民的游牧文化融入大局,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整体、人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牧民在牧场中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用日常化书写解构了以往的神秘化,揭示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共同之处,消解了距离感。
1.日常生活的平等展示
《冬牧场》之所以是作为正在不断进步发展的“汉写民”文学的代表作,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李娟对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活描写。这种日常描写很大程度上解构了少数民族在大众心目中的“神秘化”形象,通过对生活的真实再现与牧民形象的塑造,揭开披在少数民族身上的面纱,让我们意识到各个民族之间本没有任何不同,身体里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娟平等地展示了边地牧场生活的苦与乐,不单纯美化,也不过度丑化,而是用心地记录自己生活在其中每一天的所见所闻,用“无我”的姿态展示冬牧场中的每一个日夜。“无我”绝不是否定“我”的存在,而是将“我”化作一双看世界的眼睛,直白坦荡地呈现边疆的生态世界。[6]李娟对于牧场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生活中的美好她从不会吝啬展示,荒野中的朝阳、云朵、月亮,还有不时拂过耳畔的牧歌,都是来之不易的财富;而那些不顺她也不会刻意规避,食物的贫瘠、水的匮乏还有近于与世隔绝的苦闷,都一点一滴记录在册。在这里,李娟把自己融入在牧民的生活里,体验放牧、背雪等一系列活动,从一开始的只会帮倒忙,到后面的逐渐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这不仅是一次单纯的生活体验,而是要把整个身心都浸润在阿勒泰的牧场里,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与“他塑”的视角,平等地展示生活在“冬窝子”的点点滴滴,苦乐与共。
2.牧民形象的如实再现
《冬牧场》以“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如实地再现了牧民形象,人物形象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更加鲜活生动。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汉写民”文学的延续,《冬牧场》中自然也存在着边地少数民族形象,与以往以小说这“虚构”文学为代表作的“汉写民”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式的人物相比,李娟笔下的牧民是真切的从牧场中走来,不再是一个民族的符号,而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所谓的“乌托邦”式人物,是类似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多布库尔河》中的古迪娅与母亲这样的人物,身上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个性服从于共性,从而成为了一个民族的代表性符号。这种人物形象塑造在彰显着一个民族生命力与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鲜活性。李娟随着居麻一家南迁到“冬窝子”,在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居麻、嫂子、加玛的形象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男主人居麻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哈萨克牧民,会说汉语;他对于放牧有多年独到的经验,该怎么垒筑牛羊圈,该怎么给牛羊治病,都有自己的方法;同样他的风趣幽默也是在这个寒冷冬季里枯燥生活的一些调节剂,例如有次李娟在冬日的早上坐在炉子边喝热茶,不过一米远的距离还能看到嘴里呵出的白气,在靠近点儿,半米,一尺……都还是有白气的,居麻就会适时地来一句:“你要干什么?吃炉子吗?”[7]57总让人忍俊不禁。
但是真实性的真实之处在于,它会呈现人物的多面性。人之所以是丰富的,归根结底就在于人物的多面性,“非虚构文学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必然要求作者要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来对待所面對的人或事,不能任意添加自己的情感评价”[8],所以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不是扁平的,而是多面的、立体丰满的。就居麻这个人物而言,他不只是有热情幽默的一面,李娟在文本中提及他爱喝酒,并且自己这次跟随他家深入“冬窝子”的机会也是因为居麻欠的酒钱;他也会因为家里劳动力的不足而要求女儿加玛待在身边,哪怕加玛从内心里渴望上学;他也会在冬天的时候耍赖不想起床放牧,会和邻居争吵……李娟用最平淡且幽默的语言叙述着日常发生的点点滴滴,在这点滴之中汇聚成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种真实喜怒哀乐的书写把哈萨克牧民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完成了对于少数民族形象的多视角“他塑”中关于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以李娟《冬牧场》为代表的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应运时代而生,在生活描写、人物塑造方面为新时代少数民族形象的多视角他塑提供了载体。进入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拥有全新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这为“汉写民”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同时,新时代对于少数民族形象塑造的需求也指引着“汉写民”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将作家创作的注意力从过去的“礼失而求诸野”转变到少数民族形象塑造上来,从文学层面为中国形象“自塑”添砖加瓦。
(二)对当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增补——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
文学话语体系是文学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学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从表意上看,文学话语体系是作为人类文学活动中由交往主体通过文学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文学认知关系,具体表现为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等外在表现形式。同时,文学话语体系又具有内在思想,并且受时代与社会发展、文化构成、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时代性、人民性、文化性与包容性等特征,结合目前来看,当代文学话语体系的主流内在思想是旨在创作彰显集体与个人相结合、民族的与世界的相结合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弘扬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学活动。
文学话语体系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思想相互联系,其外在表现是内在思想的向外表达,内在思想又指导着外在表现,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这种联系具体体现在文学活动与指导思想的互融性上,例如在延安时期,文学创作领域中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导向,呈现出个人服从集体的总体态势。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让创作主体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人民的现实生活场域之中,描写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事。这种思想与外在表现的结合贯穿文学话语体系发展的始终,2021年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文艺创作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因此,当代文学的主流外在表现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活动。
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以塑造少数民族形象,书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以切身体验为经验,关注少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实际需求,符合当代主流文学话语所需的外在表现形式。《冬牧场》全书围绕着“生活”二字而展开,展现的是哈萨克族最普通的牧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其中包含的风俗与特色传统文化,李娟也从中体会到游牧文化的绚烂多彩与游牧家庭的谋生不易。南迁是靠游牧为生的哈萨克族人每个冬季必不可少的项目,经过长途跋涉,最终到达的目的地被牧民们称为“冬窝子”。“从乌伦古河以南广阔的南戈壁,一直到天山北部的沙漠边缘,冬窝子无处不在”[7]4,李娟深入“冬窝子”中,在这里,她体验到了南迁途中的寒冷与不易,不光要看顾羊群,晚上也要留宿沙漠里,这里没有坚硬的木材,也没有现代化的水凝钢筋,羊圈、围栏都要用动物粪便。但夜晚的星星,欢快的民谣,还有偶尔驻足的旅人,都是这里生活的惊喜。这些,都生发于边疆的冬牧场带来的独特生活体验。
同时,新时代“汉写民”文学的进步也丰富了当代主流文学话语所需的表达内容。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提供了一种以人民为主体,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服务的文学作品。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日益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必然会成为新时代文学书写的重要角色。《冬牧场》在展现游牧文化与哈萨克风俗等方面采取与日常生活相融并贯穿始终的方式,而并未采取之前“汉写民”文学作品所采用的“神秘化”与“神圣化”等表现手法,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学层面传播与交流方面的突破,是从细微之处入手而达到全面表现效果的一次勇敢尝试。《冬牧场》在写访客一部分中有关于巴塔的描写,虽然并没有关于这种习俗的详细讲述,但是一个民族对于民俗的郑重体现在一举一动里。扎达在看到客人认真做巴塔的时候惹不住偷笑,但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他提醒加玛和嫂子做好应做之事。不光是此处,在描写给牧民穿搭、外出放牧的时候,李娟也是在不经意间穿插入描写民族习俗,相比起过去以描写少数民族民俗民情为重点的“汉写民”文学,李娟似乎是刻意淡化,但是又正是这种随手间的提及反而使人印象深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民族对于习俗的态度而透视到一个民族的信仰与对于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情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与发展,他们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心中依然保持着对于“传承”的坚持,在他们的思想中依然怀揣着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与敬重,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要求。恰恰是李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描写民俗风情的这一描写方法,使得它们的魅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另外,新时代“汉写民”文学的精神内涵也与当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内在思想紧密贴合。它在现有文学话语体系内在思想的基礎上,增补了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积极向上的、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反映少数民族在文化、生活等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创作精神。在《冬牧场》中,李娟围绕居民、生活、游牧进行创作,第一人称的视角更加直观地体现了她在精神层面的前后变化,贯穿其中的是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冬季牧场除了寒冷,还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问题,“扛一袋雪回家,途中足足得休息五六次,到家已经给压得头晕眼花。而一天最少得背两趟雪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一天的用水量。”[7]56可她却依旧乐观,会期待着下雪,观察天上的云团,期待日暮的晚霞,会因为下了一场大雪兴冲冲地去扛三大袋雪回家,在无边的荒野中,快乐也变得简单起来。另外,居麻一家也是乐观豁达的,身上满载着游牧民族吃苦肯干的坚韧,居麻负责放羊,在黄昏倒在雪里也咬牙隐忍;嫂子在家干杂活,总是把藏在地面下的家收拾的干净整洁;加玛十九岁就能独当一面带队南迁……居麻一家是千千万万牧民家庭的缩影,正是这些牧民身上所特有的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以及险恶环境下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意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娟的生活态度,进而体现在文本当中。
《冬牧场》在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有所表现。对于新疆少数民族而言不可缺少的歌舞的现代化则是受现代化影响的典型。在放牧的闲暇时刻,居麻一家也喜欢跳舞,但与以往只能唱歌来伴奏的情况不同,音箱进入了牧民的生活,他们不再局限于自身歌唱,音箱中的音乐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也更加便捷。胡尔马西的手机中也存了满满当当的哈语音乐,大家时而听着这些音乐起舞,热闹又愉悦。李娟也会用自带的录像机记录下这些欢快的时刻,从一开始的羞怯小心到后来的热情大方,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牛羊、歌舞与牧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处处相连,李娟以亲身实践经历在迁徙与放牧之中感受游牧民族对自身文化悠久的传承与坚守,也悉心观察着其文化不断现代化的过程,通过文字将其记录并展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以此来展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三.“汉写民”在新时代文学话语体系下的进步作用
随着时代发展,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日益明显,对于少数民族形象在文学层面的“他塑”愈发成为大众了解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文化习俗等的重要方式,新时代“汉写民”文学在场景呈现与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进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形象“他塑”在文学层面的完善,并使之成为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当代文学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发展活力。而因新时代“汉写民”文学的进步而深受影响的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有着深切影响。
(一)开启少数民族形象在文学层面多视角塑造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自述
从“汉写民”文学本身的进步而言,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转变书写重点,从寻求“避风港”式的精神慰藉转移到少数民族形象塑造上来,开启了少数民族形象在文学层面多视角塑造的新篇章,进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起到推进作用。“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眼光那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令我们打开眼界。视他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天性,这是最基本的礼貌。然而,置身于他人之中来看我们自己,把自己视作人类因地制宜而创造的生活形式之中的一则地方性案例,只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案例、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却是困难得多的一种境界。”[9]由此可见,“汉写民”文学的多视角“他塑”的书写方式在展现我国少数民族形象,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根据中国内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来看,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少数民族一起参与国家构建的历史成果”[10],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持续性事业,内容多、范围广,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生活与文化状况必然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中国沿着中国道路,以中国模式,展现给世界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颠覆性的中国国家形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人民安居乐业。”[11]以《冬牧场》为代表的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从实地体验入手,结合作家的个体经验对于边地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腻描写,并着重展示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文学的方式全方位地再现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生活现状,真实地呈现少数民族生活、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与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状况,完善了对少数民族形象的“他塑”,再与少数民族自身在文学层面上的“自塑”相结合,共同致力于完善少数民族的整体形象,进而为构建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国家形象增添文学层面的新力量。
(二)丰富当代文学话语,深入实践中国形象的自塑
新时代“汉写民”文学的加入使得当代文学话语体系又有了全新的发展,更好的深入实践国家对于中国形象“自塑”的要求,成为国家形象“自塑”事业中的重要推动力。拉铁摩尔提出边疆学说,并在其论著中表示:“当一个社会共同体占据某地域时,边疆便被创造出来。自此,随着该社会共同体的活动和成长,或者另一社会共同体的影响,边疆随之发生变迁和形成。因为历史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边疆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2]所谓“边缘”,其实是一种相对而言的说法,而看待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中华文化,更应该超越政治、地域、历史等因素的限制,从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角度出发,把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地方叙事”从遗落的境况下中捡起,使其不再作为一种被遗落的“地方话语”,而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部分。李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书写对象,通过多视角“他塑”的塑造方式,完善了汉族视角下哈萨克族的书写空缺,让淳朴的民风民俗、日常生活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入读者的视野中,丰富了大众对于哈萨克族文化的接受与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呈现多元格局,由于汉族人口数量庞大而造就了大批的以汉族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但是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人心,当代文学话语也随之变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相继盛放,與描写汉族生活的作品水乳交融,呈现中国民族团结、文化多样繁荣的全新面貌。同时,书写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生活地域等的“汉写民”文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逐步融入新时期文学主流话语当中,从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方面完善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从而催生更多优质的文学作品,使国家形象的“自塑”要求在文学层面得到有效实践。
《冬牧场》作为李娟的代表作品,呈现着她一贯清新细腻的写作风格,用活泼生动的文字记录着她在“冬窝子”中与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显现出文学在民做团结繁荣中的纽带作用。同时,《冬牧场》更是“汉写民”文学在当代话语体系下的延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呈现着由“想象”转向生活,由地方贴近主流的话语形态。“汉写民”文学作为“多民族文学”中的特殊部分,从民族形象“他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完成了少数民族形象构建中对于真实“他塑”的空缺,并以其进步性加入主流文学话语,从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两方面完善着当代文学话语体系,而当代文学话语体系的进步将促进从文学层面建构中国的民族团结、文化多样繁荣的国家形象。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新时代的“汉写民”文学会在未来的多民族文化沟通中承担起桥梁的大任,让各族文化水乳交融,更好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构建中国国家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写民”文学会愈发与时俱进,更加成熟,呈现繁荣的全新面貌。
参考文献
[1]陈金龙.新中国70年国家形象的建构[N].光明日报,2019-09-06(011).
[2]董军,“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开题会综述[J],现代转播,2012(1):121-123.
[3]赵辉辉.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形象[N].光明日报,2021-09-14(006).
[4]雷鸣.突围与归依:礼失而求诸野的精神宿地——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边地书写[J].当代文坛,2010(1).
[5]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中国图书评论,2010(07):120-128.
[6]许慧楠.诗性空间中的身心对话——李娟散文中的回归意识与审美建构[J].美与时代(下),2021(12):86-89.
[7]李娟.冬牧场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8]高善琴.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真实性散谈[J].文教资料,2010(18):4.
[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10]成苑.从自塑到他塑:全媒体视域下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路径研究[J].科技传播,2021,13(04):102-104.
[11]张进军.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话语体系研究[D].华侨大学,2017.
[12]Owen Lattimore, The Frontiers in History,in:Owen Lattimore,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Collecte
d Papers,1928-1958,London:Oxford UP,
and The Hague:Mouton&Co.,1959.
基金项目: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RW2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