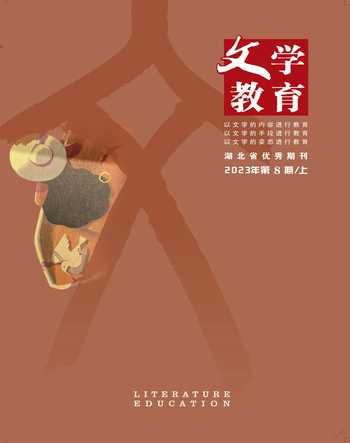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哀郢》中“冀壹反之何时”的精神实质及历史语境
范昱杉
内容摘要:《哀郢》发出“冀壹反之何时”之叹的情境是屈原不止“去君”,而且逾境“去国”;不是待召于郊,而是因罪被放逐。周代礼制,自疏去君之臣三月内等待国君召还,但臣子因罪被放逐的情况不在这一礼制范畴内。与作于去君待召时期的《离骚》等篇章相比,《哀郢》“冀壹反之何时”精神实质的独特性在于,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层面,个人被国君重用的仕进追求让位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父母之邦的眷恋。两汉九体拟骚作品对屈原“冀壹反”的心态进行了传承与重构,其希冀回返的精神实质更多偏重于期待被国君重视,属于个人进退、仕隐之抉择的范畴,这种精神实质的差距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屈原作品忠君爱国精神的纯粹与彻底。
关键词:《哀郢》 冀壹反之何时 待召之礼 屈原 九体拟骚作品
《哀郢》是屈原所作《九章》中的一篇,其中“冀壹反之何时”是此篇乱辞中的一句,这种希冀回返国都、再得面君的心态不仅贯穿于《哀郢》全文,而且多次出现在屈原创作的其他作品之中,构成其情感抒发的落脚点之一,被司马迁概括为“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应该注意的是,《哀郢》发出“冀壹反之何时”之叹、抒发希冀回返的心态,其背景不同于《离骚》等篇目,因而也有着特殊的精神实质和文本建构方式。不过,这种心态总体上受到周代自放之臣等待国君召还这一礼制的影响,应该将其置入这一历史语境中加以观照。
本文重点分析《哀郢》中“冀壹反之何时”的心态有着哪种独特的精神实质,是借助怎样的文本逻辑进行传达的,并探讨这种希冀回返的心态产生于怎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对周代礼制背景、楚国政治现实和屈原遭遇等相关史实进行阐述和辨析。此外,汉代九体拟骚作家对屈原作品中希冀回返的心态进行了怎样的传承与重构,体现了楚辞与汉代拟骚类作品精神实质方面怎样的区别,这两个问题也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在周代待召之礼的礼制背景下观照《哀郢》“冀壹反之何时”的心态,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能够帮助辨析《哀郢》创作的历史背景,加深对屈原《哀郢》创作心态的认识,准确区分不同创作时期、不同作家在作品中传达的希冀回返心态在精神实质上的差别,从一个侧面精确把握屈原作品忠君爱国的“骚义”。
一.弱化对个人仕进追求的表达
“冀壹反之何时”[2]一句是屈原渴望回返国都、再得面见君主的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表达。流放在外而希冀回返的心态,在屈原各个时期的作品中经常作为贯穿全文的抒情落脚点被反复申述。《哀郢》按照遵循长江和夏水而漫游的空间顺序,抒发流亡在外九年未能回返的忧闷与悲哀,“哀见君而不再得”“何须臾而忘反”“至今九年而不复”分别是作者回顾流亡路线、思念终古所居、讲述窘迫的政治遭遇几个抒情单元的情感落脚之处,长期流亡、远离故乡、仕途困顿在屈原作品之中统一归于对回返国都、再得面见君主的希冀心态。与《哀郢》同理的还有《离骚》[3],作者借受女媭责备、向舜帝陈词二事坚定了自己的政见,借一上昆仑与浮游求女二事写期望弥合君臣分歧而不得,借灵氛之占与巫咸之告的矛盾写自己在是否远逝这一问题上的犹疑,希冀回返的心态贯穿于作者设计的每一个浪漫诡谲的艺术想象情境之中。
但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之中,屈原这种希冀回返的心态有着不尽相同的文本呈现。与作于屈原自疏去郢时期的《离骚》等篇目相比,《哀郢》对个人仕进的追求、渴望国君重用的心态明显弱化。在接受上官大夫的谗言之后,楚怀王“怒而疏屈平”[4],这种情况下屈原由于“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5],不满于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自己、不接受联齐抗秦的谏议,因而选择“远逝以自疏”,王逸将屈原这种因谏不从主动疏远君主的行为及心理动因概括为“贤愚异心,何可合同,知君与己殊志,故将远去自疏,而流遁于世也”[6],指明作为《离骚》创作背景的流放在外是屈原因与国君政见不合、不被信任而作出的主动行为选择。
在使得屈原作出上述选择的心境支配下,屈原在《离骚》中对于希冀回返国都这一心态的表达,与渴望国君再度重用自己、采纳联齐抗秦的建议、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等个人仕进层面的追求关系更加密切。虽然联齐抗秦这一主张的出发点是对楚国现实政治需要的考虑,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但从文本对比结果来看,相较于《哀郢》,作于自疏去君时期的《离骚》等篇目对于个人仕进追去的表达的确更加显著。《离骚》的行文逻辑以与女媭、舜帝交流政治见解与遭遇,向昆仑之神求助却受阻帝阍、周流求女却终于无果,情灵氛占卜、向巫咸询问建议作为艺术想象与情感抒发的三个环节,陈词围绕个人仕途中的主张与际遇展开,与神明沟通象征与国君沟通,是否远逝的抉择在当时的礼制背景下几乎等同于国君是否再度重用自己——据《礼记》记载,“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7],两周时期大夫三谏而国君不从,则自疏待命于郊,这种做法被称为“以道去君”[8],如《谷梁传》中记载:“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9],认为赵盾因与君王政见不合且入谏不被采纳,出奔去君到郊外驻守,以求等待君命;再如柳下惠所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10],也是对这项礼制的反映。这一礼制的另一项内容是如果国君在三个月的限期内悔悟,决定听取该臣子的谏言,可以“赐之环则还”[11],以玉环作为信物召还自放于郊的臣子。
反观《哀郢》对于希冀回返这一心态的表达,极少流露渴望再度被国君信任而受到重视这种内涵,即不再将个人仕进追求作为希冀回返的目的,个人仕进追求在文本中的表达被弱化了。此篇第一处抒发希冀回返的心态是“哀见君而不再得”,此处作者主要是在回顾沿循长江、夏水一路漂泊流亡的经历;第二处抒发希冀回返的心态是“何须臾而忘反”,此处作者主要表达对终古所居之故乡的思念;第三处抒发希冀回返的心态是“至今九年而不复”,此處作者在为谴责“荏弱而难持”的令尹子兰妨碍国事蓄势——全篇消解了《离骚》中借助香草美人的比况与浪漫奇谲的幻想来表达遭受奸佞离间而仕途困顿的愤激。由《哀郢》文本的上述情感逻辑可见,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层面,强调的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与对父母之邦的眷恋,不再像《离骚》那样,以谏言不从而自疏去君、期待再度被国君任用作为“冀壹反”心态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强调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父母之邦的眷恋
分析《哀郢》与《离骚》在希冀回返这一心态背后精神实质的差异,首先应该对《哀郢》的创作背景进行讨论。王夫之认为《哀郢》作于秦将白起破郢的背景下,“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12],即将“哀郢”理解为屈原在郢都被破后的悲哀心境,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哀郢》“冀壹反”却不可得的原因是郢都被占领而无法回返。但是,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史记·楚世家》记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13];《资治通鉴》也记载,白起破郢发生在“周赧王三十七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拔郢都、烧夷陵之后,“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14]。而屈原于顷襄王三年(前296年)自沉汨罗,《哀郢》不可能是白起破郢之后所作。实际上,《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年(前297年),此年楚怀王逃归为秦追获,再度被困秦国。并且,屈原已于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被放逐于鄂渚,距离写作《哀郢》已经有近九年的时间[15]。
此次放逐与楚怀王十六年时屈原“自疏去君”的性质已经不同,孔颖达曾在对 《诗经》的疏解文本中辨析两周时期“放”臣的区别:“是放者,有罪当刑,而不忍刑之,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者,彼虽无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16]楚怀王十六年时屈原进谏不入遂“远逝以自疏”应当属于后者,而楚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放逐于鄂渚、九年不得复还则应属于因罪被放。根据两周时期的礼制,三谏之后国君“不用其言”而“自去”的臣子待放于郊,此时“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17],若国君三年内未召还这类臣子,或是“赐之玦则往”[18],那么臣子此时可以逾境去国。此外,如前所述,大臣三谏未从自放于郊三月等待君主召还是此项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放的原因是三谏而君主不从,再度被召还的情况往往是君主悔悟、采纳其谏言,因此,自放的情况下希冀回返往往与个人得到君主重用的仕进追求密切相关,《离骚》中希冀回返的心态与个人仕进追求的表达密不可分这一现象可以视作明证。而《哀郢》的创作背景决定了,发出“冀壹反之何时”的感叹不再属于上述礼制范畴。从这一视角可以解释,在屈原此时希冀回返的诸多目的中,再次得到君主重用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父母之邦的眷恋是更加紧迫、更具支配性的心理因素,也成为了“冀壹反之何时”之叹的精神实质。
从《哀郢》作品文本来看,屈原对希冀回返这一心态的抒发总是与担忧国家命运、眷恋终古所居的父母之邦相联系。此篇以哀叹百姓在战乱中离散相失起首,这种哀叹始终笼罩着第一个抒情单元回顾九年流放经历的过程中,“哀见君而不再得”的感叹由此发出。屈原将国都郢称为“终古之所居”“故都”,表示自己漂泊的灵魂不曾有一刻停止向往回返。在交代了“至今九年而不复”的遭遇之后,屈原集中批判“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的子兰,指责怀王听信少子的主张“入秦不反”被困于秦、危及国家命运。
参考《史记·楚世家》可以发现,自楚怀王十七年以来,秦多次大败楚军,攻破楚国数城,齐、韩、魏等国与秦国结盟使得楚国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楚怀王逃归被抓获复囚于秦[19]——屈原写作《哀郢》时楚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中。屈原作为出身于楚国宗室的贵族,在楚国国运飘摇、自身被国君放逐九年未召还的条件下,本来可以选择到他国另谋出路,“一言投合,俯仰卿相,士之欲急功名者,舍是莫是归者”[20]。且先秦时期臣子不被君主召还而去国是比较普遍的行为选择,《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21],孟子认为大夫三月未被君主召还则有权载质出境去其他国家;《毛传》将《诗经·卫风·考槃》视为卫庄公时期的去君之辞,抒写贤者不用于君的情况下“不复入君之朝”[22]的誓言,被概括为“长自誓以不忘君之恶”[23];《郑风·遵大路》中去国者直接申明“无我恶兮”“无我魗兮”[24],表示并非自己弃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屈原始终抱持着希冀回返的心态,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其忠君爱国思想的有力彰显。
三.两汉九体拟骚作品对“冀壹反”心态的传承与重构
两汉九体拟骚作家也多次在作品文本中表达对于返回国君身边的渴望,这可以视作对屈原所作的楚辞作品中希冀回返心态的传承。具体来说,两汉九体拟骚作品对希冀回返心态的传承往往表现为渴望国君意识到应该采纳自己的谏言。
以东方朔《七谏》[25]为例,作者借助屈原事迹抒发己意,在《初放》中“言我将方舟随江而浮,冀幸怀王开其曚惑之心而还己也”[26];在《沉江》中慨叹“安眇眇无所归薄”,“言己放流,不得内竭忠诚,外尽形体”,认为自己流放在外是无所归附的状态;在《怨世》中讲述自己在“贤者避而不见”的情况下打算“壹往而径逝”,王逸注指出此处“言己思壹见君,尽忠言而遂径去”;《怨思》“冀一见而复归”处王逸注:“言己自怜身老,不足以终志意。幸复一见君,陈忠言”;《哀命》“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词”,王逸注指明此处“思一见君而陈忠言也”,且《楚辞章句补》载糜信一位此言是“朔自为”。再度面见君主以陈忠言构成贯穿此篇骚体赋希冀回返心态的精神实质。
另一方面,两汉九体拟骚作品借助对屈原希冀回返这一心态的重构,展示了两汉政治生态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大部分作品中希冀回返心态的精神实质更多偏重于期待被国君重视,属于个人进退、仕隐之抉择的范畴。具体表现为将远逝作为一种姿态而非最终结果。以严忌《哀时命》为例,全篇抒写“不知进退之宜当”[27]这一出仕与入仕之间的矛盾,在欲进无门的情况下却不甘于退遁,这种内心挣扎是其希冀回返心态真实目的的生动注解。并且,两汉九体拟骚作品常将避世隐居作为希冀回返而不得的退路,如东方朔《七谏》中“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王逸注指明此处“言己怀忠信之计,不得列见,独处岩穴之中”。此外,部分九体拟骚作品鼓励士大夫相信國君,不要轻易选择远逝,这可以视作在希冀返回而不得的情况下对士大夫仕隐选择的反省和思考,王褒《九怀》在《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等部分接连抒发希冀回返心态下的怅然若失、心怀遗憾,最终“圣舜摄兮昭尧绪,孰能若兮愿为辅”[28]一句直接表明作者认为“竭忠信,备股肱”[29]是人臣抱持的正确心态,这对于前文希冀回返的心态是一种同义回应。
两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生态下个人进退、仕隐的选择被更多地思考,仕途中“遇”与“不遇”的主题在汉赋、古诗中多有体现。汉代九体拟骚作品中对屈原希冀回返的心态进行重构,一定程度上是对两汉政治环境和士大夫心态的如实反映。尽管如此,这种精神实质的差距依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汉代九体拟骚作品“骚义弱而赋义强”[30],也彰显了屈原作品忠君爱国精神的纯粹与彻底。
正如王逸对屈原的评价:“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在《哀郢》一文中,屈原不仅是“去君”,而且越境“去国”了,这就是他在《哀郢》中发出“冀壹反之何时”之叹的历史语境——在当时的礼制背景下,屈原不是在城外等候君主召见,二是因被判定有罪而流放于国境之外。按照周代礼制,因政见不合或进谏不听而选择自疏去君的臣子必须在三个月之内等候国君的召见,但是因获罪而被放逐的臣子不属于这一礼制范畴,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的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哀郢》“冀壹反之何时”之叹精神实质的独特性得到了充分彰显——相对于《离骚》等写于“去君待召”时期的其他篇章,“冀壹反之何时”在希冀回返的目的和主导动机层面,由受君重托的仕途追求转变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父母之邦的眷恋之情。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两汉“九体”拟骚作品继承并重构了屈原希冀回返的心理,虽然这些作品章法、辞采更为精巧繁美,但其回返的目的和主导动机更多地体现在希望得到君主的信赖和任用上,这是一种个人进退、仕隐方面的抉择。两者精神实质上的差距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屈原忠君爱国之情的纯粹与彻底。
注 释
[1](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5页。
[2](战国)屈原著,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華书局1996年版,第485页。后文所引《哀郢》原文皆据此本,不再另注。
[3](战国)屈原著,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后文所引《离骚》原文皆据此本,不再另注。
[4](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1页。
[5](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2页。
[6](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卷第一》,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2页。
[7](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7页。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六礼记正义·卷第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33页。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九.春秋谷梁传注疏·卷第十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236页。
[10]陈晓芬、徐儒宗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0页。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2页。
[12](明)王夫之著,杨坚总修订:《楚辞通释·卷四》,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3页。
[13](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四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5页。
[1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第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6页。
[15]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七.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49页。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六.礼记正义·卷第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22页。
[1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2页。
[19]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20]游国恩著,游宝谅编:《离骚纂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77页。
[2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十三.孟子注疏·卷第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95页。
[2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78页。
[2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78页。
[2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9页。
[25]东方朔《七谏》虽名为“七”,实为九体的格局。详见曹胜高《屈原“远逝以自疏”的历史语境及其文本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26](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卷第十三》,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35页。
[27](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卷第十四》,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62页。
[28](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卷第十五》,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67页。
[29](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卷第十五》,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67页。
[30]曹胜高:《屈原“远逝以自疏”的历史语境及其文本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