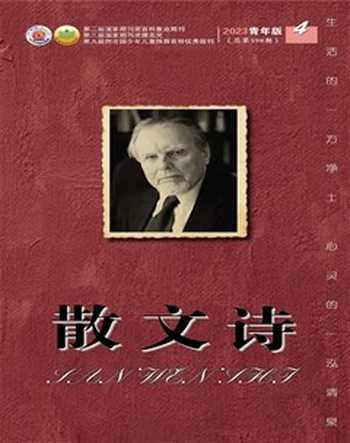故乡的仪式
马健
题记:离开,从多年的旧路一直北上,目光所及之处,山乡隐现。在时光的暖流下,轻触梦中的门扉,村庄的颜色,水一样波荡而来,如果可以,我要重回乡间的那块崖壁,哼唱一支故乡的歌谣。这轻扬的曲调是我和故乡和解的仪式。
阳光下的身影
一椽旧宅,让我的记忆有了分流。小时候,总爱拨开墙角的野菊花,或是骑到那棵年老的枣树上,对它发号施令。午后,太阳暖暖地扑向我的脸颊,从阴雨的日子告别了厚重的云朵。母亲的声音总是回荡在耳畔,孤身时,微风会替我重播母亲的话语。梦中,我常常遇见半抹身影,像风那般模糊,却有着最熟悉的味道。如果不是阳光阻挡了我的视线,我想,我会看清她的模样。
那时,母亲喜欢在阳光下盘坐,无论是做手工,还是做杂务,她总爱面朝阳光,安静地感受每一分温热,这似乎是她的力量之源。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患有风湿,向往太阳会让她拥有更多笑容。想想,这是令我后悔的诸事之一,过去,我没能陪她好好晒几次太阳,如今,我只能在记忆中填补这份缺憾。
日子大多如流水一般顺滑,某个时刻,我清晰地认出了那个影子,像梦中轻抚我的母亲,我曾告诉父亲这个梦,他微微一笑,然后转身走向温暖的田野。
即便如此,无论过往还是将来,母亲,都会拥有天空一样的颜色。
父亲的信
长大后,我远离了故乡,像一位负罪之人,不断闪躲着记忆的闸门。我与父亲的联系都集于遥远的村落,一次偶然,父亲却打破了这长久的桎梏。
某一天,伴着夜灯升起,我从深绿色的邮筒中找到了一封褶皱的信笺。二十多年的岁月,竟是父亲先给我写了一封信。
回家后,我将信封平整地铺在桌面,谨慎地剪开一角,缓缓抽出那张些许发黄的信纸,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写成这样一封信的,于他,这是比整理庄稼更为艰难的事情。过去,他只是习惯用沉重的工具整理田野,我无法想象,初中没有毕业的父亲,会用他那粗大的手掌,写下如此工整的文字!
微暗的台灯照亮我的目光,这些笔迹,饱含了父亲久久的思绪。他大概写了许久,像对待庄稼一样严谨,从他那生涩的言语中,我渐渐明白,这是一个父亲想同儿子进行一场该有的交谈。
父亲的信,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我的冷漠,在那一刻彻底崩塌。
深夜,我手中紧握着父亲的叮嘱,感到仿佛有千万钧的重量袭来,而我则变成了一根羽毛,还未找到回家的方向,便向四周飘动着。当我再次听到熟悉的歌声,自然会寻到去往故乡的路。
群山物语
我喜欢沿着乡间小道,一路打马,拥抱群山,倾听它们千百年来的回声。我的故乡位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河的山谷,青山和秀水孕育了这座隐秘的村庄,庄北的一条柏油路,一头连着外面的天地,一头伸向群山的腹地。
年少时,我喜于和群山交谈。闲暇时,我与朋友们总爱攀登到南山顶,围坐在岩壁之上,聆听来自天空、大地的言语。日子久了,隔着山谷和黄昏,自有空灵的回响来回交织。我们偶尔会被远处的红云吸引,思绪任由晚风吹拂,兴许,几声鸟鸣会将我们的思绪收回。群山之外,有雨水反复试探这片无物之地,年少的日子,让我学会了放牧自我的孤寂,在山水间端坐,叙述隐秘的过往和琐事。
有人说群山是通往天空的梯道,我却从未注意。
当秋日的田野被庄稼染成金黄,农民们将庄稼收割回家,庆祝的日子便要来临了。家家忙于张罗庆典,备足了新衣裳、新用具,在南山顶上,他们欢庆着丰收的日子,像愉悦的黄莺放声歌唱。
瞬间,群山也会为庆祝献上礼赞,仿佛狂欢的歌谣。我想,那条梯道大概是通往春天的门户。
河边,一抹云霞
村前的小溪自高山的涧底生成,冲破层层岩石,为村庄绕上一条丝带,然后,缓缓向东延伸,涓涓长流,追逐着海的声音。
我的诸多回忆,都与这条溪水相连,它勾勒了我多彩的童年。沿着小溪,可以领略山川河谷的风貌,不必擔忧世事,这一刻,抛却不该有的愁苦,望着河边的风景,你可以安坐整晚。
除了帮父亲收拾庄稼,我们还会聚在溪边一起放牧,几个人围坐一团,将胖乎乎的牛羊拴在树干上,任它们原地划圈,只要不离那寸草地。天气回暖,连群山也会随之欣喜,换上嫩绿的装扮,要知道,万物皆会背负青春的风暴,迎接下一个季节。而我们,在人生的河底起起伏伏,习惯了生活的样子,顺流而下,或溯流而上,就如同和生活一道前行,彼此依附。
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会为我们重新划定眼前的日子。
如果可以选择一种生活的颜色,我希望是一抹云霞之红。
- 散文诗(青年版)的其它文章
- 青春书
- 人生如秀
- 十月(外三首)
- 我像往常一样和你对话
- 那些词语在悬崖上行走
- 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