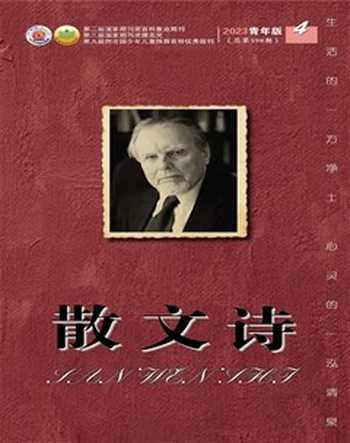人生如秀
左琦

左右互搏
夜晚的散步,有两个选择。
往左,走两公里,有一条河。这条河在白日里有众多拥趸:舞剑者、做操者、骑行者、冥想者。它只有在夜里,才会安静地拥抱自己,观赏自己随季节而变化的、丰腴或消瘦的身体。它只在夜里,才发出独有的声音,细细吟唱,未成曲调先有情。
它放慢脚步和我同行。它的一侧竖着几栋寂寞的樓宇,零星的光亮在单元楼里闪烁。地面横呈巨大的坑洼,像个天洞,核心处,卧着一台复工日期不详的挖机。
它的另一侧是老旧民房群像,它们在沿河景观道存在之前就已存在多年。那些玻璃上带着雾气的窗户里,昏黄的灯盏可亲。
没有路灯也不必慌,跟着河流走。星儿稀疏,月儿清瘦,权当这条河是从天际挪移来的,权当它是借由夜色来与我对谈的。它代表着这个城市温柔的部分,而我仿佛拿到了一张稳妥的居住证。
往右,走两公里,是商业街。熙攘的夜市里,小吃,古风,展览,花灯,民俗……让城市活力四射。月影交错,炫彩夺目。湖中架桥,水雾缭绕,荷花灯时隐时现,缥缈如幻境。水光月影与灯火夜肆交汇映衬,桥上游人如织,桥下水幕成画,让夜风情万种。
声影和色彩冲撞,地面的烟火和天空的焰火呼应,青砖黛瓦与霓虹流岚交融。人潮涌动的街道,像蠕动的河。
我体内的两个人在左右互搏,平淡,还是纤秾?静寂,抑或喧嚣?
单看一轮醉月。
打电话约两个词见面
很久没写一个句子,没打一个逗号,没遇到一个命中注定的词。
这苦恼,就像面对一片灯塔耸立的大海,买不到一张船票。或者,日子过得静水无澜,无计消散。
又或者,看谁的面孔,都是一种恍惚。
一沓纸被揉成不规则的圆,又勉为其难地撑开四角,最后被撕弃。
一些涩味事件不断僭越,让燃烧的灵感痉挛,像树叶被狂风熔冶。
我总相信,会有这样的词,最合适这世间的万有、万象、万物,它们匹配天然,它们的“出处”恰是为了它们的“来路”,随俗从流不是它们的使命。
这愉逸,就像原则遇上心动的破例。或者孤峰另起,绝响自成。
又或者,隐匿的美得到了最敞亮地释放。
于是,我在一片婆娑树影下,一丛摇曳花枝间,打了一个电话。
我想约见两个词:
一个是“憧憧”:
一个是“幢幢”。
攒了很多勇气说别离
我的确难驾驭,也实在很挑剔,直到我遇见你。
直到你被通知要调离,我才禁不住,眼睛里下起滂沱大雨。
起初,我稚拙又冒失,敏感又纤细。你懂我未及开口的言语,也明白我茫然无措时的所需。
你盼着我能长大,张开翅膀飞,在失去庇护的时候不惧风雨。
你又情愿我永远长不大,永远不会飞,让你有机会在疾风骤雨的时候,给我守护和倚傍,让我安全无虞。
我猜透你的矛盾与纠结,明了你的良苦用心和殚精竭虑。我无知天真而糊涂忙乱,在你这里,都是略博一笑的小小闹剧。
最终,你还是选择把我放进海里,尽管我会邂逅食人鱼和暗礁,尽管风浪会将黑夜和寒冷叫来,一同恫吓我的心灵。但你知道,我还会遇见更多人,他们勇敢而坚定,他们见过真正的波澜壮阔,也清楚什么是风高浪急。这些不断经受磨砺,又心怀愿景的狂傲之人、偏狭之人、才情斐然之人、不可低估之人,不同于谦谦白面书生或木讷懵懂的少年,不同于处变不惊的船夫和人情练达的客商。他们会告诉我——
风起浪落,何足惧怕?
终于,我缓慢却持续,简单却有力。你教我走的路,有花开在微风里。
我攒了很多勇气,说——别——离。
借一个未痊愈的伤口醒着
依稀记得那个雨天的照相馆,我穿一件白格子外套,头发黑亮着,服帖在两耳旁,笑起来腼腆。
母亲站在我的右边,挽着我手臂。我知道,这许多年飞向天空的途中,有她的目送在风中。
站在我左边的男人,三七开的小分头,眼睛聚光,肩膀硬挺。他的手插在裤兜里。
我没有牵住,这双注定要放开的手。
这张泛黄的合影,渐渐生长裂纹,它们在几张脸孔上延伸,分叉。它们去路崎岖,模样莫测。破冰的河床、受创的玻璃、皲裂的掌心、干枯的滩涂、错乱的枝丫……天底下的事物,大体上长得都相像,像一根根细针尖利地刺穿心脏。
人,像在泪花里洇散,剧痛在夤夜里漫漶。生活仿佛石头滚落的山坡,命运扼住咽喉的那刻,我喊出一声失音的一
“别这样!”
伤口未痊愈,我必须借它醒着。
多少次我想回到妈妈肚子里
叶子长出来。叶子绿了,叶子黄了,叶子掉下来。
好羡慕它,可以回到大地妈妈肚子里。
阴冷的雨天,剧痛的小腹,让我想到每日被秃鹫啄食心脏的普罗米修斯。我想回到妈妈肚子里。我蜷缩着,像还未出生一样。
子宫是最华美的宫殿。
我真的趴在了妈妈的肚子上,那是一个让人顿时心安的地方。像一片深海,只要靠近,就可以忘掉一切悲伤。我贴着耳朵听,仿佛有海螺身体里激荡的呼啸之音。
妈妈用粗粝的手抚摸我光滑的头发,那些手上的沟坎刮得我的头发硬生生疼。可是,这种疼却抚平了我心中更剧烈的创痛。
头发长出来,头发长了。
头发像枯草,发丝掉下来。
什么都可以循环往复,唯独我想回到妈妈肚子里的愿望,是单程列车,它驶向未知,徒留一个回身挥手的方向。
一些旧气息挥之不去
我又来到这里,我是跑着来的,有些气喘。
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气息,五斗柜的木质气息,衣柜里樟脑丸的气息,玻璃框里泛黄照片的气息,它们融进寂静如水的日子里,融进挂钟清晰的嘀嗒声里,在我睡眠的耳畔环绕。
卧室的铁皮桶里放着糖果饼干油炸货,那混合的气息告诉我,已都不新鲜了,放久了,可主人仍舍不得吃。堆放得有些闷闷的气息,别人家闻不到。
开坛了,霉豆腐、腊八豆、酸豆角,流涎水的气息。
起锅了,酿豆腐、鲜粽子、煎糍粑,常怀想的气息。
外婆银白的发在阳光里晃眼,外公缺着牙齿憨憨地笑着咳喘。他们不是去世多年了吗?这间屋子不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吗?
我在四面废墟的旷野里回望。我固执地在意识里辟出一间屋子,这里有堆叠整齐的床单被罩、洗得发白的衬衣汗衫、不忍丢弃的锈钉子烂瓦片废木料……这些气息是老者投给我的,遥远的目光,像古老、破损,但又温馨无比的秋千一样,来回摆荡。
和一棵银杏树等高
从三楼的办公室向外望,刚好可以看到银杏树最顶端的那片叶子。它的金黄,与乒乓球台的湛蓝、跑道的艳红和操场的碧绿,点缀了冬的萧瑟。
小炉煮满一壶陈皮、红枣、干姜,久久沸响。我任性地多看了几秒天空。
堆叠的文案暂且搁置,奢侈的冥想黏了上来。
我看见鱼飞上轻柔云朵,尾尖的水滴洒下珠帘;我听见风擦亮阴霾,跃金的时光瞬间永恒;我嗅到花开在沙漠,哀愁停止,雨似瓢泼。我等着困意席卷,能够舒展四肢,沉沉入梦。
幻想横冲直撞,记忆横穿胸腔。
等等——银杏树最顶端的那片叶子正在挣脱它的枝丫。我打开窗户,张开手掌。
与我等高的树,让风护送了一片置顶的叶,小兔儿似的欢蹦到我掌心。
它,黄得鲜亮。
- 散文诗(青年版)的其它文章
- 故乡的仪式
- 青春书
- 十月(外三首)
- 我像往常一样和你对话
- 那些词语在悬崖上行走
- 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