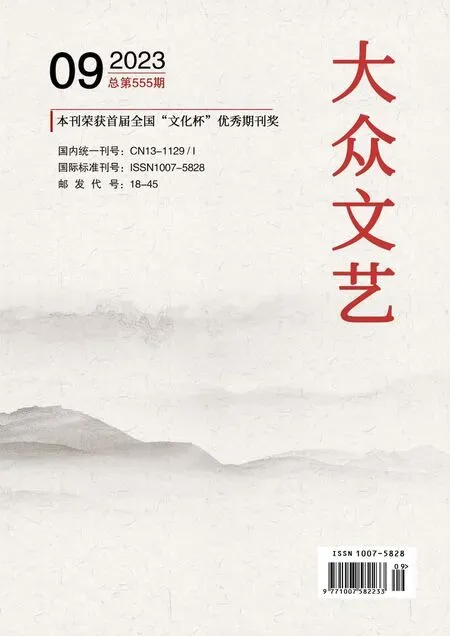人民话语、影像交融、家国情怀
——谈《长津湖之水门桥》对早期历史叙事的承革
付雅璇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我国的历史题材电影总是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将对现实的关切也融入其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追求,无论是为了描绘历史传奇,还是借历史寓言现实,抑或回望历史经验、提炼民族精神,这些影片大多以对民生本真的关怀展开叙事,以对情感本位的贴合感染大众,因而也逐渐在社会主义的电影产业中跃居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走过历史叙事归属意识形态的单一路径,近年来,从《八佰》《金刚川》再到《长津湖》等,我国的历史影像实现了英雄人物的延展,更注重通过多元塑造凸显家国情义,而《长津湖之水门桥》更是在这种转向中持续探索,赋予了作品更具震撼的呈现,使观众得以在感动中感悟,在感悟的过程里更自然地找寻到个人情愫与集体意识的交汇,使历史叙事在承革中实现内涵与文化的转型,乃至民族电影风味的建设。
一、社会本位:叙事创作的现实来源
以历史事迹为叙事对象的影片相较架空客观现实的“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等纯商业类型总是能够以与集体意识的呼应而产生更强的市场吸引力,因此这些历史电影的不可取代性即正在于其中所蕴“社会性”因素由客观而思索的深入。
(一)早期历史电影的社会依托
我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便与社会现实有所关联,而从《定军山》至后来的《木兰从军》等早期历史题材影片的故事选择和内在品格亦都隐含有与实事的贴合: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定军山》(1905年)的表现题材亦有意无意地透出一种“反抗”,而“‘华成’出品的《木兰从军》(1939年)从古装戏中挖掘历史与现实联结的元素,制造出情感张力”[1]同样也是以历史为文本并与彼时社会状况有所对照的影像呈现……
艺术始终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在历史影片中赋予“社会性”的内涵无疑正是通过现实的感染力填补了观众的心理需求,进而成功建立起超脱娱乐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由此,以史为鉴,早期电影中的历史叙事是归于“影以载道”的社会意识而实现的,而《长津湖之水门桥》等当代历史题材在电影市场中的立足亦离不开其与时事、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主流精神的互动。
(二)《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群像延展
“早期历史电影因为大多取材于以英雄造时势为史观的历史文学,往往强调英雄人物扭转乾坤和改变大局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很多影片都没有书写英雄背后的人民群像,表现群众的集体力量对世局世事所发挥的作用”[2],而在当下我国立足人本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源发于“人”的影像内核拓宽了以人为本的视角,使历史叙事更注重对大众化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力求使影片内核与客观环境密切相接,在凝合“真实的典型”的过程中,影以载道地呈现出精神内涵,《长津湖之水门桥》即是如此。
这部影片以人物为主导,却又不局限个体,而是通过对群像的描摹凸显“典型的真实”,作为主要人物,伍千里勇猛锐利却也有对亲人、对战友的柔情、伍万里桀骜洒脱却也不失战场上的大局观念……他们身上有血有肉,并未缺失大众化的一面,而这种“人”的魅力更是使影片所蕴精神通过百态人物更为鲜明,实现了历史叙事在当代更广维的传播,甚至进一步推动民族精神在历史和现实的游走中螺旋上升。
(三)融意于形:消解现实与商业的对立
当下的历史叙事虽对早期历史电影中的“社会性”内涵延续颇多,但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场域中,历史表述的电影形态却也发生了变化,即历史内容与商业形式的融合方式有了更多元、更稳定的途径。其中,“明星”与“类型”作为好莱坞商业片的重要范式,在市场中既具辨识性,亦形成有较稳定的粉丝黏性,而这两种元素亦为当代历史叙事开创了新可能。
《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市场成功也正有赖于借明星加深影片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通过类型的嵌套令“典型”更具共鸣:一方面,明星为“主流”提供了“商业”的途径,该片作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的历史献礼片,原本因题材的严肃而相对小众,但依托吴京、易洋千玺等作为主人公的“明星”效应,广大的粉丝群体和多样的话题度却带来了更完善、系统的宣传体系,使影片成功脱离出曲高和寡的“口号式”的藩篱;另一方面,战争片的类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带来了更震撼的感官体验,平河舍身炸坦克时的爆裂无声、伍千里最后被烧成灰烬时的热烈与寂静,这些场面在特效的渲染中被赋予了更具还原性、更真实的呈现,即当下的历史影片借技术手段使电影的艺术潜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并由此满足了历史叙事对“真实”的需求,带领观众回到彼时社会的面面,拓宽了影像的表现力。
二、民族韵味:历史叙事的“意”与“境”
发端于绘画,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风格成就了我国艺术作品独有的“意境”美,且延续到电影中亦是如此。无论是电影初创时期上海影戏公司的唯美视效,还是费穆、孙瑜等第一批电影作者们意蕴深邃的浪漫抒怀,抑或第四代导演镜头下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中国电影工作者立足本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升华着中国电影的风貌,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亦不例外。
(一)景物同化:凝造历史空间的感官体验
作为我国电影奠基者的郑正秋曾提出“同化”的概念,他认为“一部戏有一部戏的空气……我和剧,剧和人,人和景,景和物,物和事,事和地,地和人,一齐同化,这样做来,自然有影有戏……当然容易动人情感了”[3],这其中所指涉的“空气”即是一种具有真实感、感染力的空间,它使观众沉浸于意境中,更切实的体验剧中的人、物、事,所以正如费穆所说,“电影要抓住观众,必须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4],而这种对“意境”的关注则正是我国电影的“民族性”特征之一,它不仅体现在早期电影中,且在当代电影实践中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从早期作品来看,电影自传入以来便与我国传统的绘画、戏曲相融汇,从试制阶段《定军山》中的戏曲意蕴、商业浪潮中《火烧红莲寺》对传统侠气的依托,到上海影戏等公司对传统画风的借鉴,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而至30年代,我国电影的表达亦持续有对“意境”的考量(如1940年《孔夫子》中所营造的儒学风貌),甚至还在与外来进步电影观(即蒙太奇等)的交融承革中,成就了更鲜明的美学特性。
《长津湖之水门桥》里多次呈现宏观场景,漫天白雪的困境、血肉残骸的战场、悠然宁静的梦中故乡,这些空镜头中的环境为观众带来了剧中人的悲喜,使影片的精神力更好传达,同时在营造历史场域的同时亦未剖离民族认同的根本。
(二)见微知著:《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细节意味
有承自“意境”所塑的“民族性”,当代历史影片依托电影观与技术的突破,有了更完善、动人的构塑。《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主题意在致敬为抗美援朝舍生取义的先烈,并进而传递大无畏的民族品格,因而大量震撼人心的战争景观不仅为历史的叙事铺垫了可视空间,且更是通过历史时空的还原,加深了影片的意味,使观众同情。同时,更细节化的呈现也使影片有了更浓郁的历史感,甚至起到了传递情绪的作用。
在《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寒冷的朝鲜、热烈的战场,“烟”多次出现,并且在特定的场景中作为具象符号,对历史电影的叙事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战斗结束后,当战部统计完伤亡,伍千里在雪地独自点燃了一根烟,从微观来看,这根烟无疑成功传递出了伍千里此时内心的悲哀和源起痛失诸多战友的无奈;而从宏观的历史维度看,这根烟更是将以伍千里为代表的抗美援朝英雄们内心无言的伤感予以了外化,当伍千里将烟头插进皑皑白雪,风吹动尘埃,便不自觉带动了观众的心一齐为英雄默哀。这种意象式的道具“同化”了剧里剧外的“空气”,通过中国传统的意境美赋予了历史影像意犹未尽却回味无穷的美感。
因此,早期历史影片中的“民族性”亦为当下提供了可鉴经验,而技术加持下更为细节化的写意升华更是于民族话语体系影响颇深,使当代历史叙事更具深意。
(三)作者话语:民族蕴意的个体抒怀
历史叙事的新风貌虽继承了早期历史电影的“民族性”,但随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表达自由,历史话语更多样的个性呈现亦不容忽视。
“作者性”源于法国《电影手册》对导演决定影片风格的理论探讨,电影导演籍存在主义源泉开拓了更自由的表达,更显个性的作品遂接连而出。在我国,自第六代导演而始的个性融入使我国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作者”标签,电影风格便随之有了发散于“民族性”的蕴意,这种变化同样也为历史电影提供了新思路。
析之,《长津湖之水门桥》对历史叙事的探索亦在作者表达上深入颇多。作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著名导演的联合创作,该片多视角呈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的英雄品格,在虚实融合的意蕴中,影片对历史意义的书写,既有陈凯歌般赋予哲思的隐忍,也有徐克般的侠骨铮铮与柔情并济,更不乏林超贤重细节、快节奏的视觉盛宴……几位导演围绕对英雄情怀的表达,书写出各具创意的历史场域,丰富了影像的震撼力,也大大降低了观众在长时间观影中的审美疲劳。
因此,电影作者的个体话语赋予了历史叙事更丰富的表达内涵,使历史故事在立足“民族性”影像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个体风格的趣味传达。
三、通俗脉络:历史叙事的潜在架构
家庭伦理模式是我国电影中极为普遍且重要的一种内在架构,它符合我国传统的家国观,亦适应于市民群体的心理认同,在大众接受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吸引作用,且随当下数字媒体的发展,其在新的影像呈现中亦不乏新的情感流露,在历史影片中亦源源接续。
(一)人情与世情:历史叙事中的世态百味
《孤儿救祖记》的票房奇迹使以家庭为核心的叙事模式跃居到国产电影制作的重要位置,藉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认同成就了凝合观众审美趣味的独特标签,使之后无论“鸳鸯蝴蝶”等商业之作还是“左翼”时期众多的呼唤觉醒之作都未曾脱离这一基础模式,且思想性的融入更是推动了家庭伦理模式的进程,有如在热映于1933年的《姊妹花》中,家庭伦理情节服务于进步思潮,以亲情感化富人,此种设定虽未完全摆脱旧思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社会现实;而后,“影戏”传统经蔡楚生的继承,又在艺术表达上有了突破创新,即如《渔光曲》以小猴之死的悲剧收尾既呈现了更鲜明的阶级对立,亦充斥着深刻的批判意义,极具震撼又发人深思。质朴的伦理之情增添了故事本身的温度,因此对于极具质感的历史叙事而言,将人情融入世情,更是无疑消解了历史的枯燥,丰富了影片的趣味性,并且更是作为一种商业元素发挥着在市场中的吸引力。从20、30年代的《木兰从军》《生死同心》,到“十七年”时期《林则徐》《宋景诗》等有关历史的叙事,这些历史电影均涉及对人伦琐事、家国真情的描摹,这也使得其中所要传达的家国情义与进步思想寻得了更深入人心的途径。与之相接,《长津湖之水门桥》亦呈现出对“通俗性”脉络的依托,而“普情化”的趋向则更是实现了当下历史叙事的情感扩容。
(二)《长津湖之水门桥》中通俗情感的“普情”扩容
感性与现实的统一,使得适应集体意识的情感元素得以承延民族话语的通俗谱系与当下历史叙事相呼应,进而对大众接受发挥了一定得完补作用。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亦铺垫有多条关于家庭关系的线索,在这其中,更为立体的人物和影像呈现不仅使“通俗”更为丰富,且亦通过塑造普通人的特殊事呈现出更现代化的“普情”,建立起强烈的共鸣。
《长津湖之水门桥》进一步实现了主人公“面貌”的下移,导演之一的徐克曾指出,“战争片的要点其实就是呈现每一个角色在战争中的生命过程,以及每一个角色在大的战争背景下的起点、落点和这一过程中人物情感、性格的丰富状态”[5],所以无论是生死攸关仍难忘妻子孩子的梅生、奔向祖国方向而舍生取义的余从戎,还是在“小义”中逐渐懂得“大义”的伍万里,这些英雄形象的“典型”都是立足在大众情感之上的,正是为家、为国、为义的普世情感才使得他们的光辉更具感染力,让观众产生同情,在真实中满足了观众自电影体味、领悟、批判现实生活的期待视野,进而使“国家机器”在运行中达成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统一。
(三)景真意切:数字时代的历史情动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带动了电影产业升级,如巴拉兹所言“电影是一种视觉文化”,除情节架设的“普情化”融入外,何以推动视听升级与情感的统一,亦为当下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辩证发展的重要课题。
数字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影像革新的必然,早期历史影片中的“通俗性”亦得获了新技术话语的呈现,就《长津湖之水门桥》来看,借助数字技术,该片不仅通过拓展“通俗性”的意涵而为历史的表达提供了更全面、直观的呈现方式,且更是籍数字媒体拓宽了“可视现实”的边界与历史现实的内蕴空间:
更直观的呈现“通俗”脉络,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可视现实”,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深层情感通过心理领域的外化为影片提供了更切实的渲染力。影片最后,伍千里和伍万里紧紧依偎在战后的雪地,此时战争的喧嚣无言在质朴的情深中,这种最朴素的情感将观众带入到历史的现实中,而当伍千里被敌方点燃成一把熊熊大火,既成的历史与无奈的现实在镜头与特效的交错中发生连接,于是,观众已不再仅作为着通俗关系的欣赏者,且更是经沉浸的感官交织而成了“普情”关系的参与者,在更真实的视角中续写了来自历史的情感召唤。
循此,数字之革赋予了历史叙事“魅力”的标签,但于后续发展,何以使“通俗”免于商业“异化”,则亦为书写历史的电影余留了思考空间。
总结
概言之,由对《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浅析,当下历史电影的叙事与早期电影呈现一定的接续,而早期影像所提供的创作经验、风格意味以及内在脉络等皆为当代提供了重要借鉴。但随时代变迁,我们在窥望历史经验的同时亦应以发展为基,使历史叙事的当代创作立足过往、凝视当下,在使创作依托社会根本的基础上不应回避对如何使影片更好实现与商业相接的思考,在延续意境风格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景物本身的更精确描摹,在根植传统脉络的前提下亦应更多思考情感关系的现代转化,从而尽可能呈现出既现代又民族的风貌,将我国历史叙事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获得更强的艺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