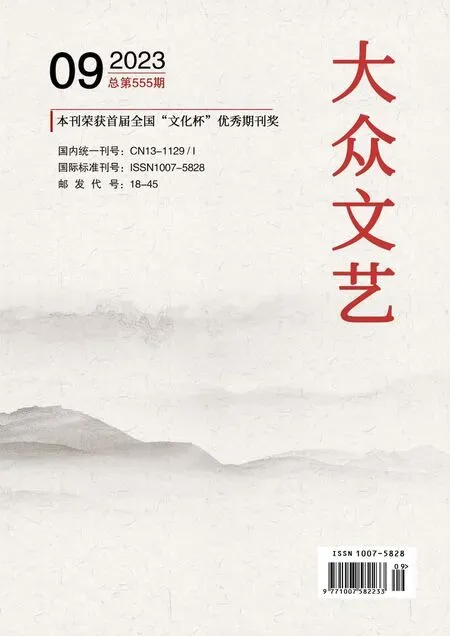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浊水漂流》:“可见”的“不可见”
吴丹娜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237016)
一、高楼与棚屋:都市图景、区隔与空间生产
《浊水漂流》是基于2012年香港深水埗食环署在“清场”时丢弃露宿者的物品,而后被露宿者诉诸法庭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电影所讲述的社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驱逐,主要讲述了刚出狱的辉哥在来到深水埗露宿的首夜,食环署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把露宿者的所有物品当作“垃圾”清理。露宿者们决心上诉,以求道歉。在这个过程中,辉哥和其他露宿者共同努力,在桥下搭建起了新的家园。但即使大家有了新的住处,还是找不到收入来源,无法改变生活。大家和谐地生存在这片区域中,辉哥结识了“失语”的木仔,也在相处中与木仔建立起良好的“非亲缘父子关系”。好景不长,木仔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木仔的离开让辉哥再一次面临离别。祸不单行,政府答应赔偿但拒不道歉,辉哥因此与其他露宿者产生分歧,当所有人离开后,辉哥孤独地在棚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将深水埗的“日常空间”做了具体的指射,正在建设中的城市是香港转型现代化的象征。影片的片名和香港的楼体以叠画的方式出现,隐含露宿者“浊水漂流”与香港城市空间的同构关系,底层露宿者的“浊水漂流”正是由于香港城市空间的压抑和现代城市化进程造成。利用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八大组合段理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影片多次出现环境、背景的描述性组合段,营造出高楼大厦带给人的压迫感,以及露宿者群体在城市中的无所适从和飘零感。[1]影片将镜头对准宏大主流叙事之外的公共区域,叙述底层边缘人面对现代化的困境,以一种真正注视的目光去观看这群底层边缘的群体是否能得到尊重和应有的尊严。
“人在外面世界的‘存有感’被削弱了,反而会感到‘各种私密感质地的张力更为强化’。”[2]这群难以被社会主流所认同的露宿者群体,只有退守至窄小的棚屋封闭空间中,才能体会到存在感和安全感。实际意义上,这些棚屋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庇护,新闻报道让棚屋成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实验基地,使他们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加斯东·巴舍拉曾提及,“家屋是心理状态的外在图解”[2]。以劝辉哥去医院为例,对切镜头的使用蕴含着某种权力关系,镜头先是以何姑娘的主观视角,从门外向棚屋内拍摄,观察屋内生病的辉哥。接着镜头反打,由棚屋内外构成的空间中以三角形构图容纳了五个人,画面中的空间被杂物挤得很满,只留下了一隅区域透着外面的世界,其中还有一半被高楼大厦所侵占。对角线构图将这群露宿者与这座城市“间离”,人物被囚禁在各种框线下,再加上昏暗光线的配合,呈现出人物内心边缘、极端的状态。
即使身处开阔环境中,人物面前也有各种遮挡物。以辉哥出狱为例,远景镜头中人物处在画面的中央,铁门、栅栏、监狱门等各种线条把辉哥框在画面中,斜线使画面带有不平衡感,可见步履蹒跚的辉哥成功重返社会渺茫的可能性。随着人物朝镜头方向走来,镜头缓慢向上升,人物渐渐被各种建筑物包围,画面紧凑而压抑。刚开始画面中还有一些由绿树、黄色路障、红绸填补的色彩,随着人物前进,画面中只留下灰色,可见高楼大厦带给人的压迫感。
这群露宿者群体与这座城市间存在着“抽离感”,他们从未被建构在社会体制之内。即使政府介入,也只是把他们视作“他者”。社会的意识形态针对所有个体进行招募,不在其中的这些“离轨者”就会被放逐,露宿者就是被遗弃的群体。空间上的高度差可以轻易地用于表现阶级群体的贫富差,展现人与城市之间难以调和的生存关系。
二、“父子”的悖论:俄狄浦斯情节的银幕投射
由老爷、辉哥和木仔形成的“非血缘”关系链条是影片的主要线索。其中,木仔的“父”有两个指射,辉哥和老爷都是作为“替父”出现,而影片着重串联辉哥与木仔之间的“非亲缘”关系链条。影片并没有展开叙述辉哥的故事,但通过他的几次“探望”,可以看出儿子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木仔生存在由母亲建构的单亲家庭中,一直处于“无父”状态,导致他本应该接受的“父之名”是一个空位,也正因为他没有被“父之名”所规训,他在社会中才存在着“失语”现象,只能用口琴传达自己的“心声”。经由辉哥的引导,两人之间形成了类似“父与子”的关系,影片的结构过程即“过渡俄狄浦斯”的过程。
在俄狄浦斯的第一个阶段,父亲还未真正地出现。木仔在单亲家庭中成长,没有父的出现,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辉哥注意到了孤身一人的木仔,将他带入到露宿者的大家庭中。通过伊恩看手相铺垫出木仔单亲家庭的身份,表明木仔之前的人生中充满“想象性的沮丧”,他的“父之名”是一个空位,他有血缘的原生家庭充满着危机。木仔对个体是无意识的,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当辉哥以“父之名”用儿子何慕林的谐音给木仔起名,帮助木仔完成了社会学层面上“自身的完整性”,却让木仔混淆了自我与他者。
俄狄浦斯的第二个阶段是“想象性父亲”的登场,即发现了父亲的存在。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系列镜像序列和个体的自我想象,“父之法”本身就是镜像序列的一部分,木仔参照别人的行为规范建构自己的想象,“父之法”成了木仔的判断标准。辉哥作为“他者”成为木仔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不断向木仔发出约束信号,告诉木仔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木仔将其内化为“自我”,根据辉哥发出的信号不断努力去确立主体性。
俄狄浦斯的第三个阶段是“实在的父亲”的出现,孩子发现父亲可以填补母亲的匮乏后,开始认同父亲,影片中由辉哥代替“父”的角色出现。当辉哥发现木仔的异常,替木仔询问性工作者时,辉哥也从符号化父亲转化到了经验性、身体性父亲,在他的帮助下,木仔带着他的口琴,完成了真正主体的形成。“菲勒斯”指男性生殖器所起的想象和象征的作用,也是拉康理论中“父亲”的象征,是社会和家庭中“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3]口琴其实是木仔“菲勒斯”的能指,也代表着他的内心空间。特写情欲表达中,莉莉用手抚摸木仔的口琴,这一刻“想象的菲勒斯”转变成为“实际的菲勒斯”。辉哥作为“禁止俄狄浦斯”的引路人,起到了“父的询唤”的作用,使木仔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去除对母体的依恋。实际的“菲勒斯”在实际的父亲那里,辉哥至此彻底成了木仔“实际意义上的父”。
当木仔带着辉哥来到城市上空,进行颠倒个体占有空间高低差的逃离时,木仔被警察抓住,回到了最原始的家庭中,这也是撕裂非血缘家庭的导火索。随着俄狄浦斯情节和阉割情节的顺利解决,使木仔可以正确的去延伸欲望和异性相处,因此他最终回归了母亲。此前木仔经过了误认,把原本属于他者的属性当成了自己,经历了象征界他者视角对他的凝视,通过镜中像完成了自我认同和外在要求的贴近过程。木仔的身份和身体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木仔的母亲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典型象征,当他从单一身份过渡多重身份的融入时,他开始撕裂了,他之前所谓的“认同”其实是一个失败的过程。[4]高楼大厦俯仰之间带来的距离感,使木仔回归到想象界的某种自我认同。木仔的母亲一句“清欣”,让他彻底与在高楼大厦下向上仰视他的“父”告别了。
木仔的疾病标志着那个时代所有的病症。木仔患的是“亲情病”,他的失语与亲情的丧失是同构关系,失语是对缺失父爱的隐喻,父爱的缺失在被主体压抑后得到复现。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的隐喻其实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5],当木仔的“大他者”空位被填补,他的失语也被治愈。
本片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但结尾却出现了超现实画面。辉哥的亲生儿子以木仔的镜像形象出现,他流畅的开口,将代表木仔身份的口琴摘下。镜头开始在辉哥和“木仔”之间正反打,两个人在连接时偶然的错位,却始终没有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两个人完全不分享任何的画面空间也就意味着他们将生死对决,他们不能分享任何同样的意义价值。”此刻连续的正反打镜头中“何慕林”与辉哥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意欲完成最终的“弑父”,代表着“父制”和“大他者权威”的辉哥在火焰中结束生命而成就结局。此刻木仔成了辉哥想象中儿子的形象,而这种镜像形象的出现,实则是一种想象性的“缺席”,情感的“在场”。这种和解并不存在于实际意义上,所以在视觉上以幻象存在。
影片其实是一个“建构”→“解构”→“再重构”家庭的过程,思考的核心是亲情是否关乎于血缘和非血缘。老爷用一支毒品让辉哥回归道友家族,露宿者群体为搭建共同的家园而合作,辉哥对木仔“父之名”的规训,都是在建构非血缘关系,试图表现底层绝望无助的小人物之间试图相互救助的状态。而无论是木仔“长大成人”后重新回归亲缘家庭,老爷死后大家的态度,还是露宿者群体的分崩离析,都是对非血缘关系的解构。在影片结尾处,辉哥日夜思念的儿子以木仔的幻象出现,这其实是辉哥心中对非血缘情感的认同。影片在认同中批判、在批判中认同非血缘关系,实则是在召唤一种理想型群体关系。
三、港片突围:现实、再现与困境
影片基于香港本土研究,存在“在地性”问题。香港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优质港片爆发式上映,经典影片种类数量繁多,囊括国内外各项大奖。但随着海外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崛起,“港片已死”成为近几年不断被诉说的命题。当大部分香港电影人选择北上延续传统港味电影时,年轻创作者们角度更加先锋,开始尝试新的出路。近几年的香港影人不断产出小成本之作,去“看见”与“发现”社会边缘的立场,触摸香港少为人知的一面,再现被遗忘的灰色地带,例如《一念无明》关注躁郁症,《翠丝》关注跨性别人群,这些优秀影片的出现都是让港片重新走上辉煌的“加速键”。
对于现代电影来说,电影荧幕就是一面“魔镜”,映照着人类的幻想。在中国的文化经验内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我们经常处于镜城状态,丧失了真实的空间和时间感。但在一幅幅镜像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结构,那个结构才是我们试图认知的社会,而那个结构也在不断地被摧毁、被形构。[6]当始终困于幻想的迷局时,打破它是唯一的路径。香港电影人选择“破镜而出”去讲述苦难,不断地经过反思,进而用纯粹的声音去讲述社会正义,作出难能可贵的社会表述。
香港电影荧幕正在从“魔镜”走向“碎窗”,通过荧幕将观众置身于他们期待的某种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有所差异的人群的遭遇。当今时代很多人不再相信苦难中的人仍然可能持有正义和道德,并不认同他们身份之下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资格,这才是我们社会疾病的表现形态。今天世界问题是固化、分化和差异,要求的最基本的尊重成了奢求。在苦难与贫穷之外的人们认为自己应该与他们相对立,让他们消失在我们视野中来作为一种保持自己安全与道德高度的方式。[6]
本片描述的是一种可见的“不可见”,是在当今世界应该被“看见”的群体。“贫穷和放逐真正对人类个体的摧残和打击是毁掉你的尊严”[6],当辉哥在街上脱掉裤子注射,镜头透过栏杆手持拍摄,间离感和窥视感充斥着画面。正如辉哥开头所说:“外面是更大的监狱”,辉哥并不在意身体上的裸露,真正在意的是他应得的尊重,而食环署拒绝道歉扼杀掉了辉哥最后的希望。影片以“辉哥的燃烧”结尾,镜头以近似固定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分钟,远处穿行的车流没有一辆为他停留,火焰燃烧的声音不断地加大。突然,画面黑幕,声音戛然而止,画面的余韵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感。辉哥告别一切后孤独地死去,也将露宿者的命运定格在大远景镜头中,展现出个体生命下的孤独与空虚。冷漠、无法沟通、情感的疏离是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周围人漠视的态度是因为在社会学意义上辉哥是不被看见的人,是与主流世界割裂的个体,透露出底层边缘人在宏大社会进程下的无力感。
《浊水漂流》展现出香港繁华经济,人人心向往之的背后遮挡了何种苦难。[7]导演李骏硕并不是站在高处去俯瞰弱势者并试图去救赎他们,而是用平等、朴素的镜头语言去坚持社会的正义,让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成为可能,使得这种在城市中流动的“新游牧民族”能够被观众“看见”,让艺术仍然成为一种有社会性的表达。影片试图抒写香港底层边缘人群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是现代都市中的游荡者,连最基本的生存状态都无法满足。但他们并不都是善良的、可怜的、摆在那里就值得同情的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陷,因而只能在滚滚前进的时代巨轮下被彻底抛弃。
经由《浊水漂流》进入到文化研究的脉络,其最终关注的是人的解放,我们应该经由影片做出某种“症候性阅读”,思考露宿者群体背后存在的问题。当文化研究进入到政治领域,开始关注阶级文化、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首先颠覆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现代国家的体制问题。在如今社会这些偏离世俗轨道的人,已然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多余人”,他们在不断地发声,但也一直在被消音。文化研究把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当成研究的对象,以一种不卖惨、不悲情、也不自怜的态度,去“发现”历史文化的书写和生产还未关注到的底层民众,寻找和发掘人民的声音,去掉“被遮蔽”,再一次“看见”。
结语:仓促时代的浮世绘
“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木仔的“结巴”是底层人被历史压抑的隐喻表现。影片在叙事之下包裹香港历史,展现关于历史的情境所造成的某种隔阂,重叠着越南难民,关乎怀旧、想象的乡愁,体现着历史的沉重。从底层露宿者的真实经历反映香港历史,展现香港作为一个“飞地”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