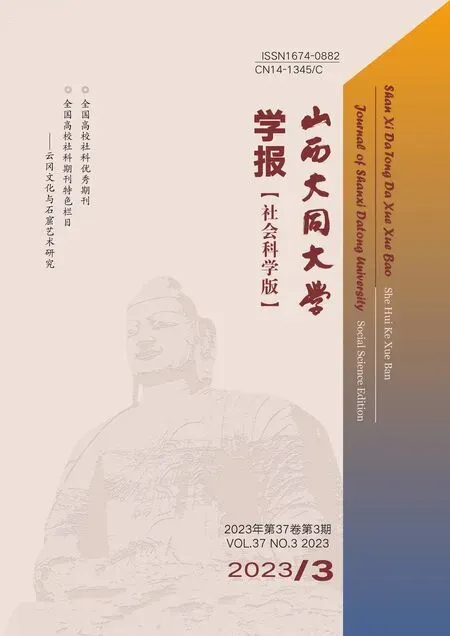论霍华德·雅各布森《J》中的遗忘、暴力与尊严
饶 雪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随着英国多元文化的建构以及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对英国犹太史的日益重视,英国犹太作家通过创作发出自己独特的关于当代英国犹太人的声音。露丝·吉尔伯特(Ruth Gilbert)认为,英国犹太文学的创作在近些年来获得了新的可见性、势头和自信,犹太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考虑“21 世纪既是英国人又是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表达出当代英国犹太人的声音和态度,一反以往英国犹太作家的沉默和道歉态度。[1](P394-406)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凭借书写当代英国犹太人问题的小说《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获得布克奖,这既肯定了雅各布森的创作成就,也体现了英国文化主体对当下英国犹太族裔的重视。布莱恩·切耶特(Bryan Cheyette)将雅各布森与其他英国犹太作家进行对比,认为雅各布森作为一位激进的男性作家勇于直面棘手的“英国性”问题。[2](P97)雅各布森是当代英国犹太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其创作的小说《J》于2014 年再次进入布克奖决选名单。学者大多从空间、精神分析、创伤、异托邦书写等角度来探讨大屠杀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犹太身份与空间的关系等问题,但鲜少有学者从遗忘的有效性及犹太人的尊严这一点来探讨《J》。笔者拟从大屠杀视角进行解读,透过主人公爱琳和凯文在集体遗忘的社会处境中被反犹主义者利用的悲惨遭遇,结合当代英国反犹主义现状,深入探讨当代英国犹太人的生存境遇,对犹太人的尊严及犹太人存在的意义作深入的分析。
一、集体遗忘与个体记忆:无法抹除的印记
德国著名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纳粹大屠杀中加害者、牺牲者、见证者的记忆与遗忘问题的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之后,面对纳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在战后的第一个十五年里,以色列和西德都采取沉默的态度,以封锁创伤性的过去重建一个新的国家。然而随着1960年代对艾希曼的审判,以及1970 年代《大屠杀》等电视系列片的制作,这种沉默的状态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大屠杀。到1980 年代,一方面由于加害者对大屠杀的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由于见证者的逝世,大屠杀渐渐被遗忘。因此,保持沉默越来越遭到否定性评价,在牺牲者一边于是出现了见证者文学,而在西德也出现了所谓的父亲文学。在大约五十年的潜伏期之后,社会政治空气发生了根本改变,记住大屠杀的戒律具有了准宗教的色彩。[3](P180)在这样一种强调大屠杀记忆的国际政治氛围下,英国对大屠杀的沉默态度越来越遭受到英国犹太人的质疑。英国历史学家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认为,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英国缺乏重要的公众认可,这与欧洲大陆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P703)英国长期对大屠杀历史缺乏重视以及进入21 世纪以来英国反犹主义事件的不断发生,是雅各布森创作小说《J》的现实出发点。
雅各布森在小说《J》中虚构了一场类似纳粹大屠杀的屠杀事件,以该事件为背景,故事时间设定在大屠杀幸存者第三代后裔生活的年代,地点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村庄——鲁本港。《J》讲述的是一个构想的反乌托邦世界的故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鲁本港正是作者基于在康沃尔郡居住时的所见所闻构想出来的。虽然雅各布森声称自己无意描述某个真实的地方,鲁本港都是脑中想象出来的,但他同时表示所有地方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常年被谣言、怀疑和盲目的恐惧撕扯着。[5]《J》中的当局采取了类似于现实中西欧国家战后对纳粹大屠杀采取的遗忘态度。阿斯曼认为:“在政治舞台上,遗忘有一种作用不只在心理机制基础上发挥,而且在有意识策略和指令的基础上发挥”,她把这后一种遗忘称为“指令性遗忘”,并划分为“除名毁忆”和“特赦”两种形式,其中除名毁忆是通过抹去名字而实施的一种迫害形式,抹去一个人的存在痕迹,或者把他从历史书写、社会记忆中清除。[3](P181)在《J》中当局采取了类似于除名毁忆的“以实玛利行动”即改名行动,但不同于抹去犹太人的名字,当局为所有人重新起了一个犹太姓名,以达到在相似性中对差异性的遗忘。在当局看来,这样的行动是一种有效地对受害者的赎罪,然而本质上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再屠杀。
小说的主人公爱琳和凯文,是具有犹太血统的犹太后裔,祖辈或曾祖辈曾遭受过大屠杀的迫害,父母亲是大屠杀幸存者或牺牲者的后裔,在当局集体遗忘的指令下,爱琳和凯文生活在表面平静无差异的鲁本港。虽然爱琳与凯文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但对大屠杀的恐惧却一直存在于他们的心中,他们都同时模糊感受到与“出事”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爱琳的心脏总是时不时地悸动,按照她原来居住地的说法,当你爱着的某个人死的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颤抖,而凯文则表现出强烈的被害妄想症,对外在世界充满怀疑与恐惧。“每天,在出门之前,凯文都要调高循环播放的闭路电视音量,沏茶——要努力装作漫不经心地将杯子搁在门廊桌子上——要反复检查两次,确定公用电话是通着的,灯在闪。而后,还要弄皱那块中式丝绸门毯——一件珍贵的传家宝——用他的鞋踩皱掉”。[6](P8-9)两人都在模糊的身世处境下表现出异于其他人的病态特征。
在这种因对自己家族的历史、身世以及外在世界感到模糊而产生的病态焦虑与恐慌之下,在一次涉及凯文的凶杀案之后,爱琳和凯文决定离开鲁本港躲避“亚哈的追踪”。但当他们离开之际,“亚哈”——古德金探长闯入了凯文那不对外人开放的家。但古德金并不是来追查有关凶杀案的证据,而是在搜查其他东西。到底古德金把他当成了什么这一问题迫使凯文思考他曾经害怕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他逼迫自己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如此忧虑?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强迫性地从信箱里窥探?为什么要反复地检查门锁?”“为什么我永远这么患得患失?我究竟以为自己做过些什么,如此迫切地需要弥补?我究竟害怕自己可能再度犯下什么错误?”[6](P227-228)在这一连串的疑问之下,凯文开始了对往事的追忆,记忆中最清晰的事情就是他与父亲之间的一个约定,就是每当碰到以字母“J”开头的词时,都要把两根手指放在双唇上。“J 是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无论是作者还是书中的人物从书的开头到结尾都没有说出口的一个词,但它却像一个雄辩的沉默一样在叙事中尖叫着”。[7](P1337)这个未说出的词就是Jew(犹太人)。凯文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恐慌与警告中度过的,而那时他还不知父母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怪异的行为,现在从种种歉意、忏悔、掩盖以及对过去的事件的回忆之中,凯文渐渐明晰掩盖的事实。
阿斯曼在探讨回忆和身份认同的联系时说:“回忆不仅位于历史和统治的中心,而且在建构个人和集体身份认同时都是秘密发挥作用的力量”,[8](P63)小说中的凯文和爱琳正是通过回忆,重新建构了他们的犹太身份。凯文在模糊的记忆中尝试明确自己的身份,爱琳则通过家族残存的信件重新建立起了与过去的联系。小说中遗存下来的关于爱琳家族的信件主要讲述了爱琳的外婆离开自己的犹太父母,嫁给一个基督徒,得知父母在“出事”中遇难后,外婆寻找父母,在途中也遭遇劫难,抛下女儿科伊拉,然后在多年之后科伊拉像她的母亲一样抛下自己的女儿爱琳的故事。通过信件,爱琳明确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不管她的父亲是不是犹太人,因为正如外婆对信奉基督教的丈夫弗雷德弗所说:“它(洗礼)改变不了我的内在,我的血源,我的出身”,“根据我们的法律,科伊拉还是家族的一员,而我身为我妈妈的女儿,也是一样”,[6](P328)因此,按照犹太人的法律,爱琳也是纯正的犹太人。在小说整体的消除关于犹太人的一切记忆的语境下,雅各布森让埃斯米保留了这一珍贵的信件,不仅为揭示爱琳的犹太身份留下了一丝线索,更讽刺了下文将要谈到的反犹主义者恢复敌对状态的计划。作为一个反犹主义者,埃斯米保留这些信件,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找对了实施计划的对象,作为爱琳的监护人她只是将爱琳当作实现自己计划的工具。
身份的确定,解释了爱琳和凯文病态的特征。就大屠杀造成的创伤,阿斯曼认为:“虽然我们否定第一代加害者创伤的说法,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在加害者和牺牲者的第二代中发现某些无可争议的相似性,并识别出类似的心理伤痕。父母在关键经验上的沉默触发了无意识的传递机制(经验向下一代传递),包括加害者和牺牲者的子女”。[3](P181)这种无意识的经验传递,在《J》中延续到了第三代,作为牺牲者的后裔,虽然爱琳和凯文生活在遗忘大屠杀的时代,但他们身上仍然体现出类似经历过迫害的心理伤痕。大屠杀给犹太幸存者后裔造成的创伤,是一种因身份而产生的疏离感、恐惧感、空虚感。“犹太人仍然活在大屠杀重演的恐惧中,这种恐惧使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使他们在感受到大屠杀的重演带来的残暴后果后,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陷入瘫痪”。[9](P6422)集体遗忘可以掩盖外在的损害,达到表面的修复,但不能抹除受害者内心的创伤,是一种自我欺骗式的道德催眠,更是一种通过遗忘对犹太人进行的第二次屠杀。
二、集体遗忘与社会暴力:难以消解的仇恨
集体遗忘不仅不能修复受害者后裔内心的创伤,反而在集体遗忘之后营造出的“说抱歉”语境下造成加害者后裔内心的扭曲。在《记忆还是忘却: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一文中,阿莱达·阿斯曼区分了四种对待过去的创伤性记忆的模式:对话式忘却、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为了忘却而记忆以及对话式记忆。[10](P88)这四种处理创伤的文化模式,通过加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调和,协商出一种新的、关于过去的共同观念或记忆,都是有效地处理创伤性过去的策略。然而,在《J》中,虽然当局想采取遗忘的方式来解决大屠杀造成的伤害,但这种遗忘不是对话式的忘却,并不是遭受暴力的双方自愿加诸于自身的遗忘,而是被强加的不平等的命令。小说中,在“出事——如果真的出事”之后,国家通过电台每日宣传“说抱歉”的思想,力图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把人从回忆和悔恨造成的精神崩溃状态中解救出来。而人人都“说抱歉”却绝口不提为什么抱歉,就是为了根除指责的概念,让愧疚得以麻醉,让受害者忘记仇恨,让施害者摆脱愧疚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小说中权威的媒体哲学家瓦莱里安·格罗森贝格尔在演讲时说:“‘说抱歉’将我们所有人从相互指责的过程中解放出来,去往一个无可指摘的未来时代”。[6](P43)然而官方的态度,并不能全然代表个体的声音,“说抱歉”并不能真正化解仇恨,反而会因为这种不明缘由的“说抱歉”带来的压抑给社会造成新的扭曲。阿斯曼认为:“一个国家并不能直接影响其国民的记忆,但却可以禁止怨恨的公开表达,而后者容易重新激发曾经的仇恨,从而引起新的暴力”。[10](P88)《J》中的加害者后裔在长期的压抑状态下,被限制了仇恨的表达,被压抑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得到化解,而是通过新的暴力形式得到发泄。
在小说中,受雇于“当下”(Ofnow),作为一所非法定的公众情绪监管机构的调研员,年轻的埃斯米·努斯鲍姆在监控全国的情绪过程中,发现有持续不断的怒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城镇的每一所房屋里,怒火以及不幸都会从每一扇门廊的下头渗出来”。[6](P283)努斯鲍姆的发现挑战了“当下”的立场,揭示了“当下”自我欺骗、粉饰太平、不敢正视“出事”的虚伪。
时间证明努斯鲍姆的观察是正确的,二十年后,人们开始公开谈论努斯鲍姆关于暴力的言论,而暴力也日渐以实际的事件暴露于众。小说中的登斯戴尔·克罗普利克,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侥幸逃脱摒弃历史的命令,成了鲁本港各种隐秘传闻的非官方保存者、叙述者,在他的《鲁本港简史》中,过去的鲁本港就是一个暴力横流的地方。“那些年月里,丈夫和情人、农夫和渔夫、海难客以及走私客,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解决他们的怨憎,有如他们在远古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并不求助于法律或者其他外来的指手画脚”。[6](P97)阿莱达·阿斯曼在论述文化的功能记忆的去合法化形式时表示:“官方记忆只能和支持它的政权存在的时间一样长。在这之前,它还会催生出一个非官方的对立记忆,扮演批判的、颠覆性的功能记忆的角色。”[8](P152)小说中克罗普利克的《鲁本港简史》无疑扮演着对官方记忆的批判性角色,是官方想要在公众面前掩藏的反面回忆,这种回忆与官方回忆一样具有政治性,它在未来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力。在小说中,暴力事件的不断呈现,证明了这种反面记忆的合法性,使得官方不得不做出改变,接受遗忘策略的无效性,正视暴力的存在。克罗普利克对最近一次发生在洛温娜·摩根斯顿与她的丈夫和情人身上的凶杀案作出评价,他认为:“洛温娜·摩根斯顿案件的发生,是令人快活的恢复原状,一个像鲁本港这样的村庄,本就拥有令人自豪的勇士史,人们就应该互相杀戮……”。[6](P96)
彼得·劳森(Peter Lawson)认为“出事——如果真的出事”显示了人们对大屠杀的怀疑和否认,[11](P188)小说中,在集体遗忘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人开始对这种“说抱歉”的态度表示怀疑。“实际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的以为我们有什么可抱歉的。然而一个机构能运行的方式就是附和无中生有、人人都这么说的话”。[6](P42)雅各布森借此实际上说明了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每个人都沦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服从当局“说道歉”的态度,而丧失了表达自我的权利。“英国文化主体似乎因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受到了集体创伤”,[11](P189)在这种集体创伤之下被压抑的民众因无从发泄愤怒造成病态的犯罪行为,暴力是他们对当局采取集体遗忘策略消解矛盾的质疑。
对英国文化主体造成的集体创伤不仅表现在重大的谋杀事件,也通过每一个家庭内部的婚姻关系表现出来。在小说中,每一个看似和谐的家庭都表现出毫无理由的争端。泽曼斯基教授与其妻子德米尔扎无端的争吵,古德金探长对妻子的恼火,埃兹的父母罗达·努斯鲍姆与康普顿·努斯鲍姆之间的对抗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病态的状况,在集体遗忘所造成的模糊认知下,人们无从得到答案,只能以“事理超出了我们的掌控”来做不可知的解释。暴力在集体遗忘的掩盖下仍然潜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这种被压抑的暴力只针对犹太人,是其他族裔所不能取代的。扬·阿斯曼认为:“如果说要与过去告别,那我们应该告别的是暴力,而不是记忆,并且只有通过记忆,我们才能告别暴力”。[12](P24)小说中,官方采取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道路,忘却记忆,助长暴力。这种暴力是毫无理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没有确切的理由,只是潜藏在每一个反犹主义者心中的不言自明的选择。弗洛姆对德国普通民众在不赞成纳粹政权的政治原则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支持纳粹的心理做出分析,认为:“对孤立的恐惧和道德原则的相对削弱,有助于任何政党赢得大批大批群众的效忠,只要这个政党已经掌握国家政权”。[13](P146)小说中每一个仇恨犹太人的人对反犹主义的支持,是惧怕被孤立的盲目选择,是在群体处境下对道德原则的遗弃,是一种“群体感情的狂暴”。[14](P36)这种毫无理性的感情狂暴正是雅各布森所要批判和担忧的。在一次谈及对未来的最大的恐惧的采访时,他说:“我惧怕流行文化、缺乏独立主见、舆论一边倒、乌合之众、暴民,以及这些人追随的各种大众传媒上的表达。这个世界已变得危机四伏,无论到哪里,总聚集着一群乌合之众”。[5]反观当下英国犹太人的处境,“虽然英国犹太人普遍享有温和的容忍,但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在街上受到零星的身体威胁以及对他们的墓地的亵渎。对犹太人的人身攻击和言语攻击在二十一世纪初有所增加”,[15](P282)在表面的遗忘之下仍然潜藏着无法消解的仇恨。
三、敌对状态与个人尊严:犹太人的两种抉择
《J》以一则寓言故事开篇,讲述一匹狼和一只狼蛛比赛谁是更好的猎手。为了证明自己更优秀,狼在一个星期之内将所有猎物捕食殆尽,最后赢得狼蛛的尊敬,但狼也因此陷入没有猎物而不得不捕食自己的老婆、孩子,最后只能自己吃自己的下场。该故事寓意永远不要赶尽杀绝。整个叙事就在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之下展开,通过互为指涉、互相补充的文本,叙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切换,最后随着故事主人公爱琳和凯文身世的明晰,揭示出大屠杀之后作为捕食者的反犹主义者对猎物犹太人存在的需要。
与“当下”的对立造成的车祸给埃兹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在她看来“我们不能用一个假设就让过去静悄悄地消失,我们必须要正视出事,而不是让人们分摊其咎——况且现在为时已晚——而是要去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能治愈”。[6](P282)当局与努斯鲍姆都希望一个和美的社会,他们的分歧只不过在于,在当局看来,忽略掉矛盾、抵触、争议以及多样性,你就能获得和美,而努斯鲍姆认为只有海纳百川,将一切囊入其中,才能得到和美。努斯鲍姆将当局称为假设论者们,站在了“当下”的对立面,设想出了恢复国家和美状态的方法,就是对后裔的重组,“我们,换句话说,活下来的人还活着的后裔。这个意义上的重构:把我们当初失去的全还给我们”。[6](P292)而她所要索取的就是当局所极力掩盖的敌对状态。“我们失去的是一种深刻的敌对体验,不是指偶发的,家庭的或邻里间的敌意,不是这种要么迎面上去要么就置之不理的敌意——而是究其总体而言,不是那么随机偶然、主观臆断的一种,一种业已形成、需要长期消化的文化间的敌意。在这样的敌意之下,所有的一切,从我们用以崇拜的、到我们拿来果腹的,都能找到缘由,并且能够井井有条、一清二楚。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正因为我们不是他们”。[6](P292)而他们则特指“出事”中的犹太人,犹太人作为特定仇恨对象,对犹太人所秉持的仇恨是任何其他族裔的人所不能替代的,具有独特的犹太特质。
为了恢复这种敌对体验,埃兹与她领导的“恢复重建委员会”寄希望于寻找已经融入表面和谐的大家庭中散落的犹太后裔,像追寻化石一样,只要一个纯正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行。具有犹太血统的爱琳和凯文被他们偶然发现,然后两人在隐秘的计划下,被推向彼此,来实现埃兹想要他们完成的更新未来的计划。萨特在《反犹份子与犹太人》一书中基于二战后法国犹太人的处境对反犹份子与犹太人的关系做出了分析,他说:“如果犹太人不存在,反犹太主义者就会发明他”,[16](P8)因为“如果通过一些奇迹,所有的犹太人如反犹份子所愿都被灭绝,那么反犹份子将发现他除了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看门人或店主之外什么都不是,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法国人’这一特性将具有低的价值,因为人人都拥有它”。[16}(P19)在鲁本港这样一个被集体遗忘消除了差异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具有了相同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因为普遍存在所以在埃兹等人看来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在本质上,埃兹以及倡导恢复敌对状态的人都是反犹主义者。他们期望通过恢复这种敌对状态来恢复自己的价值。
面对这样一种操控,爱琳与凯文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凯文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他人眼中,他们到底是什么,而他努力寻求他人眼中的自己,并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缺陷以迎合他者,而是基于一个人终归要了解自己的敌人的原则,以便其更好地恰如其分地恨他们。不妥协、秉持仇恨可以说是凯文坚持的立场。但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他所能做的也就是仅仅保持仇恨的态度,而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反抗。“我根本不想改变它,我想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能留给他们的唯一报复就是——拒绝与他们为伍,要我说,就把胜利给他们吧,让他们看看这有多空虚”。[6](P408)斗争在他看来已经毫无意义,空虚感渗透进他的整个思想,让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父母、对犹太人感到耻辱,“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躲躲藏藏,的的确确,就是耻辱”“一代代人都被人践踏?耻辱”“我?在这一切中,我就是最大的耻辱”。[6](P379-380)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论及人类的绝对道德律令时曾说:“你要如此行动,使得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17](P49-50)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而因此赋予每一个人以尊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凯文会具有深深的耻辱感,因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在他看来,犹太人都沦为了反犹主义者的工具,而丧失了人格尊严。因此,在这样一种无法做出反抗而又感到耻辱的处境下,他选择了自杀。“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想,没有人可以操纵我”。[6](P409)自杀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尊严做出的最后的抗争。
而在爱琳看来,即使处于这样一种操控之下,仍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有这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改变”,[6](P408)在她的眼中仍有希望。她并不认为她怀了凯文的孩子就意味着埃兹计划的实现,相反,她认为这代表着她心中期盼的她与凯文的未来,代表着光明的前景。斯米塔·戴维(Smita Devi)等学者认为:“雅各布森也提供了像爱琳这样典范的人物形象,知道作为孤儿的痛苦以及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像科恩,她选择生养孩子”。[9](P6421)爱琳期望通过爱及乐观主义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敌对状态,然而竭力希望恢复敌对状态的埃兹却渴望仇恨,故事在爱琳与埃兹如下的对话中结束:
“这不是个好开始。”爱琳说,“我们之间有怒火。”
“恰恰相反。”埃兹答道,“这可能是个最好的开始。”[6](P410)
爱琳的话语中透露出希望通过和解的方式来消解犹太人与反犹主义者之间的仇恨,但反犹主义者埃兹只希望看到怒火的存在,这样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原则恰如其分把愤怒发泄在犹太人身上,而避免对同类造成伤害。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仇恨在新的生命之中又找到了复活的曙光,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可见的未来又会恢复到大屠杀之前的状态,雅各布森为我们预示了下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人们没有从大屠杀惨痛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而寻求理解一直是雅各布森的追求,他曾说:“灾难之后我们所期望的是对它的认知——既包括各种文字、信息,也包括深层的理解”,[5]《J》反映了雅各布森在反犹主义情绪无法消除的社会状况下对犹太人的担忧。
结语
作为英国犹太裔作家,雅各布森大部分涉及犹太主题的作品都以英国犹太人为主人公,反映他们作为少数族裔在与英国文化主体相处中的种种问题。彼得·劳森认为,在雅各布森的作品中,大屠杀被想象为是无国界的,尽管它起源于欧洲大陆,但为盎格鲁-犹太人的集体焦虑提供了反乌托邦的边界。[11](P191)《J》构想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大屠杀给加害者和受害者后裔造成的伤害,体现了当代英国犹太人的集体焦虑。英国长期对大屠杀不予关注的事实,以及近年来英国反犹主义的重新出现使得人不得不思考集体遗忘是否真能消解仇恨、英国所倡导的多元融合是否真能实现和谐。通过构想一个集体遗忘的社会,雅各布森将日记、信件、寓言故事、题词等多重文本糅合在一起,在多重叙事线索之下揭示出了爱琳和凯文的犹太身份,进而揭示出最后两个犹太人被反犹主义者用来恢复敌对状态的计划。通过鲁本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以及凶杀案件,雅各布森呈现了在集体遗忘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社会中潜藏的暴力。雅各布森在反映犹太人的创伤的同时,也展现了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强烈需求。特里·伊格尔顿评论称:“《J》是一种罕见的道德幻象和微妙的情感智力的结合。这本书深刻洞察了爱与恨、吸引与排斥、亲和与对抗的扭曲逻辑”。[7](P1337)反犹主义者企图通过繁衍新的犹太后裔,以恢复敌对状态的行为损害了犹太人的尊严,而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面对强大的敌人要么选择死亡,要么选择相信通过爱消除仇恨,但反犹主义者不寻求对话式和解的单向暴力发泄让犹太人的希望破灭,反映了雅各布森对犹太人在如此敌对的环境下的生存状况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