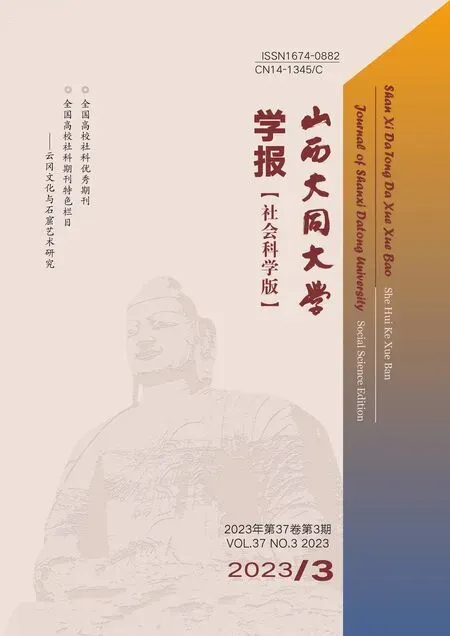论库切《凶年纪事》中后现代叙事的新探索
韩 乐,牟学苑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61)
《凶年纪事》是颇具后现代主义独创精神的作品。从内容上来说,文本中的三栏内容分别记述了JC 库切的政治评论,JC 库切的内心独白、安雅的内心独白以及安雅和男友艾伦的故事;而从形式上来说,这三栏内容分别代表了三种甚至四种不同的声音,它们一起被汇聚在同一个时空中。很少会有作家直接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如此独特的排版布局形式,而库切选择了这样的形式,有自己独特的用意。
一、神话隐喻性的梦境叙事
正如许多后现代作家在作品中热衷于神话的表述或重写那样,神话在激活一段旧有典故之余,还会再次唤起人们心中关于那些古老记忆的知觉体会,让这些故事在人类的记忆中得到延续。那么,在《凶年纪事》中多处被提及的:C 先生关于死后之事的梦境,以及梦境中的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这些具有神话隐喻性质的梦境书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C 先生的梦境在全书中频繁地出现:第一次,在《危言》(Strong opinions)的13.论身体(On the body)中,C 先生提到自己昨晚做了一个噩梦:“那是垂危之际,在一个年轻女子引领下经过遗忘之门”,[1](P59)但他不相信这个年轻女子就是陪她走过死亡之门的人,他随即把这种古怪和不合理归结为死亡的本质——“离奇”;第二次,在16.论竞赛(On competition) 里的第三栏,安雅和艾伦聊到C 先生,安雅说到C 先生向自己讲述了他的梦,那个梦里有欧律狄刻。安雅建议他把这个梦写进书里,但C 先生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书里必须都是言论,但是梦不是言论”;[1](P78)第三次,在《危言》的最后,也是第31.身后之事(On the afterlife)中,C 先生提出了:“人类肉身死后精神生活是否永存,灵魂到底能妥善安放”的问题,并认为灵魂的存留仍旧是一个未被认知的问题,而人死之后,爱人是否还能陪在身边,或陪在身边的人又是谁呢?[1](P153)而在紧随《危言》其后的《随札》(Second Diary)的01.一个梦(A dream)中,C 先生就写到了:他昨晚的一个不堪的梦:他梦到自己死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女子陪在自己的身边,让他免受了一些伤害。由那个女人,他随即想到了欧律狄刻的故事,那个希腊神话中的欧律狄刻已经死亡,俄耳甫斯却没能成功地将她从地狱带走,他认为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死亡降临的时候,人便不具有选择自己伴侣的能力了。而之后《随札》的14.关于母语(On the mother tongue)一节,安雅在邮件中对C 先生说道:“真没想到你的《随札》一上来就是一个梦,那是很早的你说过的关于欧律狄刻的梦,但你说你不会把自己的梦写进书里,因为梦不能作为见解。”[1](P197)这个部分很明显得在回应《随札》的01.一个梦(A dream)以及更早的部分,而在《随札》最后的一篇,也就是在本书的最后,安雅表示自己愿意成为C 先生梦里的那个女人——那个欧律狄刻,只不过这次先死去的是C 先生这位“俄耳甫斯”,哭泣哀求的是他,对生死感到困惑的是他,换不来结果的,感到无力的也是他。依照C 先生的看法,人之所以没有了选择伴侣的能力,是因为死亡,就像俄耳甫斯最终也没能将欧律狄刻带出地狱一样,安雅也注定只能看着他死去,而不能和他一起,这样看来,死亡似乎是一件孤独的事,来世的爱更是。
《凶年纪事》中反复出现的梦境都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文本中的任意位置,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而每一处有关俄耳甫斯梦境的出现都是与下一处有关联的,这些梦境像一个个散落在文本内部不起眼的位置,却能相交或者相切的“圆圈”。梦境的虚拟性让故事主体能够规避现实中的危险与情绪上不安的同时又让其深刻地体验到危险与不安加之于身的感情,这是一种“把自己消解掉的感情。”[2](P195)而全文中与这个神话梦境有关的情节虽然散落在书中的不定位置,从第一个梦境到最后一个,更像是C先生,这位将死的老人在表达自己迫近死亡时的恐惧以及对死亡过程的完整思考。而梦境的最后,C 先生对于身后之事的无意识恐惧在经历过这些“圆圈”里来回游离漂泊的过程后,最后被那个年轻女人安雅接住,梦境妥帖地落地。
C 先生的这些梦境,实质上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一种叙事行为——与意识中的叙事一样,梦中的叙事也是一种为了抗拒遗忘,追寻失去的时间,并确认自己身份、证知自己存在的行为。[3](P22)而梦境在全书中也扮演了情节的角色,它不仅推动故事的发展,框定叙事的范围,更构筑了人物的心灵世界,这是一个分裂、多重的世界,然而却是人物的恐惧唯一可以寄居的世界。[4](P63)C 先生一边在恐惧着关于死亡的身后之事,一边也在埋怨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对人的身后之事进行应有的解释,而之所以选择希腊神话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则大概率是因为这对爱侣的悲剧故事已经成为一种诠释“分离”的原始母题,是与含混的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所不同的有关于死亡,分离的原始存在。库切的其他作品,如《彼得堡的大师》中也有出现了这个神话故事,这个神话场景与作品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现实、梦境乃至想象相互交织,而又以内心独白、幻想、梦境的表现载体为呈现出来,其中“分离”母题用来诠释父子关系:是一位中年丧子的父亲对死因不明儿子的扼腕痛心之情与无尽怀念,如果说《彼得堡大师》中的俄耳甫斯神话是在书写亲情,而《凶年纪事》中俄耳甫斯的故事更多的是在书写爱情,书写没有血缘关系的陪伴,依恋以及迈向死亡时老年人心中的孤独与不安。
二、个体意识独立的对话叙事
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了使真正的对话得以进行,后现代主义主张开放,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5](P77)《凶年纪事》文本中的三个人物所形成的多种对话关系在文章中时隐时现,把读者带入了一个颇具后现代性的迷宫中。
首先,《凶年纪事》中各种声音都是独立且具有自我意识的,根据巴赫金的观点: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6](P29)也就是说,主人公的意识是独立于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而这种独立性并不是作者所赋予的,却是主人公本身就有的,这就不需要有一个悬挂在文本之上所谓的“正确的上帝视角”来统摄全文。比如,文本中栏C先生视角的叙事和下栏安雅视角的叙事,以及二者的想法甚至言论在很多方面都有激烈的冲突和偏差,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二者的身份地位,阶层的不同,性别的差异也让他们对相同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而作为学者和长者的C先生,对于安雅提出的很多看法都没有提出“一杆子打死”的否定态度或者作出具有价值观的评判。反而,在很多问题上,安雅都能够在她的主场,最下栏中尽情地直抒胸臆。
其次,除了主人公所具有的独立自我意识之外,这些独立的意识也构成了关于不同意识的声音对话。文本中具体的“对话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三栏三个主体的声音在同一页面甚至不同页面错位时空的对话——有人物之间的直接对话,有转述的观点,有内心的相互揣测,有跨栏的遥远回应。有学者认为:库切和文本中主要人物“我”,也就是C 先生及读者意识中建构的“我”可以说就是同一个人,即作者=叙述者=人物,[7](P130)这也佐证了库切小说的叙述者大多兼具多重身份——既是权力的反对者又是无意识的同谋者:JC 库切不再是作家库切笔下的人物,而是一个独立于这一切的个体——这样的一个库切就分化出了三个不同的“库切”,作家库切躲在叙述者“我”和人物JC 库切背后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又将自己因审查制度或其他政治因素无法言说的话交给这两个分身,而三个身份通过排列组合,两两也在对话交流:作家库切在和人物JC 库切对话;叙述者“我”时而代表故事中的人物JC 库切,时而又是真实的作家库切。
而以上具有独立意识的声音对话也符合库切的主张:库切对自己作品秉持的一贯态度是不做任何评价,不回答他人对作品的各种疑问,但他却在这样隐性的复调小说中,通过虚构的作者,对小说家的创作评头论足——众多声音和意识是独立自主,脱离了作者而成一体的,他们平等地各抒己见,从而构成了多声部曲调的合奏,在内容上形成了微观对话。
而《凶年纪事》文本中的宏观对话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心理独白,而是真实的与人发生关联和交换思想的对话——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此文本中的各种声音不仅各自独立,互不融合,还做到了共同前进,进而达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整个文章的内容就是几个人意志的结合,多种独立声音和意识彼此对话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意识开始之处,对话便同时开始,由此形成了复调结构。作为库切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风格特点就这样在库切小说中的“对话”上得到了继承和延续。
三、节奏随意的时空感叙事
叙事作品大多是时间性的艺术,读者在阅读时也一般遵循时间的顺序。所以,在读《凶年纪事》这样三栏的故事时,按照每栏故事的顺序从头至尾阅读至少三遍可能是大部分人选择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库切大可以选择把它们独立成三个独立的章节,编撰进一部书里。但他没有那样做,所以这样的三栏设计一定有他的考量和深意。
从整体上来说,《凶年纪事》整体外观形式让人联想到后现代作家克洛德·西蒙的空间形式小说《植物园》。《凶年纪事》同样具有这种后现代小说特立独行的空间感,其中交错复杂的叙述节奏或空白停顿还需要清理盘点来使其通顺。
尽管三栏内容各自都采用了传统的叙述手法,分别符合随笔评论、短篇小说的题材特点。但是,看起来随意的、没有任何可追踪性的并置或并列,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混乱和荒谬之感——《凶年纪事》乍读来有些混乱,但仔细梳理会发现库切尝试在同一空间中的不同层次上安置情节和人物的行动,其中对话等内容的尝试取消了主要的时间顺序,进而打乱了叙述时间的流动——这是他重构时空的努力。而探索情节或企图重建叙述的时空细节对读者的阅读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当我们把视线放在以小说为主的中下栏的内容时,试图以中下栏为横坐标,以带有数字序号的评论文章为纵坐标,横竖交叉出一个个栏目模块再重新放置这些小说情节的时候,得以重新参照并领略整体和部分的意义,理顺时间的进程并感受到文本中颇具空间感的内容穿梭。
先从《危言》和《随札》这两大部分整体来看,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说的:“库切这里的谋篇布局中,很用心思,暗设了首尾相接的常山之阵。”[8](P44)这暗示极其明显地说明了《危言》和《随札》两个整体在空间上的承接关系——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前后相接的部分。所以,《危言》的结束也是《随札》的开始,而上文提到的《危言》的末尾和《随札》的开头也有内容上的衔接,这也将两个叙事空间体前后衔接在了一起。
而如果我们拿出《危言》《随札》这两个部分单独来看,并将每个部分的三栏结构铺排开来会发现:这些内容如罗曼·英伽登所说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拥有两个维度,在一个维度中所有层次的总体贮存同时展开,在第二个维度中各部分相继展开。”[9](P11)根据这个观点结合《凶年纪事》的文本可得出:如果说前一个维度是空间上的维度,那么后一个维度便是时间意义上的维度。而《凶年纪事》正是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的作品。于是,要想探究出其中埋伏的草绳灰线及前后上下所关联的内容,在对《凶年纪事》的解读中,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思索的办法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叙事过程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但故事的发生却是同时的,多维的,立体的。而在叙事的过程中,话语要求叙述者一件一件地把故事讲出来,于是一件件事会被投射在文本故事进程这条笔直的线上,当读者只关注《凶年纪事》中下栏的小说时会发现:很明显,C 先生要写的故事,其中的故事情节大多是单线程的,少有空间意义上同时发生的故事。库切的叙事手法完全可以将所有的叙事投射成一条与“故事时间”进程相吻合的直线,但库切没有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他用了一些叙事的手段将故事的进程变得立体,虽然并未形成一般意义上以空间叙事手法书写成的空间形式小说,但这种排布还是呈现出了一个具有“共时感”的,精心布局过的巧妙时空。
具体来说:在《危言》的中栏和下栏中,情节的发展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空间上按部就班地展开:中栏是C 先生视角叙述的和安雅相处的点滴,下栏是以安雅视角叙述的她和男朋友艾伦的生活点滴以及艾伦策划的针对C 先生的信息偷窃事件未遂的内容。而库切善用空间上的排布去打消某种字面意义上的,或者说人们惯性以为的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这在《随札》中表现得尤其明显:C 先生,艾伦,安雅之间纠葛的主要故事线应该是:C 先生写书——出书——开庆功宴——安雅出席并与之告别——C先生送书——安雅读书——读完书写感谢信——C先生读信——向读者展示信的内容。而库切却让笔下的叙述者“我”把这一连贯的故事线打碎在了空间的排布中。于是,这条简单的情节线索被随意地截取,打断,重新被放置在了不同的空间里,时间性在此被转换成了一种压缩过的空间性,而空间性里也有断续的时间性——每个单个情节的时间线索被拉短了,同时也显得更立体,甚至还做到了前后照应,看似混乱的布局里其实有一个精巧的时空结构:首先,从这个大空间体的两块空白说起。对于这两块叙事进程中空白的处理,在《随札》中,下栏安雅讲述到了C先生邀请她和艾伦去参加自己的庆功会,她和艾伦讨论要不要去参加,中栏的C先生视角从讨论的一开始,也就是《随札》的一开始就是缺席的。此刻C先生在自己主场的中栏里保持静默,在空间上故意退出了安雅和艾伦二人讨论问题的小世界,并且似乎故意在隐藏起自己被讨论的身份,中栏一开始的空白就是最好的不在场证明。这种不在场瞬间让安雅和艾伦的聊天,乃至故事都拥有了空间立体感——仿佛有一个上帝视角在说:C 先生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暂时隐藏起来了,他并不想听到你们对他的议论——颇有一种后现代小说吊诡的在场真实感。
而在《危言》部分,下栏安雅的视角在前五小节都是缺失的,直到06.制导系统(On guidance systems)才出现,安雅视角从这里开始讲述:和C 先生在洗衣房里的初遇,而这个节奏已经落后C先生中栏的视角五个小节。而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的视角所生发出的感受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在于:C 先生看到年轻身材好的安雅,心中生发出一种形而上的痛感,而安雅也认为自己性感曼妙的身材引诱到了这位老学究。但安雅的感受明显是滞后于C先生的,这种滞后是一种既隐晦又刻意的让位:在C先生与安雅的相遇中,是C先生先注意到安雅的存在,她太耀眼了,性感得耀眼,能够引起C先生形而上痛感的耀眼——于是这空白像是在给C先生内心所经历的波澜让位:这波澜包含C先生内心隐晦的性幻想,对于安雅的各种揣测,而这些都是C先生一个人的看法,在叙事空间的行进过程中不需要安雅的参与,于是,这段空白得以让安雅暂时从C 先生的世界中离场,C先生得以有了一个机会好好地想象了一番关于安雅的各种事情。
这两处空白无关乎叙事意义上的空白,更多的是一种刻意制造出的人物缺席或不在场。这样的设置不仅将中下栏的故事情节完美地上下跌宕串联在一起,凸显了整个故事的空间感,而且人物的隐退也让读者想象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仿佛能够切身感受到C 先生内心对安雅隐晦的,难以言说的幻想;仿佛就亲身坐在安雅和男友艾伦身边,窥听着他们关于C先生的讨论。所以,这两部分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空白:其中C先生和安雅的分别不在场换来的是读者的在场。库切用这样的空白无意间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也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参与感。同时,两处空白也打破了某种情节上的顺序时间感,让情节的时间特性具有了立体的空间感。
而自这两块空白之后,中下两栏的叙事速度也大大拉开了差距。前文提到:在与安雅的相处交往中,C 先生对安雅“形而上痛感”般的感情产生得很快,但这情感去得也快:在《危言》06.论制导系统(On guidance systems)的中栏,他已经开始对这个身姿曼妙的女郎产生了一点失望之情,他在请安雅成为自己的助手之后,看到她翻译出的文本心中多少有些沮丧,认为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他心中所想象出来的默契。C先生的整个感情进程非常得快,对比起来,安雅的情感认知有些后知后觉——在C 先生对安雅的能力已经产生些许失望的时候,安雅在自己的主场下栏中才开始注意到自己是否吸引到了这个看似古怪的学究。中下两栏的叙事速度在空白结束后也保持到了故事后面:《随札》05.公众情绪(On mass emotion)中栏C 先生视角开始出现便是和安雅最后相见的那个早上,安雅替艾伦来和自己道歉以及07.吻(The Kiss)中,C 先生问到安雅今后的事业规划,在12.经典(The classics)小节中,他们拥抱并说了再见。在中栏前12 个小节的内容中,C 先生和安雅回忆了过去,梳理了现在,畅想了未来。而随后的12小节便都是C先生将自己的主场让渡出来展示安雅来信内容的部分。
最后,在宏观坐标系中,从栏目内容的填充物角度去俯看《随札》下栏的全部内容:艾伦和C先生在宴会上的对谈和争论就占据了下栏24小节篇幅的前22小节,留给安雅的部分其实并不多,只剩下了两小节的篇幅,而安雅用这部分迅速交待了很多信息:她表示自己将永远也不会原谅艾伦,和艾伦分手之后去了昆士兰,并且收到了C 先生曾经允诺送给自己的书,随后她写了一封感谢信,而此时留给安雅的叙述空间并不多了,以至于她自己不能够把信的内容呈现出来,不过这样压缩紧促的叙述空间和节奏正好将读信并展示信的机会交给了C 先生。在梳理中下两栏对于书信“写就”“寄出”“收到”的顺序可以发现:在《随札》的23.巴赫(On J.S.Bach)一节的下栏,信被安雅写好寄出,而这封信在《随札》的三栏文本空间内游荡,在13.写作生涯(On the writing life)的中栏就“已经”被C先生收到了。信寄出的时间感逆着空间感的阻力,到达C先生的手里,这其中平添了些许的不易,而这封信也补齐了C 先生本人过快的感情进程引发过快的叙事速度所造成的栏目内容上的空白。随着信到达C 先生手里,中栏的安雅在信中表示:收到了C 先生的书,从而有了这封感谢信,而从这里开始,C先生彻底退出属于他的栏目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从信里跳跃出的安雅,也就是说,至此,1/2 中栏内容和下栏的最后1/12 的内容都是安雅角度的叙述了。而在中栏结尾处,信中的安雅写到了自己和新男友的未来,说到:“他们可能会结婚吧”——这是不确定的未来,而在本属于自己的下栏中,她写到并表示愿意做C 先生的欧律狄刻,这对于安雅来说——是确定的未来。而确定的、不确定的文本都在这里戛然而止。其中,安雅完全可以在第中栏继续说自己的畅想,但她把自己乐意去做的事情放在了属于自己的主场里,这里多了一份笃定,对C 先生虔诚的笃定。至此,安雅成为C先生未来的欧律狄刻,在确定与不确定的时空里构造了一个理想且完美的结局。
于是,叙述节奏的不同不仅符合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还使得中下两栏内容的填充物也变得不同。时间本就是一去不复返的,这是自然界无法超越的规律,而相同单位内,时间的进程和容量是可以被小说家在作品中随意更改的。正如:“语言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要想达到共时性效果,唯一途径就是打破时间原有的顺序,即打破客观时间的原有顺序。[10](P15)可以被打破顺序并重组,拉快或拉慢速度的,就是小说家的叙事时间:在叙事时间中,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变成被随意堆叠的,类似于影视剪辑的进度条,可以拖动每条的位置也可以伸展拉长每条的长度,在《凶年纪事》中的三栏内容就是如此。库切在书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更多依靠的是自己的心理时间而不是真实时间来写的,而这种看似随意的书写方式打破了叙述的时间性,却是为达到空间共时性效果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