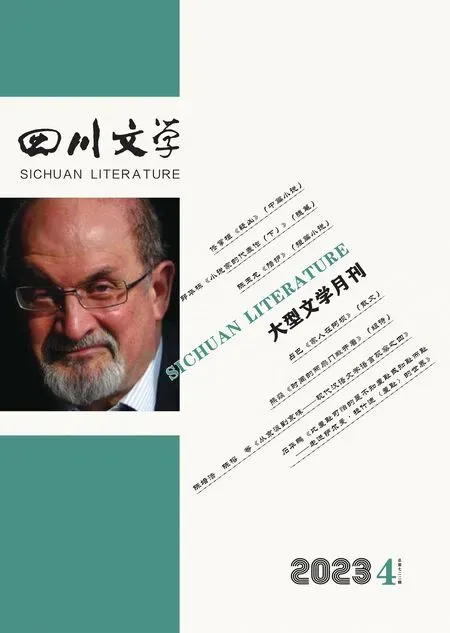梨园与墓园
□文/刘萌萌
我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会坐在她面前,看她端出孙二娘的架势,手上夹着烟卷儿,来来回回挪动沾着泥巴的小腿,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吆五喝六。天刚蒙蒙亮,她坐在马扎上,蓬着头发,脚趿俗艳的泡沫拖鞋。刀与案板的撞击中,碎白菜弹跳着迸溅出来。扶着案板的手时不时递到唇边,来上一口。梨树叶还沾着昨夜的清露。蓝色的烟雾,像一条上升的河流,荡漾在一早的晨光里。
一支烟差不多了,她终于停下来,用手背抹了把汗津津的鬓角。空气散发着热烘烘的青草气息,像是对刚刚没走多远的夏天的补充和追忆。眼前,废弃的白铁皮洗衣盆,黄灿灿的玉米面,堆成小山的白菜,隆起半坡参差白绿。她挺着肥沃的肚皮,像传说中膂力过人的大力士,一手抱盆,一手快速而均匀地搅拌。隔着横斜的梨树枝丫,我惊讶地望着几步之外朝鸡栅走去的妇人:稳健的步态,粗壮而灵活的腰身,胡萝卜似的手指灵巧地拨开插销,群鸡跌撞,沸腾而出,带着一地鸡毛的欢腾冲向食盆。
半年前,她打来电话,说从大哥手里租了一块地,就在一片开阔的梨园里。“找点事做,就不那么闷了。”听筒里哧哧啦啦交织出一片杂音。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各种消息,零星地灌入耳朵。那些渠道不同的真假难辨的传闻,像喋喋不休的小人儿,激烈争吵,各说各话。辗转于这些言谈之间,时间久了,懒得浪费力气,随它吧。乌云在父亲脸上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兀自飘走了。祖母宠护的老姑娘,香甜的老幺,他当哥的,说得出什么有分量的话?这些年,她过得并不顺心。人间种种,唯有挣扎自渡。很快,她像意识到什么,大谈菜园的规划,雀跃之态,张扬着儿童般的欢喜。之后,她打来的电话,每每沾着泥土气,和着风声,招摇着久违的生机:水灵的生菜,脆嫩的黄瓜,长藤绕架的丝瓜,鲜艳的西红柿圆得天真,老生般垂着红须的玉米……三面通窗瓦舍……生机翻涌的菜园似乎真的掩住了隐秘而荒凉的洞穴。
“老姑这辈子,吃过太多苦。”她不动声色地吸着烟,不动声色地抛出五味杂陈的大半生。天黑下来了。交错的枝丫,漏过几粒远远的灯光。她猛一挥手,一截烟蒂划着弧线消失在深浓的夜色里。
一
父亲慢慢老了,说话不多的他,越发倾心往事。他和族中的晚辈,似乎隔着一个漫长的世纪。反而是那些久已过世的老人,回想起来,像是推门刚刚走了出去,空气中还残留着温热的气息。
祖父吹着莫须有的胡子推门而入,一把掀开热乎乎的被窝。两个儿子手忙脚乱穿衣下地,挎上背篓,一阵风地跑出门,去往河边的树林拾柴。“早起自带三分财气。”被祖父奉作至理的民间话儿,许多年后被一阵热辣的风递送到我的耳边。
七八岁的祖父,去给姨父打长工。姨父是亲姨父,也是如假包换的真地主。外甥认真放牛、干活,换来几袋高粱抵付工钱。欺负他年幼,大人们把剩饭给他,即便这样,也填不饱树苗似的身子。小男孩实在捱不住,跑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两手一摊——高粱米我们都吃完了,拿什么还人家?天一亮,祖父又拾起放牛的鞭子,跟在慢吞吞的牛群后边,看着太阳越过山坡,又慢慢落到山的后边。牛群,日出,日落,手执牛鞭的小小少年,朴素而自然的元素叠加成一幅岁月的剪影,讲述着一个儿童的三百六十五天。
祖父长成少年,离开熟悉的村庄,去关外谋取生路。晚年的祖父一直为还乡做着准备。作为接应,小儿子先他返回村庄,像忠心耿耿的庄稼,迎候祖父的归来。这对父子,在差不多的年纪,一去一返,无意间,完成了一次接替与轮回。
“人到天边喜勤勤。”一生未入学堂的关内少年,朴素的道理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起伏。做学徒,打下手,送货,照顾师傅一家的日常起居,乱纷纷的,是生活也是工作。祖父用一生的经验兑换生存的教训和智慧。
有一回,送货途中经过学堂,年轻的学徒趴在窗下,听得入了迷。不敢多耽搁,每天听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也好啊。时间一长,窗内探出几颗好奇的脑袋。一来二去,彼此成了朋友。祖父到底没能掌握树枝般曲折伸张的笔画,仅能认个囫囵样儿……我时而打断父亲,问一些蠢话,比如藤蔓般繁复的家族关系。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中,祖父似乎从未离去,他不过是去了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着从前的生活。
瘦削的曾祖母,有一张黧黑的面孔,似乎她一出生就那么老了。生养了五个儿子的老太婆,执着的偏爱近乎一个谜。她接受祖父的照顾和供养,却一直为长子图谋。曾祖母打着战事将起,恐被充军的由头,将祖父诳回老家暂避,生意由长兄代为打理。含混的述说,莫测的时代背景令人如坠云雾。令我不解的是,同值壮年的大爷爷怎么无充军之虞?父亲这样说,我便这样听。翻年,躲过兵燹的祖父兴冲冲返回,作坊已不复存在,他抬头张望,巨大的谎言如同蚕茧,彻头彻尾将他蒙蔽其中。兄弟着手分家,大到资财,小至一块杉木门板、粘着蛛网的斧头、青花瓷碗、生锈的螺丝钉,在家族的口头叙事中神奇地保留下来。吃亏的是祖父,忍气吞声的也是祖父。性情温良的男人,一生也没学会与人争抢,在父亲身上,我辨认出那与生俱来的孱弱和羞涩。
四爷口讷,他的晚年几乎没留下任何消息。悄静的灯烛,不知几时敛灭了声迹。五爷晚年痴呆走失,儿女们张贴过几张寻人启事后草草收场。健壮的三爷,十头牛拉不回的犟老头,一气儿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八十三,离百岁还有将近二十个年头,毫无预兆地意外退场,想必心有不甘吧。温和迟缓的祖父,在最终的去留上,匆匆走在了几兄弟的前头。
繁茂的梨园,枝叶错杂交互,一个谜掩上另一个。默思半晌,老姑冒出一句,“命,都是命。”
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带着我,和父亲匆匆赶回老家,照顾卧床的祖父。这样说来,我是见过祖父的,就在他身边的床榻上,咿咿嗬嗬爬来爬去。安静的下午,祖父忽然睁开眼睛,伸出粗糙的大手,摸了摸我的脚丫。又一回,祖母端详我的眉眼,说我像隔壁捡来的孩子。睡中的祖父竟然接过话茬:“胡说,她哪有咱家孩子好看呐!”说完,又睡了过去。
父亲兄妹七个,侍奉祖父床前的,只有父亲和母亲这对年轻的小夫妻。祖父不忍,临终前,将一块衣料送给母亲。祖父嘱咐祖母,家中什物尽给小儿子留着,他刚成家,派得上用场。祖父下葬不久,祖母便向母亲索要布料。簇新的凡尔丁,母亲爱不释手。这块布料就是一场神奇的魔法,藏着一条裤子,也许是一件镶着盘扣的夹袄。可是,祖母伸出讨要的手,她的美梦瞬间被席卷一空。此刻,其实仍有许多办法许多伎俩。她大可借鉴黔驴技穷的媳妇们,撒泼、耍赖、倒地打滚,或干脆矢口否认。然而,母亲二话没说,噔噔噔折身回屋,捧出整齐的布料,交到祖母手上。母亲爱面子,有骨气,在心里给祖母狠狠记下一笔。她那一笔有什么用呢?直到祖母去世,我也没看出丁点儿端倪。
祖母瞒着两个儿子变卖家产,勒令父亲写下净身出户的文书。目不识丁的老太太,极内行地要求文书上加盖公章。按照民间的传统伦理,家产由男丁继承。除非大逆不道,悲愤之下,老人才可能做出有违常情的决定。而这样的个例罕有听闻。敦厚的父亲,该下过多少决心,吞下多少唾沫,才从口袋里掏出折得烂熟的文书,结巴着,向领导说出祖母几近荒唐的要求?
“你爷爷要活着,事情不会这样。”母亲说话时,祖父的棺柩久已融入泥土的黑暗,与地下的虫鸣和野草结成一体。
那些慢腾腾的清早,就像一场尚未消退的梦境。祖母倚在炕头,摸出烟,划着火柴,“嗤”地燃着了。祖父一粒一粒扣上衣纽,挺了挺腰,说起他的夜梦。那只凶悍的大鸟,拍着翅膀,哇哇怪叫着从他头顶飞过。经过一片庄稼地,他看见自己扛着锄头,从抽着紫红缨穗的玉米或挎着绿色大刀的高粱下兴冲冲走过。逝去的老父,坐在门前,眼望村头的河水,“吧嗒吧嗒”吸烟……有些情节模糊了,他使劲搔着头皮,像是要把散去的梦境从头皮下捉回来。说完了,祖父一脸茫然,巴望着祖母。沉默的祖母如同观世音菩萨,稍微弹出杨柳枝上那一点清凉,他的不安转瞬间就会消散。祖母吐出一个烟圈,弹了弹烟灰,低声说:“抽空,回趟老家,给爹烧点纸钱……”说着,两人略略欠身,挪蹭着,直到脸对脸、膝盖碰着膝盖。经常,一觉醒来,老夫妻不忙着下地,凑在一起痴人说梦。就在那些说梦、解梦的辰光里,仿佛有什么,把祖父和祖母的脸,轻轻黏合一处。
二
电话里,老姑的声音皱巴巴的,像雨水淋湿的纸团:“哥、嫂,你们回来吧,妈不行了……”在要不要回去这件事上,母亲略微挣扎了几下,最终决定,“去”,毕竟,“生死事大。”
胸口微微起伏,头发散开,枕上一片耀眼的银白,白得像月光,白得像冬夜的大雪,无意间,吓人一跳。昏迷的祖母像是香甜地睡着了。学医的燕姐攥着祖母的手腕,默数片刻,叫道:“跳得多有力啊。”一屋子人望向弥留的祖母,现出敬畏与悲哀交织的神色。
祖母八十五岁时,爬楼梯如履平地,倒是身后的大伯气喘吁吁。九十五,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惊人。我们私下议论,长寿的祖母,说不定能创造医学史上的奇迹。
生命是一个精密而奇妙的系统。下过多少雪,刮过多少风,淋过多少雨,生过多少气,蹚过多少河,走过多少独木桥,吃过多少盐……一一帮你记着呢。时限到了,再强健的心跳,也无力挽回肉体的衰朽。九十六岁的祖母,终究要从人世上离开了。
祖母当晚吐出最后一口气。众人像垮塌的墙,“哗”的一下,齐刷刷跪在床头。卧房有如狭小的舢板,哀哀哭声中微微摇荡。
长明烛在香案前“呼”地燃起。父亲、大伯、表哥、表弟,男丁不论年纪,轮流值守。守灵,是对体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不能打盹,不能分神,时刻留意火苗荣枯。烛火熄灭,于丧家是绝对的禁忌。这灯烛,与祖母此去关系重大,万不可大意。
三百六十行,老家新添了“鬼头”的行当。“鬼头”不可怕,一个健壮而机敏的中年男人。有了“鬼头”,整套丧葬仪轨有条不紊,家属松了口气。老家葬礼有“摔盆子”的习俗。有儿子的人家,摔盆是儿媳的义务。民间的说法中,摔盆子、打灵幡这些事,对当事人不利,还能带来霉运和晦气,更有甚者,身体从此衰微,一病不起。祖父去世,由长媳大伯母摔盆,这一回,自然该由母亲完成摔盆重任。这可有些小小的麻烦。我两岁时的那个下雪天,祖母赶我们母女出门,老太太嘶着喉咙,声音从身后追过来:“我死也轮不到你摔盆子!”这么多年过去,母亲认为祖母理应和她一样,说过的绝情话用小刀刻在心上。就算死了,也不能赖账。
“鬼头”在人群中问:哪个是儿媳?母亲走过去。“鬼头”略略打量过母亲,再三叮嘱,盆子要举过头顶,用力摔下去,摔得越碎越好。母亲有些不甘:“婆母有言在先……”“鬼头”看了看欲言又止的母亲,似乎明白了一切。小声说,“过去的事,莫计较……”
老姑忽然过来。“二嫂,有我呢,我帮你。”她抱起瓷盆,郑重地递到母亲手上。老姑一脸恳切,母亲不好意思执拗下去。她默默吸一口气,尽全力将瓷盆举过头顶,随即,瓷片炸裂的碎响迸溅得到处都是。在场的人,特别是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
五年前,儿女们选看墓地。祖母一遍又一遍重复:“向阳坡,要向阳坡啊。”她可不能忍受山根的阴冷。矫情的老太太,即便死了,也不肯受半点委屈。末了,她交代儿女,要和祖父的骸骨并在一处。
到哪去找祖父的骸骨呢?祖父下葬的地方几经变迁。墓穴先是遭水患,又经历土地迁移的变革,家属得知消息时,棺木早无从寻找。姑姑们瞒着高龄的祖母,不敢走漏一丝口风。并骨这件事,使得前事重新浮出水面。最终,老姑从祖父生前的随身物件里,选了一副水晶花镜、一枚象牙手戳,小心地装入骨灰盒。
祖父去世时,打幡的是刚刚成年的大伯,这一回,祖父的灵幡,由唯一的孙子、大伯的儿子刘龙来扛。刘龙人届中年,隆起的肚腹现出颓态,人却老成持重起来。较之当年的伯父,他更像一个沉稳的父亲。
父亲和刘龙坐在车里,叔侄各自紧握灵幡。灵车才启动,父亲的眼泪雨点一样落下来:妈,跟我走……刘龙颤声喊:爷,回来吧……一老一小的呼喊,迅速淹没于疾驶的车流。
三
葬礼归来,母亲和老姑互加了微信,荒疏多年的姑嫂情迅速升温,有如冬寒收尽的小阳春。经不住热情的老姑几次相邀,母亲终于决定去梨园看看。
那一年,老姑陪祖母来我家短住。隐约觉得,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到访。母亲拉着脸,祖母拉着脸,来言去语间夹杂着旧日恩怨。大人的事我看不明白,却被祖母身边的老姑吸引过去。老姑刚好二十岁,苹果绿上衣,雪白的肌肤,站在哗哗的水龙头边洗碗,腕间的银镯轻轻晃动起来,整个人明媚得像一朵花。我暗自可惜。因为是祖母的女儿,这么漂亮的老姑,我却亲近不得。
再见老姑,是在祖母的院子里。那趟行程早已模糊。唯一清晰的,是一觉醒来,老姑赤脚站在窗前,和墙外的邻居对骂。老姑还那么漂亮,脸颊光洁,披着长长的发丝。我惊讶的是,即使吵架这种难堪的事情,竟也无损她的美丽。许多年后,我学到一个名词——苹果肌,眼前浮出一张鲜润的脸,那脸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老姑。
老姑从小路尽头快步迎过来。老姑老了,胖了,斑白的发髻随意挽在脑后。老姑和母亲说着话,一手挽起我这个多年未见的侄女,一瞬间,时光仿佛从未流走,我从记忆中走到这条小路上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场秋雨给溽热的夏天画上了休止符。泥泞湿滑的土埂上,我打开手电筒,三步一滑,两步一歪,去树下围砌的茅厕。夜风湿冷,散发出泥土的腥气。远近眺望,没有一星半点灯光。老姑的屋舍隐没在一片漆黑当中。自己怎么突然出现在这片陌生的梨园?这样一想,竟有些恍惚。
晚饭过后,大家谈得最多的是这些年的生活。低沉的讲述,痛快的宣泄,眼角的碎泪……千头万绪,有如五颜六色的百衲衣,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上。老姑摸出一支烟,衔在嘴上,这嗜好遗传自祖母。横七竖八的往事,在呛人的烟雾中,纷纷落了一地。
老姑的苦水,与记忆中的听闻,形成巨大的逆流与冲撞。
传闻中的老姑,和二十世纪80年代的迪厅、摇摆舞、红唇、酒精、暧昧的男青年、嘈杂的人群、疾风暴雨的音乐搅在一处。游手好闲的老姑,摩登入时的老姑,挺立于时代的潮头。时间移易,老姑的故事也在延续。姘居,争吵,钱财,消费,耳光,激烈的撕扯……祖母的叫骂,姐妹之争,等等,这些带有暗示与倾向性的关键词索引出的,是一个漂亮的老姑、招蜂引蝶的老姑、不得消停的老姑。莫衷一是的我们,最终换算出一个“不正经”的老姑,不受拘束、野性十足的老姑。
睡意渐渐袭来,拉杂的夜谈还热着。故去的祖母突然现身在我们中间。早年的雨雪、阴霾、石子、皮屑、发炎的伤口,一股脑儿裸露出来。老姑的记忆中,祖母是个得体的老人。那一回,祖母走亲戚到了弟弟家,问她可吃过饭,祖母饿着肚子,却说吃过了。“老太太要强,不给人添麻烦……”娓娓而谈的老姑让我吃惊不小。我听说的祖母另有一番面貌,自私、懒散、狭隘……缺乏修养。
夜风吹来树木和草叶的清香,夜虫在树叶和泥土的掩护下,唧唧哝哝叫个不停。偶尔,树叶“欻”地落下来,像某种暗示或提醒,房间里的人陷入短暂的沉默。没有争论,没有辩驳,没有质疑,大家沉浸在对方的讲述里。虚幻或真实不再重要。时间像一场丰盈的大雪,盖住浮动的人心,还有那尖锐的,叫做“立场”的东西。
四
给祖母送“麻刀”是件大事,老姑提前两天就在准备了。
我和祖母的相见,不过六七回。这六七回的雨点,泼洒在我的半生时间里,像一杯水浇在沙漠,不留半点痕迹。和祖母有关的传闻,多来自旁人的回忆。母亲说,祖母没读过书,却常有连珠妙语。她挑剔儿女买来的水果,“宁吃鲜桃一口,不食烂桃一筐”。她告诫饭桌前的孙儿,“君子略尝滋味,小人吃一抬筐。”规矩和礼仪是别人的,她铁了心做小人。又一回,祖母偷了曾祖母的绸缎。寻上门的曾祖母,敌不过儿媳的伶牙俐齿,悻悻而归。我暗想,祖母要绸缎做什么用呢?印象里,她总是一件灰夹袄,短发拢到脑后,露出宽阔的额头,一口接一口吸烟。
天才蒙蒙亮,老姑轻手轻脚回来,手上抱着细长的“麻刀”。老姑说,祖母要到“那边”,得蹚过一条河。过河是有讲究的,撑着麻刀才得顺利通过。没有麻刀,过不得河,也就不能抵达“那边”。听起来,麻刀像是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通关文牒。
麻刀从开着的车窗斜伸出去,缀着细碎的花朵。狭窄的路口,老姑双手环抱麻刀,躲避往来行人,以防脆弱的花朵被碰掉。她要带去一枝完整、漂亮的麻刀,让祖母撑着它,像拄着龙头拐杖,顺利过河,去对岸享福。
墓园松柏森森。密集的墓碑,像一枚枚书签,嵌在台阶之间。墓碑上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无一例外地镶着照片。在一片向阳坡上,我们终于找到了祖父和祖母。大家从包里一件一件掏东西,烟、酒、苹果、桃子、香蕉,还有祖父最爱吃的桃酥。在这一切之上,是那贵重又脆弱的宝贝麻刀。
寸土寸金的墓园,墓碑间的空隙实在太小,我们勉为其难地站着。一见祖父母的照片,父亲眼泪鼻涕稀里哗啦淌下来。他直通通跪下去,像受尽委屈的孩子,喃喃哭诉着为人子的疏忽和愧疚……他跪在地上,说着一直未能出口的话。
我和母亲挤在别人的墓碑前。老姑教我们模仿她的样子,给周围的坟墓逐一敬酒,口中念诵有声,大意是抱歉惊扰,请多多包涵之类的客气话。一转身,父亲红着眼睛,已经站了起来。母亲和父亲一样,跪拜,叩头。不同的是,她叨念的每句话,都说给祖父。即便面对隐入泥土的祖母,她仍无话可说。
我也跪下去,叩了三个头。奇怪的是,我的眼里,莫名涌上了泪水。母亲糊弄幼年的我,说无论和谁结婚,她都保证把我生出来,而且,我将更加聪明、漂亮。不知哪一天,这个骗局不攻自破。父亲和母亲的结合,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我。这不是命运是什么?命运让我成为祖父母的孩子,我就得接受祖父的早亡和一个并不亲爱的祖母的事实。我的血脉和遗传,来自他们融入泥土化成灰的身体,来自并不完美的家庭关系。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我难以解释自己的眼泪从何而来。祖母对母亲、对我们做过的一切,不该被记恨么?为什么,我分明感到难以言喻的悲伤?这个强大到我一度以为将巫一般永生的老妇,也无计逃脱衰朽的规律,无力挣脱造化的因果,尽管,她看上去有着铁一样的骨骼和一副无动于衷的石头心肠。
五
祖母的离世,让老姑感觉自己的某一部分被带走,一同装进小匣子,埋入地下。她租下梨园,养鸡养鸭种植蔬菜,让无休止的劳动把自己包围起来,以肉体的疲惫缓解思念之痛。“妈有了新的生活,我也得过自己的日子……”老姑像是喃喃自语,又像复述旁人的劝慰。
梨园归来,时不时收到老姑的消息。她说起大哥大嫂的不是,贪小便宜,常来园中搜刮,甚至扬言过年时捉母鸡下酒。老姑每日焚香诵经,从无杀生之念,她要给这些家禽一个善终。可面对大哥大嫂,她不知怎样拒绝。我知道,老姑拒绝不了的,是来自祖父的一脉亲缘。
在梨园,微雨的屋檐下,我和老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老姑说,那时候,祖母正咽下最后一口气,燕子姐起身急急往外走,扔下一句话——“姥姥去世了,大家的缘分从此断了。”她噔噔噔下楼,扔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的人。老姑说,这一幕,她永不能原谅。
说来奇怪,面对老姑,我有一种先天的信任。尘世里,我们注定有所牵系。我想请她讲一讲祖父母、她自己的经历,还有家族的过往,却终究没能说出口。我没能克服起于祖母的隔膜?抑或是,这近于唐突的请求,终究是一种冒犯?
老姑的消息,总是发给母亲,电话,也打给母亲,一年到头,她和自己的哥哥,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父亲接电话,总像隔着千山万水,扯着喉咙在大风天里呼喊。对于电话这种通讯工具,他一直无法得心应手、收放自如。我后来渐渐明白,父亲对于内心的流露,有一种本能的紧张和羞涩。即使对着自己的亲妹妹,他也慌里慌张,语无伦次。我无法解释父亲这种奇怪的症候,然而,我清楚,老姑在电话里哪一回的倾诉,不是对着亲爱的哥哥?
梨园的那些早晨,老姑在厨房张罗早饭。父亲扔下我们母女,悄悄尾随老姑而去。隔着窗子,我看见父亲站在老姑身边,问这问那,亲近而自然,好像他们兄妹,回到从前童年的家中,从未分别。清透的阳光捕捉住这对老去的兄妹,勾勒出只能用天真形容的笑脸。
一阵风吹过,我看见梨园的树木,所有的枝梢和树叶,瞬间朝着同一个方向,战栗着,传递出一阵阵轻微的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