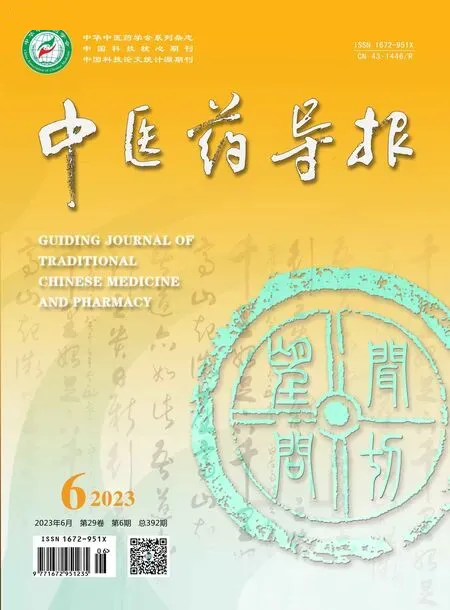王耀献辨机论治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经验
王文娜,张佳乐,薛哲哲,魏蜀吴,姜伟民,王耀献,孙卫卫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700)
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是指病原微生物反复侵袭膀胱,甚或上行累及肾脏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慢性膀胱炎和慢性肾盂肾炎。其发病率高而诊治率低,常病情多变、迁延难愈、预后复杂。尿路感染6个月内发作≥2次,或1年内发作≥3次者即为复发性尿路感染[1]。慢性泌尿系统感染属于中医学中“淋证”中“劳淋”的范畴,以中老年女性多见。当慢性膀胱炎进展为慢性肾盂肾炎时,除有尿频、尿急、尿痛等,亦会出现贫血、夜尿增多、微量蛋白尿等小管-间质受损的临床表现。其反复发作可引起肾小管萎缩,肾间质纤维化,肾组织瘢痕形成,最终导致慢性肾衰竭[2]。西医治疗泌尿系统感染仍以抗生素为主,但长期应用抗生素易引起细菌耐药。“病原微生物”之邪持续存在,人体处于一种正虚邪恋、正不胜邪的状态,则本病易反复发作。而有效的中医治疗可邪正兼顾,扶正以助祛邪外出,避免抗生素耐药,在降低本病复发率方面大有裨益。
王耀献教授长期从事肾病临床工作,在临床实践中探索出辨机论治[3]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等多种疾病的诊疗中[4-5],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优势,提高了临床疗效。笔者有幸师承王耀献,学习领悟辨机论治的诊疗模式,现将其辨机论治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的经验总结如下。
1 辨机论治
为抓住疾病诊治的关键点和病情变化的核心——病机,王耀献提出辨机论治[3]的中医诊疗模式,提高了疾病诊疗的精准性,使处方用药正中疾病靶心。这一诊疗模式具体包括“初始病机、衍生病机、对证病机、共通病机、体质病机、时空病机、环境病机、兼夹病机、药毒病机、杂合病机、对症病机、局部病机”[3]12种病机模式。辨机论治理论的提出,弥补了传统辨证论治的不足,使我们在诊疗时能打破只着眼于现阶段病位、病势、病性的惯性思考方式的局限性,以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诊治疾病。将辨机论治应用于慢性泌尿系统感染能帮助我们多方位、全过程分析和治疗这一疾病。
2 辨机论治在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具体应用
2.1 初始病机 初始病机指的是疾病发生的起源,定位于疾病的初起阶段,包含疾病的病因、病根及疾病的诱因或加重因素[3]。初始病机是疾病起病与复发初始阶段的核心病机。王耀献认为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初起阶段定位于其初起急性发作期。初始病机是湿热邪气下注于膀胱,肾与膀胱气化不利,邪伏体内,留而难去,待其虚时反复发作。
湿热邪毒的产生或为外感或为内伤。外感者多因外阴不洁,湿热秽浊之气趁机上袭肾与膀胱;内伤者多因情志不舒,肝失疏泄,影响少阳枢机和三焦水液代谢,或气郁化火,热气循经下注,与重浊趋下之湿相合,注于肾与膀胱,或因饮食不节,过食辛辣肥甘损及脾运,水谷不化为精而聚为湿,湿热注于下焦。湿为阴邪易伤阳气,热为阳邪易耗阴津,两者常胶结难解,留而难去,是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的病根和诱因。所以王耀献认为在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初始阶段,即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急性发作期,应以清热利湿为主,兼顾气阴,尽快恢复肾与膀胱气化功能,常选用知柏地黄汤加减,可适当加入柴胡、贯叶金丝桃、当归、丹参等活血行气之品,既能以气行助湿化,又能防止病情深入,热与血结,由气入血。
2.2 体质病机 体质病机主要由体质决定,体质是在人体共性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个体差异性,由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共同塑造,故分为先天体质和后天体质[3]。体质病机是探析独立个体的生理、心理及病理特性对疾病的影响,疾病是正邪之对抗,病因是始动因素,体质是影响始动因素是否发生作用及其发展态势的内枢纽。体质病机与初始病机关系较为密切。体质病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初始病机出现,同时又与初始病机互相影响。两者往往是疾病发生的基础病机。
研究[6-8]表明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患者的体质特点密切相关,王耀献在临床中亦发现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易发于老年女性,并且相关研究[9]表明超过30%的女性患者在症状消失后的12个月内仍会发生感染。其缠绵难愈的原因有泌尿系统先天梗阻、畸形,抵抗力降低,精神压力过大,女性更年期,或存在糖尿病、肾脏病、妇科疾病等基础疾病[4]。所以慢性感染既存在与先天肾气不足,气血流通不畅有关的“尿路畸形”“尿路梗阻”等先天体质病机,又与老年女性肝郁肾虚的后天体质病机密切相关,所以大部分女性患者除在发病时有膀胱刺激征等局部症状之外,平时亦有胸闷、焦虑、失眠、五心烦热、腰背冷痛等肝气不疏,肾阴、肾阳不足的表现,而且慢性泌尿系统感染常在情绪波动或者劳累的情况下发作。治疗以疏肝补肾为主,方用四逆散疏肝解郁,加狗脊、川牛膝、续断、杜仲等以益肾强腰[10]。
2.3 衍生病机 衍生病机主要发生在疾病发展的中晚期阶段,在初始病机作用于患者机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是疾病发生后病邪与患者机体相互影响的结果[3]。衍生病机类似于新生病理产物的概念,但其往往虚实胶结难解,不仅伴生新的病理产物,也伴有更深程度的虚损。
王耀献认为慢性泌尿系统感染若因失治、误治迁延不愈,不仅湿热之邪会耗伤肾之气阴,过用清利亦会耗气伤阴,加重虚损。气虚运血无力,久病入络留瘀,则湿、热、瘀、虚胶结不解,逐步进入“微型癥瘕”[11]阶段,主要表现为肾小管萎缩、肾间质纤维化。一方面,湿热瘀毒阻于肾脏,代谢废物不能从小便排出,故见高血压、肌酐升高、水液潴留等标实之象;另一方面,邪损肾体,先天累及后天,脾肾衰败,气血精微失其先后天化生滋养,故见贫血、骨质疏松症、低蛋白血症等本虚之象。王耀献认为诸多肾系疾病进展到肾脏纤维化阶段后,“微型癥瘕”便成为其核心病机。此时需以“消癥散结”治法为主线,佐以“调养脾肾、心肾”两条辅线,同时遵守“以衡为期”“扶正”“祛邪”三条基线[12],所以在治疗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衍生病机时应以扶正气,散癥结为主,常用消癥散结方加减。黄芪、当归、三七益气化瘀,鳖甲、海藻、牡蛎软坚散结,或加用苓桂术甘汤等温阳利水之法,邪正兼顾,以平为期,顾其虚实两端。
2.4 对证病机 对证病机定位于疾病当前的状态,是疾病当前所表现出证候的发生机理,即通常所说的审证求因[3]。对证病机主要通过四诊收集的症状和体征分析疾病目前病性之虚实、病位之深浅及邪正之盛衰,即狭义的辨证论治。当症状和体征等外在征象未掩盖疾病本质特征时,对证病机在临床诊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病位主要在肝、脾、肾与膀胱,病性为本虚标实,以气阴两虚兼夹湿热最为常见。初期邪实之湿热留而不去伤正,两者胶结难解,日久则热伤阴,湿伤气。反过来气虚则运湿化湿无力,阴虚又易生虚热,故湿热之邪与气阴之虚互相影响,致本病虚实反复而错杂。后期先天累及后天,气虚及阳,阴损及阳,可发展为脾肾阳虚,湿阻不化。王耀献强调:初期不能清利太过,可酌情加入党参、白术等益气养阴之品,扶正防邪深入;若气阴损及阳气,脾肾阳虚者,可加入菟丝子、巴戟天、杜仲、刺五加等温补脾肾之品;若后期热不甚,湿难化者,应注意行气透邪,可酌情加入柴胡、青蒿等行气透达之品,或加入杏仁、白蔻仁、薏苡仁,取三仁汤宣畅三焦,分消走泄之意。
2.5 时空病机 时空病机也是气象病机,其内涵为气象要素和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3]。天人相应,四时的更替、气候的变化、天地之气的交感互生时刻影响着居于其间的人。正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篇》所载:“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13]故疾病的发生通常有明显的季节“易感性”。气温降低或偏低,降水日增多、空气相对湿度高及气压变化明显时,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病率会升高[14]。
陈士铎在《辨证录·淋证门》写道:“人有春夏之间,或遭风雨之侵肤,或遇暑气之逼体,上热下湿,交蒸郁闷,遂至成淋。”[15]暑为夏季主气,易兼夹湿邪,耗人气阴。湿热下注于膀胱,作为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初始病机贯穿于本病全程。王耀献认为慢性泌尿系统感染若在夏季反复发作,可取少量金银花、鱼腥草、车前草,用开水浸泡0.5 h,每日频饮以微微清利下焦湿热。
2.6 对症病机 对症病机指的是针对患者某一症状的共性病机[3],如:疼痛的共性病机包括“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出血的共性病机包括“热迫血行”和“气不摄血”,呕吐的共性病机是“胃气上逆”。对症病机能帮助我们迅速地对标某一症状或体征,故对症病机在疾病治疗中常因其灵活性和速效性被应用。
王耀献在疾病治疗中重视患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要在针对主要整体病机治本治疗的基础上对症治标,以期尽快、尽早缓解病人的痛苦。若患者排尿过频影响正常生活时,可针对“固摄失司”的共性病机加入覆盆子、桑螵蛸以固肾缩尿;尿痛甚者,可针对“不通则痛”的共性病机加入蒲黄、海金沙以通淋止痛;小腹拘急疼痛者,可针对“筋脉挛急”的共性病机加入白芍、甘草以解痉缓急止痛;小腹坠胀者,可针对“清阳不升”的共性病机加入柴胡、升麻以升阳举陷。
2.7 兼夹病机 兼夹病机指的主要是疾病并发症的病机或者伴随主症出现的兼症,相对疾病而言是次要矛盾[3]。如:肝失疏泄不仅出现情志抑郁、烦躁易怒等主要症状,还可能出现咳嗽、气喘,腹痛、腹泻等肝气横逆犯肺胃的次要症状;肺气上逆不仅出现咳嗽、气喘等主要症状,还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胃气上逆的次要症状,甚至出现肠腑气机不降之便秘、腹胀等症状。王耀献认为针对兼夹病机进行治疗不仅可以减轻兼夹病机的影响,还能防止主要病机进展恶化,主次兼顾,这与治未病中既病防变的思想不谋而合。
慢性泌尿系统感染的主要病机是湿热郁蒸下焦,气血运行不畅,湿热可煎津灼液,加之气血阻滞,日久则聚沙成石,故慢性泌尿系统感染可并发尿路结石。砂石内阻又会进一步影响肾与膀胱气化功能,加重泌尿系统感染,使其迁延难愈,严重者还会出现急性尿潴留或肾积水,甚至影响肾功能,故在治疗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时可加入王不留行、海金沙、石韦等通淋排石之品,既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又可防治尿路结石。
2.8 局部病机 局部病机是相对整体而言,指的是以局部症状或人体体表为主要表现的疾病的病机[3]。治疗通常选用外科或手术的方式。如泌尿系统畸形、大块结石、肿瘤等压迫性梗阻引起的泌尿系统感染反复发作,单纯辨证治疗常难见效,患者甚至会出现急性尿潴留、严重肾积水等危急症。外科手术解除局部畸形或压迫成为诊治的主要手段,临床上常采取内镜下激光碎石、电灼疗法、腹腔镜或开放手术的治疗方式。在其他疾病中亦如此,当无证可辨,或是单纯的辨证治疗无法缓解病情时,不能拘泥于整体观念而固执地坚持辨证治疗,不仅难以收效,还会延误患者病情,增加患者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
在辨机论治慢性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不同病机之间相互影响,甚至部分重叠,不可拘泥于某一病机,故步自封,要结合临床实际,抓住不同阶段的关键病机,圆机活法,以变应变。
3 验案举隅
3.1 验案1 患者,女,79岁,2019年11月16日初诊。主诉:尿频、尿急、尿痛5年,加重1年。患者5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后诊断为“泌尿系统感染”,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明显缓解,但劳累后或情绪不佳时易复发,近1年发作频率逐渐增加为每2周1次。刻下症见:尿频、尿急、尿痛,0.5 h排尿1次,乏力,目涩,口干,反酸,入睡困难,寐差,大便二日一行,便干;舌质暗,苔黄腻,脉弦数,左细右滑,尺脉沉。西医诊断:慢性泌尿系统感染。中医诊断:劳淋(肝郁肾虚,湿热下注证)。治法:疏肝补肾,清利湿热。拟方四逆散加味。处方:白芍30 g,北柴胡10 g,枳实10 g,贯叶金丝桃30 g,炒酸枣仁30 g,刺五加20 g,黄芩10 g,蒲公英30 g,金银花20 g,乌药5 g,覆盆子15 g,桑螵蛸10 g,炙甘草6 g,大黄6 g,菟丝子10 g,杜仲30 g。14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两次温服。
2诊:2019年12月14日,患者症状明显缓解,排尿时偶有灼热感,予前方大黄加至8 g,加鳖甲10 g,青蒿5 g。14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两次温服。
后症状基本消失,予2诊处方稍作调整,继服半个月巩固治疗。
按语:从本病案的核心病机为初始病机和体质病机。患者为老年女性,肾之阴阳俱虚,火不温土,水不涵木。肝木失于调达则疏泄失职,郁久化热。脾失健运则水聚为湿,气机受阻,湿热之邪循经下注,故见尿热、尿痛等湿热阻滞膀胱气机的表现,且症状常于劳累后或情绪不佳时加重;肝火犯胃故见反酸;肝火扰神而见失眠;而目涩、口干、便干皆为肝火伤阴之次要症状。结合舌脉,四诊合参,证属肝郁肾虚,湿热下注,故治以疏肝补肾,清利湿热。用药以四逆散为底方加黄芩、贯叶金丝桃、乌药以疏肝清热;杜仲、桑螵蛸、菟丝子以温补肾元,固精缩尿;贯叶金丝桃、蒲公英、金银花以清热利湿通淋;酸枣仁养阴安神;大黄泄热通便,使热从大便而出。复诊时患者症状基本缓解,仅见排尿时尿道灼热感明显,故加大黄用量以增加清泄热邪之力,同时加用青蒿、鳖甲以增强其透热养阴之力,谨防热邪进一步入里与血相结。后患者症状基本消失,因本病易趁体虚反复发作,故嘱患者守方继服半个月以顾护正气,巩固疗效。
3.2 验案2 患者,女,47岁,2021年4月24日初诊。主诉:发现尿蛋白、尿潜血阳性18年,血肌酐升高8年。患者于1998年妊娠时确诊急性肾盂肾炎,未积极治疗,1年后治愈,但时有发作,2003年体检时发现尿中出现蛋白,尿潜血阳性,未予重视,2013年发现血肌酐升高,于王耀献门诊口服中药治疗一段时间后,尿频、尿急等症状未再出现,相关临床指标较稳定。患者近期自觉乏力明显、易外感,复查发现24 h尿蛋白定量明显升高。刻下症见:乏力,咽干、咽痛、咽痒,鼻塞流涕,易外感,纳眠可,二便调;舌暗,苔薄白,脉弦细。辅助检查:尿素氮10.86 mmol/L,血肌酐167.6 μmol/L;尿蛋白(3+),尿潜血(±),白细胞10个/HPF;24 h尿蛋白定量2.6 g;B超示双肾轻度萎缩。西医诊断:慢性肾盂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中医诊断:劳淋(脾肾阳虚,瘀阻肾络证)。治法:温补脾肾,化瘀消癥。拟方玉屏风散加味。处方:黄芪30 g,麸炒白术12 g,防风10 g,海藻15 g,鳖甲10 g,桂枝10 g,茯苓30 g,桃仁15 g,水蛭6 g,地龙15 g,穿山龙30 g,青风藤15 g,黄蜀葵花15 g,菟丝子10 g,车前子10 g,杜仲30 g。30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两次温服。
2诊:2021年8月21日,患者自诉感冒次数减少,晨起偶见口干、口苦。复查:血肌酐156.9 μmol/L;尿蛋白(3+),尿潜血(-);24 h尿蛋白定量1.38 g。予前方去地龙、黄蜀葵花、菟丝子、车前子、杜仲,加刺五加20 g,北柴胡、黄芩、白芍各10 g。30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两次温服。
后随访得知患者症状基本消失,相关临床指标较稳定,血肌酐在160 μmol/L左右,24 h尿蛋白定量波动在1.4~2.0 g。
按语:本病案的核心病机为衍生病机。患者慢性肾盂肾炎反复发作,“病原微生物”之邪气逐渐深入,由腑及脏,由气入血,伤及肾络,损及肾体,湿、热、瘀、虚胶结不解,逐渐进入肾元衰败的慢性肾功能不全阶段。肾气失于固摄,不能藏精,故见微量蛋白尿;肾元衰败,体内瘀血、痰湿、浊毒等代谢废物无法完全排出,故见血肌酐升高;又因邪实愈坚,损及先后天之本,逐渐由气阴损及阳气,脾肾不足,故患者自觉乏力,且卫外不固,易外感。结合舌脉,四诊合参,证属脾肾阳虚,瘀阻肾络证,治以温补脾肾,化瘀消癥。此阶段为本虚标实,用药当以补益为主,黄芪、白术、防风取玉屏风散之意以健脾益气固表,加桂枝、杜仲、菟丝子以温补心脾肾之阳气。同时因邪已成实,扶正时要兼以祛邪,故加海藻、鳖甲、水蛭、桃仁、地龙、穿山龙、青风藤以散结消癥,活血通络,茯苓、车前子、黄蜀葵花稍以清热利湿泄浊。此时病势已难以逆转,故应平衡扶正、祛邪两法,力求延缓疾病进展。复诊时患者体虚症状明显缓解,晨起偶见口干、口苦,为肝火上炎所致,略减攻补之品,加柴胡、白芍、黄芩以清热疏肝。后随访得知患者不适症状基本消失,相关指标未见明显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