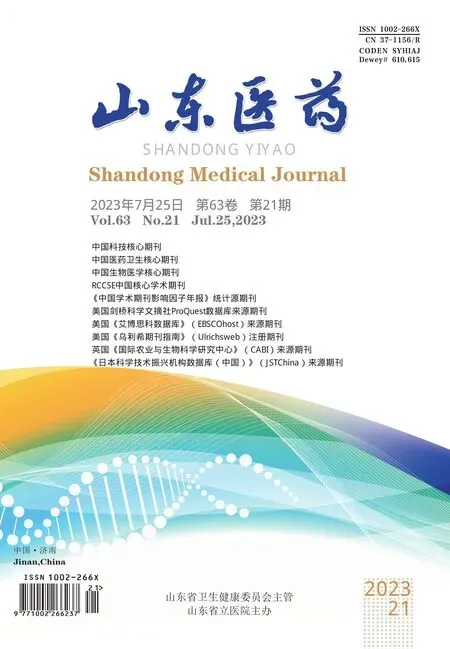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远端新发破口的原因和危险因素及防治措施研究进展
刘跃,邱昌涛,李玥锦,龚昆梅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一科,昆明 650032
B型主动脉夹层(Stanford type B aortic dissection,STBAD)病情进展迅速,病变累积范围广,已成为主动脉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1],在急性期可导致患者因主动脉破裂或多器官灌注不良而死亡,并影响幸存者的长期预后[2]。与开放手术相比,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创伤性小,有较低的死亡率,已成为STBAD的首选治疗方法[3]。然而在手术后存在一些特异性晚期并发症,包括支架移植物源性的新发破口(stent graft induced new entry,SINE)等。SINE被定义为仅由支架引起的主动脉壁新发撕裂,近端SINE通常会导致逆行A型主动脉夹层,而远端SINE(distal stent graft induced new entry,dSINE)可能会影响支架移植物远端的血管重塑,形成对原来假腔的持续灌注、新的开放性假腔和夹层动脉瘤,甚至导致主动脉破裂,危及生命[4]。有报道[5-6]指出,dSINE占总SINE的80%以上,发生率为1.3%~34.8%,死亡率高达28.6%,被认为是STBAD患者行TEVAR后引起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5,7]显示,dSINE发生时间一般在TEVAR后1~3年,并且可能长时间无症状。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增多,对STBAD患者TEVAR术后发生dSINE的原因、危险因素、防治措施,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现综述如下。
1 STBAD患者TEVAR术后dSINE的发生原因
1.1 组织学原因 夹层内膜组织处在病变状态,易受到相对较硬的支架移植物的影响,而dSINE在急慢性夹层患者中的发生率不同[8],提示可能与夹层病变的组织学特点有关。一方面,在慢性期夹层,剥离的内膜片会增厚发生纤维化、钙化,活动性降低,支架的径向扩张会持续挤压更僵硬的真腔内膜并造成损伤,从而增加dSINE发生的风险[6,9]。而在急性期夹层,虽然内膜瓣片处在急性炎症期比较脆弱,但顺应性较好,降低了dSINE发生风险[10]。而一些学者[8]则认为急性期动脉内膜层较脆弱,且滋养血管变性比慢性期更广泛,因而dSINE发生较早。慢性期患者虽然发生较晚,但其内膜片已经失去了可塑性,会持续受到支架移植物的影响,dSINE的发病率反而较高。总之,从夹层发生后到行手术治疗的不同时机会影响内膜片的组织结构,进而导致dSINE的发生率不等。另一方面,一些患者由于患有结缔组织疾病,会造成主动脉壁自身结构的破坏,变得更脆弱,容易发生dSINE。有文献[11]报道,马凡综合征患者接受TEVAR后SINE发生率是其他患者的十倍,其远端主动脉重塑不良,假腔可能会继续扩大导致主动脉破裂。此外,手术操作放置过大尺寸比的支架也会带来组织学损伤,使主动脉壁的结构紊乱,肌层和弹性纤维数量减少[12]。有研究[13]证实,TEVAR使胸主动脉局部僵硬了2倍,显著降低了其弹性贮器的功能,容易发生dSINE。
1.2 生物力学原因 覆膜支架需要径向力来压迫着陆区血管壁,以此覆盖内膜的原发撕裂口,防止血液继续流入假腔,并避免支架移植物移位。而TEVAR后刚性支架释放扩张,对脆弱的主动脉壁产生持续机械作用,这是导致dSINE发生的主要力学原因。MENICHINI等[14]认为,支架移植物在主动脉曲折度较大处释放时,会在弯曲的主动脉外侧产生更大的血管壁应力。主动脉壁长期较高的应力可能会增加主动脉应激,导致这些区域出现新的病灶,且与回弹力相比,径向力在新发破口的形成中起关键作用。
2 STBAD患者TEVAR术后dSINE的危险因素
支架移植物长期慢性刺激和主动脉壁发生病变自身脆性变大共同作用导致TEVAR术后dSINE的发生。dSINE的发生与夹层持续时间有关,研究普遍认为处于夹层急性期的血管壁比起慢性更脆弱而容易发生,但也有部分观点认为慢性期的血管壁更加纤维化和钙化,因此弹性更差,重塑能力更差,受到支架相关作用力之后更容易损伤。此外支架的远端过大尺寸比、长短、是否带有连接杆以及病变主动脉的解剖特点等也共同影响了dSINE的发生率。
2.1 覆膜支架的远端过大尺寸比 覆膜支架的选择通常基于近端锚定区直径,而远端血管真腔直径通常明显小于近端,从而导致覆膜支架远端尺寸过大。远端尺寸比定义为覆膜支架直径与远端着陆区直径之比。支架远端的过大尺寸比虽然能提供足够的径向力,避免其发生位移并覆盖撕裂口,但也对动脉内膜造成了伤害,增加dSINE的发生风险。支架太大的过大尺寸比会对血管壁施加强大的径向力,可能导致主动脉在组织学上发生结构紊乱,使主动脉变得脆弱[12],并增加dSINE发生的可能性。多项研究[9,15-17]均表明,较大的远端过大尺寸比与dSINE有关,被认为是dSINE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1]。LORTZ等[17]发现远端过大尺寸比为20%是远端SINE发生的阈值,且随着其继续增大,引起dSINE发展的可能性增加12倍。一项回顾性研究[18]发现当支架远端过大比达到40%时,dSINE的发生风险最高。
2.2 较短的支架长度 对于不同长度的覆膜支架而言,由于其近端都要覆盖夹层原发的撕裂口,近端锚定区往往相对固定,因此使用较短的支架移植物时,其远端着陆区难免会被部署到主动脉较弯曲的位置。而沿弯曲段着陆会产生更大的弹性回直力,这会导致远端支架—血管交界处壁应力增加。有关覆膜支架的最小长度,目前研究给出的临床建议并不一致。MA等[18]发现,支架长度<165 mm是dSINE发生的危险因素。而一项较早的研究则认为,支架长度<145 mm是dSINE发生的危险因素。覆膜支架越短,远端产生的回弹力越强,导致支架移植物外弯曲上的血管内膜承受更大的压力,进而引起dSINE的发生。
2.3 带有连接杆的支架 支架移植物内连接杆可以加强其弹性回直力,当带有连接杆的支架移植物置入弯曲的主动脉段时,会产生更大的回弹力。D'CRUZ等[19]通过Meta分析得出,使用带连接杆的支架移植物的患者dSINE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究其原因,可能与支架不同的制作材料和结构相关。连接杆虽然可以防止支架扭曲,但在降低支架本身顺应性的同时也会使柔顺性变差,导致支架更加僵硬,不能更好的贴附血管内膜,而在血流冲击下引起相对机械运动造成损伤。一项研究[18]发现,与使用不锈钢支架相比,使用带连接杆的镍钛合金支架移植物的dSINE发生率更高。
2.4 夹层持续时间过长 随着夹层发生后时间的推移,慢性期夹层内膜片会增厚,产生更多的纤维化和钙化,影响TEVAR术后主动脉重塑效果,更易导致dSINE的发生。一项Meta分析[19]纳入17篇文献共3962例患者,发现慢性STBAD患者发生dSINE的机会更高,发病率与夹层持续时间呈正相关。当持续时间>6个月时,其发生率明显增高[1]。此外还有研究[15]认为,急性期夹层是dSINE发展的最强预测因素,与其发生风险增加15.8倍相关。
2.5 靶向主动脉段(targeted aortic segment,TAS)曲折度高 TAS曲折度是指支架移植物释放节段的主动脉曲折度。有学者[7]用TAS曲折度指数来描述其差异性,发现高曲折度组患者dSINE的发生率大于低曲折度组患者,可作为预测dSINE发生的潜在标志物。然而,也有研究[4]认为,从无名动脉到横膈段胸主动脉的曲折指数与dSINE无关。但支架在弯曲部位具有更明显的引起血管拉直的趋势,产生更大的弹性回直力,且在其远端表现得更明显[15],会进一步扩大和拉直自身以及所部署位置的主动脉段,导致远端边缘与主动脉成角,此时支架强大的径向力使远端夹层内膜瓣片不均匀受力,导致主动脉壁损伤的风险增大,更容易发生dSINE。
2.6 主动脉锥度比小 锥度比定义为主动脉(近端着陆直径-远端着陆直径)/近端着陆直径[19]。锥度比每增加10%,导致主动脉相关再次干预风险增加甚至可达到4.5倍。在慢性主动脉夹层中,近端主动脉直径和远端真腔直径之间的差异约为10 mm,然而大多数可用支架(除定制支架外)的最大锥度差仅为5 mm[1]。这就导致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在行TEVAR治疗时,远端覆膜支架直径与着陆区血管真腔相比,仍然显得相对过大而产生更大的径向力,更容易损伤管壁发生dSINE。
2.7 楔形并置角大 楔形并置角定义为垂直于移植物的平面与远端着陆区的主动脉中心线之间的角度,当长度较短的支架远端着陆区位于曲折的主动脉段时,远端平面容易发生倾斜,导致支架需要扩张而向主动脉壁施加径向力时,其远端往往扩张不一致,引起动脉内膜受力不均匀。长度过短和柔顺性较差的覆膜支架往往导致其远端易与血管壁之间成角,增加内膜损伤形成破口的风险。LESCAN等[18]经过分析发现,发生dSINE的患者具有更大的楔形并置角,是最显著的危险因素。
3 STBAD患者TEVAR术后dSINE的预防措施
dSINE通常会导致患者预后不良,部分需要再次干预,使得TEVAR的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因而预防就显得格外重要。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增多,一些减少其发生的技术不断被报道,包括锥形支架技术、PETTICOAT—snowshoe技术、远端限制性支架技术、术者改良支架移植物技术、新型特异性支架技术等。
3.1 锥形支架技术 锥形支架不仅符合正常主动脉的生理解剖特点,而且适用于真腔明显变细的主动脉夹层患者,极大减少了支架远端尺寸过大对内膜的损伤。一项较早的研究[20]发现,夹层患者的动脉锥度差明显大于健康人,且使用锥形支架可以缩小近远端管腔直径的相对差异,使dSINE的发生率明显降低。有文献[21]报道了在43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中使用远端锥形限制性覆膜支架平均随访28.7个月期间,未观察到dSINE,同时主动脉重塑效果满意。此外,一些学者[16]为了应对远端着陆区逐渐变细,从远端到近端依次重叠放置两个或多个直径逐渐变大的锥形覆膜支架,以防止远端尺寸过大。这种技术使用的支架移植物两端有15~20 mm的锥度差,很大程度上避免了dSINE的发生。
3.2 PETTICOAT—snowshoe技术 PETTICOAT—snowshoe技术是对主动脉夹层临时延伸诱导完全附着技术(PETTICOAT)的改良,其本质上类似于限制性裸支架技术,区别之处在于其裸金属支架往往较长,远端一般可延伸至腹腔干上方。有文献报道,使用远端裸支架延长至腹主动脉段,避免了覆膜支架远端在主动脉易弯曲成角的位置释放主要径向力,从而降低dSINE发生的风险。ORIMOTO等[24]通过对比分别接受标准TEVAR和PETTICOAT—snowshoe技术治疗的患者,在术后2年多随访期内接受后者治疗的未发生dSINE,证实了该技术在短中期的疗效。此外,在腹主动脉中放置较长的裸支架,会累及内脏分支血管,可能导致再次干预时操作困难。虽然该技术目前仍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改变了传统TEVAR手术的观念,不仅封闭处理了夹层近端破口,还兼顾扩张了远端管腔,并增强了远端支架与动脉内膜的贴附,压闭假腔,更有利于远端假腔内血栓的形成,从而促进了动脉真腔重塑,减少了远期并发症,在临床应用中逐渐得到推广。
3.3 远端限制性支架技术 根据真腔直径大小,预先在远端着陆区放置合适的小直径的限制性支架,然后在其中置入主要的覆膜支架,可起到限制其远端扩张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尺寸过大造成dSINE的发生。ZHAO等[22]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TEVAR时采用限制性裸支架可以显著降低支架移植物远端过大,降低dSINE的发生率并改善主动脉重塑,远端过大比大于20%可作为部署限制性裸支架的指征,且再次干预率也明显降低。此外,与在远端着陆区预先放置裸金属支架不同的是,MASADA等[23]报道了预先放置小直径短覆膜支架的新方法“Cuff支架”,在随访期间dSINE的发生率和再干预率均显著降低,其产生的径向力也较小,有效性得到了证实。
3.4 术者改良支架技术 为了减少支架远端径向力对动脉壁的损伤,有的术者会在手术台上拆除成品的胸腔支架移植物最远端Z形支架,然后再重装并放置在患者夹层的真腔内。TILO等[24]最先报道这一方法,并对1例有结缔组织病的主动脉夹层患者使用,随访14个月没有发生dSINE。对高危患者来说,虽然该方法可作为应急处理方案,避免在等待定制覆膜支架期间发生主动脉不良事件,但目前关于此项技术文献报道极少,且这种方法需要医生对支架移植物进行改良,增加了不确定性。
3.5 新型特异性支架技术 理想的支架需要满足在良好的覆盖病变的情况下,使远端径向支撑力降到最小,避免加重夹层内膜片的损伤,特别是在慢性期夹层内膜片较厚、真腔极为狭窄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适用。BURDESS等[25]报告了一种专门用于慢性STBAD的新型特异性支架移植物,它的特点是近端没有倒钩,且低径向力的远端Z形支架位于内部,末端支架被移除,在近3年的随访期间,仅发生1例dSINE。然而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且由于该支架近端没有倒钩,锚定效果尚不明确,存在发生内漏和支架移位的风险。WANG等[26]报道了一种新型两段式支架系统“Fabulous支架”,由近端覆膜支架和远端裸支架缝合在一起,采用多锥度设计,具有更稳定的径向支撑力和柔顺性,在促进主动脉重塑的同时兼顾预防dSINE的发生。
4 STBAD患者TEVAR术后dSINE的治疗方案
dSINE发生后,可先采取保守治疗,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而有关手术干预指征,目前文献[5]报道的是尽管加强了药物治疗,仍然导致主动脉形成假性动脉瘤、假腔持续变大(6个月内>5 mm)、动脉破裂、引起灌注不良、产生反复疼痛或出现新的症状。STBAD患者TEVAR术后发生dSINE的治疗方案包括再次TEVAR和开放修复手术。
4.1 再次TEVAR 在dSINE发生后,可通过再次TEVAR置入新的覆膜支架以延伸覆盖新的远端破口,减少假腔血流,且操作相对简单,对患者造成二次创伤打击小。LI等[15]通过对比发生dSINE后采用不同干预措施,证明了尽早进行再次TEVAR是有效可行的。一项研究[5]通过长期随访发现,再次TEVAR可以明显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建议使用锥形覆膜支架以避免反复干预。还有文献报道使用PETTICOAT—snowshoe技术成功治疗一个靠近腹腔干动脉的dSINE病例,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总之,由于该技术避免了开放手术所带来的体外循环和深低温停循环风险,减少了相关并发症,尤其是对于老年和身体虚弱的患者,可作为对目前以开放修复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的一种替代。
4.2 开放修复手术 开放修复可以作为对发生dSINE时行再次TEVAR治疗失败后的补充,且在使用手术移植物进行再修复时,患者预先存在的支架移植物可被用作近端吻合的平台。目前关于dSINE的开放修复指征并不统一,有文献报道TEVAR后晚期发生dSINE是再次开放手术治疗的适应证。也有文献[5]报道,dSINE发生后产生有症状的假性动脉瘤且远端主动脉最大直径>5 cm的患者,或dSINE靠近内脏动脉的患者行开放修复。然而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由于特殊的组织学特点,导致其首次TEVAR后包括SINE在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高,并且指南[2]并不推荐其为治疗首选,在发生dSINE后再次行TEVAR仍具挑战性,覆膜支架产生的径向支撑力会持续作用于本就脆弱的主动脉壁,导致远期并发症的高发,所以再次干预时建议开放修复。
综上所述,STBAD患者在成功实施TEVAR之后,并发症dSINE的发生仍然会引起主动脉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甚至需要反复干预,使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并且部分患者早期缺乏典型症状,给临床诊治带来了许多挑战。临床实践中应当以预防为主,在首次发生夹层后,根据患者主动脉解剖、夹层特点等,尽量选择个性化腔内治疗,采用具有合适锥度、柔顺性较好和最小远端过大尺寸的支架移植物,在选用较长覆膜支架的同时,也要兼顾脊髓、分支动脉的血流灌注,注意把握合适的治疗时机,发挥最佳治疗效果。